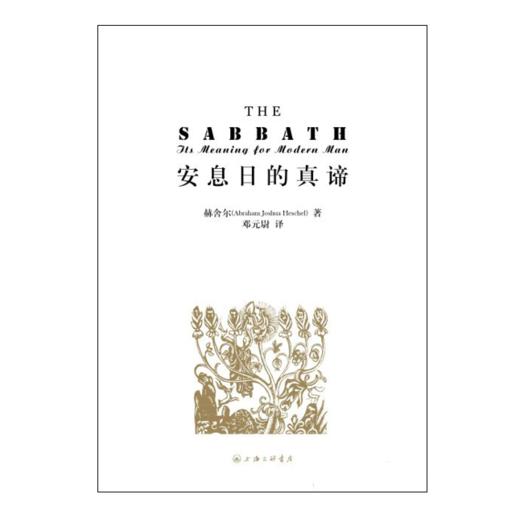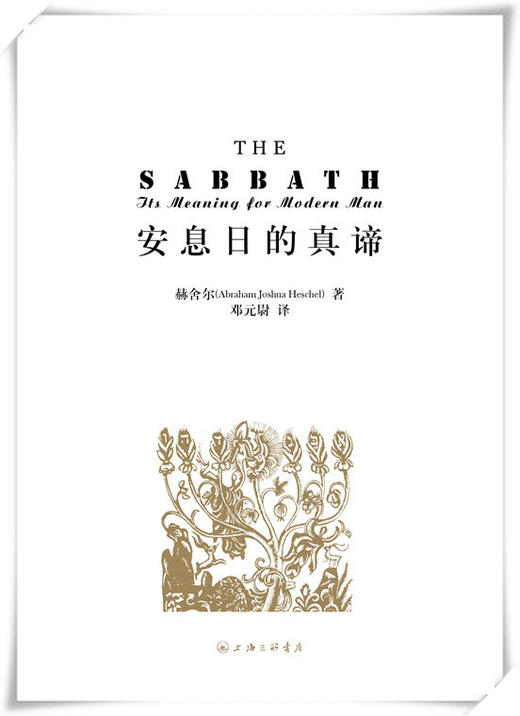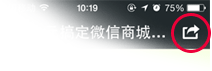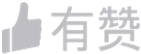商品详情
| 报佳音号 | 6384 |
|---|---|
| 外文书名 | The Sabbath, Its Meaning for Modern Man |
| 作者 | [美]赫舍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 |
| 译者 | 邓元尉 |
| ISBN | 9787542642196 |
| 出版社 | 上海三联书店 |
| 出版年月 | 2013.7 |
| 开本 | 32k |
| 页数 | 178页 |
《安息日的真谛》特点
20世纪谈安息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杨腓力喜爱、毕德生推荐的犹太神学家赫舍尔,受到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一致推崇!
《安息日的真谛》内容简介
本书是20世纪谈安息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赫舍尔以优美、热切、满怀对上帝所造万物的爱,所写下的《安息日的真谛》一书,在出版之后,就被推崇为是犹太信仰的经典作品,帮助数以千计的读者在现代生活追寻生命的意义。赫舍尔在这本简短而深邃的小书里,默想第七日的意义,引入一个带来巨大影响的观念:一种不是呈现在空间中、而是呈现在时间中的“圣洁的建筑学”。他主张,犹太教是个时间的宗教,犹太教所楬橥之生命意义,无法在空间及充斥于空间的物质中获得,只能在时间及弥漫于时间的永恒中领受,因此“安息日就是我们的大会堂”
《安息日的真谛》作者简介
赫舍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 1907~72),波兰出生的美国犹太拉比,二次大战时在纳粹德国失去母亲与姊妹,流亡至美国后,在美国犹太神学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America)担任神秘主义与伦理学教授。他集学者、作家、行动家与神学家等多种身份于一身,一生追寻真正的自由与信仰,也是作品广受基督徒阅读的犹太神学家之一,其中《先知》入选《今日基督教》二十世纪百大好书。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除本书外,还包括《觅人的上帝》、《人不是孤岛》等。赫舍尔曾与马丁路德·金博士一起参与1965年的美国民权运动游行,他写道:“当我在赛尔玛游行,我的脚在祈祷。”(When I marched in Selma, my feet were praying.)
作者的最后一个安息日,与家人和许多朋友共享了一顿美好的晚餐,饭后有位来宾朗读其年轻时写的意第绪语诗篇。他那晚入睡后,便再也没有醒来了。在犹太传统里,一个人在睡梦中过世,被称为“上帝之吻”;而在安息日过世,则是一个虔诚人配得的礼物。作者曾经写道:“在敬畏神的人,死亡是项殊荣。”
《安息日的真谛》译者简介
邓元尉,(台湾)政治大学哲学博士,研究专长为宗教哲学、宗教暴力与和平等。著有《通往他者之路》(橄榄,2008),为探究犹太法典诠释的第一本中文专著。另有《现象学与汉语神学》(合著,道风书社,2007),译著《第五向度》(商周,2001)。现为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安息日的真谛》推介语
“《安息日的真谛》一书无疑是赫舍尔最钟爱的作品,它不仅仅是本谈安息日的书,更是我们这一世代,对犹太礼仪生活的原动力所作最出色的研究。”
——吉尔曼(Neil Gillman)博士
《神圣的碎片》(Sacred Fragments)作者
“这是一本不朽巨著!阅读它,并准备让自己面临改变。”
——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牧师
《头等大事》(First Things)主编
“赫舍尔的《安息日的真谛》无疑是谈论犹太信仰精深的拔尖之作。”
库希纳(Lawrence Kushner)拉比
《安息日的真谛》目录
- 前言:时间的建筑学
- 第一章 时间的殿堂
- 第二章 超越文明
- 第三章 空间的光辉
- 第四章 惟独天国,别无一物?
- 第五章 “你是惟一”
- 第六章 日子的同在
- 第七章 永恒寓于一日
- 第八章 直观永恒
- 第九章 时间中的圣洁
- 第十章 务要贪婪
- 跋:圣化时间
- 附录:父亲的安息日(苏珊娜·赫舍尔)
《安息日的真谛》前言
前言:时间的建筑学
科技文明就是人类对空间的征服。但这样的征服,往往得牺牲一种基本的存在要素,这要素就是时间。处身科技文明中的我们,以时间换取空间;生活的主要目标即是在这空间世界里扩展自己的权力。然而,拥有得愈多,不表示愈真实地存在。我们在这空间世界所获得的权力,在时间的疆界上戛然而止;惟有时间才是存在的核心。
控制这空间世界固然是我们人类担负的一项任务,然而,如果我们在空间之域争取权力的同时,却失落了对时间之域的一切渴望,危机就此诞生。在时间之域中,生命的目标不是拥有,而是存在;不是占有,而是施予;不是控制,而是分享;不是征服,而是和谐共处。一旦对空间的控制、对空间之物的攫取,成为我们惟一的关注,生命就走上了岔路。
没有任何事物比权力更为有用,但也没有任何事物较权力更加可惧。过去,我们常常因为缺乏权力而受到剥削;如今,剥削我们的却是权力所带来的威胁。热爱工作的确能带来快乐,然而当我们在工作中贪得无餍,却会跌入悲惨的境地。汲汲营营的心壶在利益之泉中破碎;世人若出卖自己,甘受物的奴役,便会成为这利益之泉中破碎的器皿。
科技文明根源于人心渴望征服与管理各种自然力量;工具的制作、纺织与耕作的技艺、房舍的建造、航海的技术──这一切都在人类的空间环境中不断取得进展。时至今日,空间之物占据人们的心思意念,影响所及,包括众人的一切活动,即便诸般宗教也经常受到如此的观念所宰制。神祇居住在空间之中,厕身于特定所在,诸如群山、众林、或树或石,这些有神祇居住的地方特别被当作是圣所。神祇总与某一独特的地点密不可分。“神圣”这个特质被视为与空间之物有所关联,因此,首要的问题是:神在什么地方?人们狂热拥护这个观念,认为上帝就显现在宇宙当中,结果却因此认定上帝只显现于空间之中、而非时间里面,显现于自然、而非历史,仿佛上帝只是物、不是灵。
甚至泛神论的哲学也是一种空间宗教:至高的存在被认为就是无限空间本身。“神即自然”,上帝的属性就是向外延伸的空间,而不是时间。对斯宾诺莎(Spinoza)而言,时间仅止是一种偶然运动,一种思维模式。他并且打算以几何学这种空间科学来建构哲学,这意味着他拥有的是一个空间取向的心智。
初民的心智很难不借助于想象力来理解一个观念,而想象力正是驰骋于空间之域。诸神必定有其可见的形像,没有形像的地方就没有神灵。对圣像的崇敬,对圣山或圣所的崇敬,可不只是为多数宗教所固有,更是存在千代万国的世人心中,不论他是虔诚的人、迷信的人,抑或反对宗教的人。所有人尽皆不断向国旗、忠烈祠、为君王或民族英雄而立的纪念碑,宣誓他们的忠诚。无论何处,对忠烈祠的侮辱都被视为是种亵渎,使得忠烈祠本身变得如此重要,世人反倒任其所纪念的事物遭到遗忘。纪念促成了遗忘,手段取消了目的。因为,空间之物任由世人摆布;纵然这些事物极其神圣而不能玷污,却无法保证不为人所利用。为抓住神圣的特质,为使神灵永远临在,世人遂塑造神灵的形像。但是,一位可被塑形的神,一位可被局限的神,不过是人的影子罢了。
空间的光辉,与空间之物的华美,在在使我们着迷。物,是一种拖累人们心神、宰制我们全副心思的东西。我们的想象力倾向于将一切概念形像化;在每日生活中,我们首要关注于感官所向我们表明之物,关注于眼目所见、十指所触之物。对我们来说,实在就是物性(thinghood),由占据空间一隅的物质所构成;就连上帝也被多数人设想为一种物。
我们惟物是瞻,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看不见整个实在,以致我们无法认出:物只是物,物实际上只是材料。显而易见的,当我们这样来理解时间时,那无物性、非物质的时间,于我们而言就好像毫无实在可言。
的确,我们知道如何应付空间,但在面对时间时,非得使之臣服于空间之下,否则我们将手足无措。大部分人辛勤劳动,仿佛只是为着空间之物而作,至终,我们在被迫直视时间的面容时会惊骇不已,受困于对时间深植不移的恐惧中。我们遭受时间的讥笑,它就像是只老奸巨猾的怪物,张开熔炉般的大嘴,一口口吞噬人生的每一寸光阴,将之焚烧殆尽。于是,我们在时间面前退缩,逃到空间之物那儿寻求荫蔽。我们将自己无力实践的意图寄望于空间之上;于是,财产象征了我们的压抑,庆典象征了我们的挫败。但空间之物无法防火,它们只会火上加油。难道,拥有财货的喜悦,足以化解我们对时间的害怕?特别是这害怕终究会变成对那无以逃避之死亡的恐惧。被夸大的物,伪装成幸福,实际上却是对我们真实生命的威胁;倘若我们致力于空间之物,这更多是自寻烦恼,而不是得其祝佑。
世人不可能躲避时间问题。我们愈多思考,便愈了解到:我们无法藉由空间征服时间。我们只能在时间中掌管时间。
灵性生活的更高目标,不在于积存大量信息,而在于面对神圣时刻。比方说,在宗教经验中,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物,而是一种属灵的临在。真正能在灵魂里留下痕迹的,并非行动所经过的场所,而是某个带来洞察的时刻。这洞察的时刻是个机会,能带领我们超越物理时间的限制。一旦我们无法感受到时间中这种永恒的荣美,灵性生活就开始腐化了。
我在此无意轻视空间世界。贬抑空间与空间之物的祝福,也就是贬抑创世大工,而那本为上帝眼中“看着是好的”。不可单单从时间的角度看世界;时间与空间彼此关联,忽略任何一方都将使我们陷于半盲之境。我在此所要抗议的,乃是世人向空间无条件投降,甘为物之奴仆。我们绝不可忘记:并非物使时间有了意义,乃是时间使物有了意义。
和空间比起来,圣经谈得更多的是时间;圣经在时间的维度中看待世界。圣经对世代与事件的关注,远多于对列国与物事的关注;圣经更多关心历史,而非地理。为理解圣经的教导,我们必须接受其前提,这前提就是:时间对生命的意义就算不比空间重要,也绝不逊色;时间有其自身的重要性与独立性。
圣经希伯来文没有“物”(thing)这字的同义字。后期希伯来文用以指“物”的“davar”,在圣经希伯来文中则意味了:“言语”、“字词”、“信息”、“报导”、“音讯”、“劝告”、“要求”、“应许”、“决心”、“语句”、“主题”或“故事”、“言说”或“表述”、“职务”或“事务”、“行动”、“善行”、“事件”、“方式”或“方法”或“理由”或“原因”;但就是没有“物”的意思。这只是因为圣经语言的贫乏吗?还是说圣经的本意就是希望指出一种合乎中道的世界观,提醒我们不可用物性来表达实在(reality;源于拉丁字 res,即“物”的意思)?
宗教史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就是农业节日转变成纪念历史事件的庆典。古人的节日与自然节气紧密相连,他们在时序变迁中,欢庆在自然生活里所经历到的事情;于是,节日的价值取决于自然带来怎样的物事而定。可是,在犹太教里,却出现了变化:逾越节本是个春季节日,却成为欢庆出埃及的日子;七七节本是在麦子收割的尾声举行的古老收割节(hag hakazir;出二十三 16,三十四 22),却成为欢庆在西乃山赐下律法的日子;住棚节本是庆祝葡萄收成的古老节日(hag haasif;出二十三 16),却成为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时居住在棚里的日子(利二十三 42〜43)。对以色列人来说,尽管自然界的循环与我们肉身生命的存活息息相关,但是历史时间中的独特事件,比自然循环中的反复历程具有更多的属灵意义。当其他民族的神祇关联于处所或物事时,以色列的上帝却是事件的上帝:祂是奴隶的救赎主,是律法书的启示者,祂自己乃是显现在历史事件中,而非显现在物事或处所中。于是,一种对于不具形体、无以思量者的信仰,就这样诞生了。
犹太教是个时间的宗教,以时间的圣化为目标。对于那些空间取向的心智而言,时间是凝滞不变、反复循环、同质无异的,他们认为所有时刻都无甚分别,只是空壳,不具实质;圣经非但不是如此,反倒觉察到时间的多样化特质:没有两个时刻是同样的,每一时刻都是独特的,是在当下那惟一的时刻,是独一无二、全然宝贵的时刻。
犹太教教导我们,怎么与时间中的圣洁相连、与各种神圣的事件相连,学习如何在一整年的岁月之流里,把一个个浮现出来的美丽安息日视为圣殿,尊崇敬奉;换言之,安息日就是我们的大会堂。至于我们最重要的“至圣所”,就是赎罪日,这是一个无论罗马人或德国人皆无法焚毁、即便背离了信仰亦无法遗忘的“地方”。据古代拉比所言,并不是因着我们守赎罪日,而是缘于这日子本身,缘于“这日子的本质”,人们在其中忏悔,才得以赎回吾人之罪孽。
我们可以将犹太教的礼仪刻画为是关于时间之诸般意义形式的艺术,宛若是种时间的建筑学。对这礼仪的遵行,像是守安息日、月朔、各式节日、安息年与禧年,大多取决于一日中的特定时刻或一年中的特定时节而定。比方说,“唤祷”(the call to prayer)的仪式,即依循着黄昏、清晨、晌午的时序进行。犹太信仰的主题尽皆寄于时间之域。我们记得出埃及的那日,记得以色列民站在西乃山脚的那日;而我们对弥赛亚的盼望也是在期待一个日子,期待那诸日终结之日。
在一场精心构思的艺术表演中,最为重要的理念或角色不会随便出场,而是像皇室典礼中的君王般,在某一特定时刻、以某种特定方式出场,来显明其权柄与领袖地位。而在圣经里,字词的使用同样是极度讲究的,尤其那些在圣经世界的广阔意义体系中,如火柱般具备引路功能的字词,更是如此。
最著名的圣经字词之一,就是 qadosh(圣/圣洁)这个字;它比其他任何字词都更能表达出上帝的奥秘和尊荣。那么,在世界历史中,第一个被认为是圣洁事物的是什么呢?是一座山吗?还是一座祭坛?
首次出现 qadosh 此一着名字词的,自然是创世记中创世故事的尾声:“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换言之,qadosh 这个字被用在时间上;这是一个具有何等深意的做法!事实上,我们在创世记载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一节经文曾经指出,空间中的事物是可以被赋予圣洁性质的。
这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宗教思维正好相反。神秘主义者的心灵会期待,在天地获得建立后,上帝会创造一个圣地──无论是圣山或是圣泉──随之在其上建造一间圣所。然而,就圣经而言,天地建造完成后,最先出现的却是那时间中的圣洁,也就是安息日。
在历史的开端,世上只有一种圣洁,即时间中的圣洁;直到在西乃山上,上帝之言即将被道出时,才宣告了一种在人里面的圣洁:“你归我为圣洁的民。”只有当百姓遭到试探去敬拜物,也就是敬拜那金牛犊后,上帝才吩咐设立会幕,那在空间中的圣洁。首先是时间的圣化,其次是人的圣化,最后是空间的圣化。时间由上帝使之为圣;空间,也就是会幕,则由摩西使之为圣。
虽然节日所纪念的事件都是发生于时间之中,但是这些节日所举行的日期,仍旧依据着我们生活中的自然事物而定。比方说,逾越节和住棚节总在满月之际庆祝;所有节庆都在某个月份中的某日来举办,而月份则反映了自然界中周期性发生的事情;犹太人的月份便是从朔月开始算起,直到另一轮新月再度出现在夜空中。相较之下,安息日全然与月份和月之盈缺无关,安息日的日期并不依凭于任何诸如月朔这类自然事件,而是依于创世的行动。因此,安息日究其本质乃是彻底独立于我们的空间世界之外。
安息日的意义在于欢庆时间,而非空间。我们一周有六天生活在空间之物的宰制下;但到了安息日,我们试着让自己与时间中的圣洁有所共鸣。在这日子,我们被呼召去分享那时间中的永恒事物,被呼召从创世的结果转而关注创世的奥秘,从受造的世界转而关注对世界的创造行动。
《安息日的真谛》跋
跋:圣化时间
外邦人将他们对上帝的意识投射为某个可见的形像,或将上帝与某种自然现象、某种空间之物连结起来。但在十诫里,世界的创造主显明自己的方式,乃是透过一个历史事件,透过一个时间中的事件,这事件就是祂将祂的百姓从埃及解救出来,并对他们宣告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在地上曾经有过的最宝贵事物,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的两块石版,它们是无可比拟的无价之宝。摩西曾上到这山去领受它们,并待在那里四十昼夜,既不吃饼,也不喝水。上主交给他两块石版,在上面写下十诫,这是在山上,上主从火中对以色列民所说的话语。但四十昼夜结束后,手里拿着两块法版的摩西下山之际,却看到百姓围着金牛犊跳舞,他便把手中的法版扔掉,在众人眼前摔碎了。
“在埃及,每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都会根据“此乃创世之地”的说法来宣称它的优越性。”相较之下,创世记则是说到创世之日,而非创世之地。
众神话皆未提及创世的时间,圣经却偏偏说到空间在时间中的受造。
人人都知道,大峡谷要比小沟渠更能引发敬畏之情;人人都知道,虫子与老鹰有多么不同。但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对时间的差异具有同等的鉴别力?历史学家兰克(Ranke)宣称,每个时代离上帝都同样近。但犹太传统则宣称,在时间中有一种时代的阶层,每个时代都不一样。世人可以同等地在任何地点向上帝祈祷,但上帝却不是同等地在任一时代向世人说话。比方说,在特定的时刻,先知预言之灵便离开了以色列。
对我们来说,时间只是个用来度量某个物理量的机制,而非我们栖居于其间的生活领域。我们的时间意识出自于对两个事件的比较,发现其中一个事件比另一事件更晚发生;出自于我们听到一段旋律,意会到一个音符接续着一个音符。对我们的时间意识而言,事件的先后之别是最基本的。
然而,时间仅止是在时间中各事件之间的关联吗?忽略与过去的关系,当下的时刻就没有意义了吗?再者,难道我们仅止是知道,对空间之物有所影响的时间中的事件吗?如果没有任何与这空间世界有关的事发生,难道时间就不存在了吗?
若欲认出时间的终极意义,需要一种独特的意识。我们全都生活于时间之中,是如此紧密地贴近它,以致我们反倒无法注意到它。空间世界围绕着我们的存在,但这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则是时间。物只是海岸,真正航行的旅程是在时间之中。
存在从未藉由自身获得阐明,存在只能透过时间方得以厘清。当我们闭上双眼专注凝思,便能够获得毋须空间的时间,但我们绝无法拥有毋须时间的空间。在属灵的眼光看来,空间乃是冻结的时间,所有的物都只是凝滞不动的事件。
我们可以从两种观点来觉察时间:一是空间的观点,一是属灵的观点。从快速移动的火车车窗看出去,我们会有一种印象,就是我们自己仍静止不动,移动的是窗外的风景。同样的,当我们的灵魂被空间之物所运载,在凝视实在时,时间显得是在不断移动。然而,当我们学习去明白,乃是空间之物在不断移动,我们便领会到,时间才是永不消逝的,事实本是空间世界在时间的无限扩展中滚动。如此,暂时性便可被定义为是空间对时间的关系。
实际上,所谓的空间,乃是一无边界、连续而空虚的实体,它并不是实在的终极形式。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在时间中运行──从太初直到终末的日子──的空间世界。
对常人的心智来说,时间在本质上是短暂无常、稍纵即逝的。然而,真相是:当我们凝视空间之物时,时间从心头倏忽而过。这是一个传达给我们某种暂时感的空间世界。那超越空间、不依于空间的时间,乃是永存的;反而是这个空间世界愈趋朽坏。物在时间中朽坏,时间自身则不改变。我们不该说时间流逝,而应说空间流经时间。不是时间逝去,而是肉身在时间中逝去。暂时性是这空间世界的属性,是空间之物的属性。至于那超越空间的时间,却超越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划分。
纪念碑注定要消逝,灵的日子却永不过去。我们在出埃及记中读到一段关于以色列民抵达西乃的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在这日,就来到西乃的旷野。”(十九 1)这是一个令古代拉比感到困惑的表述:在这日?它本该说的是:在那日。这令人困惑的表述只有一种含义,就是赐下妥拉的那日从未过去;那日就是这日,就是每一日。无论我们何时研读妥拉,对我们而言,它都“宛如是今天才赐给我们的”。出埃及的那日也具有同样的含义:“每个世代的人,都必须把自己看成是彷佛曾亲身走出埃及。”
一个伟大日子的价值,并不是以它在月历上占据的空间来衡量。亚基巴拉比呼喊道:“所有的时间,都不若歌中之歌被赐给以色列的那日有价值,因为,所有的歌都是圣洁的,但歌中之歌乃是圣洁事物中最圣洁的。”
在灵的领域,一秒钟与一世纪并无差异,一小时与一世代也没有分别。族长犹大拉比(Rabbi Judah the Patriarch)发出吶喊:“有的人以一生的光阴获致永恒,有的人却在短短一小时中获致永恒。”美好的一小时,或许有着彷如一生之久的价值;归回上帝的那一瞬间,或可恢复那些远离祂的失丧岁月。“在此世若有一小时的悔改与善行,胜过来世的全部生命。”
我们已说过,科技文明是人战胜空间。可是,时间始终不为所动。我们可以征服空间上的距离,却无法重拾过去,亦无法预知未来。人在空间之上,时间更在人之上。
时间是人所面临最艰巨的挑战。我们全都身在同一队行伍中,走过时间的领地,永远到不了终点,却也无法获得立足点。时间的实在远非我们所能触及。空间展露在我们的意志面前,我们可以随自己高兴来塑造和改变空间之物。然而,时间却不是我们所能掌握。时间既切近又远离我们,既内在于一切经验,又超越一切经验。时间独独属乎上帝。
因此,时间乃是他性(otherness),一个远非任何范畴所能含纳的奥秘。时间和人的心智好像是两个不相干的世界。可是,只有在时间中,才有众生的团契和共性(togetherness)可言。
我们每个人都占据空间之一隅,彼此排斥地据有一方天地。我的肉身所占据的那一部分空间,是其他任何人所无法进驻的。然而,无人可占有时间。没有任何时刻是我可以独自占有的。这独特的时刻固然隶属于我,却也隶属于众生。我们分享时间,却占有空间。藉由争夺空间的所有权,我是其他人的竞争者;藉由生活在时间的奥秘中,我是其他人的同代人。我们旅经时间,却占据空间。我们很容易屈服在“空间世界乃为我而在、为人而在”的假象之下;但对时间,我们就不致产生这种假象。
神与物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原因在于,物是一种有别于存在整体、彼此分离的个别存在。看见一物,就是看见某种分别而孤立的事物。尤有甚者,物乃是、且可以是为人所拥有者。时间却不允许任一瞬间可在其自身且为其自身地存在着。时间既非全体,亦非部分。时间不可分割,除非我们在心里分割。时间永远超出我们的掌握。时间总是圣洁的。
永恒时间的伟大视野很容易被我们所忽略。根据出埃及记,摩西所看到的第一个异象是:“⋯⋯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三 2)时间就像是永恒燃烧的荆棘。尽管每一时刻都必须消逝,以容让下一时刻的到来,但时间本身却并没有被烧毁。
时间自身就有终极的价值,它甚至比满布星辰的穹苍更加庄严而令人生畏。时间以最古老的光华缓缓流逝,它所告诉我们的,远比空间以其破碎物语所能说的多得多;时间乃是以个别存在为乐器,由此合奏出交响乐;时间释放大地、使之成为现实。
时间是创世的历程,空间之物是创世的结果。当我们注目于空间,可以得见创世的产物;当我们直观于时间,则将听闻创世的历程。空间之物展现出一种虚假的独立性。它们卖弄自己那虚假的、有限的持久性。这些被造之物将造物主隐藏起来。只有在时间的维度中,人才能遇见神,并开始意识到,每一个瞬间,都是创世行动,都是太初,都开启崭新的道路通往最终的实现。时间是上帝在空间世界中的临在,也正是在时间中,我们才能够觉察到万物的合一。
我们所领受的教导是,创世并不是一个只发生过一次便一劳永逸的行动。使世界得以存在的行动,是个持续不断的历程。上帝创建世界,此一创建仍不断在进行。只是因着上帝的临在,才有当下的时刻。每一个瞬间都是创世的行动。一个时刻,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太初的闪现,是太初的记号。时间是恒常的创新,是不断创世的同义字。时间乃是上帝恩赐给空间世界的礼物。
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一个在其自身并藉其自身而存在的世界,不可能更新,也不需要造物主。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就是一个与上帝隔绝的世界,只有物本身的世界,是未实现的实在。一个时间中的世界,则是一个通过上帝而向前进发的世界;是无限设计的实现;在这世界中的物,不是为自身,而是为上帝而存在。
为能见证世界创生的永恒旅程,就需在礼物中觉察赠礼者的同在,就需明白时间之根源乃是永恒,明白存在的秘密即是时间中的永恒。
我们无法透过对空间的征服、无法透过成就与名望,来解答时间的难题。我们只能藉由圣化时间来寻求答案。单从人来看,时间是晦涩难明的;对与神同行的人而言,时间则是乔装了的永恒。
创造是上帝的语言,时间是上帝的诗歌,空间之物则是歌中的音符。每当我们圣化时间,便是与祂共同唱和。
生而为人的任务就是征服空间与圣化时间。
我们必须是为了圣化时间的缘故来征服空间。在周间,我们被呼召要借着与空间之物打交道来圣化时间。在安息日,我们被吩咐要在时间的中心同享圣洁。即使我们的灵命枯竭,即使我们紧绷的喉头吐不出任何祷词,安息日的安宁静谧依然带领我们通往无尽平安之境,并使我们开始意识到永恒的真义。在这世上,没有任何观念可以像安息日的观念一样,蕴涵如此丰富的属灵能力。在千秋万世之后,当许多我们所珍爱的理论仅存断简残篇,那帷宇宙的锦绣依然发光如星。
永恒寓于一日。
《安息日的真谛》书摘
附录:父亲的安息日
——苏珊娜‧赫舍尔(Susannah Heschel)
每当礼拜五晚上,我的父亲举起祝圣杯、闭上双眼、吟诵祝酒祷辞时,总是令我情绪澎湃。随着他吟唱那古老而神圣的家族旋律,祈祷祝圣那酒与安息日,我总感到他也祝福了我的人生,祝福了桌边的每一个人。我多么珍惜这些时光。
我们家就如每一个敬虔的犹太家庭,礼拜五晚上是一周的高峰时刻。母亲和我会点亮安息日烛台,瞬时间我感觉自己的心境、甚至包括自己的身体,都得到了转化。在点亮餐厅的烛光后,我们会走进客厅,那里有几扇向西的窗户,可以看到哈德逊河(Hudson River),我们就在那儿赞叹顷刻来到的落日之美。
那份随着我们点起烛光而到来的平安感受,多少也与礼拜五的紧张忙乱有关。父亲常说,迎接一个圣洁日子的预备工作,与这日子本身一样重要。整个早上,母亲忙碌地采买食品,到了下午,当她作菜时,紧张的气氛便逐渐升高。父亲会在日落前一或二小时,从他的办公室回来,好预备他自己。而当这一整周的工作时刻即将结束之际,我的父母都在厨房里,疯狂地要想起他们可能忘记预备的事项──水煮开了吗?遮炉片(blech)盖住火炉了吗?烤箱启动了吗?
霎时,时间到了──这是日落前二十分钟。当我们点亮烛光、祝祷安息日之到来时,无论在厨房还有什么事没能完成,尽皆抛诸身后。父亲如此写道:“安息日之来到,像是一种抚慰,抹去恐惧、哀伤与黯淡的记忆。”
父亲很少在礼拜五晚上到会堂去,他喜欢在家里祷告,而我们的晚餐通常是安静、缓慢而放松的。我的父母并未参与很多社交活动,但大约每隔两个月,他们会邀请一些朋友或同事来参加安息日晚宴。菜单千篇一律:我们的哈拉面包(challah)译1是在当地的面包铺买的,母亲会煮鸡汤、烤小母鸡、准备色拉和青菜。至于餐后甜点,父亲会削一颗金冠苹果,试着不要削断苹果皮,我们大家就共享这颗苹果。母亲对厨艺并不热衷,父亲也总是吃得很清淡,因此,这些食物并不会令我们感到兴奋。尽管如此,在每一次用餐前,父亲总会举起他的叉子,看着我说道:“妈咪是位好厨师。”
在我们的安息日晚宴上,有一个不常见的规矩:
父亲从他的姊夫、一位克比基尼彻拉拜(Kopycznitzer Rebbe)那儿得到一份礼物,是两个长形镶银的香料盒,里面放着番石榴枝和尤加利叶。虽然通常是在安息日结束时的祝祷礼,才会祝福并闻它们的馨香之气,但我们会在举行祝酒祷辞之前便祝福与闻香气,这是一个哈西德派译的习惯,这习惯在拉比文献中的依据可参考我父亲在本书的讨论。
当有客人参加我们的安息日晚宴时,几乎都是来自欧洲的流亡学者,餐桌上的谈话也总是围绕着欧洲打转。他们总在谈论他们认识的德国学者,这些犹太学者要不是已经流亡到美国或以色列,就是已经遇难了。他们并不会谈到大屠杀的迫害经过,也不会在安息日说出“大屠杀”这词,但他们会谈论在马克思‧范恩瑞许(Max Weinreich)的书《希特勒的教授》(Hitler’s Professors)里面作为纳粹分子曝光的非犹太学者。父母大部分的朋友就像父亲一样,大战前曾在德国的大学求学,而在战争结束二、三十年后,他们对于那些曾感到钦佩不已的学者,居然曾是纳粹分子,都感到震惊不已。在这些谈话里,德国文化无处不在。早在我在学校阅读到霍桑(Hawthorne)、梅尔维尔(Melville)、埃默森(Emerson)、梭罗(Thoreau)之前,我的成长过程中就已不断听闻歌德(Goethe)、海涅(Heine)、叔本华(Schop-enhauer)以及胡赛尔(Husserl)。因着在家里从父母那儿领受的文化世界,我一直感觉自己在美国不过是个过客。
安息日谈话也经常以东欧、以父亲出生其中的那个哈西德世界为重心。他喜欢向他的客人讲述哈西德教师的故事,或是同他们叙述哈西德经典的教训。父母的朋友很少来自那个世界,但对父亲而言,每逢安息日,总是要回到他年轻的岁月,追忆他的家庭与好友。
在安息日的时候,父亲甚至连阅读习惯都改了。他不再阅读学术书籍,不再阅读哲学或政治学的作品,转而阅读希伯来宗教经典。因着在安息日禁止书写,他会在书里夹着餐巾纸或回形针,以致多年后我可以分辨出他曾在安息日读了些什么书。那些书在每一个安息日带领他回到童年时的故事,回到他在拥有高贵宗教情操的人们中间长大成人的那份感受。(曾经有个类似的情境,与本书的法文版有关,这书在法国以《时间的建筑师》〔Les Bâtisseurs du Temps〕为名出版。据他信中所言,伟大的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在他床边桌上一直摆着我父亲的作品,直到生命末了。)
在安息日的早上,我们会参加在犹太神学院举行的礼拜,那是父亲任教的学校。来自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一起聚会。那是一个正统派的礼拜,完全以希伯来语进行,男女分开坐。许多个礼拜,我们聆听即将毕业成为拉比的学生的讲道,而在从会堂走路回家的路上,学院的成员通常会严格评论这场讲道的素质。回家的路程只要十五分钟,但父亲习惯每走几步路就停下来讨论某个观点,接着再继续走,因此这路程常常要花上半个小时。当我还小的时候,他会让我坐在他肩头上;随着我年龄渐长,他的同事会帮他来逗我玩。
安息日的午餐是非正式而轻松惬意的,这是嬉笑玩耍的时间。午餐过后,父母每周例行要先小睡片刻,接着享受下午茶,再到河滨公园散步,在街上蹓跶。他们会在那里遇见亲朋好友,沉浸在安息日午后漫步的时光中。
实际上有两种安息日经验,一是在秋季和冬季的月份,那时的安息日大约从礼拜五下午四点开始,礼拜六的五点左右结束。另一者是在春季和夏季的月份,那时的安息日从礼拜五的八点或八点半开始,直到礼拜六的九点甚至更晚才结束。在冬季月份,礼拜五晚上在晚餐过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父母会坐在餐桌前喝茶读书。而在春季月份,漫长的安息日下午则成为这日子那安详平静的焦点所在。
父母经常邀请学生来参加安息日午后的下午茶时间。母亲会提供奶酪和饼干,各种糕点,有时甚至奉上豪华的“老爷蛋糕”(Herrentorte)──这是一种长条状面包,切成长片状,铺上一层又一层各式鲜鱼与蛋色拉,抹上奶油奶酪和鳀鱼调成的奶霜。父亲会注意到每个学生,询问他们的课业、家乡的拉比,以及未来的目标。当太阳渐渐西沉,他为每个人预备一本祈祷书以进行晚祷。我们一起为安息日的结束祝祷,之后学生们就离去了。
周日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在冬季的月份期间,父亲偶尔会在周日的早上教课,母亲则会弹钢琴。不过,几乎每逢夏季,父母就会在洛杉矶租间房子,靠近舅舅们的家。租到的房子偶尔会离会堂太远,无法步行抵达,这时就会有朋友来到我们家,参加安息日早上的礼拜。母亲会为每个人准备好一本轻便的祈祷书,访客则会一直待到下午。当安息日在礼拜六晚上结束时,时间已经晚了,我们也马上上床入睡。周日的早上是安息日之后的安息时光,父亲从事他的研究,母亲则去弹钢琴。夏季的周日下午充满了音乐。我们会前往舅舅家,他是一位会拉小提琴的物理学家。他有一间大琴房,里头有两架钢琴,他的朋友们会自行编制演出三重奏、四重奏或五重奏,就这样镇日演奏室内乐。那房子有个很大的游泳池,就在琴房外面,当母亲演奏时,父亲和我会漂浮在水面上,读本书,聆听乐声。
当本书于 1951 年出版时,父亲在美国只待了十一年。他在 1940 年抵达美国的时候,英语还不太好,但他对这语言的掌握很快就取得显著的进展,并开始以相当丰富和诗意的风格来写作。真的,我的父母常常因为本书早期读者的反应开怀大笑,因为这些读者无法想象这本书竟是父亲写的,他们相信这书实际上出于母亲的代笔!这本书的用语相当符合它的精义,书中那宛若哀歌与诗篇的语调,在在从读者心中唤起他想描写的安息日心境。
在本书出版的那个年代,美国的犹太人正迅速被同化,许多犹太人会在公开表达自己的犹太信仰时感到局促不安。就连在拉比与犹太领袖当中,也普遍拒绝接受犹太神秘主义、哈西德派,甚至拒绝神学和灵性。情况就像是他们渴望一种非宗教的犹太教──一种无神、无信仰、无信念可言的犹太教。对他们来说,工作、社交、购物、单纯作个美国人,这一切都与安息日有所抵触。
在试图重新引介安息日的重要性的同时,父亲并没有严厉责备犹太人忽略了他们的宗教诫律,他也没有以拉比文献的绝对权威来要求他们遵行犹太律法。在那个年代,神职人员著书立论的流行风潮是以宗教促进心理治疗,但父亲一反此一潮流。他坚持认为,安息日无关乎心理学或社会学;安息日并不是用来让我们冷静一下,或是提供家人共处的时光。安息日也不表示对现代社会或世俗世界的拒斥。对他来说,安息日乃是文明建构不可或缺的一环,不可与文明分离。与许多新近探索安息日的进路不同,父亲并未强调「仪式」的重要性(他相信诸如“习俗”与“礼仪”这些语词应从犹太词汇中剔除),他也不把安息日视为凝聚犹太认同的手段。
但父亲谈论安息日的进路确实反映出某些政治关怀以及那个年代的语言特质。本书一再出现自由与解放的论题。他写道,我们需要安息日来保存文明:“世人必须勇敢无歇而沉着地为一己内心的自由奋斗”,以使自己不受制于物质世界的奴役。“内在的自由端赖于不被物所辖制,就像是不为人所辖制一般。许多人拥有高度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但只有很少的人足可不役于物。这一直是我们的问题──如何与人共处却不受制于人,如何与物共存却不为物所困。”
父亲将犹太教定义成是一种以时间中的圣洁为其核心关怀的宗教。有些宗教建造起宏伟的教堂或圣殿,但犹太教建立安息日,作为一种时间中的建筑物。在时间中创造出圣洁,与在空间中建造大教堂,要求的是不同的感受力:“我们必须是为了圣化时间的缘故来征服空间。”父亲的意思,并不如某些人联想的那样,以为他是在暗示要贬损空间,或否定以色列地的意义。他对捍卫以色列及其神圣性所作的努力,可在他的《以色列:永恒的回声》(Israel: An Echo of Eternity)一书中获得证实。在安息日与以色列这两个例子中,他都强调,对其之圣化乃取决于人的行为与态度。圣化安息日,乃是我们身为上帝形像的一部分,但也成为一种寻求上帝之同在的方式。他写道,并不是在空间中,而是在时间中,我们才找到上帝的形像。在圣经里,没有任何事物或地方是凭借自身而是圣洁的;就连应许之地也未被称为是圣洁的。诚然,土地的圣洁和节日的圣洁取决于犹太百姓的行动,是这些人使它们为圣洁,但更进一步,他告诉我们,安息日的圣洁优先于以色列的圣洁。即使人民未能守安息日,安息日仍是圣洁的。
我们是怎么形成安息日特有的气氛呢?父亲强调,神圣性是我们所创造的质量。我们知道该对空间做些什么,但我们如何形塑神圣的时间?他写道,一周有六日我们利欲熏心;安息日则更新我们的灵魂,使我们重新发现真实的自己。“安息日乃是上帝之同在于世,向世人的灵魂敞开。”上帝并不在空间之物中,而是在时间之流的时刻中。我们如何觉察上帝的临在?有一些有益的安息日律法──也就是那些要求我们放下世俗的需求、停止工作的律法。《米示拿》(Mishnah)在列举出某些范畴、以构成“工作”的内涵时,描述了几种类型的活动,都是为建立科技文明所必须的。但父亲更进一步。他说,在安息日不仅是不可生火,甚且是:“不可升火──即便是义怒之火亦不可为。”在我们家,有一些话题是在安息日得避免谈论的,例如政治、大屠杀、越战等,另有一些话题则备受重视。守安息日并不只是不去工作,更是要创造全然的安歇,这也是一种庆祝方式。安息日是关乎灵魂、也关乎肉身的日子。在安息日哀伤乃是罪,这是父亲经常复述并总是遵循的一项教训。
在安息日会发生一个神迹:灵魂苏醒,加添的灵到来,安息日圣洁的光辉充满在家里的每个角落。怒气消退,紧张远去,每个人的脸上都光采焕发。
创造性的安息日始于一种热切感。父亲以醒目的方式扭转我们预期的观点。并不是我们在渴望一个休息的日子,而是安息日之灵孤单地在渴望我们。我们是安息日的伴侣,当每周我们祝圣安息日,便是迎娶安息日。这段婚姻塑造了我们,因为“我们的本质为何,取决于对我们而言,安息日的本质为何。”同样的,安息日也不仅止是在礼拜六出现;他写道,这经验的深度是透过我们在周间六日的行为所创造出来的;这六日乃是向安息日而去的朝圣之旅。
安息日带着它自身的圣洁而来;我们不只是进到一个日子,而是进入一种氛围。父亲引用《光辉之书》(Zohar)说道:安息日乃上帝之名。是我们在安息日里面,而非安息日在我们里面。对父亲而言,问题在于觉察到这圣洁的方式──不是我们有多么守安息日,而是我们如何守安息日。严格遵行为安息日制订的律法还不够,真正的目标乃是促使安息日成为对天堂的预尝。安息日乃是天堂的隐喻以及上帝之同在的见证;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期待着,弥赛亚到来的时期就是安息日,而每一个安息日都预备我们好进到这经历中:“一个人除非可以⋯⋯学会品尝安息日的滋味⋯⋯否则他将无法在来世享受永恒的滋味。”上帝乃是在第七日将灵赐给世界,“(世界的)存续却有赖于第七日的圣洁”。他写道,我们的任务变成是如何将时间转化为永恒,如何全神贯注在时间上:“一周有六日,我们与世界争战,压榨大地以谋求好处;但在安息日,我们特别关注那深蕴于吾人灵魂中的永恒种籽。我们的双手为世界据有,我们的灵魂却另有所属──归属于那至高上主。”
在父亲的最后一个安息日,我们与许多朋友共度一个美好的晚餐,饭后有位来宾朗读父亲年轻时写的意第绪语诗篇。他那晚入睡后,便再也没有醒来了。在犹太传统里,一个人在睡梦中过世,被称为上帝之吻而在安息日过世,则是一个虔诚人配得的礼物。父亲曾经写道:在敬畏神的人而言,死亡是项殊荣。
- 报佳音
- 主内书籍文创礼品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