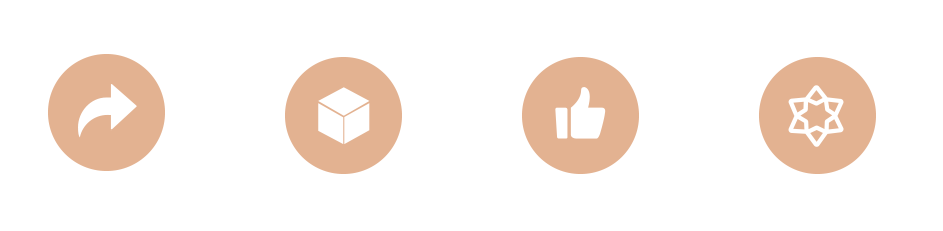2013年秋天,下决心从龙感湖离开。现在看起来,已经建成的房子等坛坛罐罐似乎不算啥,但对当时来说,就是要抛弃大部分身家。
 (二层楼房后的矮小房屋就是龙感湖时的住所)
(二层楼房后的矮小房屋就是龙感湖时的住所)
那时候全社会的土地流转还没有成为常态,不少土地是留给了本村的亲房代为种植,只要年底回来给袋谷子吃即可。这种情况下,留守的乡亲是「 0田租种田 」的“既得利益者”,如何能放弃?

(苦竹基地)
一个个地劝说:“各位大叔是种田能手,土地流转后,到农场帮忙和管理,我承诺收入不会少于过去!同时,咱这个地方种草籽(当地紫云英的俗称),撒菜籽饼,土地还能越来越肥,给子孙留点好田……”大义也讲,实际利益也说,一家一家做工作,三个月后,终于把土地流转合同签下来了。

(农场请的人都是当地的乡亲)

(紫云英)
当时的六组是阻力最大的,主要是组长自己在经营农药化肥,对于我们这种釜底抽薪、断人财路之举,视为眼中钉。
第一年,就是不同意流转。第二年,他自己的亲兄弟直接说:“人家一亩地550元,作为兄弟,我只收400元,你把田租给我,你自己拿去种!”就这样,六组长又过来找我补签土地流转合同。另一个小组,也是类似的,担心榨油坊的生意受到损失,只能一步步来。

(拍摄于2014年苦竹基地)
2014年夏天,村里有乡亲过来说:“小李,我跟你合作打野猪如何?拉电线,打了野猪一人一半......”这才知道山脚下的稻田还有“猪患”。
邻居大叔也说:“不打(野猪)的话,母猪带着小猪仔一晚上糟蹋十几亩…”坚决不听劝,只是默默在山脚下种了不到一亩地红薯和豆子。

秋收的时候,还有一大半红薯和豆子是好的,野猪从没到稻田去,只在山边吃了一小部分红薯和豆子。这也愈发让我相信“万物皆有灵”,人与动物的心念是可以相通的——如若不然,鸟妈妈如何跟鸟宝宝交流?野猪之间如何交流?不过是难度更高的“外语”罢了。


所以才有了后面的对话:“王哥,经过这些年的教导,我出师了。种100亩地,产量和成本控制都赶不上您,你又能干,还身先土卒,我怎么都比不上;如果种植300亩,产量和成本控制估计能跟您打个平手;如果种植600亩,我有信心全面超越您。"大概意思如上,王哥听后沉默了,后面每年团队年终聚会,王哥都带着嫂子和孩子们一起过来。

在油铺村山脚下过去居住的房屋还在,有时候过去还能记得当时的点点滴滴——如何因为旁边梨园要打药,就把梨园承包过来,后面因为要驱虫,平生第一次学会了如何自制酵素。


(置顶公众号,第一时间收到谦益最新消息)

文:李明攀 | 编:咸明慧
分享
收藏
点赞
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