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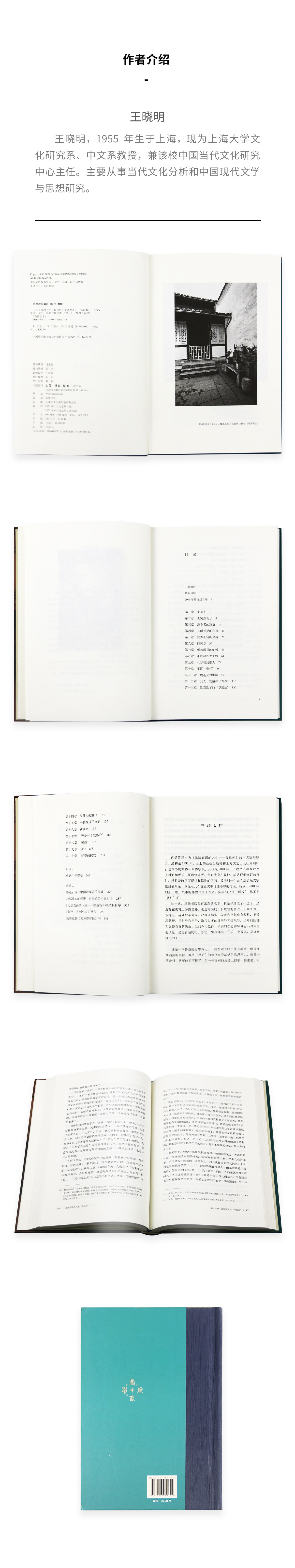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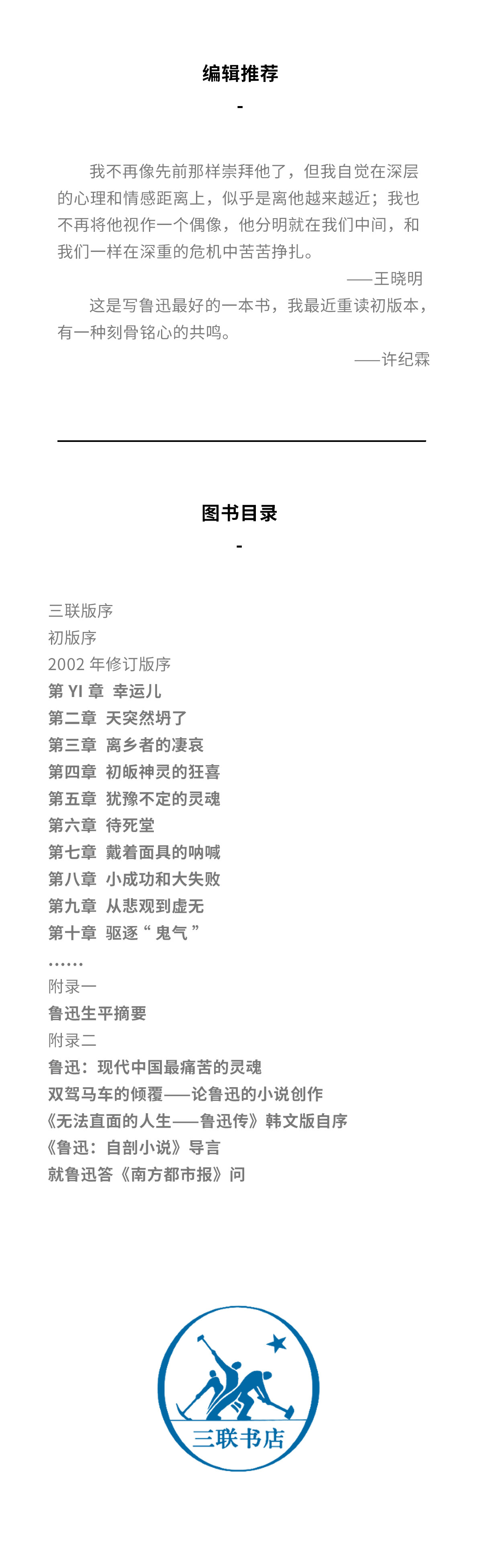


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王晓明
这是写鲁迅最好的一本书,我最近重读初版本,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共鸣。 ——许纪霖


三联版序
初版序
2002年修订版序
第一章 幸运儿
第二章 天突然坍了
第三章 离乡者的凄哀
第四章 初皈神灵的狂喜
第五章 犹豫不定的灵魂
第六章 待死堂
第七章 戴着面具的呐喊
第八章 小成功和大失败
第九章 从悲观到虚无
第十章 驱逐“鬼气”
第十一章 魏连的雄辩
第十二章 女人、爱情和“青春”
第十三章 没完没了的“华盖运”
第十四章 局外人的沮丧
第十五章 一脚踩进了漩涡
第十六章 新姿态
第十七章 “还是一个破落户”
第十八章 “横站”
第十九章 《死》
第二十章 “绝望的抗战”
附录一
鲁迅生平摘要
附录二
鲁迅: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
双驾马车的倾覆——论鲁迅的小说创作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韩文版自序
《鲁迅:自剖小说》导言
就鲁迅答《南方都市报》问


当然,在和“鬼气”的对抗中,鲁迅并非处处失败。自从回国以后,他就不再是一个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他赖以对抗“鬼气”的主要力量,也早已不是那种明确的理想主义信念,而是他的生命的渴望发展的本能。不甘心“待死”也罢,想告别魏连殳也罢,都主要是这本能勃发的结果。因此,即便在思想上挣不脱“鬼气”的包围,他也会在其他方面继续挣扎。到1925年,他终于在一个方向上打开了缺口,那就是对女人的爱情。
我们都还记得,一直到1920年代初,他的生活中可以说是毫无女性的温馨气息的。为了不使母亲伤心,也为了维持自己的名誉,他甘愿过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但是,虽说自己愿意,这样的日子却非常难捱,1918年初,他的一位生性洒脱的堂叔病逝,他在信中向朋友慨叹:“家叔旷达,自由行动数十年而逝,仆殊羡其福气”, 就透漏出他对自己这状态的不满有多么深切。随着对民族和社会的失望日益加深,又与周作人闹翻,大家庭的理想破灭,内心深处的虚无感弥漫开来,他这不满也一天比一天壮大。他不是看出了原先的那些牺牲的无谓,不想再那样“认真”么?他不是说从此要顾自己过活,随便玩玩,不再一味替别人耕地么?原先重重地压在背上的那些责任感,似乎日益显出它们的轻薄,他势必要一次次反问自己:你个人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不就是冲出单人禁闭的囚室,寻一位真心喜爱的女人吗?他在虚无感中陷得越深,那孝道和婚姻的束缚力就越减弱,我简直想说,正是那“个人主义”的情绪,激活了他追求爱情和个人幸福的激情。
他开始和姑娘们来往,有的来往还相当密切。到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之后,他的客厅里更出现了一群聪明活泼的女大学生。有一次过端午节,他请她们来家中吃饭,竟喝得有了醉意,“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之颧骨”,又“案小鬼[指许广平]之头”, 手舞足蹈,开怀大乐,那久受压抑的生命活力,勃然显现。
就这样,在1925年夏天,鲁迅和这群女学生中的一个——许广平——相爱了。
(此处空一行)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比鲁迅年轻近20岁。虽是南方人,身材却颇高,好像比鲁迅还要高一些。人也不漂亮。但是,她却是那群女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 ,对社会运动,甚至对政治运动,都满怀热情。她敬仰鲁迅,也能理解他,对他的追求就更为热烈。你不难想象,当她表白了爱情,又从他那里收获同样的表白的时候,她的心情会多么兴奋。
但是,鲁迅的心情却复杂得多。他爱许广平,但对这爱情的后果,心中却有疑虑。这疑虑还是来自虚无感,它就像一枝锋利的双刃剑,既戳破孝道之类旧伦理的神圣性,又戳破个性解放、“爱情至上”之类新道德的神圣性,它固然锈蚀了鲁迅的精神旧宅的门锁,却也会当着他的面,把他打算迁去的其他新居都涂得一团黑。传统的大家族当然是无价值的,孝道也可以说是无谓的,但那新女性的丰采,恋爱婚姻的幸福,是不是也是一个幻象呢?鲁迅早已过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年龄,再怎样喜爱许广平,也不会看不出她的缺陷。社会又那样险恶,在1925年,无论北京的学界还是官场,都有一股对他的敌意在蜿蜒伸展,一旦他背弃自己的婚姻,会不会授那些怨敌以打击的口实呢?倘若种种打击纷至沓来,他们的爱情禁受得住吗?在写于这时候的短篇小说《伤逝》中,他把涓生和子君的结局描绘得那么绝望,把他们承受不住社会压力、爱情逐渐变质的过程表现得那么可信,你就能知道他的疑虑有多深,思绪怎样地偏于悲观了。
所以,他最初的行动非常谨慎。他向许广平表明,他无意和她正式结婚,在名分上,他还保持原来的婚姻。这实际就是说,他并不准备彻底拆毁那旧式婚姻的囚室,他仅仅是自己凿一个洞逃走。他也不想马上和许广平同居,固为条件还不具备,还需要作些准备。
首先是钱。为了购置砖塔胡同的房子,他已经欠了朋友800块钱的债,一直无力偿还;他又才被章士钊革职不久,倘若因为与许广平同居而遭人垢病,打输了官司,那岂不是要落入涓生式的恶运了吗?其次,他也不愿在北京与许广平同居,离母亲和朱安太近,同在一座城中,毕竟不大方便。北京的空气又日渐压抑,后来更发生“3·18”惨案,搞得他几次离家避难,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总得另寻一处安全的地方。
当然,他最担心的,还是和许广平的爱情本身。这里既有对许广平的疑虑,也有对自己的反省。“我已经是这个年纪,又有这么多内心的伤痛,还能够容纳这样的爱情,还配得上争取这样的爱情吗?”“让她这样与我结合,她的牺牲是不是太大了?”“即便她现在甘心情愿,以后会不会后悔?”“她究竟爱我到了什么程度?”…… 我相信,每当夜晚,他躺在床上抽烟默思的时候,类似上面这样的疑虑,一定会在他心中久久盘旋,去而复返。他面前似乎已经浮出了一条逃离绝望的清晰的生路,但他何时往里走,又怎样走进去,却不容易下决断。
1926年初春,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新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的林语堂,是鲁迅的老朋友,邀请他去厦门大学任教。那里远离北京 ,邻近广东,不但气候温暖,政治空气也似乎比北京要和暖得多,每月又有400块钱的薪水,正是一个适合开始新生活的地方。鲁迅欣然应允,就在这一年8月离京南下,适逢许广平要回广州,便一同动身。
但是,尽管有这么合适的机会,又是与许广平同行,他仍然不作明确的计划。他只是与许广平约定,先分开两年,各自埋头苦干,既是做一点工作,也为积一点钱,然后再作见面的打算。 你看,他还是用的老办法,当对将来缺乏把握、难下决断的时候,就先将决断往后推,拖延一阵子再说。
(此处空一行)
鲁迅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厦门岛。可是,几乎从第一天起,种种不如意的事情就接踵而来。地方的荒僻,人民的闭塞,学校主事人那样势利,教师中的浅陋之徒又这么多,再加上若干职员和校役的褊狭懒散,终至使他连声叹息:自己还是天真了,民国首府的北京都那样糟糕,厦门还会好么?
他尤其恼火的是,他在北京的那批学者对头——他称之为“现代评论派”的,如今也纷纷南下,有的就直接到了厦门大学,和他做同事。譬如顾颉刚,他曾公开说佩服胡适和陈西滢,现在然也到厦门大学来做教授了;自己来了不算,还推荐其他的熟人来,这些被荐者来了之后,又引荐另外的人,这在鲁迅看起来,简直就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 他写信对许广平抱怨:“‘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 远远地躲到厦门来,竟然还是会遇上他们;在北京受排挤,跑到这里来还可能受排挤,这怎么能不教他光火呢?
于是他这样向朋友描述自己的心情:“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曰:仰东硕杀!我勿要带来者!” “仰东硕杀”是绍兴土话,意思是“操他妈的!”厦门大学竟然逼得鲁迅不断要在心里骂出这样的话,他当然不愿在这里久留了。到厦门不到4个月,他就开始想走。一个学期的课还没讲完,就已经向校方递了辞呈。他原想在厦门大学工作两年,现在却提前一年半离开,当他独自一个人在夜灯下写辞呈的时候,先前的种种走投无路、屡屡碰壁的记忆,一定又会涌上脑际吧。
处在这种经常要骂出“仰东硕杀”的心境里,他对与许广平的爱情的疑虑,自然会逐渐加重。1926年11月,他写信对她说:
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积几文钱,将来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一些事(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倘同人排斥,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多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须熬。末一条则太险,也无把握(于生活)。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
他是真的想不好:虽然列出了三条路,想走的却是第三条;但他不知道许广平是否真愿意和他携手共进,也不知道这条路是否真能够走得通。疑虑重重之际,就干脆向许广平和盘托出,既是试探,也是求援。
许广平是多么敏感的人,立刻就觉出了鲁迅的心思,她知道他有疑虑,也知道这疑虑的深广,她甚至还想到了他的可能的后退,这自然使她深为不满,就用了这样激动的口气回信说:
你信本有三条路,叫我给“一条光”,我自己还是瞎马乱撞,何从有光,而且我又未脱开环境,做局外旁观。我还是世人,难免于不顾虑自己,难于措辞, 但也没有法了。到这时候,如果我替你想,或者我是和你疏远的人,发一套批评,我将要说: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你自身是反对遗产制的,不过觉得这份遗产如果抛弃了,就没人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遗产。……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的权利,我们没有必吃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因了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我们打破两面委曲忍苦的态度,如果对于那一个人的生活能维持,对于自己的生活比较站得稳,不受别人借口攻击,对于另一方,新的部分,两方都不因此牵及生活,累及永久立足点,则等于面面都不因此难题而失了生活,对于遗产抛弃,在旧人或批评不对,但在新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以任何无理批评,即批评也比较易立足。……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了管理人行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这是就正当解决讲,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
这信写得很动情,也许是急不择言吧,许多话都说得很直。她一下子挑穿了鲁迅不愿意解除旧式婚姻的内心原因,又用那样热烈的口气激励他作出决断。她甚至不隐瞒自己的焦急和不快,最后那一段话,简直是在赌气了。
幸亏是这样的急不择言,反而打消了鲁迅的疑虑。说到底,他最大的顾虑正在许广平本人,现在从她的这封信,他看见了她的真心,许多担心和犹豫,一下子消散了。他立刻回信,语气非常诚恳,不再有前一封信中的含混,态度也很乐观。似乎是决意要走第三条路了: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动的巨变而失力量。 ……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 ……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我觉得现在H.M. [即“害马”,对许广平的昵称] 比我有决断得多……
一个多月以后,他更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 这所谓“枭蛇鬼怪”,就是指许广平。
正在他终于确信了许广平的爱情的同时,广州的中山大学接连来信,热情地邀他去担任国文系的教授和主任。这无疑从另一面增强了他的勇气。人世间不但真有值得信赖的爱情,他自己也还有可以阔步的生路,无论从哪一头看,他的境况似乎都比涓生好得多,在争取新生活的方向上,他确乎应该试一试了。
从事后的旁观者的眼光看,这自然是又有点陷入错觉了,但是,一个刚刚开始全身心浸入爱情的人,多半会情不自禁地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是玫瑰花,会以为自己一拳便能打出个新天地,鲁迅的这一点错觉又算得了什么?他内心的虚无感是那么深厚,他大概也只有靠这样的错觉,才能够摆脱它的羁绊吧。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1927年1月到广州,住进中山大学之后,即由许广平陪伴在旁,即便有客来访,她也并不回避。10个月之后他到上海,更在虹口的景云里租了一幢3层的房子,与许广平公开同居。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20年之后,他总算逃出来了。
(此处空一行)
身边有了许广平,鲁迅似乎年轻了许多。他的衣着现在有人料理,头发和胡须现在有人关心,在那么长久地禁欲之后,他终于体会到了女性的温暖和丰腴,他的整个心灵,都因此变得松弛了。在广州,他与许广平等人接连游览越秀山,白天逛花市,晚上看电影,满脸欢愉,兴致勃勃。到上海之后不久,又和许广平去杭州游玩,虽然是七月份,暑热逼人,他却毫不在意,去虎跑品茶,到西湖泛舟,快活得像一个小孩子。陪同游玩的许钦文和章廷谦都暗暗惊喜,从他们十几年前做鲁迅学生的时候起,还从未见他表现过这样浓的游兴。
鲁迅本是一个善感的人,你只要读过他的《社戏》,就一定会记得他对家乡风物的那份善感的天性。可是,由于家道中落以后的种种刺激,到了青年时代,他却对自然风景失去了兴趣。他在东京那么多年,只去上野公园看过一次樱花,而且还是和朋友去书店买书,顺路经过才进去的。他在仙台整整两年,附近不远就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松岛,他也只去玩过一次。回国以后,住在杭州那样优美的地方,一年间竟只去西湖游过一次,还是朋友请的客。别人都连声称赞“平湖秋夜”和“三潭映月”,他却以为“不过平平”。1924年他写《论雷峰塔的倒掉》,居然把雷峰塔和保俶塔弄错了位置,你当可想象,他平日对这些景致是如何不留心。以后到北京,住的时间更长,游玩却更少。即使去西安,主人安排他游览名胜古迹,他最感兴趣的地方,却是古董铺。弄到最后,他甚至公开说:“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
不知道他说这话有多少调侃的意味,倘是讲真话,那他是错了。对自然风景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每个人的天赋当中,多少都埋有亲近大自然的情感萌芽,只是由于后来的经历不同,有些人的这个天性得到激发,变成酷爱自然之美的多情者,有些人的天性却遭受压抑,便自以为对山水缺乏敏感了。面对优美的自然风景,我们会不会深受感动,这实在可以作为衡量我们的精神是不是正常发展的重要标尺。因此,看到鲁迅在广州和杭州玩得那样快活,我想谁都会为他高兴,他童年时代的善感的灵性,那《社戏》中的天真的情态,终于在他身上复苏了。
当然,爱情在他身上唤起的,绝不止是亲近自然的游兴。一说到爱情,人总会习惯性地想到青春,想到年轻的生命,尤其鲁迅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更容易把爱情看成青年人的专利,许多人鼓吹爱情至上的最大理由,不就是青春和生命的天赋权利吗?许广平是那样一个富于活力的姑娘,又比鲁迅年轻那么多,鲁迅一旦与她相爱,这爱情就会对他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要求他振作精神,尽可能地焕发生命活力。倘说在绍兴会馆时,他自安于“农奴”式的枯守,还可以倚仗老成和冷静来抵挡世俗欢乐的诱惑,甚至克制和压抑生命的本能冲动;他现在却必须完全改变,要竭力振奋自己的人生热情,竭力放纵那遭受长期压抑、差不多快要枯萎的生命欲望。男人毕竟是男人,鲁迅即便把人生看得很透,也总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富于活力的人,一个能够让爱人崇拜的人。他当然有自卑心,所以才说自己“不配”; 但他更多的是要强心,他希望自己能有活力,至少在精神上依然年轻。事实上,也只有当这要强心在他头脑中占上风的时候,他才会坦然地接受许广平的爱。只是这要强心一面允许他拥抱许广平,一面却又暗暗地告诫他:你必须像个年轻人!
鲁迅本就是情感热烈之人,假如他真正率性而行,至少在精神上,他的许多表现自然会洋溢出青年人的气息。他对黑暗的毫无掩饰的憎恶,他那种不愿意“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决绝的态度,都是极能引起青年共鸣的性情。但是,他毕竟又是个思想深刻的人,40年的经历早向他心中注入了一种深广的忧郁,迫使他养成一种沉静的态度,不喜欢雀跃欢呼,也不主张赤膊上阵。不轻信,更不狂热,选一处有利的屏障,伏在壕堑中静静地观察:这正是他到北京以后逐渐确定下来的人生态度,也是真正符合他的深层心境的人生态度。因此,一旦他有意要振作斗志,焕发精神,以一种青年人的姿态置身社会,他的言行就往往会逾出其“常态”,显出一种特别的情味。
比方说,他从来就是个实在的人,说话都是有一句说一句的,可在砖塔胡同的家里与姑娘们笑谈的时候,他却屡次提到自己床铺下面藏着一柄短刀,又详述自己在东京如何与“绿林好汉”们[指光复会中人]交往,言语之间,时时露出一丝夸耀的意味。再比如,到1920年代中期,他对青年学生已经不抱什么期望,所以“女师大风潮”闹了半年多,他一直取旁观态度。可是,一旦与许广平们熟识,他的态度就明显改变,代她们拟呈文,起草宣言,还一个一个去联络教员签名,组织校务维持会,里外奔走,口诛笔伐,终至被章士钊视作眼中钉,我不禁想,倘若他并不认识许广平她们,他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吗?即便出于义愤,站出来声援学生,也不过是像联署那份宣言的马幼渔们一样,说几句公道话了事吧。
同样,他向来就不大赞成学生请愿,不但对“五四”运动作过那样冷淡的评价,就在1926年3月18日上午,他还硬把许广平留在家里,不让她去执政府门前请愿:“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东西等着要抄呢!” 可是,当“3·18”惨案的消息传来,死难者中间又有他熟稔的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他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他接二连三地写文章斥骂当局,口气激烈得近于切齿,我难免又要想,倘若他不是对刘和珍们怀有亲近的感情,他的反应会不会有所不同?身为这些年轻姑娘的亲近的师长,对她们的惨遭屠戮却全无救助之力,望着许广平们的悲愤的眼光,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猜想,大概正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才使他下笔的态度格外激烈,诅咒的口气也格外决绝吧。推而广之,他在1920年代中期的公开的文章中,依旧勉力唱一些其实心里并不相信的希望之歌;在明明已经深觉沮丧的情形下,依旧戴着面具,表现出充满热情的斗士的姿态,所有这些“心口不一”的行为背后,是否都有那爱情或准爱情的压力在起作用呢?
不用说,他到广州与许广平会合以后,这压力就更大了。有活力的人不应该老是神情阴郁,于是他勉力说一些鼓舞人的话,有一次甚至断言:“中国经历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朵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 有活力的人不但应该对将来抱有信心,更应该投入实际的革命,许广平就正是这样做的,她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对“国民革命”满怀热情,于是鲁迅藏起他先前那个彻底的怀疑意识,也来热烈地赞扬北伐,赞扬革命。尤其是对青年人发表演讲,他更是慷慨激昂。他称赞广州是“革命策源地”,而现在已是“革命的后方”;他向中山大学的学生呼吁,要他们用“革命的精神”,“弥漫”自己的生活,“这精神则如日光,永远放射,无远弗到。”。 他更说自己“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在一次演讲会上,他甚至提高了嗓门,大声号召说:“广东实在太平静了,我们应该找刺激去!不要以为目的已达,任务已完,像民元革命成功时说的,可以过着很舒服的日子! 读着他这些激进的言辞,我仿佛能想象到当时的情景:一个黑瘦矮小、年近半百的人,迎着台下年轻听众们的热切的目光,用绍兴腔提高了嗓门大声呼喊——为了焕发青春的气息,他的确是尽了全力了。这也自然,身边有许广平,四周又是初到广州时的青年人的热烈的欢迎,任何人处在这样的境遇里,恐怕都不免要兴奋得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吧。
(此处空一行)
但鲁迅毕竟不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1927年旧历初三,他和许广平等人漫步越秀山,当踏上一个小土堆时,也许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身手还健,他执意要从那土堆上跳下来。他是跳下来了,但却扭伤了脚,半天的游兴,就此打断。这脚伤还迟迟不肯痊愈,半个月后他去香港作演讲,还是一拐一拐的,走得很费力。不知为什么,每当读到他在广州的那些激昂的言辞,我总要想起这件事,它似乎是一个象征,既表现了他的心情的活泼,更表现了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45岁才尝到爱情,以当时人的一般状况,已经太晚了,他无法像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那样忘情地拥抱它。在整个1920年代中期和晚期,他常常都情不自禁地要用恶意去揣测世事,要他单单在争取个人幸福的事情上卸下心理戒备的盾牌,他实际上也做不到。因此,即使他决意和许广平同居了,即便他努力显示一种勇敢的姿态,他内心还是相当紧张。
这紧张也井非无因。就在他到厦门不久,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间已经有一种传闻,说他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又从上海同船去厦门,“大有双宿双飞之态”。 他们还没有同居,议论就已经来了,真是同居了,那流言真不知要飞舞到怎样。事实上,1928年2月,他和许广平同居不到半年,就收到过这样一封信:“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 写信人自称是崇拜鲁迅的青年,却如此看待他和许广平的爱情,这教他作何感想呢?社会上永远有好奇者,有好事者,有小人,有庸众,你就是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只要你是名人,就总会有流言粘在背上,有恶意跟踪而来。干脆想通了这一点,不去管它,人反而能活得自在,鲁迅同辈的文人中,就颇有一些人是放浪洒脱,无所顾忌的。但是,鲁迅做不到这一点,愈是心中“鬼气”蒸腾,愈是把社会看得险恶,一点小小的流言,就愈会引发他广泛的联想:形形色色的遗老遗少的攻讦,报章杂志上的恶意或无聊的渲染,学界和文坛上的有权势者的封锁,最后是经济上的拮据和窘困:他已经很难摆脱那个涓生和子君式的悲剧的梦魇了。
正因为心头总是压着那个梦魇,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之后,依然左盼右顾,如履薄冰。他将许广平的卧室设在3楼,自己则住2楼,对外只说她给自己当助手,作校对,除了对极少数亲近朋友,一概不说实情。即便去杭州,实际上是度蜜月,他也要遮遮掩掩。动身之前,他先要杭州的朋友预订1间有3张床的房间;到了杭州,许钦文等人接他们到旅馆,住进那房间后,正要离开,他却唤住了许钦文,眼睛盯着他,“严肃地说:‘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他并且指定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将自己和许广平隔开——这是怎样奇怪的安排! 一年半以前,他鼓励许广平到中山大学给他当助教,口气是何等坚决:“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对语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 可你看他这住房的安排,不正是自己要作流言的囚人吗?越是知道他白天玩得那样快活,看到他晚上这样睡觉,我就越感到悲哀,除了喝醉酒,他大概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放松过吧,陪伴心爱的女人到西湖边上度蜜月,都会如此紧张,这是怎样可怜的心境,又是怎样可悲的性格?
这样的紧张一直持续了很久。从一开始,许广平就没有向亲属说过实情。直到1929年5月,她已经怀了5个月的身孕,她的姑母到上海,她才将实情告诉她,并请她转告家中的其他人。在鲁迅这一面,也是从这时候起,才陆续告诉远方的朋友。但即使是通报,口气也往往含糊,譬如他给未名社的一位朋友写信,说那些流言如何气人,于是他索性“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房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 这哪里只是通报,中间夹着这么多解说,而且到了最后还是含含混混,并不把事情说清楚。也许他并非存心如此?那么,心里明明想告诉别人,写出来却这样吞吞吐吐,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许广平将实情告诉姑母后,对鲁迅说:“我的亲人方面,如由她说出,则省我一番布告手续,而说出后,我过数月之行动[指生产]可以不似惊弓之鸟,也是一法。” 什么叫“惊弓之鸟”?莫非在下意识里,他们自己也并不真能坦然?
一个人受多了压抑,就容易丧失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的能力,甚至连评价自己,也会不自觉地仿照周围人的思路。尤其当与社会习俗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是再明白自己应该理直气壮,心理上还是常常会承受不住,不知不觉就畏缩起来。鲁迅和许广平这“惊弓之乌”的紧张,是不是也正来源于这一点呢?当然,他们愿意将消息公诸亲友,总还是因为有了信心,你看鲁迅这时候写给许广平的信:“看现在的情形,我们的前途似乎毫无障碍,但即使有,我也决计要同小刺猬[对许广平的呢称]跨过它而前进的,绝不畏缩”, 就明显表露出终于松了一口气的轻松感。但是,要到同居一年半以后,才刚刚松这一口气,他们先前的屏息担心,未免也太过分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之一。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鲁迅能够打开一个缺口,也就应该可以冲出“鬼气”的包围:如果这样来看,他和许广平的同居就正显示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他在冲出包围的途中,要经历那么多的犹豫和权衡,这会不会使他终于争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觉就变了味呢?男女爱情,这本是为人的一项基本乐趣,倘若你必须要耗费那么长的生命,经历那么深的痛苦,才能够获得它,你还能说它是一项乐趣吗?用太多痛苦换来的幸福,它本身已经不完全是幸福,它甚至很容易变成一笔债,将承受者的脊梁压弯。因此,一想起鲁迅硬拉许钦文同眠一室的情景,我先前那因他们同居而产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鲁迅是获得了胜利,可恰恰是这个胜利,宣告了他可能难得再有真正的胜利。


一部影响深远的鲁迅思想传记,代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界努力冲破启蒙话语,力图回到“鲁迅本身”,从个体生存的心理结构和思想困境的角度去重新解读鲁迅的重要尝试。
作者以鲁迅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发展为经纬,以其三次努力抵抗自己的“鬼气”和“绝望”为主轴,把鲁迅思想气质中的怀疑、矛盾、阴郁乃至黑暗刻画得深入骨髓,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在情感和心理的共鸣中,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的鲁迅那巨大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悲剧。
作者曾解释如此理解鲁迅的原因,是“想要打破那一味将鲁迅往云端里抬的风气,想要表达对鲁迅的多样的情感,不仅仅是敬仰,是热爱,还有理解,有共鸣,甚至有同情,有悲哀;我更想要向读者显示生活的复杂和艰难,不仅仅是鲁迅,也是我们自己,不仅仅是过去,也是现在和将来”。


王晓明,1955年生于上海,现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兼该校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当代文化分析和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研究。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一家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出版机构。建店八十余年来,始终秉承“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坚持“一流、新锐”的标准,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







![香水史诗[新知文库113]](https://img01.yzcdn.cn/upload_files/2020/06/23/FpS7TxHopTB_jpYvFXCvfEZHhTD1.png?imageView2/2/w/260/h/260/q/75/format/jpg)
![阅读力: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聂震宁 著]](https://img01.yzcdn.cn/upload_files/2017/07/26/FsGXVff02FPRLqbxDE47NEOpBk1s.jpg?imageView2/2/w/260/h/260/q/75/format/jpg)
![迷楼(精装)[宇文所安 著]](https://img01.yzcdn.cn/upload_files/2018/06/21/FrttrzzscalmfCJKIEdvL73mSnus.jpg?imageView2/2/w/260/h/260/q/75/format/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