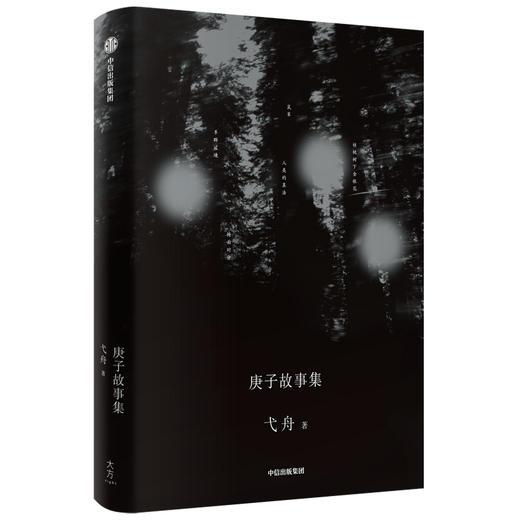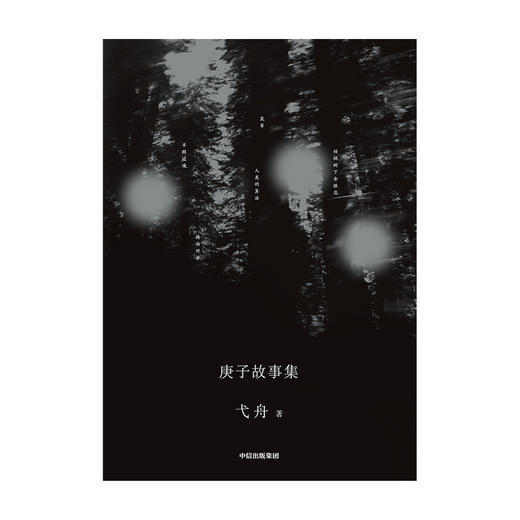庚子故事集 弋舟 著 李敬泽、苏童、田耳共同推荐 鲁迅文学奖得主 短片小说故事集 中信出版社图书 正版
| 运费: | ¥ 0.00-15.00 |
| 库存: | 55 件 |
商品详情
李敬泽、苏童特别推荐!鲁迅文学奖得主弋舟2020年短篇小说集
《收获》年度榜单作品

书名:庚子故事集
定价:58元
作者:弋舟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0-08
页码:177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ISBN:9787521719727

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郁达夫小说奖得主弋舟2020年全新短篇小说集。李敬泽、苏童、田耳共同推荐,《收获》年度榜单作品。
《庚子故事集》是弋舟创造的当下生活世界,绵延致密的细节与具体而微的想象相互交织,是2020庚子年的记忆保留之书,描述了2020年大事件之下的日常停靠,人们努力在困境中寻找生活的微光。
特有的明暗交界美学风格。弋舟对人性复杂性和人本质意义的深刻思考,保证了小说的艺术品质,也使他的作品散发出一种诗性的光芒。作品语言细密,深刻婉转,可读性强。

子年对许多人而言是充满难度的一年。弋舟在《庚子故事集》中用五个短篇故事创造了一个当下的生活世界:一个193斤失败的胖子藉由一次邂逅奋力逆流而上,一对年轻男女藉由仓鼠推演出新的爱情,两位女同事疫情之后各怀心事在餐厅相聚……庸常的命运与残酷的现实遭遇,人物在人世颓败转折处却显出顽韧的生机。弋舟拂去生活的表象而直抵核心,他描述了生活的内面——我们为什么活,为什么爱,以及,为什么孤独。

代自序:钟声响起
核桃树下金银花
鼠辈
人类的算法
掩面时分
羊群过境
代后记:等光来

弋舟,当代小说家,历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新人奖、郁达夫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刘晓东》等多部,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我们的踟蹰》等多部,长篇非虚构作品《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随笔集《从清晨到日暮》《无论那是盛宴还是残局》等。
年复一年,弋舟以他小说里一个又一个斑斓的寓体,持续命中着某些你我心头秘而不宣的重要关切。他那藉由小说完成的精神表达,让他在当代中国文学现场独具辨识的高光。
——李敬泽(小说家,评论家)
弋舟尽管发出他孤僻的歌声,而他孤僻的歌声却征服着另一些孤僻的人。
——苏童(小说家)
同辈作家中,惟有弋舟能将学术声口直接接驳于日常细节,再以先锋余韵对当下作焕然一新的赋形,这使得他的小说灵动且厚实,汁液横溢且宏阔幽渺。在小说这一领域,我们只能眼睁睁看他一骑绝尘。
——田耳(小说家)
弋舟《核桃树下金银花》借书写一次邂逅,指引我们奋逆流而上,“指认此生的第一棵树木”,“一头冲进漫天遍野的壮观花海”,那是火光和灵韵绽现的源头,那是置身于具体事物中而目击本源、“语语都在目前”,那是新鲜的感受力还未被僵死的语言所驯化的时刻……
——金理(评论家)
弋舟小说所追求的,正是我所乐见的情感的深刻,他即是我所说的那种语言的信徒。
——阿来(小说家)
弋舟的叙事净省、硬朗而准确,同时也拥有珍贵的密度感,这足以使他跻身中国*优秀短篇小说的作者行列。
——格非(小说家)

《桃花树下金银花》节选
重新下马,我推着那家伙走。这是眼下行走在玉林街唯一正确的姿势。我当然可以还骑着它,跑慢点儿,但我没法想象一个胖女孩像个跟在大统领座驾边儿慢跑的保镖那样地尾随着我。谁能想到呢,我从张桓那里抢来一匹快马,原来却终究是要推着走的。如果知道是这样的局面,张桓他也是会宽恕我的吧。
我们走在四月的玉林十巷里。不必说,路面完全被我们堵塞了。这却给予我们一种满盈的豪情。我们最大程度地充斥了虚无的时光,拥有了结结实实的肉身者的尊严。迫于无形的压力,路人一定是要给我们让道的,贴着墙根,让我们簇拥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先行,款款而过,我们就是这样被世界礼遇,连风都得绕着我们走。
想必她的心情也与我仿佛。证据是,走了大约十分钟后,她开始显得有了些闲情逸致。
“核桃树开花了嗦。”
她指着排污沟边浓荫蔽日的树木说。
对于树木,我是一窍不通的。顺着她的胖指头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了一种树。这树,大约有二十米高,树皮灰白,纵向排列着浅纹,花苞完全颠覆我对花朵固有的认知,差不多就是我眼里认定的果实,只在顶部有那么一点儿花的意思。
“我家地里种了好多核桃树。”她说。
我不觉得她这是在卖弄,因为种核桃树这类事儿,在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值得卖弄的事儿了。很久以来,人们卖弄着的,早已经是种摇钱树之类的把戏了。可我还是感到了羡慕。让我羡慕的,除了种核桃树这事,还有她大大方方说出此事的从容和磊落。我想我是做不到的,我也是个只配跟人吹嘘栽种了摇钱树的家伙。所以,尽管我们同样是个胖子,也许还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一个失败的胖子,但至少,她在种核桃树这类事儿上,境界遥遥地领先了我。
“真不错。”我赞叹道。
她话头一转,说:
“还有金银花,我妈在核桃树下还种满了金银花。”
我一时有些转不过弯儿,仰着的脑壳不由自主地埋下来,好像生怕一不小心践踏了那核桃树下的金银花。没错,我出现幻觉了,感觉不是行进在玉林街的某一巷里,而是如沐春风,徜徉在一派田园风光中。
“知道啥是金银花不?”
“不知道,”我说,“—噢不,我知道,冲凉茶的咯。”
我不想在她面前暴露我的无知,不是好强,竟只是温柔的不再与世界拧巴的心情。
“没错,可是你肯定不知道它还叫别的啥名字。”
她和我对视了一眼,我们的眼神胖胖地对撞了一下。
“它还叫忍冬花。”她说,“因为开出来的花先是银白色的,再变成金黄色,才被叫成了金银花。”
“还是叫金银花好听,又是金又是银的。”
我依然是个只晓得摇钱树的浅薄蠢货。
“其实没那么富贵,金银花一点儿也不娇气,种上能有三十年的收成呢。”她停了话头,发出一声缥缈的叹息,“马上五月了,田里的金银花就要采摘了。”
说完这话,她便离我而去,仿佛直接去往田野里摘金银花去了。
我当然是回不过神儿,换了谁都会一下子回不过神儿。何况我还推着辆电动三轮车,于是只能傻在那儿不动。只要想象一下当你从某个动人的、关键还是与某个人共享着的蓝图里突然被遗弃,你就会明白我当时的滋味。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我可能是中暑了。推着辆电动三轮车,即便是在巴适的四月里,一个胖子也会汗流浃背,更可怕的是,这个胖子方才还因为有了另一个胖子的加盟而变得怀有了温情和善意,变得不再觉得自己纯然就是一个失败的胖子,变得鄙视自己的摇钱树思想,变得对植物学发生了轻微的兴趣,变得萌生了一丝去见识田园风光那种自己经验之外景致的愿望—变得就像他自己的一身肥肉那样的柔软。
不是说好了吗,“没事儿,就一起找找呗”。
我不能不做出判断:嗨,死胖子,你今天撞鬼了。哪儿有什么电动三轮车,什么烤兔,什么玉林街,什么飞机场,全是楼,全是楼啊。但做出此种判断的同时,我的脑子里依然充斥着一派自己未曾经验过的风光。
当年,在四月的玉林街上,你可曾看到过一个被雷蒙的、茫然无措的失败的胖子?那天我骑着一辆抢来的电动三轮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穿行在玉林街上。我不甘心,我在拼命地找,拼命地找。我找的既是玉林街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职工宿舍,也不是玉林街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职工宿舍,要“找到点儿什么”这个念头本身,也许才是左右着我的真正的动力。
当暮色四合,我将三轮车开回到学校门口时,好几个张桓一起向我扑来。
那是张桓,张桓的哥哥,张桓的爸爸,以及张桓的亲戚们。他们是一个纸片儿的家族,在我眼里,就是好几个张桓。还没下马,我的后脑壳就挨了一巴掌。那也不过是纸片儿般的一巴掌,但却将我的眼前打出了华丽的金星。
知道吗,我看到了硕果累累的核桃树,我看到了一望无尽的金银花。
许多年过去,如今快递小哥没啥神气的了,新事物成为旧事物,都是这样的结局。
刚刚我还趴在家里的露台上,看小区保安扭着一个快递小哥往外赶。这位小哥端的像张纸片儿,不能不让我将其想象成我的同学张桓。如若真的是张桓,那么他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快递楷模。可这显然没有可能,我为自己滑稽的想象而沮丧。多么无聊啊,或者多么伤怀,一转眼,你就是一个无所事事、胡思乱想的中年胖子了。
我回身进到客厅,倒在沙发上,安静地聆听楼下的吵闹,从呵斥与争执,到辱骂与咆哮。
我一直在周而复始地减肥,这差不多成了我毕生的志业。效果最好的时候,我减到了一百四十五斤—那可真是个像模像样的公子哥儿。但我最初并不知道,上帝赋予我沉重的皮囊,本来是要平衡我灵魂中根深蒂固的轻浮的。这是上帝和我之间一桩很严肃的密约。我就是我自己灵魂的秤砣,是我自己船身的压舱石,我轻了,灵魂便四方飘散,我轻了,就得翻船。大学毕业两年后,在二十四岁的时候,一百四十五斤的我搞砸了家里原本非常兴旺的企业,一夜之间,连居住的房子都得抵押给银行还债。那是我老爸一生的心血。一个公子哥儿倒下了,他在半年之内,体重重新攀爬到一百九十斤以上。
我跟着爸妈离开了成都,就像是一个拖累着双亲的巨型婴儿。我们一家人在西安开了爿只有两张桌子的串串店,每天呼吸充满牛油与花椒味的空气,至少还可以让我们不觉得已然背井离乡。
有那么一个深夜,我在浓厚的川味儿中失声痛哭,老爸不得不连哄带吓地把我拖到街边儿去,以免我惊走店里本就稀缺的客人。他手足无措地站在我身边,而我干脆一屁股坐在了马路牙子上。我这个失败的胖子无法完成蹲姿,要么站着,要么只能坐着,上帝没收了我身体折中的姿势。老爸系着脏兮兮的围裙,神情木然,只能说一些“从头再来”之类的废话。后来我哭累了,抬头发现,自己原来是坐在一棵核桃树下的,黑暗中密实的树叶混为一个整体,从而在夜风中神圣摇曳着的就是整个树冠。那是我唯一认得的树木。
我知道我得振作起来。这并不说明我天生有自强不息的品质,我只是在十七岁时被上帝调教过。可我一旦振作,体重便开始下降,就像是一个悖论。我惧怕自己重新变得轻浮,于是振作一段时间后便重回消极气馁,在某个深夜坐在核桃树下恸哭一场,继而,再度振作。朝三暮四,我活在时重时轻的轮回里。
说来也很神奇,最重的时候,我没突破过一百九十三斤,最轻的时候,也再未跌至一百七十三斤以下。从一百九十三斤到一百七十三斤,这个区间,俨然是我开展生命运动唯一可行的活动半径,我的跑道并不长,只能折返在这样的一个摆幅里;我所有的悲伤与欢乐,见诸肉身,不过起伏在这样一截微不足道的波段里。不过区区二十斤—等我有一天终于勘破了这个秘密,我就突然得到了解放。因为我看到了本质,看到了生命的限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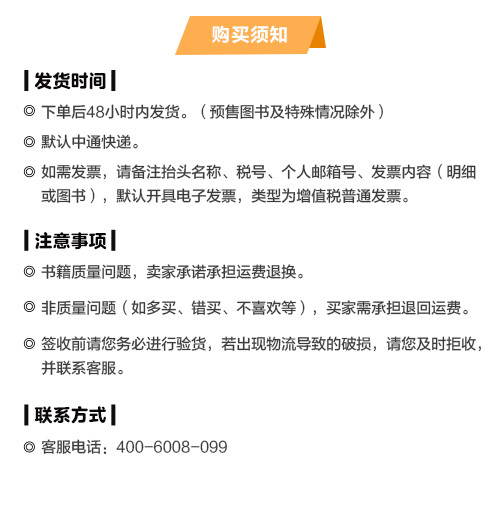
- 中信出版社
- 中信出版社坚持“我们提供知识,以应对变化的世界”的出版理念,以高端优质的内容服务,多样化的内容展现形式,为读者提供高品质阅读与视听内容,满足大众多样化的知识与文化需求。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