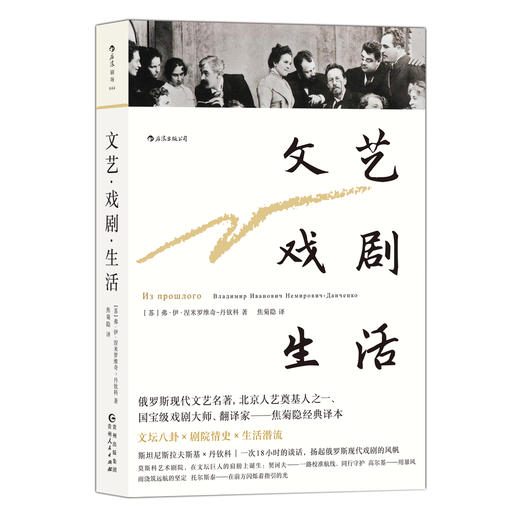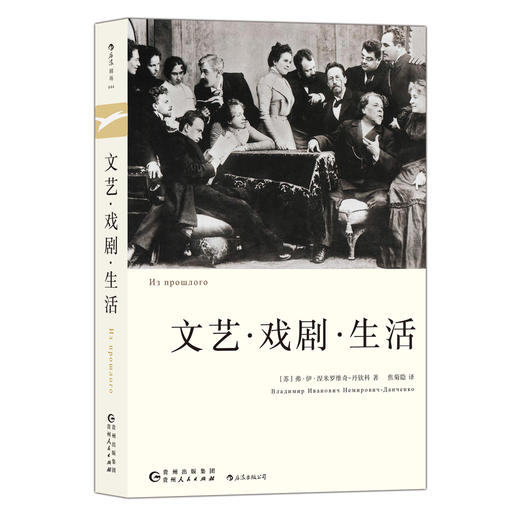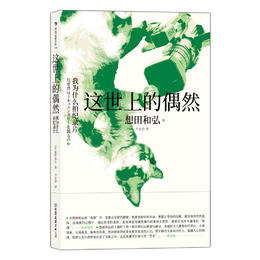文艺 戏剧 生活 俄罗斯戏剧大师回忆录 绝版文艺名著,俄罗斯文化爱好者必读
| 运费: | ¥ 0.00-10.00 |
| 库存: | 80 件 |
商品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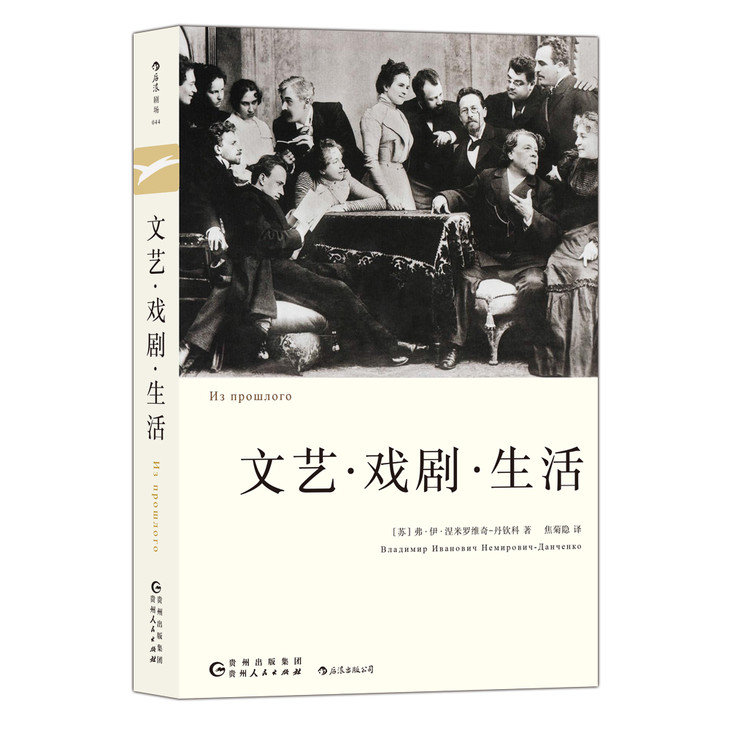
人人都爱契诃夫,他为契诃夫建了一座剧院
俄罗斯戏剧大师回忆录
绝版文艺名著,
俄罗斯文化爱好者必读
北京人艺奠基人之一、
国宝级戏剧大师、
翻译家焦菊隐经典译本
契诃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
文坛大佬、戏剧巨匠的交往八卦
《海鸥》《樱桃园》《万尼亚舅舅》
诞生的幕后故事
一部妙趣横生的创业史、
一封写给契诃夫的情书
著 者:[苏]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
译 者:焦菊隐
字 数:273千
书 号:978-7-221-15996-0
页 数:416
出 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张:13
尺 寸:143毫米×210毫米
开 本:1/32
版 次:2020年8月第1版
装 帧:平装
印 次: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0.00元
编辑推荐
后代的人们,请不要往我们生活中的这一类事情里钻研得太深。像我们这样的人,在一生的光阴里,做的事情实在很少。人们只需知道一个中常的人在他一生当中都做了些什么有益的事情,并把他们所传留下来的这些有益的事情保持住就够了。不过,这些都是纤弱的、不太深刻的。然而,只要遗产本身是巨大的、有价值的,就不会被任何数量的、不合情理的,甚或是有价值的瑕疵所玷辱。相反地,借着这些,后代人想象中的这些人物反而更有人性,更接近我们。人们必须记住:当初,造出粗盆瓦罐传给我们的不是神仙。我们要的是现实的乐观主义,而不是偶像崇拜。
——丹钦科
***
☆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
一次18小时的谈话,扬起俄罗斯现代戏剧的风帆
☆ 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
莫斯科艺术剧院,在文坛巨人们的肩膀上诞生
☆ 文坛八卦×剧院情史×生活潜流
一群文艺中年的创业史,一部百炼成钢的导演艺术秘籍
本书将带领读者穿越俄国现代戏剧的万神殿,潜入生活、社会和戏剧的洪流,去感受文学与戏剧大师们的思想激荡,去见证一座人民的艺术剧院是如何诞生的。
20世纪40年代,戏剧家、翻译家焦菊隐先生在幽暗与愤懑中感受到本书作者丹钦科的召唤,倾注心血将它翻译成了中文。十年后,另一座人民的艺术剧院在北京诞生,而建院“四巨头”之一就是焦先生。从此,这本回忆录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照进了不同文化背景下有着相似经历与诉求的文艺、戏剧、生活。今天,当我们再度翻开它,依然能够触摸到那束光的温度。
名人推荐
太阳召唤着我,艺术召唤着我,丹钦科召唤着我。我唯一的安慰,只有从早晨到黄昏,手不停挥地翻译这一本《回忆录》。每次读到《海鸥》经丹钦科的演出而成功的叙述,欣悦和感动就必然交织着使我心酸一次。我把这本《回忆录》的译名改成了《文艺·戏剧·生活》。
——焦菊隐
在19世纪末的俄罗斯,能够认识到契诃夫戏剧美质的戏剧家,只有正在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起筹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丹钦科。契诃夫被丹钦科的诚恳所打动。这样就有了在世界戏剧演出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海鸥》首演……一个演出造就了一家剧院,也拯救了一个剧作家,这在世界演出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童道明
莫斯科艺术剧院是由两个人创建的,一个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另一个是丹钦科。也许是命运捉弄人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名字常被人们提到,而丹钦科的名字却很少为人所提及,这是不公平的。他们俩都付出了同样多的劳动。他们一生都紧密合作,相互之间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迈克尔·契诃夫
没有丹钦科就不会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氏将会永远做着工厂经理,将会永远在每出戏里都演主角,从悲剧一直演到闹剧,将会永远停留在单纯的形象与声音的路程上,而我们也永远不会接受到他那划时代的伟大理论。
——《莫斯科艺术剧院》
著者简介
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1858—1943),生于格鲁吉亚奥祖尔盖蒂,苏联戏剧导演、剧作家、戏剧教育家、评论家。早年从事剧本和小说创作,1898年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共同创建莫斯科艺术剧院,此后联合执导了契诃夫的《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和高尔基的《底层》等名剧。1928年以后成为剧院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将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搬上舞台,并重排了《三姊妹》。1936年获“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
译者简介
焦菊隐(1905—1975),生于天津,原名焦承志,戏剧导演、戏剧理论家、翻译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建人之一。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8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52年被任命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开创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导演代表作有《龙须沟》《虎符》《茶馆》《关汉卿》《蔡文姬》等,译著有《文艺·戏剧·生活》《契诃夫戏剧集》等。
内容简介
本书是苏联戏剧家丹钦科的回忆录,记述了他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共同创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心路,几十年中与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等文坛巨匠在舞台上合作的往事,以及俄国新剧场改变世界戏剧格局的历程。这是一部妙趣横生、用情至深的艺术奋斗史,也是一本作者由毕生舞台经验锤炼总结的导演艺术秘籍。
本书初版于1936年,同年便有英译本问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书中所记载的俄国文化生活给世界戏剧带来的冲击。中译本初版于1946年,由焦菊隐先生根据英译本翻译,戈宝权、王以铸、吴启源等先生根据原俄文本校对,此后多次再版,对中国戏剧的导表演艺术和剧院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目 录
第一部分 契诃夫
第二部分 一个新剧场的诞生
第三部分 高尔基的剧作在艺术剧院中
第四部分 艺术剧院的青年时代
第五部分 托尔斯泰的剧作在艺术剧院中
译后记
校订后记
出版后记
译后记
一
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七十寿辰的时候,高尔基寄给他一封贺信,开头就说:
亲爱的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
你是一位戏剧艺术的伟大改造者。你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共同创办了一所模范的剧院,这是俄罗斯文化中的重大成功之一……
丹钦科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立上,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等量的功绩。但是,他在全世界进步的剧场艺术的领域里的成功,或者还更重大。
弗拉基米尔·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于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生在高加索,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死在莫斯科。从青年时代起,他的心里就怀着一个创造新的文艺剧场的梦想。他,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在不如意的环境里痛苦地挣扎了若干年,终于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合作,成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受着政治的和社会的压迫,经历了经济的、政治的、战争的和革命的种种困难,终于使艺术剧院成长起来、发展起来,以至占有领导全世界戏剧艺术的地位。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死后,他独力主持着这一座雄伟的艺术大厦。当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的时候,艺术剧院全体参加了卫国战争,迁到萨拉托夫城。丹钦科以八十岁以上的高年,在战争中,仍然尽量维持着艺术剧院的一切新的传统,为全世界保卫着一个新演剧体系的榜样。他在萨拉托夫不断地复演着从前的剧目,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火热的心》、阿·托尔斯泰的《沙皇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如契诃夫、普希金和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古典作品;并且计划,要到已经恢复了和平的各城市去巡回演出。诺维科夫说:“艺术剧院全体,那种从无一瞬刻间断的、深刻而有力的艺术活动,正是这个剧院经常有新的成就去充实艺术的保证。”(见《国际文学》英文版和法文版,一九四二年,三四号合刊)这句话,也正说明了艺术剧院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丹钦科在一生之中,是如何毫无间断地用新的成就去充实这个剧院的。所以,丹钦科的传记作者索博列夫肯定地说:
他整个人生的志趣,是向着唯一的目标:……创立艺术剧院。
而创立艺术剧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我们可以从他一生的戏剧活动里,综括出四项相互联系的成就作为回答:
第一,为了创造一个新的剧场,必须培养出成为这样的剧场的骨干新演员。于是,丹钦科首先和旧的戏剧教育方法做斗争,给戏剧学校的行政、训练、课程、教授方法等等,建立一个新的制度。
第二,为了使新演员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必须反对采用程式化的、形式主义的、肤浅的、庸俗的、无内容的剧本。于是,丹钦科专心去发掘、团结、鼓舞一向被忽略或者被残害的作家,去培养和艺术剧院怀着同样理想的作家,并且改编文学巨著,发扬文学遗产。
第三,为了使这样的剧本的价值不受损害,必须摧毁旧的导演和表演方法。于是,丹钦科提出“导演是一面镜子”“导演必须死而复生在演员的创造中”“导演是教师,又是组织者”和“演员内心体验”的理论。
第四,为了保证这种理论在实践上的实现,必须使“行政屈服于演出”。于是,丹钦科实行了“戏剧行政是为演出而存在”的集体创作制度。
这四种工作范例,便是丹钦科这一本经典著作《回忆录》的宝藏一般的内容。这无须我们再赘述了。
只有丹钦科——教育家——才懂得如何培养和领导青年,懂得不但要以声音、造型、舞蹈、剑术去训练演员,而且要以伦理的、文化的修养和内心情绪的培养去充实演员;只有懂得了如何改造戏剧教育制度,才能造就出克尼碧尔、莫斯克温和无数的划时代的演员。只有丹钦科——小说家、剧作家、批评家——才能使契诃夫、高尔基和托尔斯泰三个巨人在舞台上出现。若不是他第一个认识到契诃夫的内在深度,这一位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伟大剧作家的医生,便会永远埋没在尘土里;其他从生活的各角落聚拢来的、对戏剧做出不同贡献的许多人物,就更不必论了。只有丹钦科——优秀的组织者——才善于领导,善于和恶劣的环境斗争;才能在无数阻碍、挫折和压迫之下,使莫斯科艺术剧院有了光辉的历史;才能像主妇一样地给导演预备好工作环境,使新的导演和表演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也才能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名字和全世界蕞科学、蕞先进的演剧理论成为一体。只有丹钦科——实际战斗者——才证明了新的演出机构和制度不是空想;才证明了艺术剧院既不是一次偶然的成功,也不是一个突然降临的奇迹。
如果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偶然的成功或是突然的奇迹,它早就因为反动政治的压迫而被消灭了。这一个剧院所以没有被消灭——相反地,却更加壮大起来——主要是因它的创办者把一生都贡献在正确的理想上,这样不顾一切地去苦干。一八九八年,当艺术剧院成立的时候,丹钦科正是四十岁,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只有三十六岁。他们的成功,虽然是历史上不多见的例子,虽然有着许多不同的因素,而蕞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现实主义的艺术的忠诚。
丹钦科的理想,不仅仅是要改造俄罗斯的戏剧艺术,而且也要改造全世界的戏剧艺术。他说过:
倘若不但是在美国和在意大利,而是全世界的剧场里都以这种新的制度作为它们的第一个信条,够多么好啊!
丹钦科在召唤着我们!
然而,领导新的戏剧活动或者新的演出机构的人物,本身必须首先像丹钦科这样拥有一个更高的理想:为进步的人类的文化事业而奋斗。他必须尊重生活,尊重现实主义的艺术;他必须没有偏见,没有幻觉;他必须懂得爱护和培养很多的演剧人才,并且引导这些人对艺术生出和他同样的虔诚与信念;他必须能够发现导演和演员,能够用灵魂去了解剧作家,鼓励他们,用全力灌溉他们,使他们在舞台上开花,创造出指导人生的活的画像;他必须认识到自己对观众所负的责任,通过演出为广大的观众服务,并且教育广大的群众为美好的生活而斗争。他又必须具有革命的勇气,为真理和理想奋斗;具备科学的方法,去实现这些理想和真理;具备民主的精神,去和别人合作,并且使合作的人相互合作,创造集体的制度,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蕞后,他为了人类的自由与和平,必须宁愿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必须懂得:一颗麦粒,必须死在土里,才能永生。
丹钦科是具备这一切优良品质的巨人。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
丹钦科是艺术剧院的母亲……而母亲的辛劳,是不容易令人注意的。
是的,他不但是艺术剧院的母亲,而且是新的戏剧教育制度的母亲、新的表演与导演体系的母亲、全世界新的戏剧运动的母亲。
在这一本《回忆录》里,我们可以从莫斯科艺术剧院发展的历史和成就中,看出它在俄罗斯文化生活和全世界戏剧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也就可以看出丹钦科在这里边的地位和作用。
二
我们首先要记住,丹钦科创立新的制度,是在沙皇政府的反动势力压迫之下开始的!
我举出这个事实,是为了向某种只求“做官”的所谓“戏剧家”发出一个警告。不幸的是,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有些人竟像海边的“软体动物”一样,越是在大时代的狂潮涌涨的时候,就越紧紧把住一块危石,不让大水撼动自己。他们在自鸣苟安之时,却忘记那洪流终会连危石都冲到海底的。这些人,正是把戏剧看成做生意、看成做官,而没有看成神圣的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的人;这些人,是极端自私的、出卖偶像老招牌的、不忠于人类的。他们不但没有理想,没有热情和忠诚,而且还与真理和正义为敌!
比如,我遇到过一个人,他对我对待戏剧工作的严肃态度加以批评之后,说:“我们戏剧圈子,本来就是‘鸡皮狗蛋’,你想改革是没有办法的!何必呢?这就是这么一行!”这个人,正负着我国唯一的一个戏剧学校的领导责任。由他这个想法可以推知他的行为——也一定是除了“鸡皮狗蛋”以外,就不会有别的了。
这是我自己的错误:没有深思熟虑,就像做梦一般地加入了那个戏剧学校。那里分教员和学生这样的形式,但是,不但没有像瓦赫坦戈夫所要求的不能只“教”学生,还要“教育”学生,而且,对丹钦科所要求的以声音、造型、舞蹈、剑术和一般文化课程作为基本训练也只是例行公事。我看不出那个地方的行政当局的教育目的是什么——除了他的“鸡皮狗蛋”的理论。我要求当局建立新的教育制度,要求加强课目内容和充实训练方法,至少,要求不要贻误青年,然而,所得的答复,反是一串“鸡皮狗蛋”的对付。本来,有些人和臭虫、老鼠一样,自己情愿生活在黑暗当中,不敢去朝向太阳。他们既已习惯于黑暗,反而认为光明是反常的、反动的、破坏性的。如果有人强迫他们去面对太阳,他们就必然为了存续自己的残喘,拼命号召一群怕光的同道来向你狂咬。《圣经》上说:
“凡是为恶的,就必怕光。”凡是自觉到没落之必然性的,就必然用尽全力去打击新的和向上的。
然而,我的错误是:向耗子要求光明——这岂不是一种梦想吗?
没有合理的教育,我们用什么去完成培养演剧的下一代人的工作呢!
在这个学校里,我又遇到一次演出:分配演员——导演没有权利;装置、道具和服装——导演也没有权利提出任何意见。不但由一个流氓专断地把排演的时间给导演规定得极短,而且导演没有过问那出戏在什么时候才可以正式上演的权利。不但如此,这一切工作,都被学校当局交给这个负着特殊“任务”的流氓来总管。因此,这个人便可以对导演下命令,随时独裁,随时贴出“师生一体凛遵勿违”的布告,而且,他还能在演出期间,强暴地不通知导演而开除演员。而这一切,反都是那个学校的校长加以鼓励、予以表扬的!
这,更令我日夜思念着丹钦科!
在这种压迫之下,我的梦想和热望,只有寄托在另外一个工作上,那就是:把丹钦科的《回忆录》很快地译出来,好供给全国戏剧工作者一本教科书,同时,也好向全国戏剧界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
像一个囚徒想挣出牢狱一样,我每天从头到脚,就仿佛有一只凶兆的蜘蛛在不断地蠕动。愤怒的火、失望的冷水和早知就不该来这里的追悔,在我的心里激斗着,像炸弹将要爆裂。夜里,梦想将我唤醒,而现实又使我不能再睡。披起衣服,呆坐在床头;或是走到黑森森的庭院里的树下,蹲在那里,看着在一片黑暗之中微弱地燃烧着的香烟的红火头。在晨曦之前,瞪着东北方的一颗大星,看着它从银白变成橙黄,又随着朝霞由墨紫化成赤红而消逝下去,盼着白亮的太阳出现。一片寂静的宇宙,这时,只点缀着工人和农民行路的几下草鞋声。等到噪鹊的喧叫引起人类的骚动,我那为侮辱、欺凌、狡诈而受的苦痛,就更加剧烈起来。在这时,太阳召唤着我,艺术召唤着我,丹钦科召唤着我。我唯一的安慰,只有从早晨到黄昏,手不停挥地翻译这一本《回忆录》。然而,如噩梦一样的经历,时时侵入我的脑子。就在这种极度不安、极度错乱的心情下,我译完原书的三分之一。
如果有许多人为某一种病推荐许多的治法,那就证明这种病是不治之症了。这个学校的病症,是无法可治了。于是,我决然逃出魔窟。可恨的是,学校当局不放我走。不但扣下我应得的导演费,而且还派了那个负着特殊“任务”的流氓请我“吃讲茶”,并在江边码头上拦住我的去路,向我动武!幸而有青年学生的保护,我才逃到了重庆,在那里把全书译完。重读开头三分之一的译文,发现若干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又把这三分之一重新译过,把全稿校改了三道。每次读到《海鸥》经丹钦科的演出而成功的叙述,欣悦和感动就必然交织着使我心酸一次。
我把这本《回忆录》的译名改成了《文艺·戏剧·生活》。
全稿经过重译、校改、重抄之后,正待付审的时候,传来丹钦科死在他的戏剧岗位上的消息!
三
半年不断的劳动,使我病倒在床上。这时,听说戈宝权兄在丹钦科去世后一个半月,(一九四三年)才收到他亲笔签名赠送的一册俄文本的《回忆录》。我的译稿,本是根据John Cournos的英译本的初版(My Life in the Russian Theatre,一九三六年九月,由Little Brown & Co.在波士顿印行),这英译本根据的是当初尚未印行的丹钦科手稿(俄文本经过修正之后,在一九三八年才出版,比英译本迟了两年)。为了对丹钦科忠实,我就扶病去访问宝权兄,请他按照俄文本,对我的译文加以严格的校订。宝权兄的热忱,从他不倦地帮助别人的事实上得到确切的证明。他答应了这个请求。他那时也正在病着,但还勉强给我校订了约四分之一。在这一部分里,他不但把译音(Cournos所用的是旧的译音制)上的错误和俄英文不同的地方一一改正过来,并且把每一个极细微的语意也都弄得很恰当。这使我深深地感动!不幸,他的病况转重,只好停止工作,而后来,虽然他已逐渐痊愈,可是要能从医生那里得到继续工作的准许,至少要到明年了。
因为急切地想把这本书公之于全国的读者,我当时情愿把我的中译本早日印行一版,等到戈宝权兄病好,对照俄文本完全校订之后,再行改版重印。宝权兄也热诚地答应将来对再版仍做详细的校订。同时,我觉得,英译本既是由俄文手稿译成的,那么,把从英译本来的译本先行出版,再版时再依据俄文本的面貌改版,对于读者和研究丹钦科的人们也许是很有用处的,因为这样就等于得到他的两个稿本的中译本:一个是初稿的译本,一个是定稿的译本。从这两个稿本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丹钦科的写作过程和他的严肃的工作态度。
俄文本比起英译本来,主要的变动都是为了使《回忆录》更真实。所以,在俄文本的卷首,作者加题了一句:
为了使回忆具有某种意义,
它们应该首先是真诚的
而不是臆造出来的。
俄文本 英译本
第一部契诃夫 契诃夫
第二部一个新剧场的诞生 新剧场的诞生
第三部高尔基的剧作在艺术剧院中高尔基
第四部艺术剧院的青年时代 第一次国外巡回
第五部托尔斯泰的剧作在艺术剧院中艺术剧院的托尔斯泰因素
总的内容却没有大动,所修正的地方只有六种情形:
第一,章节的重分。如把第一章分成两章。
第二,段落的重分。如把某两段合为一段,某一段的末尾并入另一段的开头。
第三,前后的重置。如把第一章讲到《伊凡诺夫》初版的几段,移到略前讲到同一剧本的地方。
第四,人名的增减。把初稿中没有提到的人名增加进去,如“我的传记的作者索博列夫”;或者把原有的人名删掉,如音乐学校初级课程的教员H被改为“一位演员”。
第五,琐事的删除。如契诃夫用一个字写一行的一篇十行对话,完全被删掉。
第六,叙述的增加。凡叙述略嫌不清楚的地方,都加入些解释,或者加入一些新的段落。
四
感谢戈宝权兄的热情帮助。
全书译稿,完成于前年(一九四三年)。但是,因为这是一本“滞销”书,所以找不到出版社,好容易找到一家,又被他们积压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而且几乎把原稿遗失,蕞近才把原稿退回来。这一次,由于一位朋友的热情帮助,这本现代文艺、戏剧经典的译文,才得以在中国第一次印出来。
焦菊隐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于重庆
校订后记
《文艺·戏剧·生活》前五版的译文,是根据英译本翻译的。几年来,屡次想根据俄文原本重新校订下。但是,解放以前,在重重的政治和经济的压迫之下,工作无法进行。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才开始重新翻译。由于自己的俄文根基太差,所以进行得很慢,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借着王以铸、吴启源等同志的帮助,才初步完成了这个新译本。
俄文本已经删去的句子,我依然保留下来,以供读者参考。这些地方,我都在译文的首尾,加上了一个符号——§。
新的译文只能算是一个初稿,错误和不妥当的地方一定会存在的。希望文艺、戏剧界的同志们和专家们,广大的读者们,随时提供意见,以便我改正,使这部经典著作的中文本更臻完善。
焦菊隐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 益起映创 (微信公众号认证)
- 官方直营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