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详情
基本信息
书名:资本主义的未来
著者:[英]保罗·科利尔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书号:9787542670724
出版时间:2020.7
定价:68.00
装帧:精装
纸张:书纸
尺寸:152mm×228mm×22mm
字数:227千字
页数: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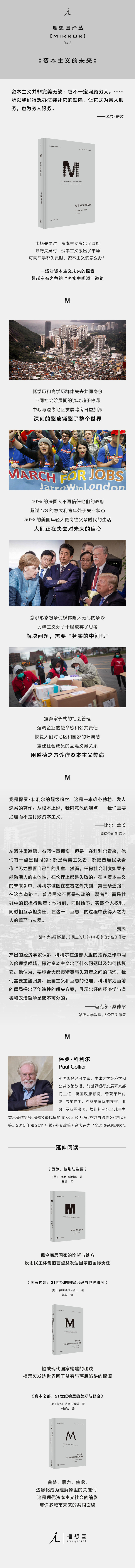
目录
第一部分 危机
第一章 新的焦虑
第二部分 重建道德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
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
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
第五章 道德的家庭
第六章 道德的世界
第三部分 重建包容性社会
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
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
第九章 全球分化:赢家和落后群体
第四部分 重建包容性政治
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道德国家的兴起
道德国家的鼎盛时期是战后的头20年。在一个充满道德使命感的辉煌时代,各国史无前例地创造了大量的互惠义务。“从摇篮到坟墓”和“新政”这两种简洁叙事囊括了在国家管理之下公民之间相互负有的极多的新义务。从孕期医疗保健到养老金,通过缴纳国家管理的国民保险,人们等于是在相互投保:这是社群社会民主主义的首要伦理准则。这一准则得到了左右两边政治派别的一致支持。在美国,它开创了两党在国会中融洽合作的时代;在德国,它带来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时代;在英国则是标志性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它由保守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中的一名自由党人设计,由工党政府实施,并由多届保守党政府维持。1945—1970年,在北美和欧洲,尽管表面上有政治竞争的喧嚣和烟雾,但主流政党领袖之间的政治分歧微乎其微。*
但社会民主主义成功的基础是一项明显到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遗产。大萧条的结束绝不只是二战无意间发挥的经济刺激产生的效果,更是一场大规模的共同事业,在走出萧条的过程中,各国领导人精心构建了关于归属感和共同义务的叙事。这样做的遗产是把每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共同体,一个有着强烈认同感、义务感和互惠意识的社会。人们乐意遵循社会民主主义叙事,把个人行为与集体后果联系在一起看待。在战后的头几十年里,富人愿意缴纳高达80% 以上的所得税率;年轻人服从征兵制度;在英国,连犯罪分子都因为警察不配备武器而自觉克制。这使国家的职能大大扩张,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议程。
但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的先锋逐渐接管了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道德国家演变为父爱主义国家。假如这些新先锋认识到这项非凡的遗产依赖于不断更新的共同身份,上述变化本不至于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但他们非但没形成这种认识,反而逆向而行。功利主义先锋队是全球主义者,罗尔斯主义者则强调受害者群体的独特身份。渐渐地,社会民主主义议程的基础瓦解了。到2017 年,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被选民抛弃了,这些政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借助第二章介绍的概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情况发生的原因。
道德国家的衰落: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是如何瓦解的
社会民主主义的崩溃是双重打击造成的:人们相互负担的义务逐渐减轻,同时,随着经济结构变化导致越来越多人的生活被破坏,人们对这种义务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一时期可观的经济增长是以经济结构日趋复杂为代价的,更为复杂的经济结构需要更多专业技能,进而意味着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促成了高等教育的空前扩张。这场大规模的结构变化对身份认同产生了影响。为了说明为什么这对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了致命打击,接下来我将描绘一个模型。一个好模型会从可以简化问题的假设出发,假设虽不惊人,模型却能得出惊人的结论。理想情况下,它能展示某种你原本没认识到但经揭示后却洞若观火的情况。通常一个模型会用一系列方程式来表示,但我将试着用几句话来描述这个模型。虽然这个模型相当简单,但需要一点耐心才能理解其原理。而耐心的回报是它颇能发人深省。这个模型一开始会涉及心理学,随后还会沾一点经济学。
它涉及的是简化的心理学理论,但绝不像怪诞病态的“理性经济人”概念那么粗糙。如前所述,“理性经济人”在石器时代就消亡了,被“理性社会人”取代。我还借鉴了乔治·阿克洛夫和蕾切尔·克兰顿开创的身份经济学理论来阐述“理性社会人”的行为方式。假设我们都有两个客观身份:工作和国籍。身份是获得尊重的来源,而这两个身份都能带来一些尊重。为了明确每种身份带来多少尊重,假设工作带来的尊重是由其产生的收入反映出来的,国籍带来的尊重由国家的威望决定。现在加入一个选项—突出性(salience)。尽管工作和国籍这两个客观身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我们可以选择更重视哪个。我认为突出的那种身份对我的尊严影响更大。设想这就像一张牌,我把它放在哪个身份上面,该身份带来的尊重就翻一倍。打这张牌还有一个更深的影响:能把我们分成两个新群体—突出工作的人和突出国籍的人。在选择突出哪个身份时,我也是在选择归属于哪个群体。归属于该群体的身份给我带来更多尊重,其程度取决于该群体有多么受尊重。
综上所述,每个人有四个获得尊重的来源。一是我们的工作,二是我们的国籍,三是我们选择突出哪个身份,四是与像我们一样选择突出该身份的人组成的群体。最后这种来源带来的尊重,它的具体水平可以设想为该群体每个成员从前三个来源中所获得尊重的平均值。那么我们会如何选择突出哪个身份?这里就需要用到经济学了:“理性社会人”从尊重中得到效用,并将其最大化,这就是此处“理性”一词的意思。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小模型应用于战后社会史了。
二战后的工资水平差异较小,而国家的声望隆盛,所以即使是收入最高的工作者也会选择突出自己的国籍而非工作,以此将从尊重中获得的效用最大化。把尊重的四个来源加起来,我们能看到,尊重在全社会的分布是相当平等的。每个人都从国籍身份中得到同等的尊重,因为他们都选择突出国籍,所以国籍带来的尊重都会翻一倍,因为每个人都选择突出国籍,所以他们组成的群体所带给他们的尊重也是人人相同。因此,造成尊重差异的唯一原因是工资的有限差距。
接着看看这个愉快的结果是如何崩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复杂性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优质的教育和与之匹配的优质工作,优质的工作带来更高的生产率,薪资便相应提高。达到一定程度后,技能水平最高的人就会将自己选择突出的身份从国籍改成工作,因为这样做能最大化他们获得的尊重。当这个过程发生时,尊重的最后一个来源—与其他人选择突出同一种身份所带来的尊重,开始出现分化。选择突出工作身份的人,因加入做出该选择的群体而获得更多尊重;而继续突出国籍身份的人得到的尊重会变少。这种分化本身会诱使更多人把突出的身份从国籍改为工作。这最终会带来什么结果?
也许每个人最终都会改变突出的对象,这是可能发生的。但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从事低技能水平工作的人继续突出他们的国籍。把这一结局与最初的社会状态进行比较会发现,高技能水平者已不再选择突出国籍,功利主义先锋队就在他们的队伍中。他们脱离突出国籍身份的群体后得到的尊重比之前更多。而继续突出国籍的低技能水平者所得到的尊重变少了,因为最受尊重的人已经脱离,所以继续留在这个群体中便没那么受人尊重了。
像所有模型一样,这个模型是极为简化的。但它让我们无须深陷细节的泥沼,有助于解释我们的社会是为何以及如何分崩离析的。整个过程中,所有人只是在努力把自己获得的尊重最大化。但由于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一道裂痕出现了。高技能水平者把突出的身份改成了自己的工作。时任《纽约时报》国际版编辑的苏珊·奇拉(Susan Chira)在接受艾莉森·沃尔夫(Alison Wolf)的采访时对这一选择做出了一种完美的表达:“工作很有成就感,已经与身份紧密交织在一起。”同时,受教育程度较低、自身工作较缺乏成就感的人会继续突出国籍,但开始感到被边缘化。
因为自鸣得意的高技能水平者比被边缘化者得到更多尊重,所以他们热衷于向其他人表明他们的确更突出自己的技能身份。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迈克尔·斯宾塞的信息传递理论中的一项重要洞见来预测他们将如何突出这种身份。为了让别人相信我已选择放弃将国籍作为我的突出身份,我需要做一些在未放弃的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我需要贬低国家。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精英频繁地贬低自己的国家—他们是在寻求尊重。这能把他们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清楚地分开。通过退出共同的国家认同,他们减少了继续认同国家者得到的尊重,所以别人对他们产生怨恨就不足为奇了。我希望你会觉得这里的一些描述很眼熟。
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技能的人组成的新阶层既包括右派人士也包括左派人士,右派信奉自由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自由地从个人技能中获得财富,左派信奉功利主义或罗尔斯主义主张的权利。后者不仅放弃了自身的国家认同,还鼓励其他人这么做。他们鼓励某些具有受害者群体特征的人把受害者身份作为自己的突出身份。
共同身份消失的后果
共同身份的瓦解影响了社会运转。随着身份分化为技能与国籍,人们对社会顶层人士的信任开始消失。这又是怎么发生的?让我们回顾一下第二章的主要内容。帮助他人的意愿是通过结合三种叙事而产生的:对一个群体的共同归属感;群体内部的互惠义务;行为与群体幸福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表明行为是有目的的。因此,如果共同身份瓦解,幸运者就不再那么愿意接受他们对较不幸者负有的义务。
大多数慷慨行为的基础是互惠。互惠带来的改变是一种飞跃:没有互惠,我们只能依靠利他主义与援救义务产生的微弱动力,互惠意识则更为有力,可以促使人们接受高税率。但互惠面临着一个协调问题:如果你已经接受义务是互惠的,那么我愿意接受我对你负有某种义务,但我怎么能知道你接受这种义务?你又怎么能知道我接受对你负有某种义务?我们如何能相信彼此在需要尽义务时都能履行义务?
实验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答案是我们需要共同认知。我们都需要知道,对方知道我们接受这个义务,“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以递归的方式回响。在一个网络化群体中传播的关于归属感、义务和目标的共同叙事,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逐渐形成的。共同归属的边界决定了互惠的限度,而我们对同处相同叙事之中的意识能让我们认识到共同认知的实际边界,从而巩固这一边界。因为叙事主要以语言表达,所以群体的规模有一个难以逾越的天然上限—共同语言。[5]但并没有类似的下限:在一个语言群体内,身份可以呈现高度分裂状态。共同身份的破坏既会削弱实行互惠的明确群体,也会妨碍互惠义务跨越不同群体的实际可行性。
毋庸置疑,我们的社会确实已经两极分化:一方是收入高于平均水平者,他们已放弃国家认同,转而认同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社会下层,他们坚持国家认同。而且在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勒庞崛起等情况出现后,两个群体无疑对这种两极分化已有清楚的认知。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大多数高技能、高教育程度者不再以国籍作为自己的核心身份,而较不幸者继续固守着他们不断下降的地位;这进而导致了整个社会中共同认同的弱化;这削弱了幸运者对较不幸者的义务感,进而破坏了1945年后形成的叙事—富人应该自愿接受具有再分配性质的高税负来帮助穷人。1970年后最高税率的大幅下调,与这一情况至少是逻辑一致的。
现在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较不幸者已意识到,幸运者的义务感削弱了,毕竟这个情况很明显,而且它对低收入者确实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对“过得更好的人”的信任程度会受到影响吗?答案一望可知:信任会削弱。如果受过良好教育者自视与其他人不同,对其他人所负的义务也变少了,那么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像过去所有人都突出同一种身份时那样信任他们。如果我们相信自己能预测他人的行为,我们就会信任他人。如果我们能稳妥地使用“心智理论”的方法—通过设想自己处在你的情况下会怎么做来预测你的行为—我们就会对自己的预测更有信心。但只有在能确定我们共持同一个信念体系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方法才是可靠的。如果我们的信念体系截然不同,我就不能和你换位思考,因为我并不生活在塑造你行为的心理世界里。我无法信任你。
功利主义先锋队甚至提出了一项理论,预测了信任的下滑,并就如何阻止下滑提出建议。剑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边沁的忠实追随者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称,解决方案是让居于统治地位的先锋队向其他人隐瞒其真实目的。欺骗可以阻止信任的下滑。当然,1970 年代以来人们发现主导公共政策的先锋队未能缓解新的社会分歧,这加重了信任的严重下滑。但西季威克离谱、弄巧成拙的主张却暗示着,问题不只在于分歧没有得到缓解,其根源要深得多。
社会民主主义瓦解的后果不仅是信任下滑,信任下滑接着又影响了人们的合作能力。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密布的关系网络依赖于信任。因此,当信任崩溃时,合作也开始瓦解。人们开始更多依赖法律机制来确保良好行为的落实(这对职业法律人是好消息,但对其他人不一定)。因为不再突出同一种身份,高技能者负有的对同胞的义务感减弱,人的行为因此也变得越来越投机。高技能者甚至会把其他人视为“笨蛋”,并为自己欺诈傻瓜的技能感到自豪。从电子邮件披露的情况来看,这似乎是金融高层中流行的一种情绪。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精准描述的那样,华尔街的商业模式就是“找傻瓜”。显然,这会增强社会中加剧不平等的潜在结构性经济力量。
- 理想国imaginist (微信公众号认证)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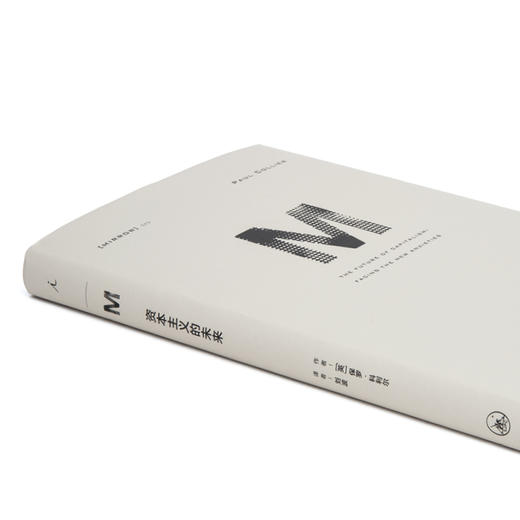




![新版 万物起源:从宇宙大爆炸到文明的兴起 [美]大卫·贝尔科维奇](https://img01.yzcdn.cn/upload_files/2024/04/12/FoGC2eo9SAPWki7_NtDjnXjQ6Yug.jpg?imageView2/2/w/260/h/260/q/75/format/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