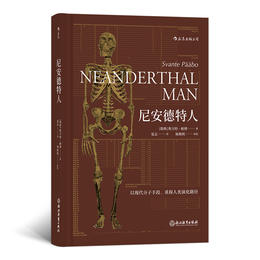商品详情
著 者:[美]林恩·H·尼古拉斯
译 者:刘子信
字 数:467 千
书 号:978-7-5139-2092-6
页 数:504
出 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印 张:31.5
尺 寸:155毫米×240毫米
开 本:1/16
版 次:2018年7月第1版
装 帧:精装
印 次: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10.00元
编辑推荐
在纳粹分子的疯狂、战争的炮火面前,油画、素描、雕塑,这些艺术品何其脆弱。虽然很多艺术品在二战期间被毁或至今下落不明,但是通过博物馆工作人员、古迹救护官、神职人员、打包工、卡车司机等人的几番努力,根特祭坛画、《抱白鼬的贵妇》、《圣母与圣子》等很多西方艺术品最终保存了下来,我们现在仍可在博物馆、在教堂中看到它们。本书将用紧凑的情节带我们回顾这些珍贵艺术品在二战前后的跌宕经历。
媒体推荐
一部读来犹如扣人心弦的冒险故事的学术著作。
——《华盛顿邮报》
因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悬疑之感,此书立即变得引人入胜且令人惊惧。
——《洛杉矶时报》
令人入迷……情节紧张……一个关于在纯粹邪恶面前的道义勇气和伟大品格的骇人故事。
——《休斯敦纪事报》
就像任何军事历史学家透彻地了解其战场一样,尼古拉斯透彻地了解艺术世界……她的作品值得在那些自称文明开化之人中广为传阅。
——《纽约时报书评》
细节丰富、讲述传神……书中充溢着关于逃亡、阴谋、背叛和牺牲的故事,这些故事触动人心又意义重大。
——《旧金山纪事报》
著者简介
林恩·H·尼古拉斯(Lynn H. Nicholas)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先后求学于美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返回美国后,她在美国国家艺术馆供职数年。在她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旅居比利时时,她开始本书的研究工作。本书是尼古拉斯的处女作,她的作品还包括《残酷世界:纳粹网络里的欧洲儿童》(Cruel World: The Children of Europe in the Nazi Web,2005)。尼古拉斯曾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和波兰“波兰之友”称号。她还担任在艺术品返还审判和美国国会中的专家证人。
译者简介
刘子信,陕西三原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主修中外文化交流考古。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通过大量采访和丰富的档案资料,详细解说了“二战”前后纳粹掠夺者对欧洲艺术珍宝的巧取豪夺,同时向读者展现了盟国全力解救这些艺术品的细节。本书用紧凑的情节,叙述了纳粹分子对“堕落艺术”的清洗、纳粹高官在被占领国的艺术品购买狂欢、纳粹分子对犹太人所有的艺术品的无情夺取;讲述了在面对劫掠和轰炸威胁时,欧洲各国博物馆工作人员千方百计转移、庇护艺术品以及古迹救护官维护艺术品的经过;讲述了各方在战后对公共和私人收藏的追索、返还过程;描绘了希特勒、戈林、画商之间的艺术品竞争以及盟国救护官和各方人士之间的博弈。
本书出版后深受好评,荣获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后本书被改编为纪录片《劫掠欧罗巴》和电影《盟军夺宝队》。
目 录
致谢 1
1 序幕:给过他们四年时间了! 1
战前纳粹在德国的艺术清洗
2 调整阶段 25
纳粹藏家组织掠夺、奥地利提供、欧洲隐藏艺术品
3 东方政策 57
1939—1945 年的波兰
4 生命与财产 81
纳粹入侵西方及其在荷兰的艺术机构
5 宽仁和残暴 115
占领下的法国:保护与没收
6 买卖与娱乐 153
法国:艺术市场欣欣向荣、纳粹文化死气沉沉
7 又有新变化 187
入侵苏联
8 步步为营 205
盟国救护努力的发端
9 炽热的铁耙 229
1943—1945 年的意大利
10 一触即发 273
盟军接管北部欧洲(1944—1945 年)
11 灰烬与黑暗 329
在帝国的废墟上搜寻珍宝(1945 年)
12 动机不纯 373
德国流离收藏的诱惑
13 顺其自然 411
五十年追查与返还路
主要人物简介 449
注释 467
参考文献 485
出版后记 492
正文赏读
1
序幕:给过他们四年时间了!
战前纳粹在德国的艺术清洗
1939年6月30日下午,一场大型艺术品拍卖会在瑞士度假名胜卢塞恩的国家大酒店举行,参拍的绘画和雕塑多达126件,均为现代艺术大师的经典作品,涉及布拉克、凡高、毕加索、克利、马蒂斯、考考斯卡以及其他33位艺术家。这批作品已经在苏黎世和卢塞恩展出了好几个星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大批买家。
坐在德国著名画商瓦尔特·费欣菲尔特及其夫人玛丽安娜(他们于1933年从卡西雷尔公司的柏林总部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分公司,以躲避国内严酷的反犹法律)旁边的,是影片《蓝天使》的著名导演约瑟夫·冯·斯登堡。由布鲁塞尔美术博物馆馆长莱奥·范普威尔博士率领的比利时博物馆管理人员与收藏家坐在后面一排。1 出席拍卖会的还有在欧洲度蜜月的小约瑟夫·普利策,以及他的两位朋友——画商皮埃尔·马蒂斯* 和库尔特·瓦伦丁。2瓦伦丁之前在柏林的布赫霍尔茨画廊工作,最近才在纽约安顿下来,正是他说服普利策先生参加这次拍卖会的;瓦伦丁受到多个博物馆和收藏家的委托,作好了购买准备。
在1939年,这种类型的拍卖会并非不同寻常。那年春天,伦敦等处也有大型拍卖会。使其与众不同的,除了待拍艺术品的当代性,更在于它们的出处。这些绘画和雕塑均来自德国的顶尖公立博物馆,包括慕尼黑、汉堡、曼海姆、法兰克福、德累斯顿及不来梅的博物馆,科隆的瓦尔拉夫-里夏茨博物馆、埃森的弗柯望博物馆以及柏林的国家画廊。待拍艺术品并非各艺术家的平庸之作,这类平庸之作或许会为了清理博物馆的仓库而被出售。参拍的作品包括毕加索的《苦艾酒徒》、凡高的大作《自画像》和马蒂斯的《浴者与乌龟》等。《苦艾酒徒》在展品目录中被描述为“画家蓝色时期的杰作”。《自画像》来自慕尼黑博物馆,后来阿尔弗雷德·法兰克福特以17.5万瑞士法郎为莫里斯·韦特海姆购得此画,那是当天的最高价。为普利策竞拍的皮埃尔·马蒂斯则将《浴者与乌龟》视为其父的代表作之一,他一直准备以远高于成交价9 100瑞士法郎的价格竞拍。3
面对如此盛况空前的拍卖,卢塞恩却没有出现该有的欢乐与兴奋。相反,约瑟夫·普利策的回忆中却有另一种情绪:“为了给子孙守住这件艺术品,我才参与竞拍的——这里面有些反抗的味道!……我竞拍的真正动机是保护这件作品。”4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次拍卖的收益会用来资助纳粹党。这一传言让拍卖师特别担心,他不得不专门给主要画商去信,保证所有拍卖款都会用在德国博物馆事业上。不过,丹尼尔·坎魏勒——其私人收藏在“一战”后遭法国政府没收、拍卖——并不相信这些话,他没有参加拍卖会。5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当时正在巴黎筹备一场关于毕加索的大展,他也没有参加拍卖会,而且他认为博物馆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参与不得人心的拍卖活动。此外,他还要求馆员对外严正声明,本馆新获的德国艺术品都是从纽约新建立的布赫霍尔茨画廊买来的。6
出席拍卖会的人也有分歧。据玛丽安娜·费欣菲尔特回忆,有些人原本同意不竞拍,后来却没能忍住。她与丈夫惊讶地发现,拍卖品中有一件考考斯卡的《波尔多大教堂》,正是他们之前捐给国家画廊(柏林)的那幅,但他们忍住了,这幅画最终没有卖出。但是,一些同行的朋友最后却向低价诱惑屈服了,拍走了诺尔迪的《红黄秋海棠》。
法国杂志《美术》把国家大酒店当时的气氛描述为“令人窒息的”。它说整个大厅挤满了好奇的瑞士看客,他们对这次拍卖的政治性很感兴趣——美国画商出价很低,法国人出价也不显眼,就连拍卖师也不像人们想的那样积极主持拍卖活动:
拍卖活动由【西奥多·】菲舍尔主持,效率很高,但他无法一直掩饰自己对个别堕落艺术品的蔑视。当展示佩希施泰因的《抽烟斗的人》时,他略带讽刺地说:“这一定是这位画家的自画像”……当撤下某些起拍价格很高的艺术品时,他会带着异样的愉悦大声评论:“没人想要那种东西”,或者说:“这位夫人不能取悦大家啊”……而当说出“撤下”一词时,他会露出笑容。7
其他描述并不比这友善。
在这种情绪中,低调的比利时购买者收获最大,他们买到了一幅恩索尔的顶级作品、高庚的《塔希提》、毕加索的《杂技演员和年轻小丑》(原藏伍珀塔尔)、夏加尔的《蓝房子》(原藏曼海姆)以及格罗斯、霍费尔、考考斯卡、洛朗森和诺尔迪的作品。买到毕加索画作的布鲁塞尔银行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49年后它竟能卖到3 800万美元以上!
当拍卖结束时,仍有28件拍品没有卖出。拍卖所得离预期很远。这些收入——大约50万瑞士法郎——首先被兑换成英镑,存入了德国政府在伦敦的账户。正如之前猜想的,各博物馆一分钱都没拿到。
这些绘画被作为“堕落艺术品”从德国清除了出去,不过纳粹政府很清楚它们的价值,这些画可以方便地为第三帝国筹集到急需的外汇。但在国家画廊(柏林)的藏品主管阿尔弗雷德·亨岑(1935年,他曾因过分热衷现代艺术被停职九个月)眼中,这次对民族遗产的拍卖表明,德国政府的无耻程度和文化堕落在艺术史上已经无可匹敌了。8
事后看来,德国政府走向这一“无耻”事件的过程是清晰可辨的。像在其他领域一样,纳粹分子把其对艺术领域已有的成见和看法推到了难以想象的极端。几乎没人能够相信或者愿意承认眼前发生的一切。
1933年,阿尔弗雷德·巴尔利用在欧洲休假的一年时间,写了三篇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艺术现象的文章,但这些文章却因其内容太具争议而被美国重要期刊退稿。9唯有他的年轻同事林肯·柯尔斯坦足够大胆,在其新杂志《猎犬与号角》上刊登了其中一篇文章;其余两篇迟至1945年10月才被《艺术杂志》刊出。雅克·巴尔赞在这期杂志中指出:“巴尔先生那三篇文章,是对那几乎毁掉我们文明的集体漠然的令人难堪的警示。”
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仅仅九周,纳粹党下属的“德国文化战斗联盟”斯图加特分会就召开了第一次公开会议,巴尔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是第一批听到新政权文化理论的局外人之一。在一座挤满斯图加特文化精英的剧院,战斗联盟的领导人阐明了这些新理论:
如果认为国家革命仅仅是政治和经济层面的,那就错了。革命首先是文化层面的!我们虽然处于革命的第一个激烈阶段,但它已然揭示了德国社会习俗那长期隐藏的根源,已然打开了通向新觉醒的道路;这新觉醒,迄今只有褐衫队* 队员自觉不自觉地拥有着;这新觉醒便是:生命的全部表达源于特别的血统……特别的种族!……艺术不是国际化的……如果有人要问:自由还剩下什么?那他会被告知:那些削弱和破坏德国艺术的人是没有自由的……在根除、粉碎那些破坏我们命脉的东西时,我们绝不会懊悔、绝不会感情用事!
掌声起初还显得犹犹豫豫,最后雷鸣起来。10
在斯图加特,行动实际上已先于言语展开了。画家奥斯卡·施莱默的一场重要回顾展于3月1日开展,才12天就被关闭了。紧接着,当地的纳粹报纸就刊出了一篇恶毒的评论:“谁愿意正眼瞧一下这些画?谁尊重它们?谁愿意辩称它们是艺术品?它们是彻头彻尾的半成品**……最好把它们也丢进垃圾堆里任其烂掉。”11这家博物馆非常畏惧,于是将所有展品锁进一个偏僻的陈列室里。这时距纳粹党首次获得国会多数席位才刚刚6天而已。
阿尔弗雷德·巴尔因其外国人身份才得以参观这些展品,他气愤之极,于是让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购买了几幅最好的绘画,“就为羞辱那些婊子养的”。约翰逊照做了,于是《包豪斯楼梯》就此落户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12
不过,这些警告并不比从前更容易让人接受,因为多年来人们对现代艺术一直持褒贬掺杂的态度。晩至1939 年,当一位波士顿艺术评论家回顾一场德国当代艺术展(很多作品来自卢塞恩拍卖会)时仍伤心地说:“在波士顿,很可能有许多人——艺术爱好者——在这场特殊的清洗中会站在希特勒一边。”13德国国内也有长期的反现代传统。早在1909年,德皇威廉就为购买印象主义绘画一事,罢免了国家画廊的馆长胡戈·冯·楚迪。犹太人马克斯·诺尔道在他1893年的著作《堕落》一书中宣称,所有现代艺术都是“病态的”,其中包括瓦格纳、马拉梅、波德莱尔及印象派画家的作品。14幸运的是,他没有活到目睹自己的理论被应用的那一天。报道1913年在纽约举办的著名军械库艺术展的报纸,就是用这个朗朗上口的词汇来描述在展“艺术品的堕落”的。同年,康定斯基展出的作品被一家汉堡报纸描绘成“一堆拙劣的线团子”,画家本人则被称为“精神错乱的画家,他再也不能为自己的举止负责了”。15 1914年以前,抗议和反抗议在保守派和现代派画家之间往复变换。这场争论变得政治味十足,不得不提交国会讨论,普鲁士议会甚至通过了一项决议来阻止艺术的“堕落”。但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这些争论都还停留在观点和品位的范畴内。
在“一战”后的那些年,未来的“堕落艺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在此鼓舞下,各博物馆广泛地展出它们的艺术品。1919年,柏林的国家画廊要在太子宫(君主制垮台后它一直空置着)开设一处“新翼”馆区,这代表着官方的许可。左右两派的评论家都为其写作了负面的文章,但该馆区还是很快成了国内外同行的典范。16 1921年,收藏家卡尔·恩斯特·奥斯特豪斯甫一去世,埃森市就从当地商会和鲁尔区各矿业公司征集资金,买下了他的弗柯望(意为“人民的草地”)博物馆收藏的当代艺术品,并将该馆向公众开放。到20年代晩期,德国大多数重要博物馆中都挂上了现代艺术品。而政府自己也在内政部任命了一位自由主义的、有国际化倾向的官员担任联邦艺术长官。在魏玛市,1919年由建筑学家瓦尔特·格罗皮厄斯创办的包豪斯学校尽管存在争议,但还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并集聚了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建筑师和手艺人。
虽然有此鼓舞人心的氛围,反对者却始终存在。20年代出现了一群艺术“哲学家”,他们以诺尔道的“堕落”理论为基础,炮制出了未来纳粹艺术信条的基本轮廓。他们的观点是杂乱式种族主义的、完全荒谬的。一位叫京特的教授宣扬道:“关于美的希腊形象绝对是北欧化的……我们可以将希腊的历史解释成北欧化的上层同异族的下层之间的精神冲突。”17他们的猛烈批判不限于现代艺术。但在面对以下事实时,他们也会感到很难处理:绝对是北欧人的伦勃朗曾画过那么多表现犹太人的作品。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约1465—1528年)因为“原罪的精神失常”而受到攻击,甚至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也被认为是可疑的,因为他在16世纪的意大利之行中吸收过的那些“影响”。18
随着纳粹运动愈演愈烈,这些观点变得更加极端。1928年,著名建筑设计师保罗·舒尔策-瑙姆堡出版了《艺术与种族》一书。在这本书里,医学文献里病态或畸形患者的照片与现代派的绘画和建筑安排在一起。这种思想派别的高潮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那本部头庞大、令人难以卒读的著作《20世纪的神话》(1930年)。该书称德国表现主义艺术是“染了梅毒的、幼稚的和杂交的”。罗森堡在书中进一步强调,雅利安北欧人创造的不仅有徳国的教堂,还有希腊雕塑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就连将罗森堡引入其核心圈子的希特勒,也难以理解这本书是如何卖出数十万册的。19但是他完全同意书中的基本观点。罗森堡那彻底的反犹态度和他作为徳国文化战斗联盟创办者的身份,将让他很快在新政权中炙手可热起来。
纳粹党早就表现出落实其艺术理念的特殊热忱了。1929年,他们在图林根州选举中获得了足够选票,从而可以在州内阁中要求席位。慕尼黑政治警察局前局长威廉·弗里克博士因此得以出任图林根州内政和教育部长。1925年,包豪斯学校全体职员在合同被当地政府的右翼多数派取消后,便离开了魏玛。尽管如此,弗里克还是将注意力转到了包豪斯的建筑上,因为他觉得与这一罪恶机构有关的任何痕迹都必须根除。在楼梯处的奥斯卡·施莱默壁画被涂料覆盖掉了。一个徳国手工艺组织搬了进来,由新近参与政治的舒尔策-瑙姆堡领导。20弗里克下定决心清除所有“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便又从宫殿博物馆的画廊中清除了克利、迪克斯、巴尔拉赫、康定斯基、诺尔迪、马尔克及其他总共70人的作品。他还禁演了布莱希特的剧作《三分钱歌剧》,并禁止音乐会上演斯特拉文斯基或欣德米特的作品。徳国其他地区将此看作一州的过激行为,弗里克也于1931年4月被解职。但他们难以预料到的是,再过不到两年时间,弗里克就会出任全国的内政部长。21
魏玛并非唯一发生过这类情况的城市。1926年,德累斯顿的一场表现主义展览遭到了不下七个组织的谴责,这些泛日耳曼的*、“民族主义的”(Völkisch)和武装的组织控诉说这些艺术家侮辱了德国陆军。德国艺术家联盟批评国家画廊筹款购买凡高的而不是“日耳曼的”作品。1930年,茨维考博物馆馆长希尔德布兰特·古利特博士被解职,原因是他所“坚持的艺术政策冒犯了健康的德国民间情感”,而且他派往奥斯陆的“新日耳曼绘画”展激起了一场抗议热潮。
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在3月的选举中,由于国会纵火案引起的恐慌与混乱以及民事权利的暂时取消,他的政党第一次赢得了多数席位。4月7日,一项旨在“重设专业人士公职人员”的法律得以通过。这项法律合法化了清除掉任何不合国家社会主义者心意的政府雇员的做法。博物馆馆长与员工、在艺术院校执教的艺术家、城市规划师和大学教授都是国家的雇员。对于那些不属于国家雇员的人,新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3月13日建议成立一个新机构——帝国文化协会——加以管理,而这个机构最终将控制所有与艺术有关的人。所有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画商、建筑师等等,都必须加入这个保护伞组织。不属于该组织的人,将不能保住工作、不能出售或展出作品,甚至不能创作。该组织不接纳的人起初只有犹太人和共产党员,后来,美术领域中凡风格不符合纳粹理念的人都不能加入。
在新政权中,艺术非常时髦。1933年10月,希特勒登上总理宝座才几个月,就为他的第一个重大公共建筑工程举行了奠基仪式,此即位于慕尼黑的“德意志艺术之家”。仪式锤断在了他的手上,其含义到后来才表现出来。22先前的艺术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现如今成了纳粹党内知识分子的领袖,并被冠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头衔——“党内以及所有配套社团所有智力、精神训练与教育活动的监管人”。而弗里克则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他开始在各州委任艺术委员。甚至连党卫军都有个艺术分支机构,即“遗产研究所”(Ahnenerbe),它赞助在世界各地的考古研究,以期证实日耳曼文化的悠久与辉煌。由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组成的各种协会一夜之间都冒了出来,开始鼓吹“民族主义”理想;杂志数也激增起来。这真是机会主义者的时刻!与这些新组织并存的还有旧的文化部,它在这股洪流中尽全力航行着,既要谋求自救,又要保住博物馆里的珍宝。纳粹用了四年时间来“精炼”它的艺术标准,最终结果是:凡希特勒喜欢的,都是可以容忍的;凡在政治宣传上对政府非常有用的,都是可以容忍的。
在德意志艺术之家落成之时,纳粹分子用多种语言出版了一款精致的小册子,其英文版《德国艺术的殿堂》(The Temple of German Art)是以慕尼黑潜在的旅游客户为目标的,这本小册子里除了景点布局图和建筑平面图外,还复印了施皮茨韦格、冯·考尔巴赫及伯克林等画家所作的19世纪日耳曼风俗画,另外还有一篇品位极差的文字:
巨大的力量将从这伟大的艺术殿堂中涌出,南部山峦中的迷人气息将穿过她的柱廊、绕过她那石灰石的飞檐;慕尼黑的蓝天将吸引德国及国外游客,说服他们在这座巴伐利亚城市、民族复兴的诞生地里徜徉。
这位幸运的无名作家继续写道,“那些诋毁美德与真理的玩世不恭之人”所坚持的“伪艺术”,“在一位将其种族的所有高贵品质尽可能融入体内的伟人的召唤下”已经被人民摒弃了;它终将被真正的日耳曼艺术即“民族的气息”所取代。
不过,这“气息”到底包括什么,起初连希特勒的核心圈子也不完全清楚。奉命给戈培尔装饰房子的阿尔伯特·斯佩尔后来写道:
我从……柏林国家画廊馆长那里借了一些诺尔迪的水彩画。戈培尔和他的夫人对这些画很满意——直到希特勒来视察并表达了强烈不满。这位部长立即召我过去,说:“这些画必须马上拿走,它们实在太不合适了。”23
希特勒想彻底摒弃魏玛时代的失败主义和左翼思想;他不喜欢对战争真实面目的描绘,而且对于他所谓的“半成品”有一种小资产阶级式的反感。艺术方面的工作人士在很长时间里都没能洞悉这一点。有些人试着折中。汉堡艺术馆馆长马克斯·绍尔兰特把表现派作品当作北欧日耳曼艺术的典型。其他人则不认同。1933年6月,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学生在柏林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以抗议“中产阶级艺术”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同时称扬国家画廊馆长路德维希·尤斯蒂博士自1919年累积起来的现代艺术收藏。尽管有这种支持,尤斯蒂还是被文化部的官僚要求停职了,他们想要一个更加驯顺的馆长,这个人既能维护现代艺术藏品,又能紧跟党的路线。但是尤斯蒂拒绝“退休”,难堪的文化部官员只好将他调到一个艺术图书馆工作,直到他达到退休年龄。
新任馆长阿洛伊斯·沙尔特担任过尤斯蒂的助手,并且曾在哈雷有过类似的现代艺术收藏,他很快就遭到了罗森堡、弗里克和舒尔策-瑙姆堡的攻击。为平息这场争端,沙尔特办了一场讲座,试图在讲座中定义日耳曼艺术的本质。他说任何日耳曼的东西都是“充满活力的”。他推崇哥特艺术,称丢勒在意大利的停留是个“错误”,他赞赏格吕内瓦尔德,称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艺术家(他将他们的风格与日耳曼古代民俗联系在一起)使德国重新找回了活力。学生们很欢迎这种革新与民族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让表现主义成了一种可以接受的德国传统,然而这并不是纳粹党所想的意思,国家画廊被关门“整顿”。
沙尔特又妥协了。他把卡斯帕·戴维·弗里德里希、汉斯·冯·马雷斯和费尔巴哈等艺术家的代表作品挂在了较低楼层,而把有争议的画作放到了楼上几层,但那里布局典雅,他根据各艺术家的主体基调,把每个陈列室装饰得质感各异。他还从其他博物馆借来顶级画作,以填补每个展览的空缺之处。诺尔迪就亲自从汉堡借出了他的《基督与群童》。沙尔特唯一的退让是放弃克利和贝克曼,反正这两人都不是他最爱的艺术家。而凡高和蒙克作为“日耳曼先驱者”被展出。
- 后浪图书旗舰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后浪出版公司官方微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