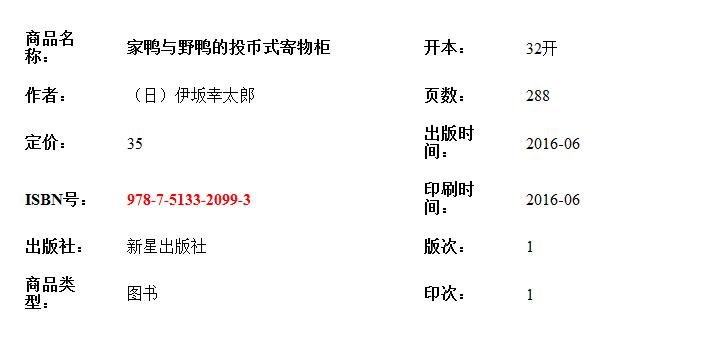如果一名艺术家迫于饥饿而去打劫水果店,那或许尚有形象可言。可我呢?正手持模型枪在书店望风。是夜太深,还是我脑子已乱?我心里毫无罪恶感,最多就是对父母有点愧疚。我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鞋店,自从附近开了一家价格低廉的量贩店后,店里的生意就每况愈下,实在算不上好。但即便如此,他们不仅同意让我上大学,还答应补贴我一个人生活所需的生活费。如果他们责怪我说:我们可不是为了让你干出这种事儿才把你送进大学的,我能做的也只有“那是那是”地谢罪了。
这是开在窄窄的县道边上的一家小书店。
晚上十点多,四周一片昏暗。即使不远处就是国道,也听不见汽车的声音。附近只有零零星星的老式民宅,全然不见人踪。
书店停车场边上立着的招牌并不华丽,等距排开的路灯均已陈旧,而从夜空密密的云缝中渗出的月光反而略显明亮。
并没下雨,可整座城市看上去就像被打湿了,潮乎乎地沉在夜色中。每一座民宅都黑黝黝的,似乎住在里面的人们全都进入了梦乡。
书店的混凝土外墙单调乏味,没有值得一提的热闹彩灯装饰。
这家书店看着有年头了,应该是个人经营的。肯定就是靠着白天卖漫画给附近的孩子们,晚上卖成人杂志给开车来的年轻人勉强维持。看他们还在用如今已极少见的鸡毛掸子,感觉也挺合这家店的风格的。
我们到的时候,书店正要关门。此时停车场里的车正在陆续离开,最后只剩下一辆看着挺旧的白色小轿车,可能是书店的店员开来的。
特意临近关门才到,因为我们不是来买书的。
我一边用余光扫着书店正面的入口,一边穿过建筑物侧边和一堵石墙之间的间隙,向后门绕去。那间隙倒不至于特别窄,不过也就勉强够一个人通过。后门上嵌着玻璃,有店内的灯光透出来。
我站在后门门前。门是木纹纹理的,门把是银色的。玻璃嵌在门上的位置正好在我脸的高度。这是块磨砂玻璃,透过它看向店里,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景象,就像从混浊的海面往水里窥视一般。
一棵不知名的树立在石墙边,对着我垂下长长的树枝。它把树枝弯成像是要从上方发起攻击的角度,似乎在威吓我。
旁边放着空调的室外机和塑料桶,空气中弥漫着尘埃与小便混在一起的气味。
我突然想起得把模型枪举起来,于是急急忙忙将手中握着的模型枪贴近玻璃窗。
地面在晃动,我以为地震了。可实际上什么事儿也没有,仅仅是我自己的腿在发抖而已。
真没出息,我忧伤地想。
嘴里哼着鲍勃·迪伦的歌。
“椎名你要做的事并不难。”河崎是这么说的。
确实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怎么说呢,这事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谁都能做到。
拿着模型枪,站在书店后门——仅此而已。唱十遍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仅此而已。每唱完两次,就用力踢门——仅此而已。
“实际去打劫书店的是我。椎名你在后门守着别让店员逃了。”那时河崎说,“后门会发生悲剧。”
我口中说到的这个河崎,已经冲进马上要关门的书店,去抢《广辞苑》了。
店里传来的动静吓到了我,我右脚一动,鞋子踩到了杂草。踩到土地的感觉极不舒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风并不太冷。我刚从关东地区搬来,本来打心底里认定东北地区的四月一定还很冷,结果发现其实也不过如此。我是说,我明明不觉得冷,可此刻却在发抖。我仰起脖子看向天空,云层已经完全盖住了月亮。
我握紧了模型枪,一边用力踢门,一边不禁又想起刚搬来那天发生的事——不过是两天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