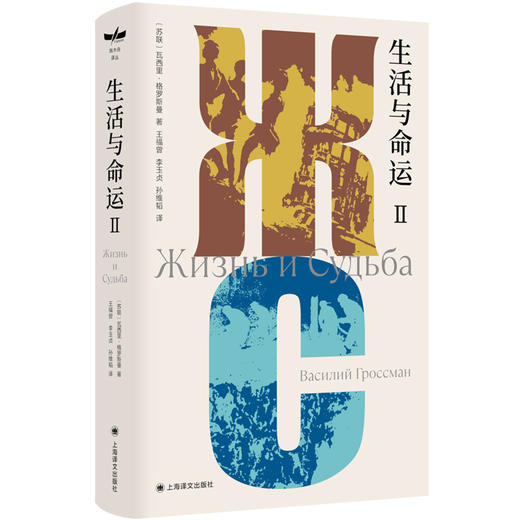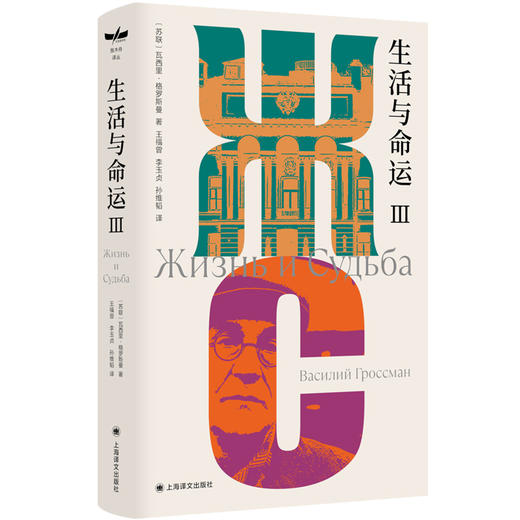商品详情



《生活与命运》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为背景展开叙述,作者格罗斯曼的笔触横跨整个欧洲东线战场。与同时期相同题材的作品相比,尽管《生活与命运》的叙事核心围绕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展开,但是格罗斯曼不仅仅着墨于刻画战争场面的惨烈。格罗斯曼刀笔所至,一副横跨整个苏联大地的历史画卷跃然纸上,从纳粹德国占领区,到斯大林格勒战场最前线,再到为避战火几乎空城的莫斯科,乃至罪犯服役苏联远东地区。通过将故事情节巧妙而精密的穿插和排列,无数被淹没于历史中的芸芸众生在书中重新鲜活起来,不论是集中营中逆来顺受的犹太囚徒,还是战争最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不论是在战争年代投机倒把、打压异己的官僚,还是坚持原则、拒绝出卖良心的知识分子,每个人物都因为真实而变得熟悉,尽管这是一个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的故事,但是它依然与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命运息息相关。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1905—1964),原名约瑟夫·所罗门诺维奇·格罗斯曼,苏联作家、战地记者。他出身于一个乌克兰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苏联《红星报》战地记者,1941年8月至1945年8月,以战地记者身份到前线,从战火初燃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再到苏联军队攻下柏林,格罗斯曼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写下了许多揭露纳粹德国集中营真相的报道。他所见证的无数惨烈的战争和人性的悲剧都成为了日后他笔下最真实有力的文字。
1952年,格罗斯曼因作品《为了正义的事业》受到苏联作协的批判,被迫对作品做出了大量删改。1960年,《生活与命运》脱稿,然而该书不但未能出版,并且手稿也于次年被苏联安全部门查抄。直至1964年格罗斯曼因病逝世,《生活与命运》都未能出版,手稿也未归还作家。在历经无数辗转之后,《生活与命运》于1980年在瑞士出版,迅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剧烈震动,许多评论家将之称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之后各语种译本先后问世,格罗斯曼也被公认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家。
1952年,格罗斯曼因作品《为了正义的事业》受到苏联作协的批判,被迫对作品做出了大量删改。1960年,《生活与命运》脱稿,然而该书不但未能出版,并且手稿也于次年被苏联安全部门查抄。直至1964年格罗斯曼因病逝世,《生活与命运》都未能出版,手稿也未归还作家。在历经无数辗转之后,《生活与命运》于1980年在瑞士出版,迅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剧烈震动,许多评论家将之称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之后各语种译本先后问世,格罗斯曼也被公认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家。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维佳,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里,虽然我身处敌后,身处犹太区铁丝网的包围中。我怕永远收不到你的回信了,我将不久于人世。我想让你知道我最后时日的情景,怀着这样的信念,我会死得轻松些。
维佳,要真正了解人是很难的……7月7日,德国鬼子闯进城来。市内公园反复广播最新消息。我接诊病人后从诊所回来,驻足倾听,播音员用乌克兰语广播战况。我听到远处有枪炮声,后来人们奔跑着穿过公园,蜂拥而来。我赶回家去,一路总是纳闷,我怎么没听到空袭警报。突然,我看到了坦克,有人喊道:“德国人冲进来了!”
我说:“别散布紧张空气。”前一天,我去找过市苏维埃秘书,问他走不走,他火了:“谈这个还为时过早,我们甚至连名单还没拟定呢。”总之,德国鬼子来了。邻居们整夜未睡,奔走相告,最镇静的只有小孩子们和我。随大流,听天由命吧。起初,我很惶恐,唯恐再见不到你了。我切盼再一次看看你,吻你的额头和眼睛,可后来我又转念一想,总算万幸,你平安无事。
天将亮,我才入睡,一觉醒来,感到分外凄凉。我虽然在自己的家里拥被而卧,但觉得犹如身在异乡,若有所失,孑然一身。
这天早晨,我想起了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早已遗忘的苦楚,我是犹太人。德国鬼子坐在载重车上,高喊着:“打死犹太人!”
后来,我的几个邻居又来提醒我。扫院子工人的妻子站在我的窗前,对隔壁的一个女人说:“感谢上帝,犹太人完蛋了。”这话从何说起?她的儿子娶的就是犹太女人,这老太婆常到儿子家去,还向我念叨过她的几个孙子。
我的隔壁是个寡妇,她有个六岁的女儿阿列努什卡。这孩子有一双美极了的蓝眼睛,我曾寄信告诉过你,她走到我跟前,说:“安娜·谢苗诺芙娜,请你傍晚收拾一下东西,我要搬到你房里来。”
“那好,我就搬到你家房里去。”
“不,您要搬到厨房后面的小房里。”
维佳,要真正了解人是很难的……7月7日,德国鬼子闯进城来。市内公园反复广播最新消息。我接诊病人后从诊所回来,驻足倾听,播音员用乌克兰语广播战况。我听到远处有枪炮声,后来人们奔跑着穿过公园,蜂拥而来。我赶回家去,一路总是纳闷,我怎么没听到空袭警报。突然,我看到了坦克,有人喊道:“德国人冲进来了!”
我说:“别散布紧张空气。”前一天,我去找过市苏维埃秘书,问他走不走,他火了:“谈这个还为时过早,我们甚至连名单还没拟定呢。”总之,德国鬼子来了。邻居们整夜未睡,奔走相告,最镇静的只有小孩子们和我。随大流,听天由命吧。起初,我很惶恐,唯恐再见不到你了。我切盼再一次看看你,吻你的额头和眼睛,可后来我又转念一想,总算万幸,你平安无事。
天将亮,我才入睡,一觉醒来,感到分外凄凉。我虽然在自己的家里拥被而卧,但觉得犹如身在异乡,若有所失,孑然一身。
这天早晨,我想起了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早已遗忘的苦楚,我是犹太人。德国鬼子坐在载重车上,高喊着:“打死犹太人!”
后来,我的几个邻居又来提醒我。扫院子工人的妻子站在我的窗前,对隔壁的一个女人说:“感谢上帝,犹太人完蛋了。”这话从何说起?她的儿子娶的就是犹太女人,这老太婆常到儿子家去,还向我念叨过她的几个孙子。
我的隔壁是个寡妇,她有个六岁的女儿阿列努什卡。这孩子有一双美极了的蓝眼睛,我曾寄信告诉过你,她走到我跟前,说:“安娜·谢苗诺芙娜,请你傍晚收拾一下东西,我要搬到你房里来。”
“那好,我就搬到你家房里去。”
“不,您要搬到厨房后面的小房里。”

- 摄影与诗歌文艺书店
- 可议价折扣(加微信13901132852 进读者群折扣)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