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岁】 监狱长的女儿 我爱读大奖小说 第二辑 杰里史宾尼利 著 儿童文学 表达力 提升阅读写作能力 治愈亲情成长宽容 中信
| 运费: | ¥ 8.00-15.00 |
| 库存: | 71 件 |
商品详情

★2018年美国童书协会儿童年度童书,英美青少年热追!
★纽伯瑞大奖作者用充满力量的故事,给孩子以前行的勇气。

书名: 监狱长的女儿
定价: 39.8元
作者: 杰里·史宾尼利(Jerry Spinelli)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 2021-01
页码: 336
装帧: 平
开本: 32
ISBN: 9787521721799

★纽伯瑞大奖作者用充满力量的故事,给孩子以前行的勇气。
★故事在主题上体现的是爱与成长,对读者有很好的启迪和引导意义。
★故事还原了每个人倔强与叛逆的青春期,孩子们会在这个怀旧的故事中找到许多共鸣,故事会引导年轻人克服并走出成长的陷阱,走向他们更好的未来。
★故事展现了一段独特的心灵成长史,作者用富有同理心的故事,引导年轻人克服并走出成长的陷阱,走向他们更好的未来!
★曲折有趣的故事,丰富孩子的表达和写作素材库,提升阅读和写作能力。
★2017年度亚马逊月度图书
★2018年美国银行街教育学院童书奖
★2018年美国童书协会儿年度童书
★2018年美国独立书商协会年度图书
★2018年语言艺术系列中值得关注的儿童读物

一段独特的心灵成长史,故事还原了每个人倔强与叛逆的青春期,困惑的青少年会在这个怀旧的故事中找到许多共鸣。——《出版人周刊》
作者用富有同理心的故事引导年轻人克服并走出成长的陷阱,走向他们更好的未来。——《纽约时报》
作为监狱长的女儿,12岁的凯米从小在监狱中长大。与犯人不同的是,即使凯米可以自由地离开监狱,但她仍然陷于困境。因为小的时候,母亲为了救凯米出车祸去世,以致凯米一直无法原谅自己。 凯米在监狱的高墙里寻找“母爱”、渐渐长大,在此过程中蜕变成一个成熟独立的少女

杰里·史宾尼利(Jerry Spinelli),美国儿童小说家、纽伯瑞奖大奖作者。现与妻女住在宾夕法尼亚。

凯米2017
如今,这里成了一座鸟舍。
它曾经是一处监狱。汉考克郡监狱。
曾经,嘈杂的波普乐响彻一间间牢房,脏话从早到晚满天乱飞。如今,雀鸟、柳莺、红色唐纳雀,在玻璃隔间里,振翅拍翼,大展歌喉。
从前的静室,是为了让犯人们保持冷静而设立的。它安装了玻璃屋顶,锡制手推车往一个小小的池子中倾倒水流。曾经,那里除了照料花草的工人,几乎无人踏足。如今,孩子们在这里玩耍。时而,蝴蝶停落肩头,他们便惊喜地大叫起来。
曾经,有两座操场——一个给男犯人用,一个给女犯人用。如今,两座操场并作了一座大花园,成了乌龟和孔雀流连漫步的天堂。花园里也有一条瀑布——与围墙等高!还有石子路。小池塘。睡莲。一英尺长的金鱼。
偶尔,一只兀鹰从天而降,随心所欲地落在地面上。
若不是换了门口的指示牌,这个地方从正面看去,多年未变:就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堡。高大、乌黑的石头墙。拱形的橡木门。高耸入云的瞭望塔,密集的垛口,以备战时之需。
监狱的占地面积有一个城市街区那么大。监狱里,住着两百多名囚犯,男男女女,三教九流,有商店扒手,也有杀人犯。
监狱里,还住着一家人。
我们一家人。
我就是狱长的女儿。
凯米1959
1
监狱里的早餐时间。油炸玉米肉饼的香气,弥漫了整个空间。每早如此。
“我可以教你怎么弄,”她说,“很简单的。”
“我想要你给我弄。”我说。
“你都快长成大姑娘了。总有一天,你得自己学会。”
“你来弄,”我对她说,“我不管。”
她的名字叫艾洛达·帕科。她是监狱的一名囚犯。她负责照看我家位于监狱入口楼上的公寓。洗刷。熨烫。洒扫。陪我玩。她是我家的管理员,也是我的看护人。
这会儿,她正在帮我梳辫子。
“好了,”她说,“梳好了。”
我抗议道,“这就好了?”我不想她这么快就梳好。
“就你这点头发,能怎么梳?”她拽拽我的辫子说。
她说的没错。我想扎一个长长的马尾辫,可我的头发太短,只能用皮筋绕一圈,扎成一个小揪。一个冲天辫。
我感到她准备离开我了。我猛地转身。“不要!”
她停下脚步,面向我,眉毛高高挑起。“不要?”
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想扎丝带。”
她睁大眼睛。然后,她笑了。笑得停不下来。
她明白我的心思:我根本不是那种会在头发上扎丝带的女孩儿。我坐在柜台后的凳子上,穿着工装裤、黑白高帮帆布鞋和条纹T恤。旁边的凳子上,放着我的棒球手套。
待她终于停下来,她说:“丝带?扎在你这个加农炮弹纵火犯头上?”
她的话,正反都有理。
加农炮弹是我的绰号。至于“纵火犯”……
两个月前,我们在学校里学习了本地土著乌纳米印第安人的历史。我从中受到启发,想以传统乌纳米人的方式,生一堆火。也不知我这个六年级小学生当时脑子里在想什么,我竟然决定在我家的浴缸里生火。
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绕道去了铁路轨道和小溪边,收集所需的原材料:一块石英石、一个生锈的铁道钉和一把从松树林里挖出的干燥苔藓。我把它们统统放进浴缸,然后自己也爬了进去。
我在铺满苔藓的浴缸里,用石英石和铁道钉相互敲打、摩擦。就在我的胳膊快要累断时,一缕烟从苔藓上升了起来。我轻吹一口气。一星火花出现了。“你在干什么?”艾洛达站在门口说。我抬头看了她一眼——接着,便大声尖叫起来,因为火花一下子变成了火焰,烧痛了我的大拇指。石头和道钉“哐啷”砸在了陶瓷浴缸上。艾洛达拧开淋浴喷头,浇灭了火焰,也把我浑身上下淋得湿透。在我擦干身子、更换衣服时,她给我烧伤的地方涂了凡士林、贴上创可贴,并告诉我,别人若问起,就说是自己切西红柿时不小心划伤了。
艾洛达敲敲我的手。“让我看看。”
我给她看了。烧伤的地方现在只留下了一块淡红色的印痕。她双手紧紧捂住我的手,捂了好一会儿。
“第一法则?”她问。
“不再玩火。”我答。她每次给我换创可贴时,都让我复述一遍。直到现在,她还时不时地让我重复。
然后,她的手从我身上拿开了,但我仍可感受到她的气息。是她的眼睛。她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可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终于明白她眼神中的含义。
“听着哈,”她打破我的魔怔,“如果你把头发留长到能编成三股,我就给你找一根丝带来。”
她又转身准备离开了。
我又突然说,“你真幸运。”
她再次停下脚步。“是啊,我是幸运小姐嘛。”
“我是认真的,”我说,“你每天都可以吃到玉米肉饼。”
“你说的对,”她说,“所以我才决定住这儿。我超级爱吃玉米肉饼。”她说着,走开了。
“站住!”
她站住了。她背对着我,静静等待着。
“你不要走。”我对她说。
“我还要工作。”她走进了餐厅。
“我是你老板!”我大喊——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只好怯怯地加了一句,“当我老爸不在时。”
她肩膀微微侧转,回头看了我一眼。她居然并不生气。她叹了口气。“奥莱利小姐——”
我打断了她的话:“我的名字叫凯米。”
“凯米小姐——”
“不!”我厉声道,“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凯米就好。”她瞪了我一眼。“快叫。”她继续瞪着我。“快!”
这下她生气了。她以小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吐出了我的名字,“凯米。”
她走开了。
那是六月中旬的一天,我十二岁那年暑假的第四天。那一天,我决定了,我一定要让艾洛达·帕科成为我的妈妈。
2
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但是这个决定其实早在一个月以前已经开始形成。在一个星期天。
母亲节那天。
和往年一样,这个节日开始于我和老爸一起开车前往小镇西边的河畔墓园。和往年一样,他把车停在草坪上,然后我们一起爬坡上山。我们在大树的右侧停下来,低头看向墓碑,和墓碑上我们已经烂熟于心的文字:
安妮·维多利亚·奥莱利
1921年4月16日生
1947年4月3日卒
贤良之妻
慈爱之母
和往年一样,我把一瓶水仙花摆在墓碑前。和往年一样,我们站在那里,默默无言,直视着墓碑。
我对于母亲,没有什么记忆。她去世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她是为了救我,被一辆送奶车撞死的。
那是那一年双厂镇最著名的一起事故。或许,在小镇整个历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我也因此成了镇上的名人。母亲舍命从送奶车下救回的女婴。老爸成了郡立监狱的监狱长之后,我更加出名了。
和往年一样,当老爸说“好”时,我就知道是时候与墓地道别了。我们回到车上,驾车离开。
接下来,我们总会去某个地方游玩。费城动物园。德拉瓦河游船。兰卡斯特县和阿米什村马车游。这一年,我们去观看了一场费城人队的比赛。我们每年会看三四场棒球赛,不过通常是在周日。我们还从未在母亲节当天看过比赛。
棒球场上,有人给现场的母亲们赠送粉色康乃馨。我们坐在右外野处。有很多界外球会从这个位置落下。和往常一样,我带了一副棒球手套。我超级热爱棒球。但由于我是女孩儿,无法参加少年棒球联赛,我的第二大愿望,就是在某场职业棒球大赛上,接到一个漏网的界外球。
第七局中场时,人人都站了起来。不过,没有人速度比得过我。第七局伸展时间,我向来是全场第一个起立的人,并为此而倍感自豪。我会确保自己充分地放松肩颈、拉伸后背。坐了那么久之后,肩颈和后背,难免僵硬难受。
然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管风琴突然停止了演奏《带我去看棒球》。广播里,播音员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就座。”三万人重新坐下。然后,他说:“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我们向天下母亲致敬的日子。”我身体微微一颤。“如果你把目光投向一垒的位置,你就会发现前排包厢里坐着我们费城人队棒球手的母亲和太太们。女士们,请你们站起来,好吗?”
前排的女人们站了起来,转过身,面向观众。她们每个人都笑容可掬地朝观众挥手致意。每个人都戴着一朵粉色康乃馨。体育场里掌声雷动,欢呼声、口哨声,不绝于耳。现场气氛如同有人击出本垒打时一般热烈。
接着,播音员又说:“现在,我们有请在场的每一位母亲站起来,接受我们的爱与感谢,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女士们……”人群中,仿佛起了一阵巨浪,成百上千的女人们站了起来——年轻的,年老的,暴风雪般的一大片粉色康乃馨——所有人都沉浸在欢呼喝彩之中。
如果让我用文字描述那一刻的想法,当时我的第一反应类似于:哇,这么多母亲啊,可没有一个是我的。这只是一个客观的估算,不带丝毫的感情色彩。
但紧接着,我的心就被触动了。
因为在我右手边,离我的肩膀只有几英寸的地方,一个人突然站了起来。之前,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她的低跟鞋,洁白得耀眼,鞋头饰有一圈带金边的白色蝴蝶结和四个小洞洞。她的大脚趾从洞洞里露了出来。她的连衣裙是薄荷绿的。她雪白的手套,在腕部有细长的开口。
我鼓足勇气,抬头看向她的脸。我吃惊地发现,她并没有面带微笑,而是一脸自豪。然后,她忽然大笑起来。她正低头看向身边,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耶,妈咪!”
之后,现场的数千名母亲,重新落座了,比赛继续进行——我呢,竟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看得出神,直到她转过头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微笑。我从未见过如此灿烂的笑容。那一瞬,我恍然以为,我与这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已经相识一辈子了。
接着,我嚎啕大哭起来。突然之间。毫无预兆。无缘无故。完全就像他们所说的,如左外场飞来一个球,突如其来、猝不及防。我止不住地哭。她的笑容立马消失了,脸上的表情,近乎恐惧。她用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捂住鲜红色的唇。“哦,天哪。”她说。然后,爸爸伸出了胳膊,一把揽住我。他抱紧我,问我怎么了,是不是想走了。我哭着说:“不要!”我拿拳头不停地锤砸棒球手套,直到流干最后一滴眼泪。
我们一直待到散场。一直到最后,我再也没有看过那位穿薄荷绿连衣裙的女士一眼,也没有一个界外球落到我们附近。
。
该如何认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当妈呢?
在过去的十二年里,对我而言,有爸爸就足够了。看看家庭照片和那张泛黄的报纸,就足够了。
当然,自从第一次听说那场事故,我就不断想象着自己的母亲。安妮·奥莱利。那位从牛奶车下救了我一命的女士。我为她哭泣。也为自己哭泣。有时候想起来会哭上一场。仅此而已。世道本就如此。其他小孩都有妈。唯有凯米·奥莱利没有。就是这个样子,没什么好说的。
可现在,母亲节过后的几个星期里,有些事情正在改变。放在以前足够的事儿,现在不再足够了。蛰伏已久的情感,因为棒球场上的一个微笑,被唤醒了,搅动了,直至它们幻化成一个清晰明确的想法:我已经受够了没妈的日子了。我想要一个妈。接着,又一个想法:如果得不到首选的妈,那我就找个替补来。
但是,谁呢?
某位老师吗?
下一位冲我微笑的女士吗?
突然,灵感被五个字点燃了。
4
“放到水池里。”
好,回顾一下前情……
学校放假的前一天,我们只上了半天课。一放学,我就飞奔回家,推开前门,跑上长长的扶梯,冲进我们监狱的公寓。我在餐桌前一屁股坐下。桌上,已经摆好了午餐。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好味多巧克力纸杯蛋糕。空杯子——但没有空多久,一只手就出现了,往杯子里倒满了荣养乳业巧克力牛奶。
一只手——在我眼里,她向来不过是一只手而已。一直有那么一只手,给我端来这个,为我擦去那个。在没妈的日子里,我靠一双双手的伺候、照料长大。它们是一名又一名监狱女管理员——凯米监护人的手。爸爸白天工作时,就把我托付给了她们。这一双双手背后也有一张张脸和一个个名字,可在我看来,她们只是一双手而已。一双按照我的吩咐做事的手。通常,不用我吩咐,她们就把事情给做了。女仆们。
那天给我倒巧克力牛奶的手,是最近出现的一双。她和之前那一双双手相比,确实有一点不同:她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艾洛达·帕科。听起来像是漫画书里的人物。我问过爸爸,这是不是她的真名。爸爸回答说是的。
于是,艾洛达·帕科的手为我倒了一杯牛奶,我吃完了午餐,就站起来离开了桌子,就在我快走出餐厅时……
那件事突然发生了。
“放到水池里。”
我愣住了,大吃一惊。我认出这是那名女管理员的声音。可我不确定她是在跟谁说话。
那声音再次响起。“放到水池里。”
我转过身。她正站在桌边,直直地看着我。毫无疑问,这话是对我说的。
“什么?”我说。
她又把话重复了第三遍:“放到水池里。”
我听见了,而且每一个字都听明白了。可是,整句话连起来,却让我懵了半天。
“什么放到水池里?”我说。在我看来,对她的话作出回应,已经算是给她面子了。我完全可以不理她,直接离开。
“你午餐用过的东西,”她说,“应该放进水池。”
她说的话,在我听来,全然陌生。真是破天荒了。我的任务,向来只是坐下、吃饭、起身、离开。收拾餐桌上的杯盘狼藉,是她的任务。
“是啊,”我说,“那你就放呗。”
说着,我甩手离去。
暑假第一天,我骑了一下午自行车,庆祝自己从书本和考试中解放出来,重获自由。我从东区,骑到北区,再到西区,穿过公园和动物园,想象着自己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从猴山上俯冲而下。
回到家时,艾洛达正在用吸尘器打扫客厅的地毯。我从餐厅经过,努力不去往里看,可还是忍不住瞄了一眼。我午餐用过的盘子、杯子、餐巾,竟然还在桌上。
到了五点钟,我又瞄了一眼:原封不动地,还在。而我爸通常六点左右到家。
现在,艾洛达·帕科随时可能走进厨房,为我们准备晚餐。她难道真的打算让我爸瞧见我午饭留下的烂摊子?她敢吗?
我一把抓起桌上的脏盘子,扔进厨房的水池,故意搞出动静来。她在隔壁听见了,说:“最好顺手洗一下。我可不想用堆在水池里的脏盘子做晚饭。洗完了放架子上沥干。”
我又愣住了,呆呆地望向水池。可我眼前一片模糊,看见的不是水池,而是自己举起杯子、盘子,狠狠砸向厨房的地面,砸得一地碎片。然后,我摆出一副女主人的姿态,说:“把那个给我放架子上,佣人。”
不过,这大快人心的场景,终究只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乖乖地洗了盘子,把它们放在架子上,然后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我没再给她任何抓我把柄的机会。我带着零花钱,去了中心商业街上的蓝鸦餐厅,在那里吃了早餐。吃的是玉米肉饼。午餐,也在那儿解决的。还是玉米肉饼。
第三天,我又像平日里那样,在厨房吧台上吃了早餐。吃完后,就把盘子扔在台子上不管了。我起身离开,等待她开口说点什么。可她什么也没说。
午餐时,我故伎重演:吃完后,把脏盘子留在桌上,就走了。这一回,我听到了。她只捏着嗓子说了一个词,“盘子。”
顷刻之间,我明白了,那一天,我为何要留在家里吃饭。我不单是在等待她说出那句话。我自己也渴望听见那句话。
我立马把盘子放进水池,清洗干净后,放在沥水架上。我甚至还用湿抹布擦了一遍桌子。
第四天,吃过早餐和午餐后,我不用她督促,就主动收拾干净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从她那句话中————“放到水池里”————我听到了这十二年来,我一直在隐隐期待的声音。它并非来自父亲,而是来自一位女士,一位已经在家中取代了母亲位置的女士。好吧,的确,其他保姆们也做过类似的事情,扮演过母亲的角色。然而这一位……这一位还做了别的事情。新鲜的事情。这一位说了妈妈才会说的话。而且是对我说的。忽然之间,童年早已过半的我,似乎被赐予了一个从不敢奢望的机会,成为另一个自己:一个母亲的女儿。
我要抓住机会。
这就是我的做事风格。雷厉风行。如果你敢拦我,那你可得小心了。我的同学们早已摸清了我的脾气。第一学年还没结束,他们就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加农炮弹”。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这位保姆就收到了一个新任务。“我想扎个辫子。”我告诉她。
这句话说出口,我自己都感到好笑,因为扎辫子是女孩的事儿,而我是个十足的假小子。但我已经决定了,扎头发,是建立起母女之间亲密关系的绝好时机。尽管艾洛达·帕科百般不情愿,我依然不气馁。我要一点一点地做她的工作。一点一点地把她磨服。我要把她变成我的妈妈。当她吩咐“加农炮弹”凯米去洗盘子时,她一定没料到,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
5
在砸门声响起之前,我已经听见台阶上的脚步声了。我飞快地跑去开门————可是门怎么也推不开。原来,我又忘了先拉开杆锁。那把巨大的杆锁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一些疯狂的、有攻击性的囚犯的侵害。比如,金刚。我把铁杆拉开,把我最好的朋友雷吉·温斯坦迎进了门。
雷吉拥有我没有的一切。她漂亮,会打扮。而且胸大。这已经够要命了。可当她撅着涂了口红的嘴唇,冲你绽放出一个电量十足的微笑时,砰,仿佛马克卡车逆火轰燃了似的,你会禁不住连连后退。她把一张45转唱片在我面前晃了晃。“瞧瞧!”她尖叫道。
我读了一下标签:
RCAVICTOR出品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想你,要你,爱你
接着,我俩开始尖叫,蹦跳……接着,这张唱片被放进了我的45转唱片机……接着,我们开始围绕着餐桌,围绕着正在打扫卫生的艾洛达,跳起华尔兹,互相挤眉弄眼地唱着:“我想你!我要你!我啊啊爱你!全心全意”————并模仿猫王最爱的唱腔,把最后一个字的音拖了老长。
我们嚎叫着,一屁股瘫坐在了地毯上。艾洛达绕过我们,走出房间,随手关上了那扇巨大的橡木门,把我俩锁在里面。我们仰躺在地上,渐渐没了气力,咯咯轻笑起来。
雷吉抽抽鼻子,扮了个鬼脸。“我讨厌这里的气味。充满一种惩罚的味道。我判你吃三年玉米肉饼。”
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作出一脸陶醉的样子。“我是准备从满十八岁那天起,就开始天天吃玉米肉饼。可以的话,吃一辈子才好呢。”
“滚,别在我面前吃。”她戳了我一下。“转过去,让我瞧瞧。”
我转过头。她扯了扯我的小辫儿。“才编了一股,”她说,“可怜。谁帮你梳的?狱长大人吗?”
“艾洛达。”
“那个女仆啊。”我可以感觉到她在用手指检查艾洛达的手艺。“还不错嘛。就是太短了,看起来笨笨的。扎个丝带,应该会好些。”
“等我头发再留长点,可以编成三股时,我再扎。”
她夸张地叹了口气。“惨不忍睹啊。”她拍了拍我的背,“转过去。脸。”
我照做了。从没有哪个医生或牙医像她这般仔细地端详过我的脸。雷吉有一个任务:在我们升入斯图尔特初中之前,把我改造成一名淑女。她哼了哼鼻子,绝望地摇摇头,说:“你的眼睛简直是场灾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嘴唇和肤色,就值得夸耀了。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
“什么?”我问。
“即便我们把一切都搞定了——头发、眼睛、嘴巴——还有鼻子。”她用手指狠狠地掐了一下我的鼻子。
“唉哟!”我痛得大叫。
她松开手。“瞧见了吗?它立马弹回原样了。这我可无能为力。”
“你可以帮我打点粉底修饰一下嘛。”我说,试图让这一切听上去没那么惨。
她没有被我的话逗笑,而是指着我贴了创可贴的大拇指说,“这个一点也不酷。让你看上去像个野小子。”
“我本来就是个野小子嘛。”我提醒她道。
她做了一个抬眼仰望苍天的动作。“救救我吧。”
她又从脚到头,把我瞅了个遍,然后摇摇头。她表情痛苦。我突然感觉很糟糕,因为她的痛苦,是拜我所赐。
她的目光,最后停留在了我的胸部。足足停留了一分钟之久。在那一分钟里,她又是叹气,又是摇头。最后,她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学?”
“劳动节过后那天。”我说。
她点点头。“好吧。我只给你这么多时间。如果到劳动节那天,你这儿还没凸出来的话,我就只好往里面塞袜子了。”她摊了摊手,“我能怎么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我很想帮她。真的。可我想不出什么法子,只能傻傻地提议:“或许,如果我憋气憋得够久,它们就鼓起来了。”
“或许吧,”她说,“如果你憋着不再拉屎了。”
“真恶心!”我尖声叫着,踢她,踹她。接着,我俩又开始在地毯上打滚嚎叫了。
我们又把《想你,要你,爱你》播放了不下二十遍,直到雷吉关上唱片机,说:“好啦,我准备好去见杀人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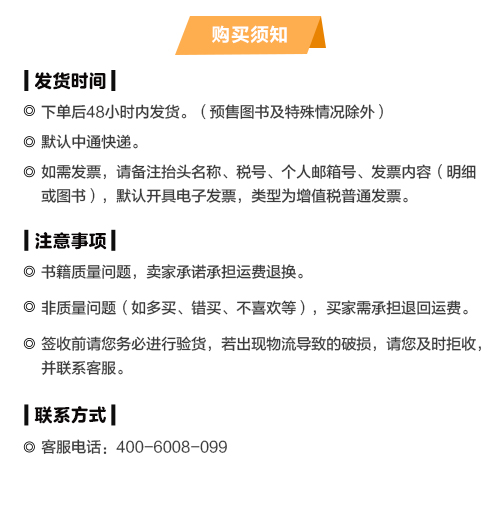
- 中信出版社
- 中信出版社坚持“我们提供知识,以应对变化的世界”的出版理念,以高端优质的内容服务,多样化的内容展现形式,为读者提供高品质阅读与视听内容,满足大众多样化的知识与文化需求。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