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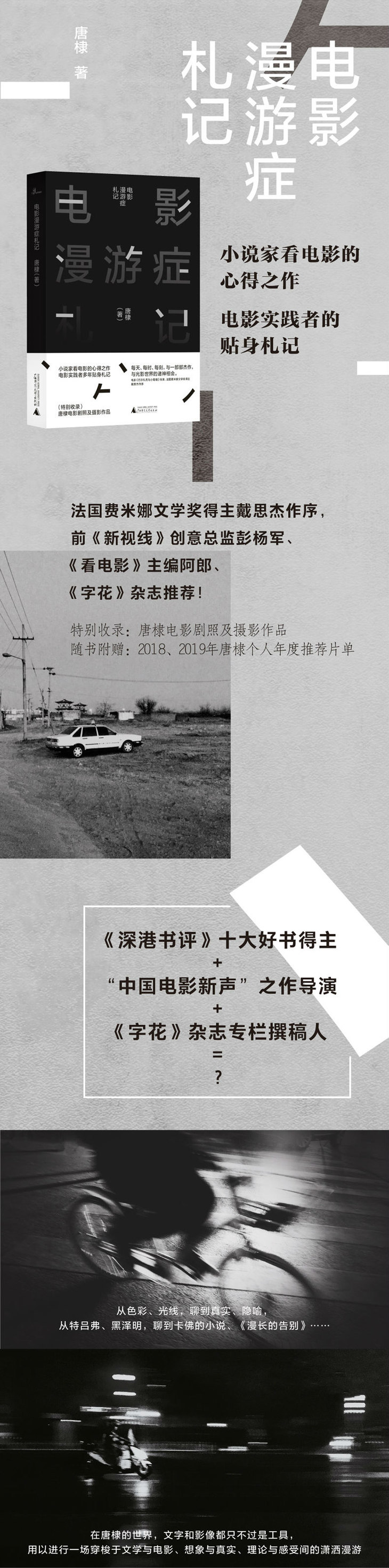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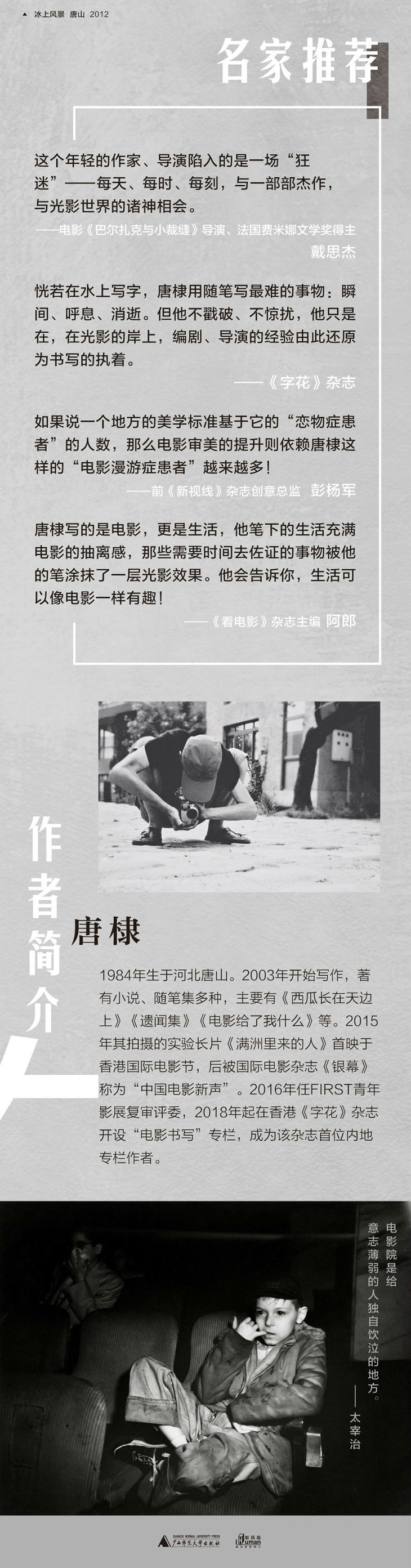
内容简介
小说家看电影的心得之作,电影实践者的贴身札记。
从色彩、光线,聊到真实、隐喻,从特吕弗、黑泽明,聊到卡佛的小说、《漫长的告别》……在唐棣的世界,文字和影像都只不过是工具,用以进行一场穿梭于文学与电影、想象与真实、理论与感受之间的潇洒漫游。
作者简介
唐棣,1984年生于河北唐山。2003年开始写作,著有小说、随笔集多种,主要有《西瓜长在天边上》《遗闻集》《电影给了我什么》等。2008年拍摄处女作《湖畔公路》,从此连续创作多部短片,2014年获新星星艺术节年度实验奖。2015年其拍摄的实验长片《满洲里来的人》首映于香港国际电影节,后被国际电影杂志《银幕》称为“中国电影新声”。2016年任FIRST青年影展复审评委,2018年起在香港《字花》杂志开设“电影书写”专栏,成为该杂志首位内地专栏作者。
目前从事电影编导、策划工作,业余撰写摄影、文学、电影相关文论,见于《世界文学》《上海文化》《人民文学》《南方周末》《书城》《单读》《新京报.书评周刊》等。
目录
导言
卷一
导演思维在窗外
生命多短,生活多长
没有什么发生
小部分时光
24秒即永恒
方向感
电影给了我什么
录像厅初记
电影初心
未知光明的前程
一场青春梦倾倒
时间的魅影
卷二
判断—观察
光线—时间
色彩—空间
摄影—艺术
瞬间—记忆
卷三
真实
声响
观看
形式
表演
隐喻(一)
隐喻(二)
冲突
悬念
背景
卷四
暴力与想象
色彩与细部
处境与氛围
破坏与建构
真理与荒诞
评价与标准
选择与渴望
战争与爱情
特写与呈现
独孤与众人
论爱与黑暗
类型与反类型
人工智能与恐惧
结语
附录 为了讲述风的故事,我们拍下了树叶——私人电影笔记
精彩书摘
背景
以唐朝为背景的《刺客聂隐娘》并没有讲聂隐娘如何成为刺客,而是讲她如何没有成为刺客。拍摄开场镜头时,很多导演会“对着一群说话、移动的人物拍摄”,唯独导演侯孝贤关注站在场景角落里的人。在镜头背后,他没有故意引导观众去看什么,而是让观众随着镜头的移动,一同感觉其中藏着的东西,仿佛在说话人的附近徘徊着一双眼睛。
《刺客聂隐娘》有几个为人称道的全景:空旷山野、雾气环绕的水中小岛、勾栏阻隔的建筑。古风,没错。但毕竟是剧情片,人物、情景的互动应该有更显著的牵引——人在景中,景有人心。由人的言语或者举动,牵引出整个环境。但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很脆弱。全景的美是单拎出来的画面美,而非电影整体跌宕而出之美,更不是人物参与之下的、融入剧情的美。某些画面可以解释成“以景喻心”,也可以解释成“无意义的填充”,一方面造成剧情断裂,一方面让碎片似的人物关系中不断出现“隔断”——在田季安与妃子在纱帐内的对话戏中,纱幔阻挡,光影变化。
导演摆明了要讲几对关系,讲对田季安与聂隐娘关系的想象。关系必有亲密与生疏,导演会预设好距离感、分寸感。光影上的单一是导演风格的体现,很难看出拍《刺客聂隐娘》的镜头和拍《海上花》(1998)的镜头调度有何不同。
另一部故事背景为当代的《烈日灼心》(2015),意在表现三个罪犯摆脱煎熬、寻求内心解脱的历程。导演曹保平不断为他们的摆脱制造负担——叫“尾巴”的小姑娘、对手下关心备至的队长、王珞丹扮演的女孩,这些都是“情”的部分。这里的“情”和《刺客聂隐娘》里的“情”不同的是,它无法改变事件结果,只能完成类型片的任务。
两部电影的结局是:罪犯依然是罪犯(《烈日灼心》),刺客终不成刺客(《刺客聂隐娘》)。
《烈日灼心》好在从真实的犯罪者和警察的角度拍了想象中的侦破,《刺客聂隐娘》好在从现代生活的角度拍了昔日的武侠。
侯孝贤定义了这个人与那个时代,让观众知道,他们脱掉古装之后,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侯孝贤偏爱写实,但他写的是现代文艺片的实,非唐朝的实。他的唐朝基本上是美术和造型拼接出来的唐朝,而不是故事里的唐朝。《刺客聂隐娘》中的唐朝,就如有一场戏是全景,唐朝房屋,午后炊烟,聂隐娘自远处归来,屋旁有几个人在做着什么事。
远景镜头里的唐朝像一幅老画,生动扎实。当镜头切到交谈的人们,呈现他们的神态时,观众会发现,人物完全不在那个氛围中,他们的语态是现代人的语态。
《刺客聂隐娘》面对新,《烈日灼心》延续旧,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它们的手法——男女相遇一定要英雄救美么?男人打斗都要上楼顶么?杀人犯总得遇上一个爱他的女人么?
“相信什么就拍什么。”侯孝贤与贾樟柯对话时说过这么一句话。也许在《刺客聂隐娘》里重现的唐朝,是侯导最相信的唐朝的样子。
看电影不是去看真事,“真实电影”的说法与电影视觉局限的本质是相违背的。侯孝贤导演只是给出了他相信的唐朝而已。
导演所相信的“真实”在《烈日灼心》里体现较少,当邓超扮演的罪犯被绳之以法,电影走向老套地说情怀、总结意义、讲道理,暗藏的剧情反转也顿时显得无力。
《烈日灼心》把观众想得太天真,《刺客聂隐娘》则把观众想得太聪明。《刺客聂隐娘》结束了,却让人觉得没完。这不是余韵,而是侯导演给出的人物线索不足以织出一张网。在侯孝贤的电影中,展示总不是最重要的。武打、争斗、历史等,很多人明确谈论的,都不是这部电影的主题。可以用和侯导风格比较接近的法国导演布列松的一句话来形容电影里的人:“那些人物身上散发着的气息,使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再是那些东西……”
无论是《烈日灼心》的紧凑还是《刺客聂隐娘》的放空,都在2015 年的某天下午给我带来了极好的观影体验—我是在影院连续看了这两部电影的。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两部电影显然没有可比性,但它们代表着当下电影的两个方向,因此我在这里把它们放在一起说一说。
从电影市场多样化的角度上看,《刺客聂隐娘》的意义大于《烈日灼心》。无论是讨论本土性还是国际性,后者都明显尴尬。这个尴尬比影院观众买票进场看到《刺客聂隐娘》中的很多长镜头时,面露尴尬的程度严重。因为,国内可以拍《刺客聂隐娘》这个程度的电影的导演不多。“一个人,没有同类。”这句话让人想起曹保平导演的青春片《狗十三》(2013),这是一部单纯而直接的电影。对于主人公李玩来说,自己在所处的那个时期中,自己在所遇上的整个大人社会中,也没有同类。
少女的孤独与侠客的孤独本质上都是人之孤独。所以,《狗十三》里所谓的“平行宇宙”完全可以是对孤独无可排遣的隐喻。
从《刺客聂隐娘》里可以深刻体会到“没有同类”的感觉,就像侯孝贤导演说:“现在,没人这么拍电影了,但我们只会这样拍电影。”我相信《狗十三》也只能出现在2013年,那时的曹保平导演没有那么多商业累赘。
《狗十三》里的女孩终归要长大,《烈日灼心》里的凶手必将死于刑罚,《刺客聂隐娘》里的刺客只能远走他乡,几组人物内心的孤独其实是一致的。
曹保平导演谈《狗十三》时说:“没人注意到我们在什么时候忽然就长大了,一切好像自然地发生了,但那一天的到来其实是很残酷的,我想让大家回头看看这一天。”
侯孝贤导演说过什么呢?大部分人无法做到不判断,只去观察。“不需要经验判断,就是去看”的意思是纯粹的感受,不要多想。
聂隐娘想做一个刺客,事实上,她剑术已成,下山杀掉田季安,一切立刻成立。只怪记忆作祟,“记忆,我想,是一个替代物,替代我们在愉快的进化过程中永远失去的那条尾巴”(布罗茨基)。对于聂隐娘来说,“昔日记忆”替代了她“挥剑的现实”,最终人物命运随之改变。
- 今日美术馆微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