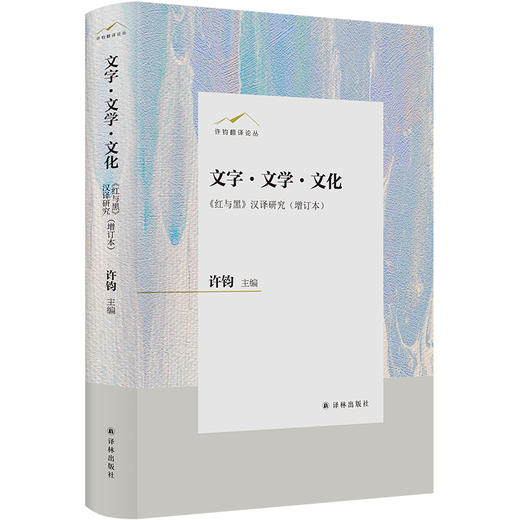商品详情
【编辑推荐】
1. 著名学者、翻译大家许钧主编,国内法国文学与翻译研究领域顶尖学者、译者共同编著,真实推动了中国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2. 全面展现20世纪90年代法语文学翻译跨圈层大论战,方平、许钧、施康强、许渊冲、罗新璋、韩沪麟、马振骋、赵瑞蕻、郝运、袁筱一、卢世光、汤守道、冯凤阁、蔡之翔、王子野、孙迁、郭宏安、罗国林、张成柱、袁莉,翻译家、批评家、出版家、经贸官员、统计师、法文系学生、退休教师……群英荟萃,百家争鸣,或惺惺相惜,或针锋相对,或“皮里阳秋”,字里行间展露出参与者真诚坦荡的交流心态和对文学、文化的无限热爱。
3. 当我们谈论翻译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当我们谈论翻译质量时,仅仅止步于找几处错译、漏译吗?不同译本,如何挑选?译者在忠实还原原作和再创造之间如何认识、取舍、实践?读者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心态和审美期待如何影响翻译?这一本有料、有趣又好读的学术书,会给你答案。
4. 全新修订,护封精装,优质纯质纸,版式疏朗,利于阅读。
【名人评价及推荐】
许钧主编的这一本《红与黑》汉译讨论汇编,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这么说,并不夸张;有一天,我们回顾这几十年来文学翻译走过来的道路,将在这一册汇编中辨认出历史留下的许多踪迹。而且我深信,这一本汇编将以它丰富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在未来的文学翻译史册中得到肯定。
——著名翻译家 方平
充分说理,十分公正。
——著名翻译家 草婴
平心而论,这次关于《红与黑》汉译的讨论给了我很深的感动。大家都是朋友,都很大度,如罗新璋先生,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观点,都摆到桌面上来说,少有那种文人相轻的酸味,持着研究切磋的态度,即使话说得冲点怪点都无所谓。例如说北大的许渊冲教授,他有他明确的翻译追求和翻译理论,并且敢于付诸实践,也有很多人不同意他,那么就摆出自己的理论来争好了,各抒己见,我看是件好事。
——著名翻译家 许钧
关于《红与黑》汉译的讨论,其意义远远超过翻译讨论本身。这是新时期人们对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化由被动接受向主动思考转变的一种体现。
——著名作家 苏童
【作者简介】
许钧
1954年生,浙江龙游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和第七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并担任国内外近20种学术刊物的编委。著作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翻译学概论》《傅雷翻译研究》等10余种,译著有《追忆似水年华》(卷四)、《诉讼笔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30余种。
【内容简介】
20世纪80年代起,法国文学经典《红与黑》陆续迎来多种汉译本,这些译本多出自名家之手,各有特色,赋予了这部名著新的生命。90年代初,《红与黑》的汉译现象在中国翻译界掀起了一场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大讨论,涉及直译与意译、形似与神似、艺术与科学、忠实与创造等翻译研究中诸多基本问题,以鲜活的实例和良好的氛围,极大推动了中国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参与这场讨论的不仅有赵瑞蕻、许渊冲、郝运、罗新璋、郭宏安等《红与黑》的译者,也有方平、施康强、许钧、马振骋、罗国林、袁筱一等翻译家和批评家,还有热爱文学的普通读者。本书所收入的论文、散文、书信等正是出自他们之手,记录下这场前所未有的讨论中翻译思想和观点的交流、碰撞,映照出文学翻译的前行之路。
【目录】
历史将给予充分的肯定
———代再版序 ………………………………………… / 方 平
《红与黑》汉译的理论与实践
———代引言 …………………………………………… / 许 钧
上编 讨论
红烧头尾 ……………………………………………… / 施康强
四代人译《红与黑》…………………………………… / 许渊冲
“译”者“臆”也?……………………………………… / 易 超
从编辑角度漫谈文学翻译
———兼评许译《红与黑》译者前言…………………… / 韩沪麟
从《红与黑》谈起 ……………………………………… / 许渊冲
斯当达与维璃叶……………………………………… / 罗新璋
译音常是约定俗成…………………………………… / 马振骋
关于《红与黑》中译本的对谈……………… / 赵瑞蕻 许 钧
关于《红与黑》汉译的通信(一)
———许钧致许渊冲…………………………………… / 许 钧
关于《红与黑》汉译的通信(二)
———许渊冲致许钧…………………………………… / 许渊冲
关于《红与黑》汉译的通信(三)
———许钧致郝运……………………………………… / 许 钧
关于《红与黑》汉译的通信(四)
———郝运致许钧……………………………………… / 郝 运
关于《红与黑》汉译的通信(五)
———许钧致郭宏安…………………………………… / 许 钧
关于《红与黑》汉译的通信(六)
———罗新璋致许钧…………………………………… / 罗新璋
关于《红与黑》汉译的通信(七)
———罗新璋致许渊冲………………………………… / 罗新璋
“应该加进去的东西……” ………………………… / 许渊冲
翻译杂感……………………………………………… / 方 平
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
———读方平《翻译杂感》后的杂感 ………………… / 许渊冲
法国牛排,还是带血的好 …………………………… / 袁筱一
《红与黑》汉译读者意见征询 …………………………/ 《文汇读书周报》编辑部 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
为了共同的事业
———《红与黑》汉译读者意见综述………… / 许 钧 袁筱一
关于《红与黑》汉译的基本看法……………………… / 卢世光
我对文学翻译的几点看法 …………………………… / 汤守道
文学翻译之我见……………………………………… / 冯凤阁
对《红与黑》汉译的看法……………………………… / 蔡之翔
妙译来自“得意忘形”……………………………… / 许渊冲
下编 专论
《红与黑》汉译漫评 ………………………………… / 许 钧
后来未必居上………………………………………… / 王子野
何妨各行其道 ……………………………………… / 施康强
也谈《红与黑》的汉译
———和王子野先生商榷 …………………………… / 孙 迁
我译《红与黑》 ……………………………………… / 郭宏安
是否还有个度的问题
———评罗新璋译《红与黑》………………………… / 许 钧
风格、夸张及其他 …………………………………… / 罗新璋
文学翻译应追求整体风格的和谐统一
———再读罗新璋译《红与黑》 ……………………… / 许 钧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红与黑》人名、地名的翻译 ……………… / 许 钧
“借尸还魂”与形象变异
———德·瑞那夫人形象比较 ……………………… / 许 钧
“化”与“讹”
———读许渊冲译《红与黑》有感 …………………… / 许 钧
从翻译的层次看词的翻译
———还是译为“小城”为宜 ………………………… / 许 钧
社会、语言及其他
———读海峡彼岸的《红与黑》 ……………………… / 许 钧
是复译还是抄译?
———评海南出版社版《红与黑》…………………… / 许 钧
批评不等于否定
———也谈罗新璋译《红与黑》 ……………………… / 罗国林
谈罗新璋译的《红与黑》
———兼谈罗新璋的翻译艺术 ……………………… / 张成柱
谈重译
———兼评许钧 ……………………………………… / 许渊冲
附录
译书漫忆
———关于《红与黑》的翻译及其他 ………………… / 赵瑞蕻
西方的“红学”……………………………………… / 赵瑞蕻
译者前言 …………………………………………… / 许渊冲
译书识语 …………………………………………… / 罗新璋
不求同言 但求同妙
———就《红与黑》复译问题看翻译批评的导向 …… / 袁 莉
给文学翻译一个方向 …………………… / 许 钧 袁筱一
《红与黑》汉译讨论受到海内外关注…… / 《文汇读书周报》讯
编后记
再版后记
三版补记
【文摘】
《红与黑》汉译的理论与实践
许钧
这个时代,无论译事还是译理,值得探讨的东西很多,但大众舆论偏偏选中了《红与黑》。的确,《红与黑》在中国的命运,大约算得上是个奇迹了。半个世纪的沉沉浮浮,居然没有淹灭,反倒向着更热闹的方向去———一个又一个译本相继问世,“一发而不可收”。这个奇迹,五十年前在嘉陵江畔吟咏着“炉火峥嵘岂自暖,香灯寂寞亦多情”的诗句,开笔首译《红与黑》的诗人赵瑞蕻一定没有能够料到,就是换了断言将在五十年后被人理解的斯丹达尔本人,怕是也要在这遍地“红”花的盛景前怔住,实在是太灿烂了,灿烂得叫人既喜亦忧,几乎要忘了寻个究竟。
斯丹达尔预备用至少五十年的时间———事实上或许更长———来等政治清明,读者知性的一天。再叫他等上五十年,等中国从硝烟炮火的战争年代脱出身来,等中国从文化荒芜的“文化大革命”走到这个空前自由的新时期,想来还不至于就失了耐性。中国人爱说,往事不堪回首,只是因为往事固然已矣,可担了历史学家用逻辑证明了的历史必然性,突然就有造化弄人的辛酸:时间的长短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况且如果说真正的艺术,越是历经岁月沧桑,就越是有“复生”(且不说“复兴”)的机会,那么,《红与黑》的汉译应该是极好的例证。
岁月是生冷的,不容改变的轨道,看上去便仿佛只有等待。然而可以作为奇迹留下的,当然不仅仅在于等待。大多数的奇迹,说到底是人在岁月的壁上磕破了头,印上血迹,后人去看,略加缀补,便成了一幅英雄壮丽的壁画。《红与黑》本身的创作过程自是不消说的,它的汉译,倘若没有这样的执着和勇气,在流年里了无痕迹地被流去,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事情。时空的差距,光凭等待,大概熬不过这五十年的寂寞。
但是既然以不为外界所动的追求挺过了五十年的时光,这件事本身所承载的,早已不仅限于斯丹达尔著下的那个四十余万字的故事。移植异地“红花”所需的水土和气候,移植的方法和手段,移植过来的结果,在喧哗过后,自然有人要问、要探寻的。浓缩在这十几个版本的《红与黑》里,大约可以把翻译能自主的或是不能自主的欢喜和悲哀、成功和失败、梦想和现实一并包揽在内了吧。
铸造一个既科学又艺术的尺度,用以梳理我们过去的译坛,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是很久以来做翻译研究的人的一个梦想。舆论对《红与黑》汉译的热衷,似乎送来一个好的契机,因为它把翻译里能够引发的问题都引发出来了。但这个梦想究竟是可疑的———五十年的追求,若一下子便有了断论,倒像是历史的嘲讽了。我们要做的,只是想从半个世纪以来问世的十几个版本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几个,就这些译家的翻译思想、艺术追求和翻译实践做一个分析与比较,通过不同形式的批评和探讨,为澄清文学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探索文学翻译的成功之路,提供一些参考。
二、复译,一个“继承、借鉴、突破或另辟蹊径的过程”
如何向中国读者奉献一个堪与原著相媲美的译本,成了赵瑞蕻先生及他之后的众多译家的一致追求。众译家一展身手,《红与黑》频频亮相,一次又一次被复译。对这一现象,赵瑞蕻先生的看法非常明确,他认为“名著不厌百回译。古今中外名著重译多得很,例子可举出不少。有了多种不同译本可以进行比较,评判优劣,对提高翻译水平极有好处”。他坦言说自己“翻译《红与黑》时年纪很轻,学识和经验都很不够,里面有许多错误”,在他之后,出现新的版本,不仅是正常的事,也是件好事。
前译和后译,一般说来,都有个借鉴和超越(至少有超越的意识)的关系。罗玉君的译本,在很多地方参考了赵瑞蕻的译本,赵先生认为,“有前人的翻译可以借鉴好的,避免错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据郝运先生自己介绍说,他在20世纪50 年代曾担任过罗玉君译本的编辑,对罗先生的译本,他提过不少意见,请罗先生修改,但该本仍留有许多错译和欠妥的地方。正是鉴于旧译本的这些缺陷,郝运先生认为有必要重译,且自己在翻译的时候,也想到会有另外的译本问世。而后来的郭宏安先生重译《红与黑》,除了对《红与黑》的特殊感情之外,“判定旧译不能令人满意或者完全满意”,乃是他决心复译的重要原因。他不满于郝运先生的译本,认为“其文字过于质木,太少灵气,不够精练,时有拖沓之感”。在他看来,郝运译本的这些特点明显有悖于原作的风格。许渊冲先生更是明确宣布,在他以前的所有译本,“都不能说是达到了翻译文学的水平,也就是说,译文本身不能算是文学作品,所以需要重译”。
在对待前译的问题上,众译家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郭宏安先生认为,“复译必然是继承、借鉴、突破或另辟蹊径的过程,因为后来者不大可能没有读过已经存在的译本,也很可能要参考一下旧译,以不掠前人之美”。在他看来,新译“没有必要步步设防,故意与旧译不同。既不苟同,又不苟异,可也”。罗新璋先生在复译时,也同样遇到如何对待前面已有的几个译本的问题。他在译按中这样说:“翻译时,碰到有些字句,真是相避为难,暗合为忧。好在这四家于我都是师辈;古人云:‘主善为师’,犹恐不及,谅不至于责我罪我。此开篇第一段,除第一句外,多有借助罗(玉君)译本字句之处,特示对原译者的尊重与敬意。”对于后来的译家,罗新璋先生更是宽宏大度,说“日后,轮到这个译本要给推倒重来之日,其中个别可取的砖砾,包括所含罗译的珠玑,尽可采掇”。事实上,一部名著,绝不是一个译家就可穷尽其“义”、推出超越时空的译作的,需要一代又一代译家的不懈努力。因此,对前译的尊重,对后译的鼓励,是一切有译德的译家应持的态度。对前译不足的“不满”,并不是对前人劳动的全盘否定。许渊冲先生有超越前译的胆识,但这种“超越”,也是在前人基础上,试图有所突破,有所进步而已。他译《红与黑》,也同样少不了参考前译,拿他自己的话说,“甚至把旧译当我自己的初稿”(见许渊冲《从〈红与黑〉谈起》,《文汇读书周报》1995年5月6日第6 版),目的是“要改得自己认为胜过了旧译文,才算对得起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使许渊冲先生的译文超越了旧译,这种超越中也有旧译的一份功劳。郭宏安先生的态度比较客观、公正,他认为他所借鉴的郝译“自有它的优点和特色,其他几位的本子亦复如此,包括受到不公正的攻击的闻家驷先生的本子。所以推倒重来、完全取代等现象在短时间内陆续出现的复译中是极少见的”。
【序言】
翻译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许钧翻译论丛”总序
从大学毕业至今,已经近45年了。回想这40多年走过的路所做的事,我自己觉得最有意义的是翻译。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做的工作,基本上只与翻译有关。我做翻译,包括口译与笔译,口译做过同声传译,也做过学术翻译、陪同翻译,有机会认识了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等先生,有的还成了很好的朋友。笔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也译过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在做翻译的基础上,我对翻译进行思考,进行研究。除了做翻译,研究翻译,我的主要工作是教翻译,培养做翻译、研究翻译的人才。这几十年来,我之所以坚持不懈地做翻译、研究翻译和教翻译,是因为我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因为我们都知道不同民族的交流离不开翻译,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翻译,世界的和平也离不开翻译。
我从翻译出发,通过翻译研究,把目光投向了人类悠久的翻译历史,在历史的审视中,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作用、翻译主体的活动、翻译研究的发展和翻译学科的建设进行思考。感谢译林出版社的厚爱,系列推出我的翻译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许钧翻译论丛”记录的就是我40余年来在翻译与翻译研究的道路上对翻译的思考与探索的印迹。
翻译活动是丰富的,有多种形态。雅各布森将翻译活动分为三种类型:符际翻译、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符际翻译和语际翻译,我们译学界有过不少研究,但对语内翻译,似乎关注不多。我在《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一文中曾谈道,“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传统,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断‘翻译’,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
翻译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在我看来,翻译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对于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我们现在了解得比较多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看,翻译能够克服语言差异造成的阻碍,达成双方的相互理解,为交流和对话打开通道。正是借助翻译,人类社会才从相互阻隔走向了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狭隘走向了开阔。从某个具体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来看,翻译通过对别国先进科技和文化的介绍,能够引进知识,开启民智,塑造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在特殊时期甚至能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成为一种文化的构建力量。
而翻译的语言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认识翻译活动对语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问题。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活动,又与写作活动不同,两种语言的交锋很容易创生“第三种语言”,进入译者母语后,能够从句法、词汇等方面丰富并拓展后者。梁启超曾讨论过佛经翻译文学对汉语的直接影响,据他介绍,当时日本人编了一部《佛教大辞典》,其中收录“三万五千余语”,暂不论这“三万五千余语”是否完全进入汉语系统,可以肯定的是,创造新词的过程是汉语逐渐丰富的过程。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新词汇也意味着新观念,语言上的变化也会对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造成影响,如是观之,我们就会明白为何“五四”运动前后,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了翻译作品,而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又为何会如此热衷于翻译了。
关于翻译的创造性,学界关注不够。翻译本身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只有凭借译者的创造才能实现。而且当我们讨论翻译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价值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翻译在这些层面所表现出的创造力。而当“本我”意欲打破封闭的自我世界,向“他者”开放,寻求交流,拓展思想疆界时,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与此同时,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作用。
在当今的时代,我特别关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翻译应该承担的使命。在我看来,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给翻译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赋予了翻译更为重要的使命。2002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曾访问南京大学。当他得知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翻译实践与研究后,充分肯定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还为我正在撰写的《翻译论》题写了一句话:“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我认为这句话很好地定义了翻译在全球化时代的使命。全球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加利访问南京大学时,曾发表了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世界化进程会对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危及文化多样性。他的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某些国家以强大的经济势力为基础,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在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谋求强势文化的地位,甚至表现出十足的“文化霸权主义”。面对这种现状,不难理解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文化多样性”的维护,而翻译因其本质属性,能够而且必须在维护“文化多样性”过程中承担重要使命。
那么,翻译要怎么做,才能承担起维护文化多样性、加强世界和平建设的使命呢?通过研究,我认识到,我们应该从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去认识翻译。有几点特别重要:一是在理解翻译的本质时,要坚持将翻译视作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作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转渡人”,译者对“文化多样性”及其重要性的体认应该更为深刻,也因此承担了更为重大的责任。只有正确认识翻译,充分看到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译者才有可能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对文化因素更为敏感,对保存和传达文化因素更为谨慎。二是在翻译中,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善待各种不同的语言。加利在南京大学所作的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演讲中就曾指出,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多元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条件,而世界的民主与和平有赖于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因为在他看来,“一门语言,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思维方式。说到底,它表达了一种世界观。如果我们听凭语言单一化,那将导致一种新型的特权群体,即‘话语’的特权群体的出现!”。翻译如要为维护翻译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语言多样性做出贡献,就要坚持开放与交流的文化心态。三是要发扬翻译精神,勇敢承担历史赋予翻译的使命。南京大学的程章灿教授在读了我的《翻译论》后,曾写过一篇富有真知灼见的读后感。在文章里,他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翻译的时代,而翻译的时代不可缺少的是翻译精神。他从我对翻译本质的定义出发,将翻译精神总结为“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五个方面。实际上,我们所提倡的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在翻译中努力再现语言、文化差异,都是这翻译精神的体现。发扬这一翻译精神,实际上便是在准确定位翻译的同时,勇敢承担起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历史等种种层面的使命,而加利所说的“发展文化多样性,加强世界和平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自然也被包括在了里面。
在对翻译进行思考与研究的同时,30多年来,我和翻译教学与研究界的同行一起,一直致力于翻译学科的建设。在这方面,我们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30周年之际,我为《中国翻译》撰写了一篇长文,题目为《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过去常有人说“翻译无理论”,现在翻译理论实实在在地存在了,不少人又说“理论无用”,这种对翻译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危害不小,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形而上思考、对翻译过程的多层面研究以及对翻译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我本人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是有明确的理论追求的,而且我认为这非常重要。理论意识在译者选择原作、研究原作、确定翻译策略、解决具体问题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而翻译活动的经验总结、理论升华更能对今后自己和他人的翻译实践有所启迪和助益,避免实践的盲目性。本论丛所收入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等著作,就是在这一方面探索的结晶。
事实上,从最朴素的翻译思考到今天多视角、多方法的科学理论,翻译研究在不断加深人们对翻译本身的理解,深化了人们对翻译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如果没有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翻译活动可能还囿于经验主义的层面。如果没有翻译的文化研究,我们可能还无法对制约翻译产生与接受的机制具有如此全面自觉的意识。而对翻译理解的深化也促使人们从社会交流、文化传承、语言沟通、创造精神和历史发展等多元角度来看待翻译的价值,对翻译的重要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有利于在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方面进一步凸显翻译的重要性。回顾我的翻译探索之路,可以看到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对翻译的理论思考也不断深入,《翻译论》《翻译学概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傅雷翻译研究》等著述,集中地展现了我和翻译界的同仁在翻译理论、文学译介与翻译家研究等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
翻译研究为我们理解和探索人类交流的历史开辟了一条新路。翻译是人类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作为一个翻译学者,我清醒地认识到,翻译历史悠久,形态丰富,翻译的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与探索。鉴于此,这一论丛是开放性的,我会加倍地努力,不断给读者奉献有关翻译研究的新成果。
许钧
2020年10月22日
于南京黄埔花园
【后记】
三版补记
译林出版社近期要推出《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第三版,韩继坤编辑来电嘱我写几句话。我眼前浮现出一张张和蔼的脸庞,赵瑞蕻、许渊冲、郝运、罗新璋、郭宏安,仿佛他们都还在,以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我。我到书架上取下了他们赠给我的书。有中国第一个翻译《红与黑》的翻译家赵瑞蕻赠给我的《诗歌与浪漫主义》,他在扉页上的赠言源自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落款时间是1994 年1月19日。在那个时间前后,我常去赵先生家,和赵先生、杨苡先生一起谈文学,谈翻译,谈的最多的是《红与黑》的翻译。许渊冲先生对翻译有独特的追求,敢于探索,勇于超越,他在1994年春赠给我的《红与黑》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诗:“试看明日之译坛,竟是谁家之天下!”同年10月,罗新璋也给我赠送了他翻译的《红与黑》,赠言中“许钧学兄指正”这几个字,深刻地展现了老一辈翻译家的广阔胸怀。郭宏安先生送给我的《红与黑》上,有他的签名,时间是1994年1月。他除了在书上给我题了赠言,书中还夹了一封短笺,嘱我:“你若有空,可翻翻看看,来信谈谈你的印象,我总觉得没有什么把握。”我记住了他的嘱咐,不仅学习了郭先生的译文,还认真拜读了许先生、罗先生等多位翻译家的译文。应该说,老一辈翻译家的翻译和对翻译的探索,成就了这部具有对话与争鸣精神的《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翻阅这部书,我心中不时涌起对他们的深刻怀念和崇敬之情。他们一个个离开了,但他们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在我的心中,他们永在!
- 译林出版社旗舰店
- 本店铺为译林出版社自营店铺,正品保障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