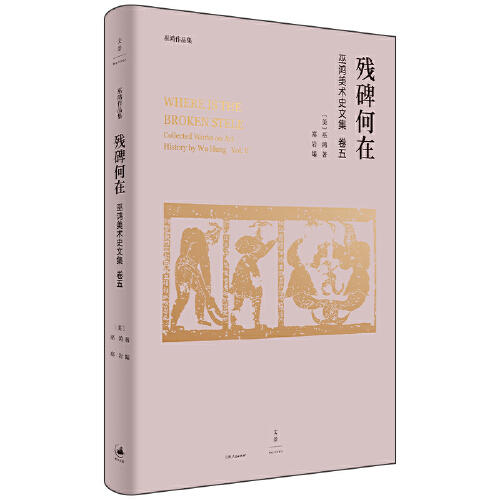商品详情
定价:139.0
ISBN:9787208161405
作者:[美]巫鸿
版次:1
出版时间:2021-05
内容提要:
“巫鸿美术史文集”是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成果的全面集成,编年汇集了巫鸿几乎所有古代中国美术史的论文和未发表讲稿,串联四十年学术历程中散落的明珠,透视学者思维发展成熟的脉络。本卷收录巫先生2005—2011年的14篇论文与讲稿,从时间性、空间性和物质性等多个角度探讨古代视觉文化中“复古”“废墟”观念的体现、中国古代墓葬艺术对主体的表现、“生器”与“明器”的理论和实践等,旁征博引,引人入胜,兼具学术思辨和可读性。
作者简介:
巫鸿(Wu Hung),著名美术史家、批评家、策展人,芝加哥大学教授。
196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72—1978年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1978年重返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随即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同年受聘主持芝加哥大学亚洲艺术教学,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2年建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该校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2008年被遴选为美国国家文理学院终身院士,并获美国大学艺术学会美术史教学特殊贡献奖,2016年获选为英国牛津大学斯雷特讲座教授,2018年获选为美国大学艺术学会杰出学者,2019年获选为美国国家美术馆梅隆讲座学者,并获得哈佛大学荣誉艺术博士。成为大陆赴美学者获得这些荣誉的人。
媒体评论:
◆ 专业评论
他的著作打破了按照材质分类,按照西方概念讲述中国故事的传统,从基本结构上改变了西方中国美术史传统写作的范式,正在构成一种具有历史关怀的、生动新鲜的叙事。不仅如此,以他为代表的这一代学者甚至在对世界范围内整个美术史学科的走向产生重要的作用。
——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巫鸿教授有关中国美术的相关研究,跨越上古与中古时期的墓葬美术、宗教美术与传世书画艺术,兼及史前时代的玉器文化与当代实验艺术,其开拓领域之广、研究力度之深,可谓前所未见。他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了当代人类学的思维与视角,创造性地将绘画、雕塑、器物与建筑有机整合为一体,从而发展出一套适用于美术史学科的、能够打通微观研究和宏观叙事的“中层研究”方法论体系,使图像、器物与建筑空间的研究能够与人和时代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相联通。
——李清泉(广州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所教授、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
巫鸿并未把艺术品作为多样而变化中的世界观的图解。相反,艺术品在他手里成为了历史中的演员和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历史的标志物。
——伊万兰?卜阿(Yve-Alain Bois,哈佛大学美术史与建筑史系前系主任,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巫鸿希望的,是通过分析美术材料本身找到一条可以跟随的线路,寻找视觉材料内在的演变路径。换句话说,也就是把美术演变的轨迹从这些概念中剥离出来,在美术中说明一个精神性的“中国”。
——胡一峰(《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
——朱志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巫鸿先生在解读中国画史名迹时不仅注意重新审视传统的读画方式和内容实质,还充分注意到绘画媒介形式的物质性特征,将绘画置于一种由创作者、观赏者共同参与动态过程,从而丰富和提升了鉴赏这幅名画的内涵和意义。
——赫俊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 媒体评论
巫鸿认为作为处理历史材料的研究者,*终能够改变西方中心格局、建立全球性美术史的途径并不是以抽象思维的方式推演出一套理论话语,而是通过对于历史的具体的作品,通过考古材料,通过历史上的书写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提炼出多元性的美术史的概念和叙事方式。
——雅昌艺术网
巫鸿是一个有着特定的视角和兴趣,并将这种视角和兴趣沿用到极为多元的研究对象之中的学者。
——《燃点》
在如今更趋多样化的美国学界,芝加哥大学的巫鸿教授可谓是*活跃的一个中国艺术学者。他的研究领域跨越了古代与现当代的壁垒,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贯穿始终并互为借鉴。
——《艺术新闻(中文版)》
目录:
58.玉骨冰心——中国艺术中的仙山概念和形象
59.说“俑”——一种视觉文化传统的开端
60.动物、祖先和人:再思早期中国艺术中的意义
61.明器的理论和实践——战国时期礼仪美术中的观念化倾向
62.镜与枕:主体与客体之间
63.东亚墓葬艺术反思——一个有关方法论的提案
64.墓中的“活者”:中国古代墓葬艺术中对主体的表现
65.“生器”的概念与实践
66.中国艺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复古”模式
67.石涛和中国古代的“废墟”观念
68.1644:残碑何在?
69.引魂灵璧
70.北齐艺术之再思
71.关于“不可移动文物”
本卷所收论文出处
◆序言/前言
总序 阅读巫鸿
郑 岩
2016年6月,作为“OCAT 年度讲座项目”,巫鸿教授在北京做了三次讲座。佳作书局(Paragon Book Gallery)借机在会场举办了题为“从武梁祠出发——巫鸿著作展”的书展。展览收集了巫先生中英文专著数十本,纷然胪列,整整铺满了七张桌子,但实际上仍有遗漏。巫先生的著述总量大,涵盖范围广,从史前一直延续到中国当代实验艺术。这套文集只是较为全面地汇集了他已有的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的论文和讲话稿,并不包括近代至当代的部分。这样选择,所设定的主要读者是兴趣集中于古代美术的朋友们。
与以往按照主题所编的几个集子不同,这套文集大致是按照文稿写作或发表的先后次序编排的,类似于编年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一种“个人的学术史”。由于作者往往长期关注同一批材料或同一个问题的研究,故有些讨论前后或有所重叠和交叉,有的文章后来发展为专书或专书中的章节。文集中删除了重复较多的篇目,重复较少的则予以保留,以便读者从中看到作者思维发展的脉络。这些文章的原稿一小部分为中文,更多的是英文写作。自十多年前开始,许多学者参与了翻译工作,的一些则多是包括我的几位研究生在内的一些年轻朋友的译笔。巫先生亲自校读了绝大部分译文。特此向各位译者及巫先生表示
感谢!
巫鸿先生关于古代美术研究的专著大多已有中文单行本,不包括在这套文集中。为便于与这些文章对照阅读,我将书名列举如下:
1.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2.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3. The Double Screen: Medium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Paint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文丹译,黄小峰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4.《美术史十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5. The Art of the Yellow Spring : Rethinking East Asian Tomb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施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6. A Story of Ruins: Presence and Absence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肖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出版者命我为这套文集写一点文字。借此机会,我谈一下对巫先生著述的“阅读史”和体会。毫无疑问,这些看法只是我个人有限的理解。
次读到巫先生的文章时,我还在读大学。大约在1986年前后,先师刘敦愿先生命我研读《一组早期的玉石雕刻》一文。刘先生曾报道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龙山文化兽面纹玉锛(或称为圭),而巫先生文中所举许多海内外博物馆收藏玉器上的纹样与两城镇玉锛所见风格相近,前者可根据后者重新断代。我在对这篇文章充满兴趣的同时,也很惊异作者如何收集到如此宏富的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材料。其实,巫先生写这篇文章时,还只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在读的硕士生。
第二次读到的巫先生的文字,是《武梁祠》的英文版。1994年,纽约大学博士候选人唐琪(Lydia Thompson)女士到山东收集资料,将这本书赠我。夏天,我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文祺老师参加沂南北寨汉墓的第二次发掘。炎热的白天,在工地挖土;太阳落山后,去村西大汶河洗澡;晚饭后,躲在营地的蚊帐中读《武梁祠》。这样的一个多月,我整个身心沉浸在汉代山东乡村的土中水中文字中,在沂南北寨,也在嘉祥武宅山。
1996年10月,在汪悦进的帮助下,我到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那时候,悦进兄刚在芝大开始他的份教职,极为忙碌。他从机场直接把我接到学校,告诉我巫先生正在给学生上课,然后就急着忙他的事情去了。我没有来得及洗一把脸,就从后门悄悄溜进巫先生的课堂坐下。巫先生注意到我,抬手说了声“Hi”,然后继续他的讲授。课后,巫先生把我迎进办公室。他身材魁伟,声音浑厚,气度不凡。悦进兄是巫先生的弟子,二人年龄相差十多岁,悦进兄按照美国习惯径称他“巫鸿”。我想了想,还是称他“巫先生”。这是中国人对于年长学者的尊称。后来他更年轻的学生们都称他“巫老师”,我不在谱籍,故而继续称他“巫先生”。现在想来,他那时只是我现在这个年纪,算不上老先生。但是,他已经出版了《武梁祠》和《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重屏》也已在印制中。我难以想象,一位在“文革”中消耗了大部分青春,又半道才用英文写作的学者,是以多大的心力做出这些成绩的。
我对巫先生早年的经历并没有直接的了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他的两篇文章,即《张光直师、哈佛与我》(载三联书店编,《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和《“不期而遇”—对书的记忆与记忆中的读书》(载《读书》,2012年,第9期),还可以参考《新京报》的采访稿《从故宫出发,走向哈佛》。这几篇文章都可以在网络上检索到全文。此外,《再造北京》(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Political Spa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一书,既写了北京城的历史变革,也道出了作者本人与这座城市的关联。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有大志向的年轻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磨难与坚持。
在芝大的五个多月,我一边听巫先生的课,一边尽可能地找来他已发表的全部文字进行研读,收获颇丰。重读《武梁祠》,我时时联想到1984年我考取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所听的堂课,即张光直教授的讲座《聚落形态》(讲稿见《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巫先生是张光直在中国大陆招收的个学生,《武梁祠》便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张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倡言聚落形态理论,这种源自中美洲考古的理论强调对古代遗址的整体揭露,注重相关遗址彼此空间和功能的联系,从讨论考古学文化谱系,发展到研究文化区域空间内人类社会的变化。巫先生整体解读武梁祠的方法虽然不能简单地说直接来源于聚落形态理论本身,但显然与这类理论相一致。此外,从中也不难看到当时在西方仍然盛行的结构主义以及新艺术史潮流的影响。
更进一步看,我认为还应该结合两个背景来理解《武梁祠》以及在此前后巫先生关于汉代艺术的一系列文章。个背景是当时西方对于早期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在20世纪上半叶,关于汉代的研究已有沙畹(Edouard Chavannes)、喜龙仁(Osvald Siren)、费歇尔(Otto Fisher)、巴赫霍夫(Ludwig Bachhofer)、费慰梅(Wilma Fairbank)等人的重要贡献,但总体上说,由于材料本身的局限,汉代艺术难以与青铜器、敦煌和卷轴画的研究相提并论。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田野调查中断,这方面的研究已大大萎缩。而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将汉代画像砖石、壁画看作绘画史的史料,或者说,是看作狭义的中国绘画史的“史前史”来写作,以讲述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故事。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包华石(Martin Powers)、巫鸿等新一代学者,开始强调这些材料特有的属性,并从汉代各种社会因素出发观照美术现象和美术作品,从而开启了汉代艺术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另一个背景是巫先生个人的学术经历。由于有在故宫业务部工作的经历,他早年的几篇文章涉及玉器、青铜器、度量衡器等研究,显示出对古代器物强烈的兴趣。他对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器物的形式分析虽然还比较简单,但已由博物馆藏品研究发展到对于考古材料的关注。从汉代画像艺术的研究开始,他更关心考古材料的整体解读。有些读者对他在《武梁祠》中所使用的“原境”(context)、“图像程序”(pictorial program)等概念充满兴趣。而这些概念所反映出的整体性,也正是田野考古材料与来源复杂的博物馆藏品之间根本的差别。如此一来,美术史的阐释就有可能与考古学材料及考古学研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对于他的研究抱有极大兴趣的原因之一。但在我个人看来,巫先生在《武梁祠》中的意图除了积累这类技术性的研究手段外,还在于以这些手段为中介,拓展艺术作品历史性和思想性的深度。在这里,美术史研究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写作,而不再是一种学科史。这在他本人的学术经历中无疑是一个大的突破。
巫先生在哈佛毕业前后的一段时间有着令人惊异的“爆发力”。《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2—3世纪)》一文,对有关母题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细密分析,成为后来学者们研究这个课题***的一篇文章;他对于四川汉代石棺空间结构与题材关系的分析,可以看作《武梁祠》的预演;《汉代艺术中的“白猿传”画像》表现出他对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兴趣。此后不久,我们便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基础上的迅速深化和扩展。在对马王堆汉墓的解读中,“原境”已不仅意味着一种物质性的结构关系,还包括丧葬礼仪以及观念的语境,而“礼仪中的美术”(art in ritual context)这个概念也从中产生;《何为变相?》这篇长文则将上述概念结合起来,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敦煌。
1997年,我与王睿君计划编辑一部巫先生的论文集,汇集到约30篇文章,其中还不包括他关于卷轴画和当代艺术研究的成果。在多位朋友的齐心努力下,这些论文被译为中文,2005年以《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为题出版,受到国内读者热情的欢迎。除了上述领域,这部书中所收的文章还涉及城市、建筑、早期道教、地域美术等诸多方面。
中国美术史的传统研究历史地形成了若干门类,或按照作品形式划分为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或按照物质形态划分为卷轴画、青铜、陶瓷、石刻等,或按照文化属性划分为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民间艺术等。特别是按照材质的分类方式,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构成了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历史的、异国情调式的想象。巫先生的研究不局限于这些传统的分类方式,《礼仪中的美术》中所收录的文章,显示出他力求突破既有的研究范畴,在方法和理论上寻求创新,其目的不在于再造一种与西方传统历史写作形式相类似的单线的历史,而在于多角度地展现中国艺术的丰富、复杂与变化。
其中《“图”“画”天地》与《五岳的冲突》两文尤值得注意,前者将“图”(即各种抽象的符号与图形)纳入美术史研究的范畴,后者则观照由自然地理到文化景观的概念转换与实践。这类文章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具体的解释,而在于体现出作者对于进一步拓展中国美术史研究视野的努力。在这一点上,2009年出版的《时空中的美术》一书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作为《礼仪中的美术》的续集,该书所汇集的文章写作时间大部分晚于前一个集子,主要是2000年前后的成果,其研究对象扩展到卷轴画和较为晚近的艺术形式。如巫先生自己所言,这些文章“以概念和方法为主导,所关注的是这些概念和方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阐释历史现象、披露历史逻辑中的潜力”(见该书“自序”)。这些文章的关键词包括“复古”“废墟”“计时”“物质性”“幻视”“性别空间”“媒材”“超级绘画”等。这些变动不居的词汇,有的来源于对中国文化本身特性的思考,有的则产生于与西方美术史研究的互动,皆表现出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
巫先生对于中国美术史的整体思考并不停留在一般性的主张上,而是通过大量实验性的案例分析来完成。我不建议读者直奔其结论而去,因为在这些研究中,材料、概念、问题、方法、理论和分析过程,构成一种十分丰富复杂而有机的关联,比某一具体的结论更富有启发性。
我出身于考古学专业,熟悉那些基于大数据分析来宏观地探究古代遗存时空关系、文化因素的类型学研究(这些研究当然十分重要),读到巫先生诸多个案研究的成果,的确耳目一新。受其影响,近十年来,对于考古材料的个案研究在国内蔚成风气。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个案研究只是巫先生的写作方式之一,他非但不排斥对于中国美术史的宏观考察,而且总是试图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思考重新建立中国美术史新结构的可能性。新的结构不仅包括材料的扩展,也包括概念、分类、分析方法等理论问题的重新梳理。作为一种“长时段”的探索,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正是建立在大量个案研究之上。书中涉及从史前到南北朝各个时期的器物、宫殿、陵墓、城市等复杂的材料,是否可以用“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这一概念贯穿始终,也许还可以讨论,但应该注意的是,这本书的确打破了美术作品材质和形态的界限,致力于寻找各种材料之间文化上的联系,使作品还原为历史中活生生的角色,而不是博物馆中静态的藏品,这一取向显然更值得提倡。
这套文集并没有收录巫先生对于当代中国美术的研究成果,但阅读他关于古代的著述,难以完全绕开他对当代的研究。1997 年,巫先生在芝加哥大学斯马特美术馆(Smart Museum of Art)筹备了个中国实验艺术(“实验艺术”这个概念本身,似乎也是他本人的发明)展览。我在回国之前,看到了他为这个展览编写的图录《瞬间:20 世纪末的中国实验艺术》(Transience: Chinese Experimental Art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的样书。此后,巫先生作为策展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举办了大量实验艺术的展览。近年来,他在当代艺术方面的著述甚至多于古代部分。我对这个领域完全外行,也曾对于一位史学家转而关心当今艺术的发展而多少感到有些困惑。大约十年前,我就此问题求教于巫先生。我记得他说了两个理由。,历史如果不被及时记录下来,可能就不存在了。也许是这个原因,他在2008年出版的一部论当代中国艺术的论文集,即题为Making History(《创造历史》)。这个题目的主体是那些艺术家,但在我看来,也可以包括其记录者。他所说的第二个原因更令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传统上多是一种古老的、静止的文化,他希望通过对于当代中国艺术的研究,致力于改变西方的这种印象。姑且不论是否可以将正在发生的事情看作历史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巫先生近年来的多项研究,的确是将古代和当代贯通起来的。如《再造北京》和《废墟的故事》两部书,都是从一个侧面切入的长时段写作。在这些文字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位深沉的批评家对于当代艺术历史根基的发掘,又可以看到一位敏感的史学家如何从生动的艺术实践中寻求灵感,反过来丰富和发展探索古代艺术的问题与角度。
巫先生对于不同课题的研究往往彼此交叉进行,写作方式十分多样。例如,他当年在哈佛就职的学术演讲便谈到屏风在中国绘画史中的意义;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杀青不久,他就完成了《重屏》这部讨论中国绘画的著作;几乎与此同时,他又开始筹划实验艺术的展览。在这种高效的、齐头并进的方式中,各个看似迥然不同的课题彼此激发,波澜壮阔。另一方面,从这套文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研究成果无不是他青灯黄卷、积年累月思考的结果,并没有倚马可待、七步而成的急就章。
20世纪90年代巫先生所参与的部分集体写作项目也值得一提。例如,与中美多位学者合作的《中国绘画三千年》(北京:外文出版社、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年,英文版见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一书的编写。(他也参与了这套丛书的另一部《中国古代雕塑》的写作,该书中文版由外文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英文版见Chinese Sculp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巫先生在这个项目中承担从史前到唐代部分的写作。由于材料的局限,在多数中国绘画史著作中,这段为漫长的历史也是为简略的部分。而在这部书中,巫先生大量引入20 世纪初以来美术考古的重要发现,以美术史家特有的笔法,构建起早期绘画史丰富而新颖的脉络。(我们将这两部书中巫先生所撰写的部分合为这套书的“别卷”,这些深入浅出的论述或可作为中国早期美术史初学者的读物。)
另一个项目是他所参与的《剑桥中国上古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比起其他各卷来,本应作为卷出版的上古卷,却比其他各卷的出版要晚得多,原因之一就是大量全新的考古材料需要史学家们消化和处理。巫先生在此卷中承担《战国时期的艺术与建筑》一章的写作。我们当然不难注意到其中他从历时性的角度入手,对于诸侯国双城制模式的质疑,但更重要的是,城市由此进入了中国美术史的框架之中。除了巫鸿先生,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罗伯特?贝格利(Robert Bagley)三位教授也参与了这部书的编写,他们皆是青铜器研究的专家,因此也都可以看作美术史家。如果说我们能从《中国绘画三千年》一书观察到考古材料对于绘画史研究的贡献的话,那么,从后一本书则可以看到这一代的美术史学者已经参与到中国历史的整体写作之中。
也许这类工作在巫先生个人的学术历程中并不那么重要,特别是《中国绘画三千年》,结构仍显得较为传统;我之所以强调其意义,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项目,将巫先生个人的成就进一步放在时代背景下来观察。学界十分推崇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印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英文版见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Fourth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一书。但有位国内的前辈曾言,如果没有考古研究所20世纪60年代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 年),张先生的这部书恐怕也难以写成。此言诚不虚!可以说,张先生是以其特有的身份、学养将中国考古学的材料放置在国际视野中观察的一位划时代的学者,而其基础则是20 世纪中国田野考古材料的积累。巫鸿先生对于美术史的研究,同样建立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比起张光直来说,巫先生所代表的一代学者更为幸运,他们在青壮年时期赶上了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开放,兼有中国和西方两方面的学术训练,可以随时往来于中西学界,及时获得鲜的考古材料,也有机会零距离地接触中国当代的艺术实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优势下,巫先生不失时机地做出了他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特有的贡献。这种贡献不在于以新材料来补充和完善旧有的框架,而在于努力建立一种全新的研究模式。一句话:这个时代需要这样一位美术史家,而他出现了。
巫先生是一位极为勤勉的学者,同时又有着多方面的行动力。除了作为一位策展人活跃在当今国际艺术领域,他还花费了大量心力推动中国与国际美术史界的交流。由巫先生发起的多种学术会议和合作研究项目,以其开放、朴素的形式,得到许多学科和不同年龄段学者的积极支持与响应。他还在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举办系列讲座,吸引了大批青年学者与学生关心和参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
......
在线试读:
1644:残碑何在?(节选)
1644年一般被认为是明朝灭亡的年份,但是有历史学家提出,这一年只是整个灭亡进程的开始。明朝的灭亡旷日持久,随后由北方满洲人建立的清政权耗费数年才巩固了其对广阔帝国的控制。这一论述是正确的,但它并不能削弱1644年非同寻常的政治意涵以及对国人的心理冲击。对那些仍然效忠于明朝的人来说,该年首都的陷落和崇祯皇帝的自杀永远意味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痛楚、暴力和灾难。这些效忠明代的人将自己称为前朝遗民(remnant subjects),他们把满洲人的征服看作文化、传统及自己种族的危机。
被迫改变服饰和发型的经历尤为惨痛,被看成向野蛮的倒退。的确,对很多汉人来说,1644年不仅仅代表着明朝的灭亡,他们自己的生命也在那一刻骤然中断,之后的时间仅仅是苟存于世。方以智拒绝为新政权效力,出家为僧,在一篇自祭文中自问自答道:“汝以今日乃死耶?甲申(1644年)死矣!”这种自我殉道的表现是一种象征的姿态与行为。其他明朝遗民如朱耷以失语和佯作疯癫的方式演出了死亡,而归庄和巢鸣盛则将自己囚禁在墓园中,与活死人无异。这种象征性的死亡或“缓死”(delayed dying)的一个作用是保存对前朝的记忆。很多明朝遗民心知肚明:他们在1644年之后成了孤儿。在表达这种遗民心态的诸多方式中,“访碑”的行动尤为意义深远,因为碑作为一个象征物将历史、传统以及死亡结为一体。
自从创造之初,石碑或碑就一直是中国文化中表达纪念的一个主要载体。如果为个人而立,碑上的铭文往往他人在是其死后撰写的简要生平,特别关注重要人物对江山社稷的贡献。竖立在寺庙或祭坛门前的石碑记载了该建筑的历史渊源。因此,石碑赋予了某个地点建构历史与记忆并将其昭示天下的合法性。当人们回望过去,石碑很自然地从其他的建筑形式中突显出来,去回应人们反观的目光(retrospective gaze)。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遗民在17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如此频繁地去查访古代的石碑,以及为什么“残碑”(broken steles)在遗民的写作中成了一个意义非凡的修辞手段。
白谦慎曾在其著作中就这一主题进行过讨论。在他所举的例子中,明遗民的领袖人物顾炎武曾数次拜谒明代皇帝位于南京和北京的陵墓,并瞻仰“巍然当御路”的“穹碑”(《孝陵图》)。顾炎武还查访了山西汾阳的一座古碑。他在此次旅途中创作的一首诗如此结尾:“相与读残碑,含愁吊今古。”(《与胡处士庭访北齐碑》)另一位著名的明遗民傅山甚至梦到过刻有“模糊字迹”的古代石碑。正如白谦慎注意到的,上述这些和其他相似的诗文创作,刻意地回应了13世纪历史中的一幕:在蒙古军队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三年之后,诗人张炎(1248—1320年)游览了城内著名的西湖。面对着一通废弃的石碑,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故园已是愁如许,抚残碑、却又伤今。”(《高阳台》)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想提出此讲标题中提出的问题:残碑何在?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据我所知,尽管石碑的形象确实出现在明朝遗民的画作中,但是没有一个是“残碑”的形象。这些画作中的一幅由来自南京的遗民画家张风(卒于1662年)所作。他曾经在清人入主中原之后游历北方,瞻仰明朝皇家陵墓。张风的这幅扇面画创作于1659年,画中一个身着明代服饰的士人站在一通巨大的石碑前。考虑到画家的政治倾向,这幅画可能具有自传的意味。石碑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和周遭荒凉环境之间的对比被绘画上方的题词进一步强调:“寒烟衰草,古木遥岑,丰碑特立,四无行迹,观此使人有古今之感。”如果说石碑的巨大尺寸暗示着来自往昔的一个厚重宏大之物,但它却毫无磨损或毁坏的迹象。而且,尽管画中人似乎是在专注地阅读碑文,但是我们看到的石碑表面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字迹。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石碑在内容和时间上都是“空”的。
张风这幅小小的扇面画是一件私人性的绘画小品,而吴历(1632—1718年)的《云白山青》则是一幅充满压抑情感的恢宏严肃之作。吴历被认为是清初绘画大家。他年轻时曾追随著名遗民学者研习文学、哲学与音乐,后自己也逐渐成长为一名忠诚的明朝遗民。在一首诗中,他将自己比作已故主人一匹忠诚的“病马”。大幅长卷《云白山青》创作于1668年,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幅画与张风的扇面画表达了同样的悲情与无助之感,但较前者多了反讽的意味。有的研究者曾提出画中使用的“青绿”(green-blue)风格可以追溯至道家的仙岛或陶渊明的“桃花源”(Peach Blossom Spring)。与“桃花源”的关联明确地体现在此画的构图中:展开长卷,我们看到一片茂盛的花木半掩着一个敞开的山洞。类似的桃花源图像在明清绘画中频频出现。《桃花源记》讲述了一个渔民进入一个隐藏在桃花丛中的山洞,进而到达一个太平世界的净土。村民们告诉渔民,他们的先祖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因避难来到这片与世隔绝之地,自此与外界不相往来。在吴历生活的时代很久之前,这个故事就成为中国知名的乌托邦寓言。
“桃花源”在明末清初成了画家为喜爱的主题,吴历曾就这一主题创作了数幅作品。美术史家林小平认为,这些关于“桃花源”的绘画“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图像存在(pictorial presence),昭示了明朝遗民对他们梦想中的遥不可及之土的幻想”。但是在1688年的《云白山青》中,原先的这个寓言故事转变成一个噩梦。刚才已经提到,这幅画的前半部分似乎遵循了传统的“桃花源”图像程式,山洞将把观众引领到藏在大山彼侧的乌托邦之地。然而当这幅画卷继续展开,绘画的后半部分使观众感到震惊。这部分画面中没有快乐的农民或神仙,只有一座纯白的石头制成的纪念碑,静静地矗立在一棵老树下面。这里既没有春天也没有花朵,只有光秃秃的树木。数以百计的乌鸦盘旋在一片寒林之上,遮云蔽日。吴历在卷尾题诗的句中如此描述这一令人恐怖的景象:“雨歇遥天海气腥。”
联想到当时的政治语境,画中的石碑毫无疑问象征着覆灭的明朝。吴历以死亡的象征替换了“桃花源”的乌托邦梦境,以此宣告了他痛苦的觉醒——时到此时,复辟前朝的一切希望都已经幻灭。《云白山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任何人物出现在石碑前,因此似乎与张风的作品有所区别。然而我的看法是,在这幅画中,游人的形象被画作手卷形式体现出的凝视(gaze)所置换。当观者逐渐展开长卷,从茂盛的树木和山洞到萧索风景的移动图像造成一种强烈的运动感,推动着我们去与石碑“相会”。观看此幅长卷的高潮出现在观者目光与石碑相会之时,但是这通石碑并没有直白展现自身的意义。与张风的石碑一样,它没有标识出时间的流逝,它那白色的碑面上也没有任何符号或铭文。它被枯树与群鸦包围,在一个充满了煎熬与折磨的氛围中标识出一个空洞的中心。
为什么这些画家没有像遗民作家在文学作品中那样,描绘出残碑的形象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张风与吴历在创作中遵循了一个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图像传统。但是这个解释没有真正回答问题,而是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广泛,它让我们进一步去想:为什么沉默的“无字碑”会成为如此流行的绘画主题?通过爬梳历史文献,我们发现拜谒石碑是中国绘画中一个非常古老的主题。举例来说,12世纪的《宣和画谱》记录了数幅这个主题的作品,并将其起源追溯至公元6—10世纪。虽然这些作品大都佚失了,但是有一幅类似的仍可以在大阪市市立美术馆中看到。这幅画尺寸巨大——高达1.25米,宽1米——其中几个图像交织成紧密的一群,一座硕大的石碑立在画面中心附近,被秃木与岩石环绕。一个骑驴的游客停驻在石碑前,沉默地观察着荒野中这壮观的纪念物。他身旁的侍童一边拉着缰绳,一边专心地看着主人。在这一片天寒地冻的风景中,没有任何移动之物,静止的人物沉浸在一片静默之中。但与此同时,这幅画又显得如此不平静,如此生气勃勃。画面中的枯树、波浪石乃至水墨的浓淡变化都赋予这幅画一种内在的生命力。
这幅画旧题为公元10世纪的画家李成(919—967 年)所作,但不少中国绘画史家认为它实际作于13世纪到14世纪之间的元代。关于它的主题众说纷纭,有几位学者将画中的石碑看作某个特定的历史古迹,把游人看成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但细细品读这幅画,我们有理由怀疑它是否真的是要展现某个具体时间或人物。画家似乎恰恰是怀着一种相反的冲动,去表现一块“无名的”石碑。碑文的缺席一定是有意为之的,因为画面中螭首和龟趺的装饰细节都是精心描绘的。这幅画应该意在表现一种笼统的情境:游人感到自己与一个不具名的“过往”不期而遇。石碑的匿名性进一步被其一般性状态所强化。尽管这幅画的每一个解读者都把这块石碑当作一处古代遗迹,但细致观察可知它并不是一处通常意义上的遗迹。在实地考察过这幅作品之后,我发现石碑的形象并没有显露出一丝的磨损或毁坏,画家以技法精巧的流畅线条描绘了它的雕刻装饰。这个形象因此被抹去了任何特定的历史性,使观者有更加广阔的心理空间去重塑它的意义。
张风的扇面和大阪美术馆藏《读碑图》的相似性显而易见。当张采用这个传统图像程式的时候,他赋予了匿名的石碑以一种当时的遗民语境中的特定政治意涵。但是如“无字碑”形象的这样一个空的能指,如何唤起对前朝的记忆乃至对崇祯皇帝自尽的回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另一幅古画,即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李公麟的《孝经图》中的一幅。这幅画描绘了在传统庙堂中祭祀先祖的情形:家族的后裔们已经在祖先的灵牌(形似小型石碑)前摆好了祭品,正谦恭地等待神灵的降临。与张风或吴历画中的无字石碑相似,这些灵牌上面没有任何铭文。《礼记》——古代中国指导人们进行祖先祭祀的一部经典文献——中的一段话说明了灵牌上面空空如也的原因。根据这段话,我们得以知道灵牌的作用并不是显出祖宗的模样,而是标识方位——它的意义就在于指出祭拜对象的位置。在漫长的祭祀仪式中,祭拜者的责任是努力地在脑中忆起故人的形象。我将这段话引用如下:
齐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齐三日,乃见其所为齐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
(祭祀那天,进入放置灵位的庙室,仿佛看到了亲人的面容。祭祀以后,转身出门,心情肃穆得像是听到亲人说话的声音。出门之后,耳边好似听到亲人叹息的声音。)(《礼记·祭义》)
放在《礼记》描述的礼仪语境中理解,虽然这些空白的灵牌或石碑在视觉上表面空无一物,但它们能使观者集中精神去追忆先人,在这一点上比具体的祖先肖像更有力量。也许这就是张风和吴历没有像别的遗民画家——比如吴宏和樊圻——那样去描绘废墟的原因。吴宏在1664年创作了一幅扇面,画面中一个文人坐在一辆漏了顶的破茅屋中,他的另一幅长卷则描绘了一座衰败的墓园,这属于很少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出现的主题。姜斐德(Alfreda Murck)将这些意象与吴宏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解读,认为它们表现了一种遗民心态。吴宏和樊圻的作品说明废墟的图像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而石涛的两幅描绘黄山残塔和石门的图册则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这证明,张风和吴历绘画中的石碑形象——它们既没有毁灭的痕迹,也不显示时间的流逝——应该是画家本人的刻意选择。这种选择的基础是:对这些绘画的理想观者来说,视觉匮乏的图像能更有力地促使他们完成哀悼逝者的祭祀礼仪。对这样一个潜在观者(implied viewer)来说,空白的灵牌和石碑其实并不空洞,而是充满了记忆中的图像与声音。
- 佳作书局 (微信公众号认证)
- 佳作书局(PARAGON BOOK GALLERY)自1942年创办以来专注于中外艺术书籍的引介和出版。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