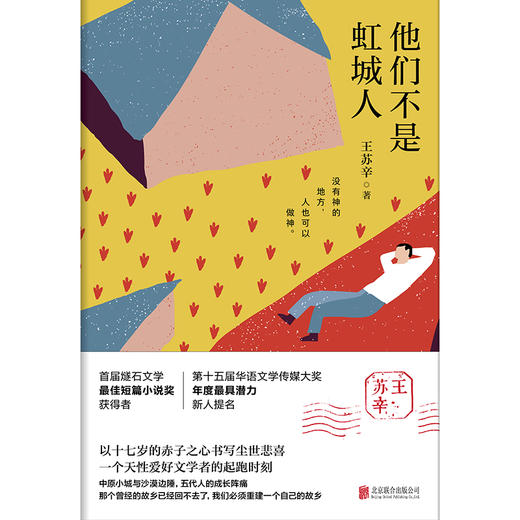商品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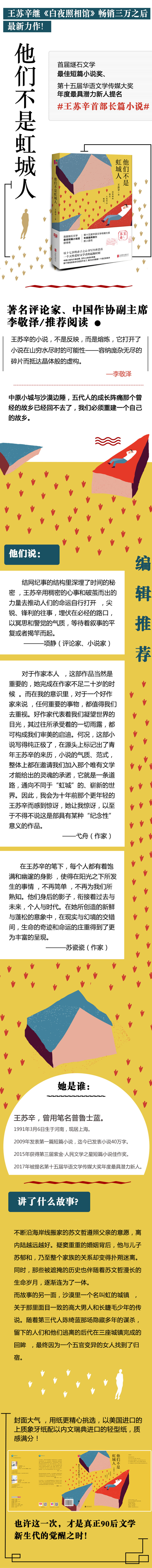
*王苏辛继《白夜照相馆》畅销三万之后全新力作!
*2018年度备受期待的新浪潮文学代表力作!
*王苏辛是韩寒ONE高赞作者《小说月报》《青年文学》等杂志常驻作家,备受年轻文学爱好者欢迎,必是粉丝力捧的实力之作!
*本书曾登上豆瓣、犀牛故事等app首页,阅读量累计两百万次。本书作者多次获得过国内重量级文学比赛奖项。在年轻90后作家当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同时在同龄的读者当中都有众多的粉丝基础。
*中原小城与沙漠边陲,五代人的成长阵痛 那个曾经的故乡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必须重建一个自己的故乡。
不断沿海岸线搬家的苏文哲遵照父亲的意愿,离内陆越远越好。疑窦重重的婚姻背后,他与儿子苏郁和,乃至整个家族的关系却变得扑朔迷离。同时,那些被遮掩的历史也伴随着苏文哲漫长的生命岁月,逐渐连为了一体。
而故事的另一面,沙漠里一个名叫虹的城镇,关于那里面目一致的高大男人和长睫毛少年的传说。随着第三代人陈绮蓝那场隐藏多年的谋杀,留下的人们和他们逃离的后代在三座城镇完成的回眸,*终因为一个五官变异的女人找到了归宿。
王苏辛,曾用笔名普鲁士蓝。
1991年3月6日生于河南,现居上海。
2009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小说40万字。
2015年获得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
2017年被提名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
第一章:逃亡的人奔跑在沙滩上
第二章:在所有观望的年月里
第三章:树上的灵魂
第四章:绿洲上的爱情
第五章:写给你的一生
附录:所有故事的开始
结网纪事的结构里深埋了时间的秘密,王苏辛用稠密的心事和破茧而出的力量去推动人们的命运自行打开,尖锐、锋利的往事,埋伏在必经的路口,以冥思和警觉的气质,等待着叙事的平复或者揭竿而起。 ———项静(评论家、小说家)
对于作家本人,这部作品当然是重要的,她完成在作家不足二十岁的时候。而在我的意识里,对于一个好作家来说,任何重要的事物,都值得我们去重视。好作家代表着我们凝望世界的目光,其过往所承受着的一切雨露,都可构成我们审美的启迪。何况,这部小说写得纯正极了,在源头上标记出了青年王苏辛的来历,小说的气质、范式,整体上都在邀请我们加入那个唯有文学才能给出的灵魂的承诺,它就是一条道路,通向不同于“虹城”的、崭新的世界。因此,我会为十年前那个更年轻的王苏辛而感到惊讶,她让我惊讶,以至于不得不说这是部具有某种“纪念性”意义的作品。 ——弋舟(作家)
在王苏辛的笔下,每个人都有着饱满和幽邃的身影,使得在阳光之下所发生的事情,不再简单,不再为我们所熟知。他们身后的影子,衔接着过去与未来,个人与时代。在她所创造的新鲜与蓬松的意象中,在现实与幻境的交错间,生命的奇迹和命运的庄重得到了更为丰富的呈现。 ———苏瓷瓷(作家)
第一章:逃亡的人奔跑在沙滩上
1
在苏郁和还是个很小的男孩时,他就学会了认同,这一切在苏文哲的意识里却是另外一回事。在他漫长的成长岁月里,苏文哲甚至从未真正听见他说过一声“不”字,但这却是他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一个儿子。他不理解的不是他需要什么,而是他明明知道不需要不喜欢却还是说了那句,行啊,爸。在很多小孩子都叫爸爸的时候他就学会了叫爸。不过,苏文哲从不表现出对这称呼的不满。或者说,在这场本来就漫长的对峙里,他在等待他说出那个不字。
他们一直都在搬家,沿着曲折的海岸线。苏郁和和哥哥苏义达从来都不知道真正的陆地是什么样子,尽管他们在那里出生,在那里迎来了母亲的离去,但那时候的他们还不足以拥有记忆,因此,即便是很久之后,他们像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选择了内陆,在那里安家,在那里拥有爱情的时候,他们依然不知道真正的陆地是什么。他们对此的眩晕感就如同曹汐在唯一一次出海中不停地看见黑色,它们铺天盖地,轰隆隆罩住了头顶,接着把整个躯体都压缩进一个狭小的空间。
苏家的院子永远都不缺水的气息,夏天的时候整座院子都会摆满巨大的水缸,苏郁和的童年一直都在水缸周围徘徊。他总是安静地坐在一隅,很多时候苏文哲下班回家,透过院子外一棵又一棵香樟树,看着苏郁和出神地望着头顶上狭窄的一块蓝天,手指拨弄着四周围可以找到的任何小玩意儿,有时候他一看就是一个钟头,等到他不得已走进去的时候,沮丧已经清晰地刻在了他的脸上。苏义达永远是一身脏兮兮的水渍,苏文哲沉默地为他换衣服,给他的水枪装满了水,然后像任何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对意气风发朝他喷水的儿子宽容地微笑,然后再习惯性地看着苏义达表现出孩子专有的表情,欢快地朝路过家门的每一个大人喷起水来。他们在那里住了五年,很多人都以为苏文哲只有一个儿子苏义达,他们总是对他的调皮表现出容忍,甚至是欣赏,有时候苏文哲也是。他甚至饶有兴趣地看着苏郁和想,为什么你就不能像你哥哥那样,像一个正常的小孩呢?
苏郁和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但那时候他早就已经是个少年了。
兴城幼儿园离他们那个住得最久远的小院只隔着一条巷子,苏文哲在附近的美术学院当老师,苏郁和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画画的热爱,因为只有在美术课上他才是认真的。他从一开始就是走神最严重的孩子。苏文哲在他很小的时候曾认为这个孩子一定是个读书的材料,他无数次想过他将成为一个温文尔雅的大学生,接着拥有一个薪水不薄的安稳职业,平静的度过一生,就算是不爱说话也没什么,他的安静也许反而会成为安定生活的可靠保证。但最终的事实却还是与之相反。
他的功课始终很差劲,苏义达的课业却始终很优秀,哪怕是在幼儿园时代,在家里调皮捣蛋的他居然也能在学校里像个乖小孩一样认认真真地听老师的话。每个周末,苏文哲总能看到小红花榜单上他的那个第一。苏郁和不知道为什么他能拿到那么多的小红花呢,但他不明白的还有为什么吃掉加餐里的肥肉就能得到一朵小红花呢,他只是很讨厌吃肥肉,所以总是丢掉,老师就责怪他不懂得珍惜粮食,然后罚他背“粒粒皆辛苦,汗滴禾下土”,但他那时候往往只记得这两句,别的全背不出。苏义达在黄昏里奔跑着跑到苏文哲的学校,大声的说:“苏郁和在办公室背汗滴禾下土,老师让爸爸过去一趟!”
每每这时,苏文哲总是很窘迫地从画室里出来,在全班几十个学生的目光中弓着背走出去,他不明白为什么苏义达在说出这一切的时候那么的理直气壮,甚至可以说是气壮山河。这个只有五岁的孩子说起弟弟的糗事来总是很兴奋,但他又无法把他眼里的目光、口里的那种语调,和幸灾乐祸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这只是一个孩子,他无数次这样对自己说。但他更加困惑的还是这个自己曾觉得一定是最难管的儿子却在学校里那么的乖巧,而他自认为会很乖很认真的苏郁和却永远只是幼儿园老师口中那句:“苏老师啊,您还是带着小和去康大夫的诊所看看吧,人家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呢,对小孩子的这种怪癖很了解呢!”最开始的时候他还会很不高兴地说:“我儿子没有抑郁症,再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忧郁呢?”的确,很多时候他都觉得最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的反而是苏义达,老师口中那个“懂事的小达”。
你怎么那么表里不一呢?苏义达记得这是苏文哲对他说过的最意味深长的话,只是那时候幼小的他只是觉得这句话很奇怪。上小学之后他把那个成语的释义记得很清楚,他甚至用红色圆珠笔把它们在课本上描得非常显眼。但他每描一遍心里就难过一遍,他不断对自己说,我是这样的,在他心里,我是这样的。只是那时,他还不知道这种难过和小时候调皮时面对总是对他微笑的父亲时的那种难过是多么不同。他那时曾万分的希望苏文哲能像寻常的爸爸那样给他一个耳刮子,或者像隔壁的李乔木他爸爸一样骂一句脏话,那样至少亲切。但是没有,他是苏文哲的儿子,即使在数年之后,他成为了一个画品商人,开办了自己的颜料厂拥有了自己的运输队,去往遥远的西部和西南部买来那些稀有的矿石,提炼出他认为最具成色的颜料时,在外貌上,在苏义达的眼里,他依旧只是一个弓着背的男人,甚至是越来越老越来越颓唐,两鬓染上白霜,眼角的纹路刻得愈加深邃,像是永远也道不尽的哀愁。
苏文哲最终还是决定带着苏郁和去康奈德的诊所。只是他始终无法把晨报上那张康奈德的照片和他27岁的年纪联系在一起,那张照片上的康奈德甚至可以用枯槁来形容,胡子很久没有刮了,衣服毛毛的,虽然黑白的报纸上他看不出衣服的质地和颜色,但他能确定的是那件真实世界里的白衬衫一定已经像是一帧老照片了,有着一道道黄渍。那是一则真真正正的大字报,粗黑的字体像是街角那个捡垃圾的老刘浓密的腿毛,一点点露出那张报纸,搅扰得苏文哲不禁恼怒异常,但他早已经学会了把自己的情绪尽可能的变得内敛,这一点他其实是从苏郁和那里学来的,或者说是从林郁那里学来的。林郁,他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还是会那样的悸动一下,像是数年以前,在那个中原小城里,雨水里的林郁,白色的裙子贴在长长的腿上。因此他始终是对康奈德有些同情的,但这种同情与其是说和这座小城市里那些对康奈德才华的流失表现得有些遗憾的人不一样,这种同情更多的是一种同病相怜。他们都曾被心中最重要的东西所抛弃了。
据说康奈德新型的研究技术不能得到大医院的采用,甚至连本来欣赏他的院长也觉得不可理喻,但他却出乎意料的采取了无比浪漫的反抗方式,至少在当时是那么的浪漫,他一纸诉状将兴城医院告到了市法院,认为他们这是对新技术的极度排斥,并且是对社会主义人才的极度浪费。他毫无预料遭到了批斗。但他还是拒不认罪,并表示兴城医院的部分领导固守旧的治疗方式从而让病人的病情更加的恶化。不久后,他就入了狱,罪名是什么,人们就不知道了,人们知道的只是关于康奈德的报道上了晨报一个很重要的版面。写文章的是时任市政府秘书的李乔木爸爸——李守信,李乔木是苏义达学校里的同学。
现实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就像不知道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平时粗声大气脏话连篇的李守信居然还会一本正经的把大道理扯得是有模有样,让人不得不心悦诚服,想到这些的时候苏文哲觉得自己再怎么说也是幸运的,他最多就是不能画人体。但他那几年也想明白了,不画就不画,他随时准备不画画。
康奈德开办这家诊所是托李守信的福,李守信如他所愿,在不久后又写了一篇表彰,表彰落后分子康奈德改过自新的事迹,并义正词严的说他的名字只是为了纪念车祸死去的年轻妻子。李守信当然不会说,康奈德袖子里掖着钱走进了李守信的家,那时候李守信正在狠狠地教训李乔木,苏义达在一旁站着大气也不敢出。
“你小子能耐了,才这么大就学会斗人了。”
“可你白天还说我做得对的嘛……”
“你还敢顶嘴,你再顶一个……”
康奈德就是在那时候敲开了李守信家的门,苏义达正在李守信家玩。在门缝里看到康奈德把什么东西放在了茶几上,李乔木说那一定是什么药材,因为他爸爸就好这个,所以才会和医院的关系这么好,和那个爱人老生病的市长张天柱关系这么好,但苏义达一口咬定那就是钱,他们为此在李乔木的小屋里喋喋不休的小声争论着,争论还未完毕就听到了李守信笑嘻嘻的把康奈德送出了门外,随后就叫老婆把什么收起来的声音,两个孩子在这样细微的声音里停止了争论,苏义达随即表示要回家,李守信自然很乐意,可苏义达突然又说:
“李叔叔,下次我作文写不来就来你这里让你教我好不好,我看李乔木的作文每次都写得不错,您文章又写得那么好,一定能帮助我作文提高的。”
李守信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在苏义达关上门的瞬间他不小心嘟囔了句:“这孩子,跟他老子也太不一样了点儿。”
康奈德诊所就在苏文哲家所在的那条街的附近,这个地段应该也是李守信给他搞定的,而他不仅帮他搞定了这个,还让康奈德名正言顺的把诊所弄成了兴城医院的下属单位,这样一来,做事就更方便了,程序也进行的无比顺利,在他退休的时候还能如愿以偿的拿到一笔不菲的退休金,真是一举两得。因此,当苏文哲看到康奈德的时候,他已然确定这就是一个32岁的中年男人了。他的肚子稍稍有些大了,只是身上收拾的很挺括,头发梳理的油光油光的,连皮鞋也是铮亮铮亮,他站起来的时候,苏文哲甚至确信鞋子上连一粒灰尘都没有落下。
康奈德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只是他盯着苏郁和看了很久,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苏老师还有个孩子吧?”
苏文哲没想到他会叫自己苏老师,他笑了笑说:“是啊,还有一个,这个是小家伙儿。”
“喔,那就对了嘛。”康奈德扶了扶眼睛,“那个孩子很不错啊,应该课业也很好吧。”
苏文哲突然有些犯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能一声声应和着,苏郁和只觉得父亲把自己的手握得生疼。
康奈德把苏郁和的手拉到自己的跟前,让他坐下,并让苏文哲先出去一下。苏文哲在诊所走廊里来回徘徊着,这么大的店面,可见康奈德给了李守信不少钱,他的脑子里突然再次想到了林郁。林郁,他记忆里的林郁,大眼睛单眼皮的林郁,手指纤长的林郁,嗓音清亮的林郁,甚至她那个性情古怪的母亲陈绮蓝也突然窜进了他的大脑里,他突然想到他第一次进林家的门,在堂屋看到的那帧老照片,林郁说那是她爸爸小时候的照片,那时候他们还住在沙漠的边上。苏文哲突然心里一凛,沙漠。这是他无比敏感的一个词汇。
他想着想着,苏郁和已经走了出来,头埋得深深的。“小和,”他突然这样叫起来,然后他意识到其实自己也从来都是叫他的大名的,甚至有时候在外人面前他也是叫他的大名而不是像叫苏义达那样,轻轻松松地来一声“小达”。
苏郁和还是没有抬起头,再转眼,康奈德已经走了出来,他一脸无奈的笑笑说:“苏老师,小和还是很乖的,就是有些自我封闭,但没什么大碍,让他多出去锻炼锻炼就好了。”
苏文哲依旧是僵硬的对他回应了一个笑脸,然后就攥着苏郁和的手走出了诊所。一路上父子都很沉默。短短的兴盛路突然变得狭长了起来,苏郁和突然有些眩晕,他一个趔趄就跌了下去,苏文哲一凛,赶忙抓住了他的手,然后他看见儿子抬起了头。他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爸爸。”他第一次这么叫,爸爸,而不是爸。在苏文哲的记忆里这是他唯一一次这么叫他,在接下来漫长的岁月里他总是会忘记这个儿子曾经这样的叫过自己,但当时他承认他是彻彻底底的被触动了。那一刻他想到的依然只有一个人,林郁。他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对这个孩子永远不能真正的狠心,真正的当做是个小辈去对待,或者像对待苏义达那样去对待也行,但是不能,永远也不可能。
“康奈德是个坏人。”他说这句话时,苏文哲愣了一下,但突然又笑了,这才是一个孩子应该说的话,不是吗?但接下来他又让他失望了。
“妈,妈妈究竟去了那里,她是不是没有死。”他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像是一枚针,瞬间就要把眼前的父亲给刺破了,瞬间就要把那段岁月给撕碎了。但苏文哲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只是认真地看了儿子一眼。
“你妈妈的确是死了,真的死了,她就是在驿城火葬厂被焚化的,那是我们的老家,当时很多人都去了。爸爸很伤心,那时候你们还那么小,你哥哥才一岁多,你还要喂奶。”他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大一通,直到苏郁和突然说了一句:“我知道妈妈没有死,她一定是没有死。”
2
他最开始的记忆是一面雪白雪白的墙。那时候他还在不南不北的中原小城里。儿童福利院每一次的翻修都是从墙壁开始。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的那里,似乎在他拥有了记忆的时候,那双昏黄的手就牵住了他。那时侯他一如既往穿着脏兮兮的衣服,但脏兮兮是别人认为的,他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的衣服是脏的,很久之后,当苏郁和穿着挂满颜料的衣服从画室走出来的时候,他也从没有像寻常的父亲那样去责怪他,苏郁和曾以为这只是因为父亲也是学画出身的缘故,但他不知道的是,实际上,在面对这件事的时候他的爸爸和他是那么的一致。色彩怎么能叫做脏呢?林郁曾说这是苏文哲说过的唯一一句浪漫的话,她那天站在暗沉沉的护城河边,头发被大风撩起来了,苏文哲当时窘迫地站在那里,弓着的身体融化在夕阳里,他低着头让自己不要去想风把林郁的裙子撩起来将会怎样,但越是这样想他越是心烦意乱。但他知道如果不说,林郁可能真的要去当兵了,去遥远的西部,去他们的父辈都曾经呆过的沙漠,但林郁说起那里的时候从来都是那么灿烂地笑着,她的酒窝很深,以至于很久之后苏文哲都觉得每个姑娘都是有酒窝的,因为他从未意识到的一点是,林郁是他唯一真正注视过的一个姑娘。
驿城区儿童福利院唯一干净的恐怕就剩下墙壁了,但它们在苏文哲到来之后就遇到了巨大的灾难。那时福利院的人们唯一能记得的关于苏文哲的事迹。那孩子的手指倒是真的很长,她们那时侯还都是姑娘,却都因为各种原因去照顾起了这帮孩子,他们大多是有残疾的,苏文哲是最难管的,因为他是唯一正常的一个孩子。因此他也是最孤独的一个孩子。
苏文哲在六岁之前从来没有走出过儿童福利院,很多时候人们都能看到那个站在大门外的男孩,但他从来没有再接着迈出去过一步,只是没有人知道他之所以不跑出去只是因为找不到理由。正如画画一样,他之所以喜欢它,也只是因为这是他所遇见的唯一不需要解释的事,色彩没有定理,光影也没有定理,感觉,更没有定理。他对于这些的理解都是自然而然的,就是那样了而已,它们摆在那里,只是一个姿态。
他曾经以为自己真的可以依靠这样不需要解释的姿态活下去,但事与愿违,每当他为此烦闷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儿童福利院那个漫长的走廊。他的手在那里挥舞着,一遍遍,但没有一个人走出来,甚至连他预想中的鬼怪也没有走出来,一切都是沉寂,一切都是静止,而他只有自己。
福利院的阿姨们只知道他醒得最早,但他们不知道,他的眼睛整个夜晚都是睁开的。也有阿姨起夜的时候看见苏文哲从床上下来,站在走廊深处,但她们只是说:“苏文哲,你不睡觉干嘛呢?”
他很早就习惯去做最后一个小朋友。阿姨们说:“这里只有你一个健康的,所以要照顾别人。”所以,摆桌椅的是他,收拾碗筷的是他,但他永远没有小红花,很久之后,当他看到苏义达的小红花时,他并不知道其实自己的困惑中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嫉妒,因此他也更不知道,其实自己对苏郁和莫名其妙的关注,依旧是一种同病相怜。
阿姨们总会时时的对他提起他刚出生时的事情,那时侯是阿姨们东躲西藏才把你们都给安全带到解放区的呀!她们每次这样说的时候,苏文哲就是一副虔诚的样子,她们看到他那样的目光时,也总是满面红光的,眼神里透着无限的希望,仿佛她们一直没有结婚也都是值得的了,这一刻这些已经不是很年轻的阿姨们会忘记她们因为战争的缘故而不能生育的事实,她们记得的只是自己专注的事业,把这些孩子带出来。
但她们并不知道自己这一管就是这么些年。苏文哲上中学之后曾经逃课去过那里,那时侯教导他的几位阿姨依然还在那里,儿童福利院不断的新来不同的孩子,有的是一大早就被放到门口的,有的是直接被丢到医院的,但福利院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更多的救助,社会上募集的资金更是有限,这个狭小的中原小城,哪里有那么多钱去给一个福利院呢,很多时候,当教育部门来检查的时候,这些已经老去的阿姨们热切地想要把这些孩子们的实力展现出来,她们拼命的想要告诉每一个人,他们和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他们可以拥有很好的技术,他们甚至可以跳舞,他们的歌声比驿城区幼儿园的孩子们还要洪亮。这一切让她们看不到那些赞扬背后的敷衍,这些从小就深度残疾的孩子,这些收留了这个小城几乎所有被遗弃儿童的地方,连送都很难送出去的孩子,每年需要大笔医疗费维持生存的孩子,能走出来怎么的一条路。但这些热切的女人们,这些早已不再是姑娘的女人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仿佛再次回到自己的革命时代,那时侯她们那么年轻,那么光鲜。枪林弹雨似乎也是给她们的绝美舞蹈。苏文哲一直都邪恶的希望能从她们的目光中看到厌倦,甚至是哀怨,但是没有。但那次他回去的时候,他看到了阿姨们愣愣的表情,她们站在那里,站在不能奔跑甚至有些不能快乐地笑的孩子里,用一种无法被孩子们理解的忧郁注视着他们,像是给他们从一开始就惆怅的成长写下了注脚。
在那一刻,苏文哲第一次知道,被碾碎的感觉是什么。十四岁的他站在人影背后,站在白墙背后,在一隅光影背后看到了他曾经在孤独中幸灾乐祸希望看到的表情,但他突然就出乎意料的难过,那时侯他不知道,他之所以难过,是因为看到了她们被碾碎的青春,看到了她们再也不能回头的,热情。
长胡子男人是在一个酷热难耐的午后来到的,福利院的孩子们幸运地吃到了冰西瓜,但那天苏文哲没有吃,他第一次想要真正的睡着了,阿姨们也没有注意到他,她们忙着招呼孩子们,那天突然来了许多慈善人士,有些据说还是什么医科专家,很多奶奶级人物也来了,他们都是想要领养孩子。几个聋哑儿童迅速就找到了家,阿姨们热忱地为每一个人拼命介绍着,这个孩子很乖,这个孩子喜欢看书,能背很长的唐诗呢。但没有人意识到苏文哲的存在,这个唯一健康的小孩,被善良的阿姨们轻易地隔离在这个也许能改变他一生的盛会里,他迷迷糊糊地睡在自己的梦里。苏文哲的梦总是很多很多,但童年的梦只有这一个他还能记得。
他记得那最初是一片很绿的丛林,他感到自己站在里面,没有一个人,但大火很快就起来了。他在那里看到了人影,有着窈窕的身姿,甚至他能看到她在火光中那带着一点翠绿的瞳孔,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只是觉得,终于是有人来了,他不再是一个人,夜晚笃笃的脚步里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奔跑了。只是他的欣喜很短暂,因为一只大手很快就把他带离到现实里来了。
长胡子男人是不是跟着慈善人士一起来的,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只是叫他苏先生,传说他此前一直是在西部,在那里做过赤脚医生,还做过乡村小学校里的语文教员,解放后就跑到中部来了,人们能记得他的,只是那双有时候看起来墨绿的瞳孔,只是那绿色淡淡的,更多时候是一种茶色,像他已经有了曲折刻痕的额头一样。他喜欢把苏文哲抱起来,胡茬子一点点扎着他稚嫩的脸。很多时候他都觉得这个突然到来的父亲是想要用长胡子遮住些什么,很久之后他看见了横亘在胡子下面的巨大疮疤,布满了男人的下颌,像是一条嵌在岁月里的,隐秘的轮廓。
他很轻易的就叫了他爸爸,像这个小城市的每一个孩子一样。儿童福利院的阿姨们几乎是在无知无觉中就送走了苏文哲,这个依然穿着长衫的苏先生带着这个六岁的孩子很快就消失在了兴盛路。苏文哲那时候依旧是迷迷糊糊的,他临走的时候突然很难过,黑兮兮的小手冒满了汗,它们淋漓地滴落在男人宽阔的手掌心。他不禁一阵酸楚,只是他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在这个承载了他所有童年记忆的小城,在这个他阔别十多年终于再次回来的小城,终于有个孩子和他是一起的了。
在那条去往新家的路上,苏文哲第一次觉得那条走廊一点都不漫长了。他怯懦地跟在男人的左边,时时有凉风从身旁吹过,他不禁缩了缩脖子。一路上他们都没有说话,他的手被男人紧紧地攥着,挣脱不掉,但也无从挣扎。那时候的建筑还很低矮,这个城市从来都不是什么中心,便是很久之后也不是。他唯一能记得的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就是夜晚从护城河畔传来的钟声。那时候,兴禅寺还是个很小很小的院落,稀稀疏疏留驻了解放前就在那里的几个僧侣,在兴城人的记忆里,他们一开始就是一大把的白胡子,只是没有人像猜测苏先生那样去猜测过他们,这些隐匿在城市角落的僧人传达着属于这个小城的唯一值得铭记的声音,而自己的历史却浅淡到几乎不曾来过一样。记忆往往是有旋涡的,人们也只是在旋涡的某个地方开始自己的回忆,所以苏文哲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他生命的谜团也只是从养父开始,而这个养父,在一开始就被他轻易地接纳了。
他为小男孩取名叫苏文哲,让他去了小城里最好的小学读书,他课业始终中等,他也没过多的要求过什么。苏文哲一直都是没什么人注意的角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八岁。兴城一小坐落在城市的边缘,旁边就是驿城一中。男人说,这个位置好,从小学到中学都不用多走路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深沉,像是早就疲累了,眼睛也倦了,半睁半闭。但苏文哲觉得,这个突然出现的父亲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过往岁月的缅怀。十张稀疏的旧照片,仿佛一屋子的夕阳,渗透到每一丝的情绪,每一刻的抚摸。这座房子是很久之前苏家留下来的,后院是一个小菜园,种着这不南不北的地方最常见的菜色,但很快它们就被洗劫一空,一列语气强硬的人撞开了他们的家门,这个菜园连同苏先生被诟病的历史被写成一页页文字,像很久之后写康奈德的那页大字报一样,只是那时候的历史很混沌,远远没有那么的明确。
只是很久之后,当苏文哲知道写康奈德大字报的人是李守信时,他第一次觉得,在这个每个人几乎都能找到千丝万缕关系的小城市里,真的是有命运这回事。
关于苏莫遮的文章在这个小城掀起了很大的风波,一时间,人人都开始寻祖问宗。连当时只有六岁的李守信也学会了用此来当做自己的资本,但是大多数人对此是充耳不闻,但苏文哲不能。一年级四班的教室里,他和这个男孩子坐得最近,驿城日报永远是李守信的垫桌布,他把报纸折了两折就把苏文哲的座位快要占完了,遍布高干子弟的驿城一小总是人满为患,但李守信占得这点座位还远远不会让一个孩子生气。但那天李守信偏偏把报纸摊开了,而在那张报纸的头条,就是苏莫遮模棱两可的历史。
苏文哲对于父亲仅限的猜测就是根据那篇文章。那是一篇猜测得理直气壮的文章,一个曾在中原度过童年的男孩,跟随传教的父亲一路跋涉,在沙漠边缘成长为说书人,来往于西部与东部的荒蛮地带,拥有一支小的驼队,总是护送形迹可疑的人和药品,以及和来历不明的女子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那篇文章写得像是一篇小说,但苏文哲却真的为它入了迷。苏莫遮差不多从那时起,就能在许多个夜晚见到迟迟没有睡去的儿子在观看那一帧帧老照片,那一刻他觉得这个孩子从一开始,就没有了童年了,他在他的生命里,很快就长大成人了,这让他很难过,因为他们居然这么快就平等了。
苏文哲是鼻青脸肿地从家里走回家的,在李守信那张极具挑衅性的报纸面前,他公开的为自己的养父辩解,不,是父亲,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只有一个亲人了,也只能有这一个亲人了,维护他是他的责任,虽然责任这种东西不应该出现在一个七岁孩子的字典里,但对于苏文哲而言,这种维护是唯一对抗孤独的方式,尽管那时候他还不明白自己如此倾心的维护父亲,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
踏过浅淡到几乎不存在的月光,苏文哲看见苏莫遮正在家里洗洗涮涮,每次从那个小屋回家之后他总要这样,苏文哲就自己回家,在那条当时还没有路灯的巷子里一直往里走,他总会在那里听到父亲的声音,这段时间来,他甚至不止一次细细的刮去了胡子。衣服总是洗得很干净,但都很旧了,像那些照片的底色。从侧面看去,他的颧骨还像过去那么高,但是整个下颌的疮疤已然说明了病症、流离带给他的沉甸甸的历史。它们早就已经沉淀成他生命的底色。
煤油灯把苏文哲的鼻子熏得黑黑的,眼睛也是酸痛酸痛的,清冷的二人居室却从来没有真正地安歇过。苏文哲差不多从那个时候起就明白了地位这东西。就如同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嘲讽他,尽管是背地里,但鲜有人去嘲讽李守信,不仅仅因为他那个父亲,更因为他这个人,这个官气十足的孩子从一开始就学会了如何树立自己的威信,但对于他来说这多半是无意识的一种举动。
苏文哲差不多从那时起就被驿城一小的孩子们自动屏蔽了,孩子们仿佛早就策划好了一样,将这个福利院来的小孩阻隔在他们的世界之外。但每次他没有交作业,或者考试没有及格依然会有孩子去通知他,替他向老师转达,但绝对没有人,绝对没有人再去和他说一句别的话,哪怕是体育课上的接力赛,也再也没有人愿意站到苏文哲这一组了。但后来就有人愿意了,因为林郁来了。
- 联合读创 (微信公众号认证)
- 阅读创造生活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