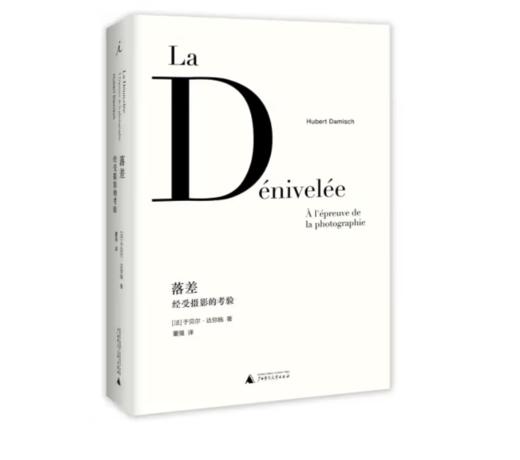商品详情
内容简介
于贝尔·达弥施是法国艺术史学家和哲学家,同时,他也无可争议地是这个时代*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思辨性的分析和理论学说,构成了法国当代思想真正的锚定点。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向摄影这一机械的媒介提出质疑,包括摄影在电影领域内的延伸。他以谦逊的态度,通过借鉴而来或直截了当的手段,不懈地浇灌着这一永远需要开拓的研究领域。
这部以《落差》为题的“摄影”随笔集,旨在分析在摄影和电影闯入艺术实践领域之后所产生的“层差”,并揭示由其造成的批评话语的断裂。本书受到了德勒兹,特别是本雅明的影响,它将达弥施在不同时间段的文字集成一册,使读者得以看到一种摄影思想的全貌。从作为序言的《关于摄影现象学的五点想法》(1963)到二十一世纪初的随笔,本书呈现出一些相同的思考,相同的疑问,并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即:无法为摄影撰写历史。而这本身,就证明这一问题是多么的恒常,多么的“构成问题”。在收录于本书的《纪念瓦尔特·本雅明〈摄影小史〉出版五十周年》(1981)一文中,达弥施写道——
“摄影不去改变历史,而是固执地动摇历史这一概念。假如有一样东西必须作为一种‘摄影小史’存在,那么,它的出发点不应该是一个源头的叙述,而是强制的重复,是它构成了摄影行为*为恒常的动力。无意识,正如人们所知,或者以为知道的,是没有历史的;但它在历史中还是起作用,而且对历史产生作用,使之动荡。摄影对记忆也有同样的作用。”
作者简介
作者:于贝尔•达弥施(Hubert Damisch,1928-)
法国著名符号学家、哲学家、艺术史家,透视历史研究**。曾任教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创立了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直至退休。主要著作有:《云的理论——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绘画史》(Théorie du nuage: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peinture, Seuil, 1972);《透视的起源》(L'origine de la perspective, Flammarion, 1987);《帕里斯的裁决》(Le jugement de Pâris, Flammarion, 1992);《来自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一个童年回忆》(Un souvenir d'enfance par Piero della Francesca, Seuil, 1997)。
译者:董强
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傅雷翻译奖组委会主席。旅居法国十二年。曾师从世界文学大师米兰·昆德拉。著有《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插图版法国文学史》,法语诗集《松绑的手》等。译著30余部,涉及文学、艺术、人文、宗教等多个领域,如《西方绘画大辞典》,《西方1500年视觉艺术史》(共六册),《西方绘画中的流派》,《波德莱尔传》,《小说的艺术》,《娜嘉》,《记忆的群岛》,《世界宗教理念与信仰史》,《云的理论——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绘画史》等。2009年获法国政府“教育骑士”勋章,2013年获法兰西学院大奖“法语国家联盟金奖”,2015年获法国政府“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16年获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LB)“荣誉博士”称号。
目录
导读: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图像接受美学
导读: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图像接受美学 / i
前言:关于摄影图像现象学的五点想法 / 001
Ⅰ
1. 不可处理 / 011
2. 纪念本雅明《摄影小史》出版五十周年 / 024
3. 从摄影出发 / 031
Ⅱ
4. 立体感及其魔力 / 047
5. 最后期限 / 059
6. 音乐会:迈克尔·斯诺作为艺术家的肖像 / 084
Ⅲ
7. 固定的活力 / 107
8. 古堡探幽 / 117
9. 缠绕的线 / 153
Ⅳ
10. 冒着失去视觉的危险:电影与绘画 / 171
11. 刺破银幕 / 203
12. 紧迫感:研究提案 / 232
13. 节奏—影像 / 245
附 注 / 261
精彩书摘
不可处理

1980年底,我刚刚读完《明室》。从一个三年前遇到的陌生人那里,收到了一张照片。当时我参加了一个有关罗兰·巴特的研讨会。照片上,我的眼睛如人所说的那样,紧紧地贴在一个小型相机的取景窗上,面对的正是罗兰·巴特本人。从他脸上可以猜到一丝淡淡的微笑,我无法确定,那是表明他的不耐烦、他对我的宽容,还是表明他已经预料到在我们之间,这样的一个小玩意将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这一预感是否源于照相机中发出的奇怪声音,那一声按下快门时的咔嚓声(他曾说那是他唯一能够在照相时忍受的东西)?几个小时之后,我发现,果不其然,在给这架借来的照相机上胶卷的时候,我太着急了,胶卷没有放好,所以根本就没有拍成。
对于这一过失行为,本来没有什么事后可说的话,假如没有一个人正好于这一时刻在场,并拍摄下了我们两人,一个正面,一个背面。一个是笨拙的“拍摄者”,天真到了要利用这次罗兰·巴特本人都不情愿地参加的研讨会的机会, 给他拍一张肖像:这在巴黎,我是想都不会想的,而我住得离他只有两步远,而且在街上或市场上遇见他的机会,甚于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虽然我们同在那里教书。另一个, 也就是构成我的靶子的“主体”,我知道他并不喜欢人们拍摄他,除非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而有另外一个人成功地做到了,他抓住了这一瞬间,并让当时的场景一目了然。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或者说,以为要拍人家却被人拍去了:面对这样一张毫无特别准备却又不乏狡猾意味的照片,我不禁产生了一种可笑的感觉,同时又有一种淡淡的负罪感,掺杂着某种苦涩;用一个词来说,是一种不适感,又无法解释,无法确定,更无法定义。它为我再现的罗兰·巴特的形象,如果将之与我所知的他的其他图像相比,并不让我产生一种悔疚,觉得当时应该带上一架我可以用得更好的照相机,也并不让我后悔当时索性就再麻烦他一次:因为那样我就可以有一张相当于家庭留念式的回忆物——尽管只是平庸的崇拜之物。但是,它又没有显示出当时场景中任何隐蔽不见的一面,因为有时候这样的偶然“巧遇”可以造成这种效果(也就是在“放大照片”后看出原来眼睛没有注意到的现象的效果)。我的不适感是来自别的原因。在我重读《明室》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原因并非如我起初所想,仅仅属于个人层面。
一切将摄影师本人包容在内的照片,或者表现他在场的照片,无论它是由一个第三者拍摄的,还是通过一面镜子的折射,都能揭示某种机构的运转、它的社会功用,以及它对私人造成的影响。就我的情况而言,我是完全顺从了一种仪式的:一般来讲,既然参加了一个研讨会,而且为了让它显得真正发生过了,就应当留下一些文本和发言稿之外的东西。比如说,应当首先有些照片,就像那些我们可以在塞里西的墙上看到的、在蓬蒂尼举办“十日会议” 时所拍摄的照片一样。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什么又那么的不经意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过失行为,看上去简直就像是虚情假意的,甚至是一种故意逃避?仿佛人们给了我一个位置,而我未能(或者说根本就不愿意)占用它,给了我一个我并没有真正选择的角色,而且并不适合我。比如说这一研讨会本身,本来我去参加就是出于友谊,罗兰·巴特本人也说是完全违心地参加的,只是为了避免制造这样一个印象:一个“拒绝参加以他的名字为主题的研讨会的人”——这是他本人的说法。就好像我本人也被迫参与了他的游戏,并且走得更远, 让他感到更为不适,让他得以通过一个伪装、虚假的摄影行为,避免形成一个“拒绝被拍照的人”的形象,但同时又无须扮演“接受被拍照的人”的形象。甚至,这一淡淡的微笑本身也是如此,因为在我几周后告诉他,我为他拍的照片完全拍坏了的时候,我又一次看到了这一微笑,他特有的微笑, 而且更为糟糕的是:拍摄行为根本就没有真正进行。因为所谓拍摄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就是一个图像印在一个有感光能力的载体上。也就是说,形成一个接下来人们可以加以处理的图像,可以任意修补、变形、变样(不过,这一图像永远都不能制造出一个可以与草图或图样对等的东西。摄影可以有模糊,有因为晃动了而产生的变虚的图像,但与绘画或素描不同的是,它永远也没有草图、写生。但它可以有拍坏了的图像)。
据我所知,罗兰·巴特并没有从我所说的陌生人手中(事实上,他只能称得上是半个陌生人,而且对我们共同的朋友来说,肯定不是陌生人)得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见证了我们在这一面对面相遇的一瞬间毫不足道的真实性,我们只被一个小小的金属匣子隔开,而且我躲在它后面,只是为了更好地接近他。
- 今日美术馆微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