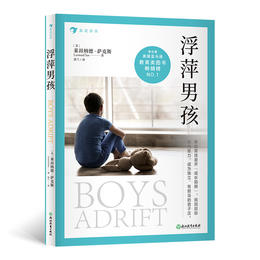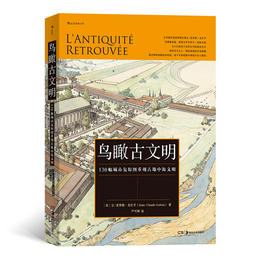走:Green和张早故事集(一位写作者的孤独旅程 不断行走、感受、书写、承受 生活的诗意呈现于微妙细节之中)
| 运费: | ¥ 0.00-20.00 |
商品详情
作 者:司屠
字 数:130千
书 号:978-7-5596-2083-5
页 数:224
出 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后浪出版公司
印 张:7
尺 寸:143毫米×210毫米
开 本:1/32
版 次:2018年10月第1版
装 帧:平装
印 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关于写作者的小说,全书没有任何好莱坞式的“桥段”,而是通过充满张力的细节,营造出游离与孤独的氛围,阅读体验更接近看一部新浪潮电影。
◎司屠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写作者,不迎合市场,但(或正因如此)也绝不愚弄读者。
◎司屠的小说有法国新小说的影子,但更为真诚,能读出作者对于爱情和写作的执着。
名人推荐
在我看来,司屠是晚熟型写作者,他的创作曲线和气质让我想起贝克特和塞尚,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时间会显示出他有多重要。另外,我很期待他老年时的写作。他应该叫写作艺术家。——孙智正(小说家)
司屠是小说家中的另类,难能可贵的同时,也注定要受尽煎熬。小说创作绝大多数时候是一种自说自话,沉浸其中,自能够打捞迷人的腔调。——赵志明(小说家)
著者简介
写作艺术家。原名姚来江,浙江余姚人,1975年生,1998年开始写小说至今。曾经做过八年警察,现从事写作和艺术工作。著有小说集《同行》《大批鲸鱼不如一匹鲸鱼来得壮观》《唐朝的瘦身运动》等。
内容简介
本书叙述了一位写作者的日常生活,坐公交车、走路、爬山、谈话、与一双鞋子互动、等待、吃饭、电话做爱,等等。小说中没有刻意的戏剧化情节,没有激烈的冲突,它在一个个平凡的动作、一段段简单的对话中,展现一段孤寂的旅程,依靠细节中的微妙张力,取得直抵人心的效果。
目录
第一章 同行………………………………… 001
第二章 秋操………………………………… 024
第三章 新睛………………………………… 039
第四章 我感到你的痛苦…………………… 060
第五章 但我不能追逐爱情………………… 085
第六章 顶峰积雪…………………………… 139
第七章 《弦上箭》…………………………… 169
第八章 在继续之中…………………………… 198
正文赏读
第三章 新睛
大山大湖产生自己的气候
那里的四个人,他们走着。随着两脚的交替前行,两手前后摆动,并且总是另一只脚对另一只手,左脚跨出时,上来右手,换成右脚时,右手同时后摆,向前的成了左手。每个人都这样,可能某个人的辐度大一点,某个人的辐度小一点。不过,当三个人伸出去左脚右手时,另外一人伸出的却是右脚和左手。
这个在那一方面没有和其他人保持一致的人转过身去,但后面这人并没有在看着她,他只是因为她转过了身来才看看她,她冲他按下了手上相机的快门。他指指她身后,走在她前面的男人走起了正步,相机斜背在肩。她点点头,快步走去,到达走正步男人的身边,弯下腰。因为她是个高个子,她的弯腰给人的感觉既勉强又很有力度,似乎比一个平常个子的人弯腰更像是“弯腰”,在那男人的大腿上她拍了两下,拍在同一个部位,第二下紧接着第一下,随即收回,戛然而止,形成一种节奏,像是在着重指出一个基本事实,“你在走正步”,似乎也以这样的方式表示了赞赏认可。
走正步的男人在她拍他时低头看着,在她拍完后侧过头去和已经直起了身子的她点点头,继续正步走去,看着她,加快了频率。高个子女孩心领神会,学他的样也走起了正步,和他走在一起。她的头昂得高高的,刻意发挥着与走正步相应的风度。一旁,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孩、她手中的相机从土路边的田野转向了走正步的男人,给他拍了一张,在那高个子女孩也走起正步时,给她,也许是他们,拍了一张。她也加入了他们。她没有走到他俩的身边去走,而是就地走了起来。在她和他们之间大概有三四个身位的间距,她也要靠后一些,大概靠后两个身位。
在三个走正步的人的后面,那男人双手插在西装短裤的裤袋里,微笑着看着这三人。
穿白裙子的女孩首先停住了脚步,但保持着手势,一手后摆,另一只手横在胸前,两只手都握着拳头,她从她的左面也就是后摆的那只手所在的那一面转过身去,问那男人,怎么样?
像——刘胡兰。他说。在像和刘胡兰之间有一个停顿,但没停顿到让人等待的地步。而刘胡兰则是不假思索的连贯。
靠。
白裙女孩说着放下了双手。其他两人也笑着恢复了平常的步伐。高个子女孩耸起双肩,双手捂着腮帮,双膝略微下蹲,左右扭动着身体向前走去。走正步的男人似乎有模仿的意思,但没来得及,高个子女孩停止了扭摆,挥了一下手,说,“No!”
比利珍啊比利珍。走正步的男人笑着对她说。
那颖禹啊那颖禹。比利珍看着走正步的男人说。比利珍是个外国女人,她用她那门语言说话的方式说中文,这在一个认识那颖禹的人听来,就好像她不是在叫那颖禹,这让人觉得新鲜、有趣,百听不厌。
Green啊Green。没有走正步的男人说。
张早啊张早。穿白裙子的女孩和比利珍一起说,因此她叫Green,其实是Green先说,比利珍当即跟进。她们笑着一起说完。张早竖起中指。因为她们走在他前面,她们说张早啊张早时是头也不回地说的,她们也看不到张早在竖中指。
比利珍转过身来,倒退着走着,把镜头对着面前的三人。三人都配合地看着镜头,一个前伸脖子、握着拳头很凶恶的样子,一个点头微微笑,还有一个和她对拍。比利珍拍下了这一幕,从相机上抬起头来,看向他们身后的什么东西。张早回头看了一下。比利珍把相机又举到眼前。三人走近了她,走过她,她的左边两人,她的右边一人。
出现了一个转瞬即逝的场景,差不多走成了一条直线的三个人,当他们走到比利珍身边时,四个人恰好处在了一条直线上。
三人走过去之后,比利珍的两旁顿时空了出来。随着他们继续前行,比利珍身后和他们之间的空间在逐渐地拉开拉大。
四个人,走走停停,不时变化着前后次序。有时某个人走在了最前面,有时这个人走在了最后面,有时他又走在了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或者与另一人并排走到了一起,在最前面,在最后面,在中间……随着他走位的变化,其他人的位置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而在他不变时,其他人也可能在变化,其中三人在变化,其中两人在变化。这些变化产生了前后队形上的种种组合。这些组合纯属偶然,没有规律,难以捉摸,你很难知道下一次会是怎样,也很难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到来。
变化的不仅是前后次序,和前后次序一样,随着前后次序的变化或者不变化,各种横向的移动也在不时发生,不时还有人停下来,这都增加了归纳的难度,根本就是一团混乱嘛,只不过这是一种平静的混乱,因其分散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内显得平静,当你最终放弃了徒劳,你就看着它们,也不再去设想和预感,任由他们在那里活动着,这样单纯的观看有其乐趣,这种单纯的运动也不乏看头,等你看进去了,那里就像是一个舞台,那几个人也就像是演员了。
虽然清楚这不可能,但也会有这样的时候,比如,刚才发生在三个人之间的前后左右的交叉换位太像是刻意安排好了的,你不禁问自己,这真的是出于偶然吗?真的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吗?毕竟它们太像是一个表演了,演的也足够娴熟、流畅,一气呵成,一点也看不出演的痕迹,但正因如此,它更像是一个表演。
停下来是这样,三个有照相机的人停下来基本上都和拍照有关,或者, Green有一次,她站住了想打一个喷嚏,但是夭折了,看到张早正看着她,她就说干吗干吗?张早摸摸她的头,Green又说,是很难受的嘛。
(在那颖禹站停在路边的玉米丛外撒尿时,比利珍自他身后拍着他,Green也发现了,也拍。你们别拍啊,那颖禹说。)
张早没有因为他没拍照,就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确实要比其他人更久地处在最前面。走着走着,他就走到最前面去了。那时他独自走着,时快时慢,东张西望,在这样一种行走里人是不会感觉到自己双脚的运动的,人的心思在四周的景物上,在天气上,在自己的某个念头上,而把行走完全交给了脚,脚自己走去,按照它一贯的节奏,以它不为人知的方式,根据探索到的道路状况,一颗石子被踢飞那也是脚自己在行动,当它被踢飞他才意识到他踢飞了它,有时也没有意识到,有时目光接触到了石子,把它踢飞的念头要滞后于踢飞它这一行动本身——但走着走着,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他意识到自己的行走,为自己的行走所吸引,沉浸在了这行走中:视四周如无物,心无旁骛,排开看不见的气流,步伐有力、清晰而规律,每一步都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和心跳的声音,只有这一声音,跟随着这声音,一步一步,感觉着这一连续,进入这连续——直到来到那一时刻,在那一时刻他将意识到他离开他们很远了、他独自走得很久了,他停下了脚步,回身等着他们。
在他不在最前面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停下来是和Green在一起,让Green给他拍照,或是他看Green拍照,和Green一起看他们拍的照片,有时他也给Green拍。
张早后退,先左脚,然后右脚,再左脚,站住了,此时右脚在前,左脚在后,两脚之间距离一鞋,他把相机举到眼前,按下快门,然后低头看了看显示屏里的照片。
这会,张早又走到最前面去了,他就要走到这条路的尽头,接下来是一大片青青的湿地,过了湿地是湖。张早停在湿地的边上,侧身看着后面的三人。
哇,有人对着这一大片青青的湿地发出了感叹。
他们站在湿地的边上,看着这一大片湿地——面对这种环境,人也会感受到自己的呼吸,满满地吸进去一口,呼出去。
青青的湿地里有许多马,黄的,白的,褐色的,有站着的,也有在奔跑的,奔跑的马的尾巴长长地伸展在身后。
有人举起了相机。
这是沼泽吗?Green问。
这是湿地,没事,可以走的。那颖禹说。
是沼泽我还敢下?张早说。
比利珍、那颖禹和Green也下了去。他们有的穿着凉鞋,有的穿着拖鞋。当他们的脚下去时,他们会期待某种感受,这感受将被证实是凉凉的(也可能什么都没想,一脚就下去了,因此会出其不意地感受到那种凉快),像是走在暴雨后的操场上。那时,他们意识的重心在脚上,也由于初次涉足还提着一股劲——脚随即遇到一股阻力,其实是到底了,比想象的要踏实。
脚落到水草中,提起,再落下,不时会带起水来。经过的大部分地方都平整,水草密集,并不泥泞。有的地方坑坑洼洼,坑中映出天空一块,顺便可以洗去粘在鞋底的泥(也可以在水草上蹭去)。有人脱掉了鞋子,一手一只拎着走,这样走一开始脚底会有硌感,这就像是那种凉快的感觉,以及来到一个新的行走环境里的新鲜感,要在走过一段时间之后,脚才会不再感受到它们。从那时起,人才算完全融入了环境。
他们向北,和湖平行地走着。目光转向东面就能看到湖。湖狭长,闪光。湖的另一头是山和山下的村庄。
前方有两匹马在亲热嬉戏。一开始他们就是在向它们走去吗?显然,一开始他们就注意上了。也许它们正好是在他们走去的路上?无论如何,他们离它们是越来越近了。他们此刻肯定是在向它们走去。
马在嬉戏一望而知,它们是在嬉戏而不是在干别的,不过它们嬉戏的方式和人还是有所不同,马没有手,没法抚摸、拥抱,好像也不会舔吻,马静静的站立,磨蹭着各自的头部,在这种情形中,它们头部的歪来扭去显得尤为激烈;马一跳一跳,跳起来的同时,头碰到一起,彼此摩挲着,这一亲热显得梦幻,人做不来。它们也用身体的其他部位磨蹭,由于它们有一个很大的头,它们的那种耳鬓厮磨最引人注目。
有一幕值得一提,当它们同方向并排站立,摩擦彼此的肋侧时,它们的头抬起,一动不动地看着前方。它们是在静静地体会?
哇,好大。Green说。
呵呵。那颖禹笑出声来。
What?比利珍问。
张早指指黄色马的阴茎说,big。
Hmmm。比利珍摇了摇头。
大家都笑了。和前一次的突然、短促(笑声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一样,这一次那颖禹笑得明确、放开。两次笑的分贝是递进的,前一次是“呵呵”,这一次是“哈哈哈”。
无论“呵呵”,还是“哈哈哈”,它们都是即时的反应,体现出一种爆发力,要比这里其他人的笑更给人以情不自禁的感觉。
他们已经走得离那两匹马很近了,他们停下来给它们拍照。花斑母马两次扭头避开了黄色马的贴靠(避开时,花斑母马看也不看黄色马一眼)。这在此前好像是没有的。黄色马低下头去,啃吃着地上的青草。那颖禹走到黄色马身边,抚摸着它。
这马昂起头来,瞅着那颖禹,那颖禹抚摸它的头部,它又把头晃了两下,明显是要晃开他,但很快它还是在那颖禹的手下平静了下来。
那颖禹搂着马头,和马耳语着什么。那颖禹摩挲着马的肋部,搔它的痒痒。那颖禹从裤袋里掏出一包薯片,(那颖禹还有薯片,张早说),拆开,取出一片塞入马嘴。那颖禹把薯片放在手掌上,让马自己伸过头来吃。比利珍从各个角度拍摄着那颖禹和马。张早双手叉腰看着那颖禹和马。Green也过来抚摸马,但她不及那颖禹那么自然,那么投入,Green的动作显得小心、局促。Green看着那颖禹抚摸着马。
那颖禹抚摸着马,他的抚摸有板有眼,看上去很合理,让人觉得马会很舒服(仿佛我们就是那马),好像抚摸马就应该像他那样抚摸。他有一些和马交流的小动作,这些小动作表明了他和马这种动物相知。在这件事上,人们看到他这样子就会被他吸引,信任他,模仿他。
比利珍和张早也过来摸了摸那两匹马。马毛滑滑的,手掌透过滑滑的马毛感觉着马暖暖、肉实的身体和这身体上的呼吸起伏。人的手在这高大而温驯的活动物皮毛上触摸的感觉很特别,踏实。
他们离开这两匹马,继续向北走着。比利珍边走边从显示屏里调出相片看。她停了下来,看着后面的那颖禹。那颖禹注意到比利珍正笑盈盈地看着他,就加快脚步,走到她身边。比利珍把相机递到他眼下,让他看一张相片。相片中,扮着鬼脸的那颖禹抓着黄色马的下颚,看着那马,马伸直马头,也在看着他。那颖禹看着比利珍,点点头说,good。比利珍要那颖禹看的就是这个了,而在他和两匹马的后面,是湿地,是地平线尽头的山群。那是五座山,第一座起始于相片中间偏右的位置,逐渐往相片的左边升高,快到达相片边缘时有所下降。第二座,它的起始部分被第一座的起始部分挡住,即它在第一座的后面一点,这两部分仿佛相交的地方就位于这张相片的中间,这一座向相片的右边起伏伸展,它最高的地方也是在快到达相片边缘时。第三座差不多就在这张相片的中间,也就是在第一座和第二座仿佛相交的地方的后面,因而,它的左边部分在第一座的后面,右边部分在第二座的后面。这是第三座。它后面第四座的起始部分几乎完全和第三座的起始部分重合了,它向右边逐渐升高,很快就高出了前面的第二座和第三座,它也是在快到达相片边缘时开始有下降。而最后面的那一座是一个山头,崛起在第一座和第三、第四座的后面中间偏左的位置,下降的两边随即分别被第一座和第三、第四座挡住,在视觉上它和第一座一边,左边,第二、第三、第四座又是另一边,不同于线条柔和的前面四座,这最后一座在远处尖尖的矗立。
- 后浪图书旗舰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后浪出版公司官方微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