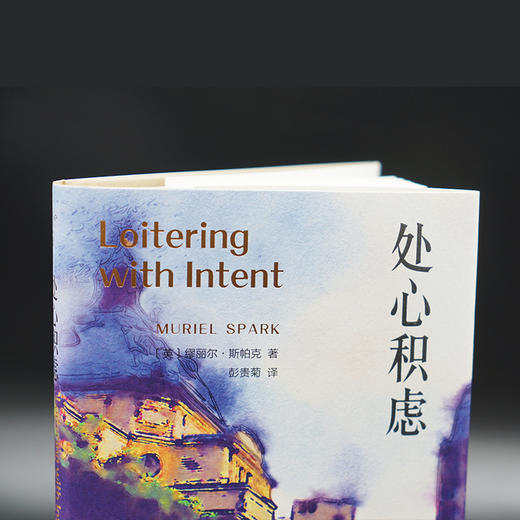商品详情

基本信息
处心积虑
(守望者·文学)
[英]缪丽尔·斯帕克 著
彭贵菊 译
ISBN 978-7-305-24702-6
定价:58.00元
开本:32
页数:236
出版时间:2022.2
CIP:I561.45
印刷工艺:精装
图书简介
一心想成为作家的芙蕾尔·塔尔博特,一直游荡在奇异的伦敦文学圈边缘,为了谋生,她误打误撞成了古怪的“自传学会”的秘书。学会的召集人是渴望操控人心的昆丁爵士,受他控制的会员都是落魄但自以为是的英伦贵族。昆丁怂恿会员“坦诚”写下他们的“璀璨人生”,但本就真假参半的传记素材,还先后受到了芙蕾尔和昆丁爵士的“艺术加工”。艺术与现实,从一开始就纠缠不清。后来,芙蕾尔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手稿被昆丁盗走,虚构进一步照进生活,真实、冰冷的死亡接踵而至……
作者简介
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1918—2006),苏格兰重量级女作家,在世界范围内亦享有盛誉,代表作有《布罗迪小姐的青春》《驾驶席》(同名改编电影由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等。鉴于其在文学文化领域的卓越成就与杰出贡献,她分别于1967年、1993年获颁大英帝国官佐勋章与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2004年,苏格兰艺术委员会创立了以“缪丽尔·斯帕克”命名的文学基金。2008年,缪丽尔被评为“1945年以来50位伟大英国作家”之一。
译者简介
彭贵菊,广东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译著有《泄密的心》《一纸瞒天》《梦幻之巅》(合译)等。
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关于小说艺术的元小说,这是一场针对小说家的阴谋。斯帕克借芙蕾尔之口,讲述了身为艺术家,她观照世界的方式以及她对艺术创作的思考。深层主题虽然严肃,但斯帕克为它套上了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且文字诙谐幽默,时常语带讥讽,轻松吸引读者与她一起踏上这趟文学兜风之旅。她塑造的女作家芙蕾尔与伍尔夫的理想遥相呼应——独立维生,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依靠写作获得成功。芙蕾尔不止一次感叹:作为一位艺术家、一名女性,生活在二十世纪,感觉真好!尽管经历了诸多咄咄怪事,可于她而言,不过是丰富了写作素材。小说最后,她对生活还以漂亮的一脚,高高兴兴踏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全书未有一字讨论女性独立,但那鲜活的女性形象已说明了一切。缪丽尔将自己对生活与艺术的看法,注入俏皮、优美的文字,带领读者通过艺术的眼睛来世界。
媒体及名人推荐
这是缪丽尔·斯帕克精巧至极的道德寓言或谜题,蕴含丰富的洞见与智慧,且答案绝不简单。——A. S. 拜厄特,英国知名作家,著有《占有》
我从头读到尾,每一页都看得很开心——有趣、出其不意且让人欲罢不能——一部奇异、妙趣横生的小说。——奥伯龙·沃,《每日邮报》
这本书让我们去思考感知的本质,以及我们自以为能了解他人思想的幻觉。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无法跳脱出自我的局限,除非通过伟大艺术的眼睛来看世界。——A. N. 威尔逊,《旁观者报》
我欣喜若狂地阅读这本书……鲜活且饱满,睿智且成熟,精彩的俏皮之作。——《纽约时报》
这趟文学兜风之旅让人欲罢不能。——《出版人周刊》
一道令人回味无穷的谜题——《新政治家》杂志
精彩书摘
二十世纪中叶的某一天,我坐在伦敦肯辛顿区一座还没有被拆掉的旧墓园里,一位年轻的警官离开道路,向我走来。他羞涩地笑着,仿佛要穿过草地,邀我打一场网球。他只是想知道我在干吗,但很明显,他也不想那么问。我告诉他,我在写诗。我请他吃三明治,他不要,说他吃过饭了。他和我聊了会儿天,然后说了再见,说那些坟墓一定都有些年头了,他祝我好运,还说有人说说话真好。
这是我的一段人生的最后一天,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太阳下山之前,我坐在一座维多利亚时期的坟墓的石板上写诗。我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客卧一体房里,房子里有一个煤气暖炉和投币煤气灶,灶上有个投币口,可投入采用十进制前的便士或先令,想投哪种就投哪种,有什么就投什么。我状态很好。我没工作。这本来是件令人沮丧的事,但理性地看,其实也没什么。房东的贪婪也无所谓,他叫亚历山大,个子矮小。我不愿意回家,怕被他拦住。我不欠他房租,但是,他反复劝我租一个大点的、更贵的房间,因为他看到我的单人间里挤满了书、报、盒子、袋子和食品,还经常有客人来访,他们或留下来喝茶,或半夜三更到访。
房东说我花着单人间的钱,过着双人间的日子。到目前为止,我还能经受住他的劝说。同时,我对他的贪婪很感兴趣。涉及租房问题,人高马大的亚历山大太太从来不出面,她决心不让人们把她当作收租婆。她的头发总是油光锃亮,刚在美容店做过的样子,指甲则涂成红色。她就像另一位租客一样,进出都会礼貌地点点头,只是她显得更高人一等。我微笑回应,内心默默欣赏她。我对亚历山大夫妇没有什么不满,只是不同意他们让我租一个更贵的房间。即使他把我赶出去,我也不会对他们心生怨恨,我主要是对他们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我感觉讨厌鬼亚历山大先生是个中翘楚,经过精挑细选,与众不同。我不想在回租屋的时候碰到他,但我知道,如果碰上他,我肯定有所收获。我很清楚,我的内心有个恶魔,特别喜欢看人原形毕露的样子,不只是如此,不仅是原形毕露,还要暴露更多,更多。
那时候,我有几个很棒的朋友,有善有恶。我几乎身无分文,但精神饱满,因为我刚刚逃出了自传学会(一个非营利机构)的魔爪,学会里的人认为我不是坏就是脑子有毛病。我会告诉你自传学会的故事。
那天我坐在肯辛顿破旧的墓园里写诗,还同一位腼腆的警官交谈。那一天的十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封信,称我为“亲爱的芙蕾尔(Fleur)”。
“亲爱的芙蕾尔”,我出生的时候被冒险地取了这个名字,总是这样,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倒不是说我长得丑,就是觉得芙蕾尔这名字取错了,可它毕竟是我的名字。有些阴郁的人还叫乔伊(Joy)呢,很多腼腆的人叫威克多(Victor),叫格劳丽亚(Gloria)的人一点也不显赫,叫安吉拉(Angela)的人却很物质,一个人在漫长而充满变化和渗透的一生中,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人。我就遇到过一个叫兰斯洛特(Lancelot)的人,但我向你保证,他和骑士精神不沾边儿。
不管怎样吧,这封信写道:“亲爱的芙蕾尔,我帮你找到了一份工作!……”信写得很无聊。写信的是位热心的朋友,我已经忘记她长什么样了。我留着这些信干吗?干吗?我用粉色带子把它们捆成薄薄的一叠,按1949、1950、1951这样归类。我学过秘书专业;可能我就是觉得,信就应该分类存起来,我确定我当时认为它们有一天会变得很有意思。事实上,这些信本身没啥意思。例如,在即将转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之时,有家书店写信讨债,说不给钱就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当时我欠书店钱。有些店家还比较宽厚。我记得当时我觉得那封威胁采取进一步措施的信挺好玩的,值得保存。可能我给他们回了信,告诉他们我好害怕他们不断接近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可能我没有这么做,只是在心里想过。显然我最终还了钱,因为收据就在那儿,五英镑八便士九先令。我总是想买书,几乎所有的账单都是买书的。我曾经有一个珍本,我在另一家书店用它抵了账,我不是藏书家,除了内容,珍本的稀缺性对我没有吸引力。我经常从公共图书馆借书,但也经常逛书店,渴望拥有某些书,例如,《亚瑟·克拉夫诗集》和新版《乔叟文集》,我会同书商交谈,赊一笔账。
“亲爱的芙蕾尔,我帮你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给位于诺森伯兰的那个地址回了信,陈述了我作为秘书的优点。一周之内,我就搭上了公共汽车去贝克莱酒店接受未来雇主的面试。时间是下午六点,我考虑到是高峰时间,提前到了,他比我还要早,我到服务台前询问怎么见他,他从旁边的椅子上站起来,走了过来。
他很瘦小,但不算矮,白发,脸瘦削,高颧骨,颧骨部位发红,但脸色苍白。他的右肩膀比左肩膀靠前,好像总是做着握手的动作,所以,整个人看起来是歪斜的。他有一种气场,好像在说:我是大人物。他就是昆丁·奥利弗爵士。
我们找了个桌子坐下来喝雪利酒。他问:“芙蕾尔·塔尔博特——你有一半法国血统吗?”
“没有,芙蕾尔这个名字只是我妈妈想出来的。”
“哦,有意思……好,对了,我来说明下那份工作的内容。”
……
我现在已经在公寓里,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塔尔博特小姐,我不会随便把任何人请到我家里来。”我回答说,可以理解,大家都一样。环顾四周,我看不到书,它们都在玻璃柜里。但昆丁爵士对我的回答——“大家都一样”并不满意,这样显得我和他平起平坐了。他开始解释,说我没听懂他的话。他说:“我的意思是,在这里,我们组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圈子,我们的目的很特殊,这项工作是绝密。请你记住,我面试了六个姑娘,最后选了你,塔尔博特小姐,请你记住这一点。”此时,他已经坐在豪华的桌子后面,靠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双手抱在胸前,指尖相对。我在桌子的另一边坐下。
他挥手指着一个巨大的古董柜说:“秘密都在那里。”
我并不吃惊。尽管他显而易见是个怪胎,并且,我感觉他在做的不会是什么好事,但他的言谈举止没有让我感觉到直接的人身威胁。我很警觉,实际上是兴奋。我正在写的小说,我的第一部,《沃伦德·蔡斯》,完全占据了我的生活。我发现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在我写小说的整个过程中,从第一章开始,我所需要的人物、情境、图像和词语,就这样出现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进入了我的视野。我是一块磁铁,把我需要的经历吸过来。我并没有照原样把它们搬到小说里,我从没想过把昆丁爵士塑造成他本来的样子。我从他那里得到的两样东西让我非常高兴——他指尖相对的样子,还有他挥手指着柜子说“秘密都在那里”,这些文字生动展现出他多么想表现自己,多么渴望能相信自己。我可以马上辞职走人,不再和他见面,也不会想起他,但会带走这两样东西,还有更多。我感觉自己就像他挥手指着的胡桃色柜子,我在心里说道:秘密就在这里。同时,我也关注他。
多年之后,我已经习惯了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艺术思考,但当时我还不太熟悉。提姆斯太太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让我兴奋。她是个糟糕的女人。但我欣赏这种糟糕。我得说,1949年9月的时候,我对于是否能完成《沃伦德·蔡斯》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无论我是否能完成那本书,我都照样为这些人和事感到兴奋。
昆丁爵士继续向我交代工作。提姆斯太太拿来了邮件。
昆丁爵士没理她,只对我说:“我吃完早饭才处理邮件,它们太烦人。”(你得明白,那个年代,邮件都是早上八点到,不用上班的人,边吃早饭边读来信,上班的人在公共汽车上读。)“太烦人了。”在此期间,提姆斯太太走到窗边说:“它们都死了。”她指的是一盆玫瑰,花瓣掉落在桌子上。她收起花瓣,塞进花盆,然后把花盆捧走了。她边做这些边看了我一眼,发现我在看着她。她从我身边走过,我继续看着她刚待过的地方,一副目光呆滞、心不在焉的样子,可能这样成功骗过了她,让她相信我不是有意在观察她,只是盯着她站的地方看罢了,心里在想别的事情。也许我根本没骗她,这种事情很难说清楚的。她走之前一直嘟嘟囔囔说着玫瑰凋零的事。她很像一位熟人的太太,走路的样子也像。
我把注意力转向昆丁爵士,他正等着他的管家离开,两眼半闭,双手的姿势好像要做祷告,胳膊肘搭在椅子扶手上,指尖相对。
他说:“人性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我发现它真的是不可思议。你听说过一句古话吗?事实比小说还要离奇。”
我回答说听过。
记得那是1949年9月的一天,空气干爽,阳光明媚,我记得我看着窗户,阳光不时抚摸着棉布窗帘。听来的东西我记得很牢。当我忆起过去的某次际遇,或者一些旧书信唤起我的记忆,我会一下子想起大量与听觉相关的印象,然后才是视觉形象。因此,我记得昆丁爵士说话的方式、他的确切用词和语调。当时,他对我说:“塔尔博特小姐,你对我说的话感兴趣吗?”
“哦,当然感兴趣啦。是的,我也认为事实比小说更离奇。”
我本以为他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看不到我把头转向了窗户。我明白,我看着别处是为了捕捉我本能的一些想法。
“我有几个朋友。”他说完,停顿下来,以便我能理解他的意思。我恭谨地把目光转向他的话。
“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朋友,都是重要人物。我们成立了一个学会。你懂英国的反诽谤法吗?亲爱的塔尔博特小姐,这些法律可是很详细、很严苛的。例如,不得败坏一位淑女的荣誉,不是指因为对方是淑女而故意这么做。讲述真实的生活经历,自然会涉及仍然在世的人,真的很难做到这一点。你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吗?就是我们这些生活得风生水起的人——我的意思是,我们过着不平凡的一生。你知道我们在为子孙后代记录真相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们成立了一个自传学会。我们已经开始写各自的回忆录,都是真实的,全部是真实的,只记录真相。我们把这些回忆录放在一个安全的所在,等七十年之后,回忆录里提到的人都不在人世的时候,再解封。”他指着那个漂亮的柜子说。些许阳光透过折叠的棉布窗帘,照在柜子上。我很想去公园走走,趁着昆丁爵士暴露出其他东西之前,细想一下他的性格。
“此类文件应该放在银行里保管。”我说道。
“是的,”昆丁爵士不耐烦地说,“你说得对。我们的传记式回忆录最终有可能放到那里去。但那是将来的事。现在,我不得不说,我的朋友们多数都不擅长文学写作;而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承担了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人,无论男女,有丰富的生活经历,非常丰富。那些天翻地覆的日子和战后生活啊,让人难以抱有期望。呃,问题是,我在帮他们写回忆录,他们没有时间。我们组织友好的见面会、聚会、集体活动等。待我们的组织更成熟一些,我们会到我位于诺森伯兰的家里集中。”
这就是他说的话,我喜欢听。在穿过公园走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回味。我已经把它们记下来了。
- 三联生活周刊图书旗舰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