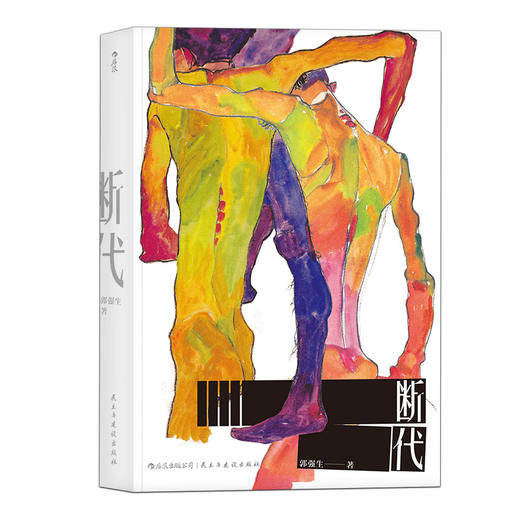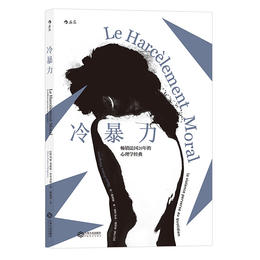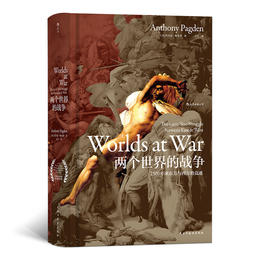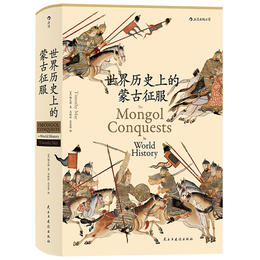商品详情

著 者:郭强生
字 数:193千
书 号:9787513919456
页 数:312
出 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印 张:9.75
尺 寸:143毫米×210毫米
开 本:1/32
版 次:2018年7月第1版
装 帧:平装
印 次: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元
编辑推荐
《断代》是台湾中生代重要小说家郭强生构思二十年的得意之作,为郭强生首次引进大陆的作品,也是郭强生继前两本小说《夜行之子》《惑乡之人》之后,持续状写同志世界的痴嗔贪怨、探勘情欲版图的曲折诡谲,对时间、生命流逝做更进一步省思的经典作品。
《断代》的故事背景,时空承接白先勇的经典同志小说《孽子》,从八〇年代的台湾社会写起,一路写到二十一世纪的当代,在时代的剧烈变迁之间,纵向描绘了一个世代的同志形象。郭强生借这本作品,抛出“爱是什么?”“同志/我的存在究竟是什么?”等终极提问,让我们通过这些问题更清楚地看见自己。
《断代》以推理小说的手法展开,由三条看似关联薄弱的叙事线入手,在同志世界中表演伪装、真假莫辩的氛围里,通过各个角色的心理活动或成长回忆,构筑出一个个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谜题,直至故事的末尾读者一窥故事背后的真相,方得恍然大悟。书中不仅对因同志身份而被迫处于社会边缘的心理刻画入微,更触及了成长、衰老、死亡及死后的“游魂”,运用这些元素,对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爱情,完成了一种立体而独到的诠释。
名人推荐
如果并列《孽子》和郭的同志三书,我们不难发现世代之间的异同。《孽子》处理同志圈的聚散离合,仍然难以摆脱家国伦理的分野。相形之下,郭强生的同志关系则像水银般的流淌,他的人物渗入社会各阶层,以各种身份进行多重人生。两位作家都描写疏离、放逐、不伦,以及无可逃避的罪孽感,但是白先勇慈悲得太多,他总能想象某种(未必见容主流的)伦理的力量,作为笔下孽子们出走与回归的辐辏点。郭强生的夜行之子不愿或不能找寻安顿的方式。在世纪末与世纪初的喧哗里,他们貌似有了更多的自为的空间,却也同时暴露更深的孤独与悲哀。
——文学评论者 王德威
相较于《夜行之子》偶尔流露出辞溢于情的感伤主义,《断代》的文字则更为凝练精准,刻画入微地呈现了同志肉身情欲和爱恨嗔痴的浮世绘,比起白先勇不遑多让;他犀利又深刻地直捣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恐同和恋同的灰色地带,且又将性和政治交互指涉谐仿,可说是直追创作《美国天使》的汤尼·库许纳(Tony Kushner)。
——酷儿与性别理论学者 张霭珠
这部文字沉稳,布局有戏剧的精巧,却又不失之晦涩繁复的长篇小说,处理的是中老年男同志的处境与心境。同志作为台湾异性恋霸权境内的异族,在1990年代同志文学大兴之后,早已不是什么冷僻的文学题材,然而郭强生的视角有其独到之处,从题材到风格,都有别于张致艳丽的“传统”同志文学,自有一股老派的、深厚的底蕴。
——文学评论者 朱宥勳
获奖记录
☆ 2016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小说组入围作品
著者简介
郭强生,1964年生,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纽约大学(NYU)戏剧博士,目前为台湾东华大学英美语文学系教授。曾获时报文学奖、金鼎奖、台湾文学金典奖、开卷好书奖、九歌年度小说奖、金石堂年度十大影响力好书奖等多项大奖肯定。已出版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夜行之子》,长篇小说《惑乡之人》《断代》,散文集《就是舍不得》《何不认真来悲伤》《我将前往的远方》,文学论著《文学公民》等。
内容简介
曾在交际圈风光无限的老七已步入中年,在亲密好友重病离世之后,还是坚持在台北闹区独自守着“美乐地”酒吧。曾经被一个大学生伤得很深的他,对于追求了大半生的爱情,仍然怀着哀怨的心情。
小锺在高中时被同学姚诱惑,却也让他初次尝到情欲的滋味。大学时期他和姚再次相遇,姚的身边多了好同学阿崇,学姐Angela,四人之间的感情复杂暧昧,似假还真。对姚的不解,对未来的迷茫,这些青春的悸动,随着美好黄金年代的逝去,不堪回首。
在便利店打工的阿龙,默默守护女友小闵,打算存够钱之后,小两口一起开一间进口服饰店。他一直怀揣着一个令他困惑羞耻的秘密不愿正视,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对面酒吧的老板倒卧在店内……
通过这些主要角色的回忆和忏情告白,一种特殊边缘身份的集体记忆和情感结构,在郭强生兼具宏观与微观的笔下深刻地展现了出来。
目 录
1 人间夜 1
2 关于姚…… 33
3 旧 欢 51
4 重 逢 71
5 在迷巷 97
6 沙之影 129
7 梦魂中 161
8 勿忘我 183
9 痴 昧 217
10 痴 魅 233
仿佛在痴昧/魑魅的城邦 王德威 285
在纯真失落的痛苦中觉醒——郭强生专访何敬尧采访 297
沙影梦魂,众生情劫:谁是凶手?张霭珠 301
正文赏读
2 关于姚……
我已经对你感到十分着迷,必须向你揭晓,你是何许人也。
——奥斯卡·王尔德,The Picture of Dorian Grey
那时候的台北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高楼,上课不专心时目光闲闲朝窗外瞟去,老树油墨墨的密叶静静晃动,犹如呼吸般吐纳着规律节奏。衬底的天空总是那么干净,即便是阴雨的日子,那种灰也仍是带着透明的润泽。
几朵乌云睡姿慵懒,隔一会儿便翻动一下身子,舒展一下筋骨。
应该就是那样的一个阴雨天,我拎着吉他从社团教室走了出来。
那年用的吉他还是塑胶弦,几年后才换成钢弦吉他。正值校园民歌风靡的巅峰,走到哪里都像是有琴弦琤当背景。走过旧大楼长长的走廊,无心转了个弯,想回自己班级教室看看的这个傍晚,我并不知道这一个转弯将是人生另一条路的起点,更无法料到接下来发生的情节,会在我的记忆中保留一辈子。
十七岁的我看起来跟其他的高中男生没两样,军训帽里塞一小块钢片,把帽子折得昂首挺尾,书包背带收得短短,装进木板把包包撑得又硬又方。功课还过得去,在班上人缘尚佳,但不算那种老师会特别有印象的学生。放了学总不舍得回家,参加了吉他社,练得很勤。成长至今一路都还算循规蹈矩,若问那时的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想象,或许最大的希望是三十岁前能拥有一部车。家庭婚姻这些事还太遥远,大学联考可以等高二以后再来担心。那时从没觉得自己有太大企图心,也从不认为自己相貌出众。生活里除了上课与练吉他之外无啥特别刺激的事,难免也会让这个年纪的我感到有点闷,但顶多也只是被动地跟自己耗着,睡觉看电视发呆,无聊至极的时候,甚至帮还在读小学的弟弟做劳作。我还不会,或是说不想,去处理这种青春期的闲与烦。
那种心情就像是扫地扫出来的一堆灰尘毛球,不去清它的时候好像也就不存在。所以若说十七岁这年的我真有什么可称为遗憾的事,大概就是这种自己也不甚理解的虚耗。一直到这天拎着吉他行过走廊,我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跟其他同学有什么不同。不明白自己的这种被动,或许是在抵抗着什么。
在自己班级的教室外驻足了。
毫无心理准备的我,一步之隔,欲望与懵懂,从此楚河汉界。
角落里最后一排靠窗的那个位子上,有人还坐在那儿。那人低着头,用着完全不标准的姿势握着一管毛笔在赶作文。教室里没开灯,昏暗暗只剩窗口的那点光,落在摊开的作文簿上,那人潦草又浓黑的字迹。
大概因为是留级生的缘故,姚瑞峰在班上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没人清楚他怎么会弄到留级的。他除了体育课时会同班上打成一片外,下课时间多不见人影,还是习惯去找原来已升上高二的那些老同学。发育的年龄,一两岁之差,身量体型就已从男孩转男人了。此人在班上格外显老,一半是因他那已厚实起来的肩膀胸肌,一方面也由于那点留级生的自尊,在小高一面前爱装老成。但是任谁都看得出姚的尴尬处境,班导师从不掩饰对他的不耐,特别爱拿他开刀来杀鸡儆猴:“留级一次还不够吗不想读就去高工高职你们若不是那块料也不必受联考的苦干脆回南部做学徒……”
被罚站的姚立在黑板旁,一身中华商场定做的泛白窄版卡其服,小喇叭裤管尖头皮鞋,没一样合校规,竟然脸上总能出现忏悔的悲伤,让人分不清真假。下了课,其他同学都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避开不去打扰。我的座位就在姚旁边,平常互动虽也不多,但碰到这种情况,我总会等姚回到座位时,默默把自己上一堂课的笔记放在他桌上。
很多中南部的孩子都来挤北部的高中联考,姚也是那种早早北上求学的外宿生。可想而知,家乡父老多开心他考上了北部的明星高中。那表情也许不是装出来的。看见没开灯的教室里的那家伙,不用猜也知他欠了多篇作文。
学期就快结束了,那人正在拼了命补作业。过了这学期,高二开学大家就要重新分组分班。我选了社会组,当教员的父亲并没有反对,觉得将来若能考上个什么特考担任公职也是不错。重理工的年代,社会组同学铁定是不会留在原班级了。站在教室外,想到过去这一年,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回忆。
若真要说,可能就是姓姚的这个留级生吧?出于同侪的关心,我常会注意姚的成绩究竟有没有起色,奇怪他每天都在忙什么,怎么作业永远缺交被罚?
因为他的漫不经心,因为他两天不刮就要被教官警告的胡渣,因为他那张塞满了球鞋运动裤漫画作业簿参考书的课桌椅,都让我无法忽视姚的存在。
姚惯把东西留在学校不带回家,外地生没有自己的家。一个学期下来,他的杂物持续膨胀,多了雨伞泳裤汗衫篮球与工艺课的木工作业,颇为可观。有的塞在课桌椅的抽屉里,有的藏在座位底下,或挂在椅背上,猛一看像是有某个流浪汉,趁放学后教室无人偷偷溜进来筑起了克难的巢。
发现有人走到身边,姚没停笔,匆忙看了我一眼。“喀喀喀,我完蛋了,今天补不出来我国文要被当了!”
那家伙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好心情,让我吃了一惊。
“你怎么还没回家?”
“刚刚社团练完。”
那家伙停下笔。“让我看你的吉他。”他说。
没想到接过吉他姚就行云流水拨弹起来了,金克洛契《瓶中岁月》(即Jim Croce 演唱的Time in a bottle)的前奏。只弹了前奏,唱的部分要出现的时候他就停了,把吉他还回我手上。
“我破锣嗓子。”那人道。
两人接下来并不交谈。我也没打算走,对方也不介意有人一直在旁边看他鬼画符。校园变得好安静,刚刚姚弹过的那段旋律仿佛一直还飘在空气中。突然觉得这景象有趣,我想象着自己也是离家的学生,和姚是室友,我们常常晚上就像现在这样,窝在我们共同租来的小房间里。
室友,多么新鲜的名词。不是同学,不是兄弟,就是室友。在家里排行老大的我,底下两个弟妹,一个国中,另一个才国小。回到家里对弟妹最常出口的一句话就是:“出去啦!不要随便进我房间!”但是那一天的黄昏,和姚这样自然地独处在教室的角落,一个假装的房间,我第一次发现到,男生在一块儿不一定就得成群结伙吃冰打球。
“你唱歌给我听。”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唱歌应该很好听。”
“为什么?”
“因为你说话的声音很好听啊!”
那家伙并不抬头,翻起作文簿算算到底写了几页,又再继续振笔疾书。
“怎么样叫说话声音很好听?”
“嗯…… 就是,睡觉前听的话会很舒服的那种。”
“喔,你意思是说,像李季准那种午夜电台的播音员吗?”
也不懂这句话哪里好笑,竟惹得那家伙先是扑哧一声,接着一发不可收拾:“哈哈哈—对对,哈哈哈,就像那样。”
平常只见姚爱摆一张酷脸,要不歪着嘴角笑得顶邪门。原来那人大笑起来是这样的。他这样开朗的笑容很好看,我也跟着笑了。
★
姚的长相称不上帅,至少在当年还剃着平头,土气未脱的时期,他不会是让人一眼留下深刻印象的那型。五官比例中鼻子有点嫌大,一脸青春痘被挤得红疮疮的,那口整齐的白牙齿恐怕是他最大的加分。但是他的笑声让人觉得很温暖,平日吊儿郎当的留级生其实一点也不顽劣。眼前的姚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迷人的组合了,一个还带着童心的,十八岁的,男人。
只有两人独处的当下,那家伙仿佛变了一个人。果真就为他唱完了那首《瓶中岁月》。姚要我再唱一首,说是这样写作业才不无聊。但是这回姚没有安静地听歌,我一面唱,姚一面插话跟我聊起天。
“ㄟ(即拼音ei)我跟你说,我前几天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
姚的语气平淡低缓,顿挫中和吉他的弦音巧妙呼应着,有一种奇特的温柔。我等对方继续开口。
“晚上差不多快十二点了—啊?我也忘了我那天在干吗。对啦跟以前的同学打弹子(即打台球)。反正我常常在街上晃到很晚。这个不重要。快十二点了。我在火车站那边,等了半天公车也没来,大概已经收班了,我就想用走的吧也还好。然后有一辆车就停到我身边。我觉得我在等公车的时候那辆车好像就在附近了。车子停下来,一个大概三十多岁的男的摇下车窗问我需不需要搭便车。那个人西装笔挺,还蛮帅的,我想说也好啊,男生搭便车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对不对?上车就闲聊啊,我也没注意他好像在绕远路。我跟他说我住外面的学生套房,他就问我一个月多少钱,然后跟我说很贵,他家空房间很多,可以租给我,打八折。平常他经常出差不在家,所以等于我一个人住四十坪(约合132.16 平方米),他也希望有人看家比较安心。我想就去看看吧,搞不好还真给我碰上这种好运——”
和弦早已不成调了。是姚这样乡下出来的男生不懂得防人?还是像我这样的台北小孩太过警觉世故?
突然不希望对方再讲下去,同时却又非常想知道后来发生的事。
“到了他家,他又说太晚了。要不就干脆睡他那里。他家在内湖嗳,我已经累了,就想说别再跑来跑去了。他家只有一张床,不过两个男生,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我先洗完澡就睡下去了,过一会儿醒来发现他躺在我旁边,用手在摸我那边。干!我跳起来,教他不要这样,很变态耶!我实在很困,但是他就不让我睡,一直摸我,我最后受不了了,跟他说我要回去了。”
“那他…… 那个人就开车送你回去了?”
“当然没有。我跟他说我要坐计程车,给我五百块。离开的时候已经早上快五点了。我最后是走去总站等第一班公车。”
想象中共租的小房间里已经没有音乐了。姚说,没想到给他赚到了五百块。
开始感觉到晕眩。上下学通勤的公车上,我也碰过类似这种教人不舒服的事。
沙丁鱼罐的空间里,有人在后面顶。不是偶然的擦撞,而是有规律地,持续地,朝着身上同一个部位。根本连旋身回头都不可能的车厢人堆里,碰到这种事只能假装毫无反应,闭起眼默背着英文单字。从没跟任何同学问起,是否他们也碰过这种令人厌恶、又教人不知所措的经验,因为难以启齿。
羞愧。为什么是挑中自己?
震惊。那会是什么样的人如此胆大包天?
下意识里某个看不见的警铃已经从那时候开始时时作响。如今回想起来,那种偷偷摸摸只敢在对方身后如动物般摩挲的低劣举动,已悄悄启动了我对自己身体突然产生的自觉意识。
我已经发育得差不多快成年的男体。
不敢向任何人提起公车事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真正厌恶的是那种偷袭的行为,而非有人对我的身体有如此的兴趣。
国中时跟比较要好的男同学牵手勾肩也是常有的,整个人趴伏在对方冒出闷湿体热的背上,有一种很安心的亲切感。但上了高中后,班上同学便很少再有类似昵玩的行为。为什么其他人就比我先明白了?明白大家现在拥有的已经是不一样的身体,不再是不分彼此。现在的这具以后将有不同的用途,十七岁的我不是不知道答案。但想到这具身体将成为生殖制造的器具,想到和女生裸裎相对,我的惊慌不亚于被陌生男人触撞。
公车上的偷袭令我感觉到污秽,并非因为身体受到侵犯,而是被这样污秽的人挑中,成为猥亵对象。这似乎是在暗指,我与他们根本是同路货色。
害怕自己身上或许已散发了某种不自知的淫贱气味,已被对方认出,正好借此恐吓:你的存在已经被发现了,莫想再继续伪装了,我们随时可以将你绑架,带你回到那个你本应该属于的世界,如果你敢不乖乖就范的话……
但是这种事姚竟然在旁人面前说得如此坦然。
那么现在该轮到我来说在公车上的遭遇吗?大家交换了这种秘密以后就算哥儿们了,是这样吗?我不安地避开姚的注视。
- 后浪图书旗舰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后浪出版公司官方微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