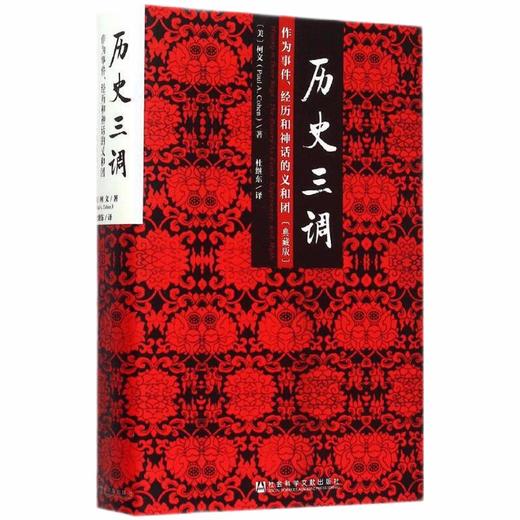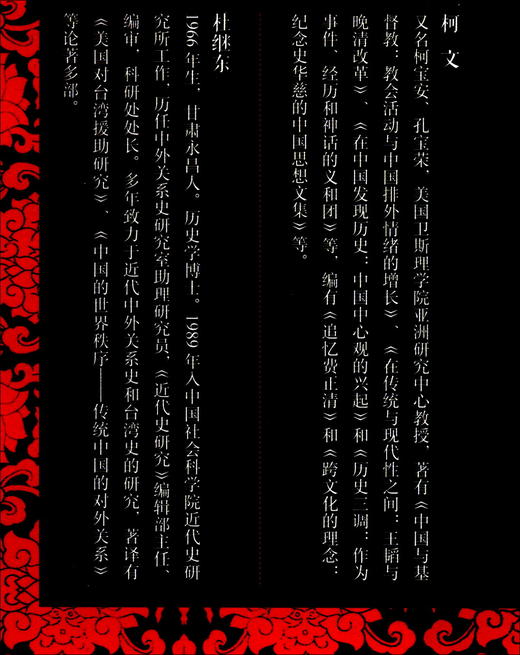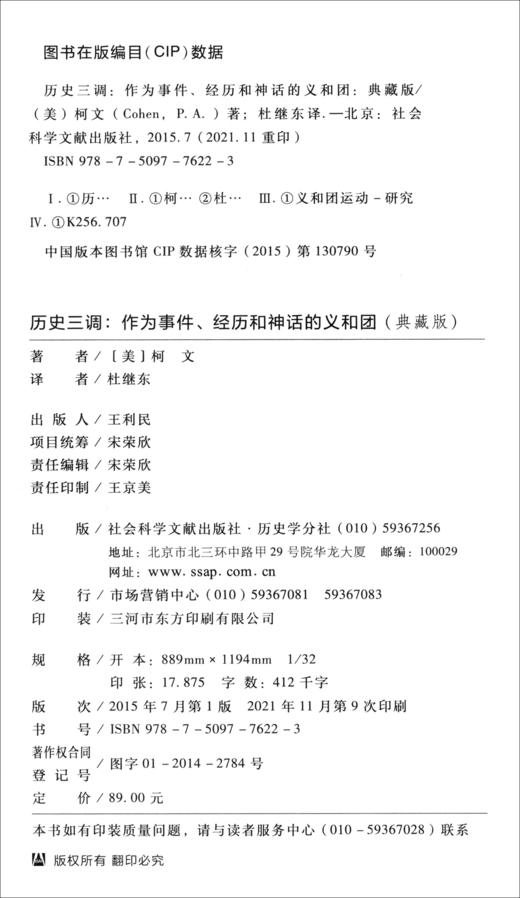商品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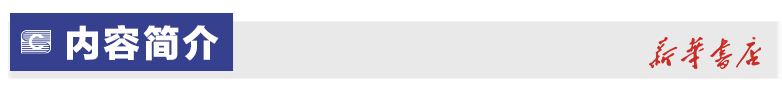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典藏版)》荣获1997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东亚历史学奖,1997年新英格兰历史学会图书奖。书中以义和团为例向人们解说了认识历史的三条不同途径,即历史的三调:事件、经历和神话。该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讲述义和团的历史,而在于探讨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配角’。”
因此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历史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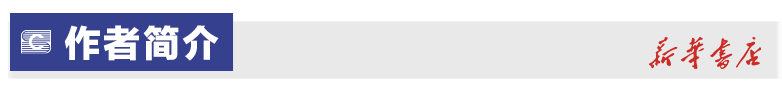
柯文(Paul A.Cohen),又名柯宝安、孔宝荣,男,美国人,1934年6月出生于美国纽约。美国卫斯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53年入芝加哥大学接受本科教育,1955年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s) 教授和史华兹 (Benjamin I. Schwartz) 教授开始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62年至1965年,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安默斯特学院任教。1965年到麻州卫斯利学院任亚洲研究和历史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卫斯利女子学院历史系主任,并将其主要精力都放到了教学之中。

史学家就是翻译家
中文再版序
英文版序
鸣谢
第一部分 作为事件的义和团
绪论 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
第一章 义和团起义:叙事化的历史
第二部分 作为经历的义和团
绪论 人们经历的过去
第二章 干旱和洋人洋物的存在
第三章 降神附体
第四章 法术与妇女秽物败法
第五章 谣言和谣言引起的恐慌
第六章 死亡
第三部分 作为神话的义和团
绪论 被神话化的过去
第七章 新文化运动与义和团
第八章 反对帝国主义与义和团神话的重构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与义和团
结论
缩略语
注释
文献目录
索引
主要外国人名地名对照表
译后记……精彩书摘
正如周锡瑞的研究所表明的,这种权力真空状态也为野心勃勃的天主教教派——安治泰领导的天主教圣言会提供了在该地区建立和稳固传教据点的机会(始于19世纪80年代末)。教民数量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是教会吸收了一些违法分子(自1860年基督教传教工作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以来,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不法之徒被教会的保护伞所吸引,因为急于招收教徒的传教士是不受大清法律约束的。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与土匪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例如,在1895年,大刀会打败了一大股土匪,其中一些匪徒因害怕被“富人”捉拿,就信了天主教),天主教与大刀会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1896年春夏,大刀会在江苏和山东交界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攻击教民及其财产的行动。这些行动是苏北某地的一场土地划界纠纷引发的,与天主教的教义无关。虽然这些行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教民和传教士无一伤亡),但在此过程中,大刀会的纪律严重败坏,当大刀会由(或多或少受到欢迎的)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变成(绝对不受欢迎的)骚乱制造者时,(由后来担任山东巡抚的毓贤领导的)当地政府就开始转而对付大刀会的首领了。刘士端和其他大刀会首领(共约30人)被逮捕处死,虽然大刀会组织没有彻底消亡,但它在鲁西南的高潮时期已经结束了。
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一系列事件,如果不发生义和团起义(或者其规模没有那么大),上文所述的历史很可能不会受到历史学家们的重视。即使受到重视,也会被赋予不同的含义。然而,大刀会失败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使得该组织在1895~1896年的活动具有了值得回味的重要意义,也使该组织在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
中文再版序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 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英文本出版于1997年)中文译本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对此我深感荣幸,并想借此机会就当初的工作及其与我近年来的著述之间 的关系向中国读者做一些说明。对于一名经常被人们与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国中心观联系起来的学者而言,《历史三调》代表着我学术方向的重大转变。毫无疑问,我 在本书中用很大的篇幅努力探寻义和团及1900年居住在华北平原的其他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就此而言,研究方法也许可以被视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但是,我也对 当时卷入事件中的外国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感兴趣(尽管程度大为降低),且经常指出中外双方的共同点,展示了(至少在某些时刻)一种比中国中心观更具有普 遍人性的研究方法。
更重要的是(正如我在本书中说明的),我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 作的'配角'"。这与历史研究的惯常程序大不相同。在此类研究中(不仅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在其他研究领域也是一样),作者们往往把自己的情感置于一个 广泛的参考框架中得出结论,希望以此加强其研究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我在《历史三调》的开篇即提出一系列问题,但从未回答这些问题。虽然我把义和团当作延 展的个案进行研究,但我在结论部分特别说明,在义和团与我感兴趣的重大问题之间,没有必然的或独一无二的联系。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其他许多事件,也能被用来 达到这个目的。本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对中国历史有所说明,而在于对历史撰述有关的普遍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与中国中心观没有特别的关联。
在 西方学术界日益流行的关于中国的其他研究主题,也对中国中心观提出了挑战,在某些情况下,它被弃之不用,但在更多情况下,研究者把它与其他研究方法微妙地 结合起来加以发挥。大约30年前,当我初次描述中国中心观时,我明确地把它与中国历史研究联系起来。《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我确实把介绍中国中心观的 那一章题为"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只要历史学家们选择研究的主题大致明确地集中在中国的某个领域(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宗教领域)__ 尽管近年来学术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但这还是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__那么,在我看来,中国中心观就仍然是非常有用的。不过,中国中 心观是有局限的。 当学者们探讨一些"去中国中心"的课题及研究方向,包括跨国的历史现象 (如移民、现代全球经济的出现、亚洲区域体制的演变) 或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问题(如研究历史的多种方法、比较史学研究)时,或将中国从一个实体的空间"非地域化",又或将"中国"重新定义 (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自我认知)时,中国中心观就不适用了。
这些研究方向虽然指出了狭义的中国中心观的局限性,但对中 国史研究却做出了超乎想象的重大贡献。其中一些贡献是通过下述途径实现的:它们消除了数世纪以来围绕"中国"而人为创设的种种壁垒(中国人与西方人创设的 一样多);它们颠覆了关于中国历史的狭隘论述(出自中国历史学家之手的不比出自西方历史学家之手的少);它们丰富了我们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对"中 国"的了解和认知;它们使我们能够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更客观公正(更少偏向)的比较研究;它们还通过打破武断的和误导性的关于"东方"和"西方"的 区分,纠正了我们(西方人)长期以来作为典型的"他者"对中国的看法,使我们能够不把中国__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__视为典型的异类,而视为正常的同类。
我 想对最后一点做详细解释,因为它已成为我研究工作中越来越重要的关注点。西方人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的看法是夸大其词、不符合实际的,这些看 法往往(虽然不全是)来源于西方中心观。我要特别指出,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我在所有论著中都是严肃地看待文化问题的,从未否认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存在着 重大的差异。但是,我同时也认为,过分强调这些差异的历史研究方法容易导致这样那样令人惋惜的扭曲甚至夸大。其中一种扭曲是以文化本质化__断然赋予一种 文化一些特殊的、据信其他文化不可能具有的价值或特征__的形式出现的。例如,正如阿玛蒂亚;森极其雄辩地指出的,极权主义的东方和自由宽容的西方这类老 套说法,容易遮蔽这样的可能性:印度或中国在历史上或许也具有宽容或自由的传统,极权主义或许也是西方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特点。实际上,这些传统看法完全不 符合历史事实。阿玛蒂亚;森指出,"说到自由和宽容",如果优先考虑思想的实质内容而非文化或地区的话,可能更有意义的是"把亚里士多德和阿育王归为一 类,把柏拉图、奥古斯丁和考底利耶归为另一类"。
当历史学家试图理解另外一种文化中生活的人民时,如果过分强调文化的差异性,不 仅使人们更难以理解那个文化中那些复杂的、常常矛盾的因素,难以理解那个文化的前后变化,而且看不到这些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中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的思想 和行为重合或呼应的那些反映跨文化和人类内在特点的方面。我认为,如果我们想对中国人的过去进行更充分、更丰富、更公正的了解和认知,我们就必须同时重视 这个普世特点和文化的差异性。重视这个特点,也是我们超越西方和中国历史学家(尽管运用不同的方式,出于不同的原因)常常对中国和中国历史设定的壁垒和边 界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虽然我在大约50年前发表的关于王韬的一篇论文中,就初次探讨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融合或共鸣问题,及其所 反映的人类基本心理倾向,但直到我研究义和团起义时,我才开始深入思考这个观点。在《历史三调》中,当我竭力对义和团的思想和行为给予"合理化"或"人性 化"的解释时,我常常依靠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且常常扩大中国的"他者"范围,除了西方以外,把非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包括进来。当我讨论1900年 春夏义和团危机高潮时期华北出现谣言和群体性歇斯底里时,我就使用了这样一个事例。当时流传最广的一个谣言是说洋人和中国教民往各村的井里投毒,污染水 源。据时人记载,井中投毒的指控"随处可闻",是挑动中国老百姓"仇视"教民的"重要因素"。
一个有趣的问题与这个事例中群体性 歇斯底里有关。为什么向大众投毒?特别是,为什么向公共水源投毒?如果我们认可这样的说法,即谣言(一种形式的叙事或故事)传递了信息,谣言的大范围传播 反映了与社会危机中民众的群体性忧虑相关的重要且具有象征意义的信息,那么,解答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努力确定谣言引起的恐慌与产生谣言的环境之间是否具有 密切的关联性。绑架引起恐慌的现象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区都有很长的历史。在这样的事例中,人们最关心的是孩子们的安全,正如"绑架" (kidnap)一词所表明的,孩子们往往是主要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向民众投毒的谣言,是全体成员都处于潜在的危险中的人们对诸如战争、自然灾害或流行 性疾病等重大危机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反应。
对其他社会的经验加以考察,可以充分证实这个推论。投毒和其他类似的罪行,在罗马时期被 栽赃给第一批基督徒,在中世纪黑死病流行时期(1348年)则被栽赃给犹太人。1832年巴黎流行霍乱期间,有谣言说毒粉已被广泛投布于该市的面包、蔬 菜、牛奶和水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参战的所有国家都流传着敌方特务正在向水源投毒的谣言。1923年9月1日东京大地震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地震引发 了熊熊烈火),谣言即开始流传,指控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不仅纵火烧城,而且密谋叛乱并向井中投毒。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新闻报道即指责汉奸往 上海的饮用水中投毒。20世纪60年代末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比夫拉地区就盛传着向民众投毒的谣言。
在许多此类事例中,谣言都指向 外来者(或内奸),他们被或隐讳或明确地指控试图毁灭谣言流传的那个社会。这种现象与义和团起义时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的人们指责教民挑战中国神祇的 权威,应该对1900年春夏华北的干旱负全责。与此相同,指责洋人和他们的中国追随者向华北的水源投毒的谣言,把外来者描绘成剥夺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最重要 物质的坏人。关于井中投毒的谣言的广泛流传,直接反映了当时老百姓最沉重的群体性忧虑:对死亡的忧虑。
2001年夏我做了一次关 于义和团的演讲,我想引用其中的一个论点,对我关于过分重视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这些问题的讨论做一个总结。那次演讲的题目是人们不大可能用的"对义和团的人 性化解读"(听众主要是西方人,有一些挑战性)。我在演讲中所持的立场为:文化是各个族群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展现自身特点的多棱镜。除此以外,文化还具有疏 远族群之间关系的潜能,由此加快了模式化、夸张化和神话化的进程。鉴于整个20世纪义和团在中国和西方一直处在这一不同寻常的进程中,我在演讲中竭力说明 义和团与生活在面临类似挑战的其他文化中的人民有哪些共同点。我没有否认义和团的文化独特性(当然也没有把他们描述为天使),我只是要纠正所谓的非人性化 例外论,这种理论几乎从一开始就导致了对义和团历史的误解和扭曲。
。。。。。。
- 新华一城书集 (微信公众号认证)
- 上海新华书店官方微信书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