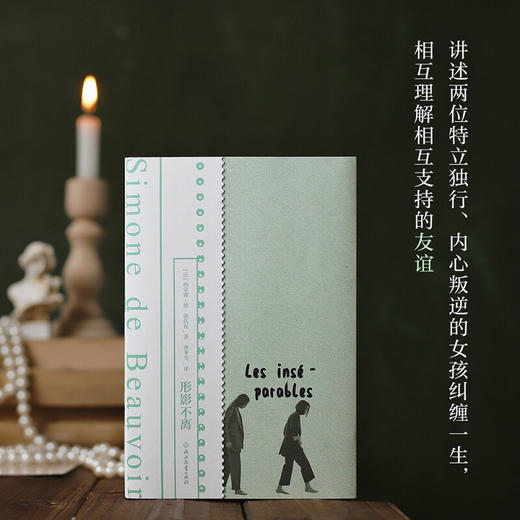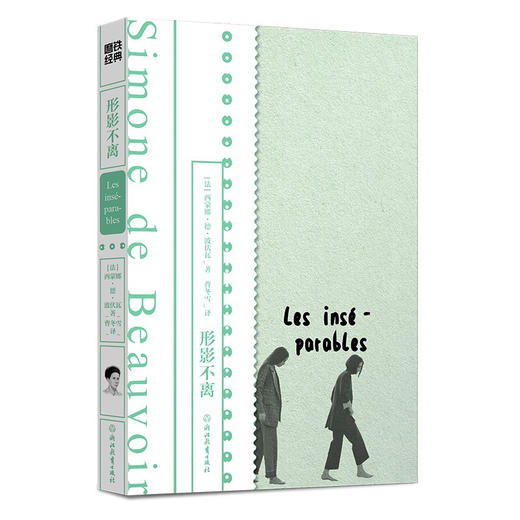我认识的所有孩子都让我感到厌烦,但安德蕾不一样。课间活动的时候,我们俩一起散步,从一间教室走到另一间,她总能把我逗乐:一会儿形神毕肖地模仿杜布瓦小姐那些突然的动作,一会儿模仿校长汪德鲁小姐柔滑的嗓音。她从她姐姐那儿知晓了一大堆学校的小秘密:这些女老师属于耶稣会,头发边分的是初习修女,发了誓愿之后,头发会改成中分。杜布瓦小姐才三十岁,是她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她去年参加了中学毕业会考,一些高年级学生在索邦见到了她,她当时红着脸,为自己的裙子感到窘迫。安德蕾的大胆无礼让我有些愤慨,但我觉得她非常有趣,当她即兴表演两位老师的对话时,我帮她演对手戏。她对老师们的夸张模仿惟妙惟肖,上课时看到杜布瓦小姐打开点名册或合上一本书,我们俩经常心照不宣地碰个肘。有一次我甚至捧腹大笑,要不是平时举止端庄、品行良好,老师早就让我站到门外去了。
刚去安德蕾家玩的时候,我惊愕不已:除了她的兄弟姐妹,安德蕾家还有格雷奈尔街她亲戚家的一群小孩和其他玩伴,所有这些孩子追着跑着、喊着唱着,乔装打扮成各种模样,一会儿跳上桌子,一会儿掀翻椅子。有时玛璐会出来干涉一番,她十五岁了,喜欢摆出一副小大人的神气,但她刚一出面,卡拉尔夫人就说:“让这些孩子玩吧。”我感到不可思议:孩子们万一在哪儿磕破摔肿,弄脏衣服,打碎盘子,她也居然无所谓。“妈妈从不生气。”安德蕾边说边露出胜利的微笑。黄昏将至,卡拉尔夫人走进被我们蹂躏过的那间房,扶起东倒西歪的椅子,擦一擦安德蕾的额头:“你还一头的汗!”安德蕾紧紧贴着母亲,有那么一瞬间,她的脸庞起了微妙的变化。我觉得有些不自在,便扭头不再看她,尴尬中也许还混有几分嫉妒、些许渴望,以及对神秘事物怀有的那种恐惧。
人们告诉我,应平等地爱爸爸妈妈。安德蕾毫不掩饰她爱妈妈甚于爸爸。“爸爸太严肃了。”有一天她平静地告诉我。卡拉尔先生让我感到困惑,因为他跟我爸爸很不一样。我父亲从不去做弥撒,我们跟他说起卢尔德奇迹时,他只是笑笑。我听他说,他只有一个宗教信仰,那就是对法国的爱。父亲不信教,对此我并不感到难为情,就连极为虔诚的妈妈似乎也觉得他很正常。一个像爸爸这样的高等男人,不同于女人和小女孩,他跟上帝一定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相反,卡拉尔先生每周日都跟全家人一起去领圣体,他蓄着长胡须,戴一副夹鼻眼镜,空闲时忙于慈善事业。在我眼中,他光滑的毛发和基督教美德让他变得女性化,贬低了他的地位。我们只有在极少的场合才能见到他。家中事务都是卡拉尔夫人在操持。我很羡慕她给予安德蕾的那种自由,不过,虽然她总是一团和气地跟我讲话,但在她面前我总感到不太自在。
有时安德蕾对我说:“我玩累了。”我们就去卡拉尔先生的书房坐下,不开灯,这样别人就无法发现我们。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这真是一种全新的乐趣。平时父母跟我说话,我也跟他们说话,但我们不是在聊天。跟安德蕾是真正的交谈,就像爸爸在晚上跟妈妈的那种交谈一样。安德蕾在烧伤康复阶段读了很多书,令我吃惊的是,她对书里的那些故事似乎信以为真:她讨厌贺拉斯和波利厄克特,欣赏堂吉诃德与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仿佛这些人有血有肉地存在过一样。对于历史长河中的人与事,她也有着泾渭分明的立场:她热爱希腊,厌恶罗马;对路易十七及其家族发生的不幸无动于衷,却为拿破仑之死黯然神伤。
她的很多观点都具有颠覆性,但鉴于她尚且年幼,老师们也就原谅她了。“这孩子很有个性。”学校的人这样说她。没过多久,安德蕾便补上了落下的功课,我差点没能超过她的写作成绩。她很光荣地将自己的两篇作文抄写在学校范文本上。她钢琴弹得很好,一下步入中等生行列,她也开始学小提琴。她不喜欢缝纫,但心灵手巧,熬制焦糖、做油酥饼、做松露巧克力球,样样在行。虽体形娇弱,但她会侧翻筋斗、跨一字,做各种翻转动作。不过,在我眼中,她最大的魅力并不在这些方面,而在于一些我从未真正理解的奇怪特征:当她看见一只桃子或一朵兰花,甚至仅仅听到别人在她面前提到桃子或兰花时,她就会微微颤抖,胳膊上起一层鸡皮疙瘩。在这一刻,个性—她从上天那儿得到的馈赠,以最动人心魄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惊叹不已。我心里暗想:安德蕾一定是那种神童,将来会有人为她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