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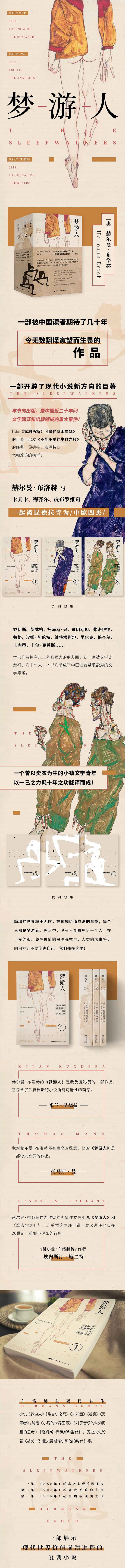

书名: 梦游人
定价: 198
作者: 赫尔曼·布洛赫
装帧: 平装
开本: 16
用纸: 轻型纸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18143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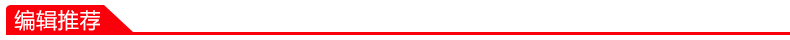
赫尔曼·布洛赫与卡夫卡、穆齐尔、贡布罗维奇一起被昆德拉誉为“中欧伟大的四位小说家”。
一部被中国读者期待了几十年,令无数翻译家望而生畏的重量级作品!
本书的出版,是中国近二十年间文学翻译和出版领域的重大事件!比肩《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的巨著,启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经典,昆德拉、富恩特斯竞相效仿的榜样!

《梦游人》是布洛赫的长篇小说,创作于1928年至1931年间,是一部开辟了现代小说新方向的巨著。小说分为三个部分,从1888年德皇威廉二世登基开始,到1918年他退位为止,跨越了威廉二世的整个统治生涯,展现了现代世界的价值崩溃的进程。
小说一部《1888年:帕塞诺夫或浪漫主义》展现的是价值崩溃的一个阶段,传统的价值观开始衰落,但依旧是确定的。主人公约阿希姆·冯·帕塞诺夫遵循长子继承庄园、次子从军的传统,成为一名中尉,而其好友贝特兰德则背离传统价值,退伍后成为一名商人。后来,约阿希姆因其兄长死于一场决斗而退出军队,回家顶替兄长接管庄园,并在妓女卢泽娜和隔壁庄园主的女儿伊丽莎白之间周旋挣扎,尽管感到无助,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依附于传统的价值系统,与门当户对的伊丽莎白结婚。
小说第二部《1903年:埃施或无政府主义》展现的是价值崩溃的第二个阶段,价值观已经蒙上面纱,陷入混乱状态,人只能盲目地抓住他视为价值的东西。主人公埃施在科隆丢掉了簿记员的工作,怒火中烧,试图向警察局检举同事南特维希,最后却寄出了一封举报贝特兰德的信。在这中间,工会领导人马丁·盖林格给埃施在曼海姆的码头找了一份仓库办事员的差事,埃施在那里认识了海关检查员科尔恩,后者想把自己的妹妹埃尔娜嫁给他,他则为了将飞刀表演者的女搭档伊隆娜从危险的表演中“拯救”出来而辞掉工作,组织起了女子摔跤比赛。事业再次挫败后,埃施回到了科隆,与他的旧相识、酒馆老板娘亨特延大嫂结婚,试图以此使混乱的世界恢复秩序。
小说第三部《1918年:胡格瑙或现实主义》展现的是价值崩溃的第三个阶段,人在不受价值束缚的世界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主人公胡格瑙逃离军队,在摩泽尔小城“度假”,遇到小城军队指挥官约阿希姆·冯·帕塞诺夫少校和当地一份报纸的发行人埃施,他冒充一家子虚乌有的集团的代理人,买下埃施的报纸,却在战争末期的动荡与混乱中杀死了埃施,并胁迫埃施太太与自己发生关系,之后过上了小资产阶级商人的安稳生活。与这一主要情节平行的,还有小城里一位律师的妻子汉娜·文德林、在埃施家里的孤儿玛格丽特、曾被埋在战壕里的泥瓦匠格迪克,以及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和伤员的故事。此外,还穿插着十篇论述“价值崩溃”的随笔和十六篇“柏林救世军姑娘的故事”,而“柏林救世军姑娘的故事”的叙述者“我”(贝特兰德·米勒,哲学博士),也是“价值崩溃”随笔的作者。前两部中连贯的叙述在第三部中被这种“复调叙事”打破,哲理随笔、抒情散文、诗歌、戏剧、报刊文章、商业信函等文体轮番上阵,这种同一主题下的变奏丰富了小说形式的可能性,也暗合了小说所要展现的在不同理性层面走向价值崩溃的主题。

第一部 1888年:帕塞诺夫或浪漫主义
第二部 1903年:埃施或无政府主义
第三部 1918年:胡格瑙或现实主义

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1886.11.1—1951.5.30),奥地利小说家,与卡夫卡、穆齐尔、贡布罗维奇一起被昆德拉誉为“中欧伟大的四位小说家”。布洛赫生于维也纳,父亲是纺织厂老板,母亲是犹太富商的女儿,他在20岁时接管父亲的纺织厂,后结识卡尔·克劳斯、托马斯·曼、茨威格、罗伯特·穆齐尔、埃利亚斯·卡内蒂、爱因斯坦等人,40岁时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心理学和哲学,45岁时出版首部长篇小说《梦游人》,1938年流亡美国,1944年成为美国公民,晚年主要从事群众心理学研究,1950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次年心脏病发作,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去世。主要代表作有小说《梦游人》《维吉尔之死》《未知量》《着魔》《无罪者》,随笔《小说的世界图景》《对于音乐的认知问题的思考》《詹姆斯·乔伊斯和当代》,以及历史文化论著《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和他的时代》等。

第一部 第一章(节选)
卢泽娜被约阿希姆在餐厅里表现出来的那种传统的拘谨客气迷住了,她愉快得甚至忘了自己对他穿便服出现感到的失望。那是一个凉爽的雨天;但她不想放弃自己的安排,所以在午餐过后,他们乘着马车穿过夏洛滕堡驶向哈维尔河。卢泽娜在马车里已经摘下了约阿希姆的一只手套,现在他们沿着河边的小径散步,她拉起他的手臂,挽着。他们缓步前行,穿过一片景色,这片景色在寂静中满怀期待,然而能够期待的只有雨水和夜晚。天空柔和地悬浮着,有时和大地被一片雨水的面纱牢牢地联结在一起,而对于在寂静中漫步的他们来说,似乎同样除了期待便一无所有,他们十指交叉紧扣在一起,犹如尚未绽放的蓓蕾上的花瓣,而他们的整个生命仿佛都涌上了指尖。他们肩并着肩,从远处看像是一个三角形的两边,一言不发地沿着河边的小路往前走,也不知道将他们拉到一起的是什么。但走着走着,卢泽娜出人意料地弯腰俯向他放在她手中的手,在他还没来得及抽开的时候,吻了一下。他望着那噙满泪水的双眼,望着因啜泣而抽搐的双唇,总算说道:“当你在楼梯上遇到我的时候,我说,卢泽娜,我说,他是得不到你的,永远得不到。而此刻你就在这里……”但她并没有抬起嘴巴,迎接那预期的一吻,而是近乎贪婪地再次俯向他的手,当他试图把手抽开的时候,她就用牙齿咬,不过并不用力,只是像一只小狗在玩耍一样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咬,接着,她满意地看着那个印记,说道:“现在我们,接着走吧。下雨,没关系。”雨静静地落在河里,在柳叶上发出轻柔的沙沙声。一只小船半沉在河岸附近;在一座小木桥下,一股细流更加迅速地倾入平静的河流中,而约阿希姆同样觉得自己漂走了,仿佛充盈着他的渴望的是他心中一股柔和、轻盈的溢出物,一股呼吸的洪流,渴望与心上人的呼吸混合在一起,迷失在无限安宁的海洋里。夏天仿佛融化了,雨水显得很轻盈,从树叶上淅淅沥沥地滴落下来,垂悬在草叶上,晶莹剔透。一片柔和的雾纱在远处升起,当他们转身的时候,雾已经在身后将他们包裹住,因而他们走着却像是站在原地不动。雨下得更大了,他们躲到了树下,树下的土地依然是干燥的,这片遭到禁锢的夏天残骸在周围得到释放的事物中几乎显得可怜巴巴。卢泽娜摘下帽针,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拘束令她厌烦,而且也是为了避免针尖扎到约阿希姆,她脱下帽子,背靠着他,仿佛他是一株能够庇护她的树。她向后仰起头,而他则把头垂下,他的双唇触到了她的额头以及额前漆黑的鬈发。他没有看到她额头上淡淡的、有点愚蠢的沟纹,或许是因为他靠得太近,没法看出来,又或许是因为视觉已经彻底融化为感觉。她感觉到他的双臂环抱着她,他的手握在她手里,她觉得自己仿佛在一棵树的枝杈间,而他在她额头上的呼吸就像雨水在树叶上淅淅作响;他们纹丝不动地站着,灰蒙蒙的天空与水流融为一体,小岛上的柳树仿佛漂浮在一片灰蒙蒙的虚幻的海上,不知道是上面那一片还是下面那一片海。但紧接着,她看到自己外套的袖子湿漉漉的,便柔声低语地说他们得回去了。
然而,尽管雨水打在脸上,他们还是不敢太匆促,因为这会驱散其中的魅力,直到在一间小旅馆里喝着咖啡,他们才回过神来。现在,雨水越来越急剧地敲打着走廊上的窗玻璃,同时薄薄地在檐沟上溅起。只要女店主一离开房间,卢泽娜就会放下自己的杯子,再拿走他手中的杯子,然后捧着他的头,向自己的头靠近,那么近——他们还未曾接吻呢——他们的目光交融在一起,那股甜蜜的紧张情绪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接着,他们坐在有车顶覆盖、雨篷垂下的马车里,如同置身于一个漆黑的洞穴,雨落在他们头顶的皮革上,发出微弱、柔和的滴答声,透过两边的窗口望出去,除了车夫的斗篷和两条湿漉漉、灰蒙蒙的马路,就再也看不到世上的任何东西了,而紧接着连这些都看不到了,他们的脸垂向彼此,相碰,交融在一起,如河流一样梦幻着,流淌着,不可挽回地迷失,再次发现,又再次永远沉没。这是一个持续了一小时十四分钟的吻。接着,马车停在了卢泽娜家门口。然而,当他打算和她一起进去的时候,她摇了摇头,他便转身走了;但是,与她分开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他走了几步又转身回来,在自身恐惧的驱使和她的恐惧的拉动下,抓住她在渴望中依然一动不动地伸着的手;他们如同已经沉入睡梦的梦游者一样,登上在他们脚下嘎吱作响的漆黑的楼梯,穿过漆黑的门厅,进入昏暗的雨天中的卧室,倒在盖着暗色厚毛毯的床上,再次寻找已经被夺走的吻,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脸是被雨水还是被泪水打湿了。接着,卢泽娜挣脱了出来,引导他的手来到她衣服后背的扣子上,她歌唱般的声音是幽暗的。“解开。”她低声说道,同时扯开了他的领带和背心的纽扣。接着,仿佛由于一阵突如其来的谦卑,说不清是对他还是对上帝,她跪了下来,头抵着床脚,迅速解开了他的鞋子。哦,这多么糟糕啊——他们为什么不一起下沉,忘掉自己身上的罩壳呢?——但他又是多么感激她让事情变得简单许多,而且是如此动人;哦,带着释然的笑容,她拉开毯子,让他们倒在了床上。但是,浆洗过的衬领尖利的硬角割着她的脸颊,依然令她感到厌烦,她解开他的衣领,把脸挤入尖利的直角间,命令道:“把这个脱了。”现在,他们感受到了放松和自由,感受到了彼此身体的柔软,感受到了他们被急迫的激情扼制住的呼吸,以及从他们的恐惧中升起的欢愉。哦,从这具包裹着骨骼,柔软的皮肤在上面伸展、覆盖的活生生的肉体中奔涌而出的可怕生命,从他此刻抱在怀里的骨架和排满肋骨的呼吸着的胸膛发出的可怕警告,现在压着他,它的心对着他的心跳动。哦,肉体甘甜的芬芳,潮湿的气息,胸部下面的软槽,漆黑的腋窝。但是,约阿希姆依然感到困惑,他们双双都依然感到困惑,不明白他们感受到的欢愉;他们只知道,他们在一起却仍需要寻找彼此。在黑暗中,他看到了卢泽娜的脸,但这张脸似乎漂浮开了,在她漆黑的发岸间漂浮着,他不得不伸出手去触摸,确认它还在那里;他找到了她的眉毛和眼睑,眼睑下面是坚实的眼球,找到了她脸颊的美妙曲线和张开来迎接他亲吻的嘴唇。渴望的浪潮一阵拍着一阵;在洪流的裹挟下,他的吻找到了她的吻;而当河边的柳树不断生长,从一个河岸延伸到另一个河岸,如同一个神圣的洞穴将他们包围,平静的永恒之海就酣睡在这安宁的洞穴中,这时,他感到窒息,他不再呼吸,仅仅在寻找她的呼吸,他非常微弱地说出了那句话,她听到的那句像一声呼喊的话:“我爱你。”于是,她打开了自己,如同水里的贝壳她打开了自己,于是他沉入了她的身体里。
第三部 第四十四章 价值崩溃(节选)
士兵的逻辑要求他把一颗手榴弹扔到敌人的双腿间:
军队的逻辑通常要求一切军队资源都得到最严格、最严密、最有成效的利用,如果必要的话,要用在灭绝人类、毁坏教堂、轰炸医院和手术台上:
商人的逻辑要求一切商贸资源都得到最严格、最有效的利用,以便摧毁一切竞争,给他自己的生意带来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不管那是一家贸易行,一家工厂,一家公司,还是其他经济体:
画家的逻辑要求绘画的原则始终都得到最严格、最全面的贯彻,哪怕可能会创作出非常难懂的、只有创作者自己才能理解的画作:
革命者的逻辑要求革命的冲动得到最严格、最全面的满足,从而完成一场以自身为目的的革命,就像政客的逻辑通常要求他们为自己的政治目标获取一种绝对的专制:
资产阶级野心家的逻辑要求,“致富”的口号要得到最绝对和最坚定的严格遵从:
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这种对严格的逻辑的绝对投入,西方世界取得了它的成就,——通过这种全面,这种废除其自身的绝对的全面,它最终必将达到荒谬的地步:
战争就是战争,为艺术而艺术,在政治中没有后悔的余地,生意就是生意,——这一切都意味着相同的东西,这一切都属于相同的富有攻击性的激烈精神,充满了异乎寻常的、几乎可以说是形而上的不顾后果,那种冷酷的逻辑直指目标本身,仅仅指向目标本身,既不顾左也不顾右;而这,这一切,就是我们时代典型的思维风格。
第三部 第六十五章
埃施是个鲁莽冲动的人。任何小事都能让他做出自我牺牲。他渴望简单直接:他想创造一个极其简单的世界,好让自己的孤独紧紧地拴在上面,就像拴在一根铁柱上。
胡格瑙是个承受了许多大风的人;即使进入一个通风不良的房间,他仍承受着大风。
有个人从自身的孤独中逃到了印度和美国。他想通过世俗的方法解决孤独的问题;但他是个唯美主义者,所以不得不自杀。
玛格丽特是个孩子,由性行为产生的孩子,背负着原罪,独自留在原罪里:可能会有人偶然向她点头,询问她的名字——但这种转瞬即逝的同情心无法拯救她。
没有一个象征不需要另一个象征——直接的经验是处在一系列象征的开头还是结尾?
在一首中世纪的诗歌中,一系列的象征始于上帝,又复归于上帝——在上帝中保持平衡。
汉娜·文德林希望事物井然有序,如此一来,象征就会在平衡中返回自身,就像在一首诗中一样。
一个人告别,另一个人逃离——但他们都逃离混乱;然而,只有永远不准备走的人才不会被枪毙。
没有什么比一个孩子更令人绝望了。
精神的孤独总是可以逃入浪漫主义,心灵的孤独总是可以逃入亲密的性爱——但根本的孤独,直接的孤独,却无法逃入象征。
冯·帕塞诺夫少校狂热地渴求家庭熟悉的安全感,渴求可见事物中不可见的安全感。他的渴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可见逐渐沦为了不可见,而另一方面,不可见却逐渐变成了可见。
“啊,”浪漫主义者披上陌生价值系统的斗篷,说道,“啊,现在我是你们的一分子,不再孤单了。”“啊,”唯美主义者披上同样的斗篷,说道,“我依旧孤单,但这是一件漂亮的斗篷。”唯美主义者是浪漫主义伊甸园里的那条蛇。
孩子能立刻亲近一切事物:既是直接的又是象征的事物。这就是孩子的激进之处。
玛格丽特哭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愤怒。她甚至对自己都缺乏同情心。
一个人越孤独,就越脱离他所处的价值系统,其行动就越明显地取决于非理性。可是,依附于一套陌生而独断的系统的浪漫主义者,却是——这显得不可思议——完全理性的,没有一丝孩子气。
- 中信书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美好的思想和生活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