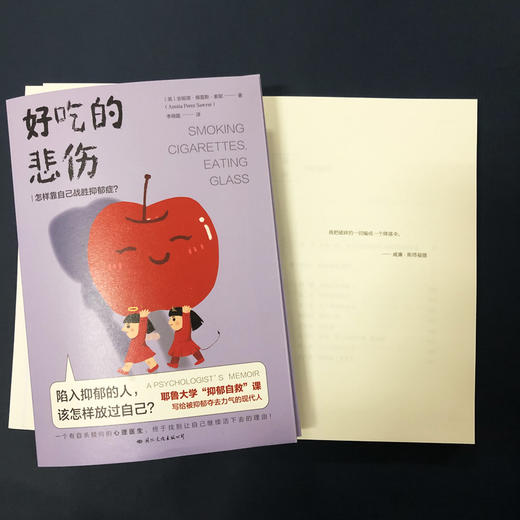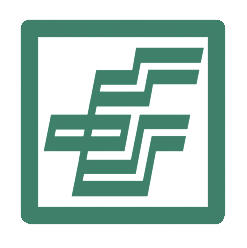好吃的悲伤 安妮塔·佩雷斯·索耶 著 耶鲁大学“抑郁自救”课 一个心理医生战胜抑郁症的自愈故事 心理学
| 运费: | ¥ 3.00 |
| 库存: | 100 件 |
商品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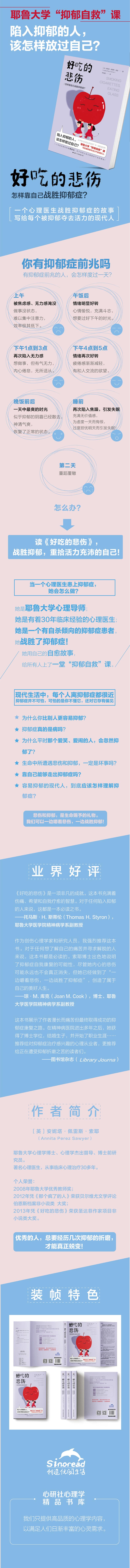

商品名称:好吃的悲伤
作者:(美)安妮塔·佩雷斯·索耶
定价:56.8
出版时间:2019-11-01
ISBN号:9787512511484
印刷时间:2019-09-18
版次:1
印次:1

我一边品尝着悲伤,一边战胜了抑郁症
改变对待悲伤的态度,可以化解内心抑郁和自杀倾向
一个有自杀倾向的抑郁女防,终于找到让自己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一】耶鲁大学“抑郁自救”课:怎样靠自己战胜抑郁症?
【二】你有抑郁症前兆吗?
在这个心理医生的自愈故事中,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三】当一个心理医生患上抑郁症,她会怎么做?
她是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员;
她是有着30年临床经验的心理医生;
她是一个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
她用自己的自愈故事,给所有人上了一堂“抑郁自救”课。
【四】陷入抑郁的人,该怎样放过自己?
内心抑郁的人,需要了解的5个问题:
ONE 为什么你比别人更容易抑郁?
TWO 抑郁症真的是病吗?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待抑郁症?
THREE 为什么那个平时爱笑、爱闹的人,会忽然抑郁了?
FOUR 生命中所遭遇的悲伤和抑郁,是坏事吗?
FIVE 靠自己能够走出抑郁症吗?
【五】一个心理医生战胜抑郁症的自愈故事,写给每个被抑郁夺去力气的现代人!

在现代生活中,每个人离抑郁症很近。
抑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懂它,还对它存有偏见。
悲伤是块巧克力,味道好极了。
这是一个关于悲伤、抑郁、坚持、改变和成功的故事。
心理医生安妮塔·佩雷斯·索耶,曾是一名内心充满黑暗和悲伤、有着 倾向的抑郁女孩。她曾被误诊为精神病并被送入精神病院,期间遭受了89次电击治疗,病情急剧加重。为了搞清楚自己的内心到底怎么了,她开始阅读心理学书籍,尝试自我的内在探索,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病情有所好转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后,成为一名受人尊敬心理学系教员和心理医生。
成功走出抑郁症的索耶,决定把这写下来,用自己的自愈故事,给所有人上了一堂“抑郁自救”课——悲伤和抑郁并不可怕,它是命运赐予我们的考验,是我们认识真实自我的途径。所有你曾经历的悲伤和抑郁,终将成为你生命的滋养,让你更好地活下去。

安妮塔·佩雷斯·索耶(Annita Perez Sawyer)
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心理学杰出督导、博士前研究员。
心理医生,从事临床心理治疗30多年。
个人荣誉:
2008年耶鲁大学优秀教师奖;
2012年凭《那个疯了的人》荣获贝尔维尤文学评论伯恩斯档案非小说类大奖;
2013年凭《好吃的悲伤》荣获圣达菲作家项目非小说类大奖
编译者简介:
李晓磊
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北京理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士,
曾任职于世界上大的两家跨国公司诺基亚和微软。

序言:总有 ,苦涩的悲伤也会泛起甜甜的味道 01
部分:被扭曲的悲伤
章 他们认定我疯了 003
第二章 哈姆雷特和我 015
第三章 令人恐惧的电击 027
第四章 再试一次 035
第五章 欢乐颂 045
第六章 魔鬼、圣人和哈罗德·瑟尔斯 051
第七章 多的医院生活 065
第八章 准备做个正常人? 081
第二部分:当悲伤遇见阳光
第九章 从前门走出去 097
第十章 尝试一场恋爱 107
第十一章 香槟、蛋糕和生米 115
第十二章 变幻的魔法 127
第十三章 人类的“蝙蝠雷达” 135
第十四章 另一张椅子 141
第十五章 从未体验的快乐 153
第十六章 他被割掉了舌头 161
第十七章 动人的纪念 169
第十八章 新的出路 175
第十九章 正确的抉择 187
第二十章 为了 191
第二十一章 看我曾战胜了什么 199
第三部分:悲伤是一份加了苦难的美食
第二十二章 无法逃避的事实 209
第二十三章 我们可以做到 221
第二十四章 找回丢失的记忆 229
第二十五章 身体知道 235
第二十六章 小安妮塔 247
第二十七章 跟詹妮听歌剧 255
第二十八章 诡梦 263
第二十九章 还没到吗? 271
第三十章 平衡、节制、平和 277
第三十一章 未来可期 285
致 谢

悲伤,是心灵成长的代价。
有一天你破碎重生,
所有的悲伤将化为一份美味的食物,
滋养你仍在继续的生命。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正在长大或已经长大的孩子,
他们内心有伤,不善表达,不被理解;
献给所有积极关注病人的、灵魂有光的治疗者;
献给所有理解我、给予我帮助的家人和朋友;
献给所有相信我的人。
部分:被扭曲的悲伤
我觉得我没有疯,我只是一个对自己充满悲观,有着自杀倾向的女孩子。
但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一点,他们被我的自杀倾向吓坏了,所以他们才会用如此粗暴的方式对待我。
然后,我就真的要疯了。
章 他们认定我疯了
1960年5月
涨潮的海水拍打在岸边冰冷的岩石上,浪花四溅散开。我们住的小屋就在这岸上。天空很晴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咸咸的味道。萨拉在纱门外催我快点出去。大家想去游泳,可我没准备好。“你们先去吧,”我对她说,“一会儿我就去找你们,别担心。”
她皱起了眉。我不愿看到萨拉因我心烦的样子,但我仍然无法说服自己动身。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像是在想该拿我怎么办。良久,她说“那好吧。”就跟其他人一起朝海滩跑去。“你也快点,别再磨蹭啦!”她边跑边喊。
那个周末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我们,或者说我高中的朋友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计划蒙托克角之行。虽说我们是高中生,但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青少年,因为青少年应该是朝气蓬勃的,而我只有死气沉沉,无论别人说什么我只是轻声附和。朋友们说话时,我脑中总会响起一个奇怪的声音,有点像铃声或高频的嗡嗡声,而朋友们似乎变得很遥远,就像一些我可以用手移动的玩具。
那个周末,我打算自杀。等朋友们走后,我会在身上绑上沉重的石块,义无反顾地走向大海,直到海水漫过我的头顶,将我淹死。但我还没有想好什么时候去做。
也许是因为我真的不喜欢游泳,也许我还在琢磨一些实施计划的细节,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把泳衣换好。当我终于打开纱门,萨拉、芙兰,以及其他人早已不见踪影。我一脚踏进了阳光里。
我紧紧地抓着浴巾,低头看着脚一步步踩进温暖的沙子里,将一串串深深的脚印留在身后。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我抬起头,向声源处望去,一群人正围着一辆褐色的雪佛兰,之前它并没停在那里。那好像是我父母的车。啊哦,我想。
我加快了脚步。一时间,闪闪发亮的沙子,哗哗的海浪声,与脑中的嗡嗡声掺杂在一起,让我感觉自己轻飘飘的,像是被巨大的热气球送到了空中,感觉好像飞了起来。我摇摇头让自己回到现实,步子迈得更快了。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站在了那辆车旁,紧挨着萨拉。她站在那儿,跟我父母面对面地站着。啊哦。
“真的没什么好担心的。”萨拉跟他们说。她在维护我——她的确是我的朋友——但她看上去比她说得更担心。他们跟她说了什么?
萨拉转向我。“你爸妈觉得你在这里不安全。”她用抱歉的语气说,“他们想让你离开,立刻。”芙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艾米丽和施特菲决定继续去游泳。萨拉向后退了几步。现在只有我独自一人面对着我的父母。我,这个被通缉的罪犯,终于要被抓捕归案了——就差当着朋友的面给我铐上手铐了。
这个场景透着一股怪异,令我感觉似乎是在做梦。
车子从长岛的尽头离开,开始了漫漫的返程之路。父亲开着车,母亲阴郁地坐在他旁边。的沉默。只有每当从烟盒里抽出一支又一支香烟时,才会偶尔传出玻璃纸和打火机的响声。随着每一次呼吸将烟雾连同这可怕又由衷的叹息,长长地吐出,淹没了整个车厢。
我静静地蜷缩在后座上,心里自责着:如果你动作快点,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我努力集中精神,试图重塑现实,期望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象着一幅画面:我走进了海里,被淹死了,电台发布了我的死讯。而现在,这成了泡影。
计划的失败令我难以接受,我的灵魂仿佛从现实中抽离出来,进入了另一个平行空间。车里和车外的似乎变得异常渺小,而我就坐在远的包厢里,观看着这出人间戏剧。慢慢地,纷杂的颜色消失了,时间也静止了。
“入院。”父亲嘴里叼着烟,对着门卫室吐出这两个字。一条正式到不能再正式的车道,从门卫室通往深深的某处。入院,听到这个词我不禁打了个冷战。父亲灰着一张脸,嘴里衔着香烟,听上去像个行将伏法的黑帮老大,我究竟做了什么?
车慢慢沿着山道往上爬行,几座建筑零星地分布在一大片庄园之上。终,车停在了一座大得令人喘不过气的精神病院门前。这里离我家住的市中心不远,以前我经常能远远地看见这些建筑。高而冰冷的铁栅栏将整片区域牢牢围住,正常人是进不去的。我不属于这里。
“我发誓我不是认真的。”我绝望地恳求着坐在我身旁的父母,但他们只是看着对面的医生。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医生坐在办公桌后面,跟我父母谈着入院的事情。“求你们!不要把我留在这里!”我即将滑向宇宙的无底深渊,而我的父母是我与地球连接的绳索。他们如果撇下我离开,我就完了。
三个人盯着我。无动于衷。
“求求您,求求您,求求您,求您带我回家吧。”我伸出双手,苦苦哀求着母亲。
她表情僵硬,双唇紧闭,努力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反对声。以前她总能用她那双深色的眼睛,带着恳求的眼神说服我,不要违背父母——实际上就是我父亲——的意愿。她垂下的肩膀,她的叹息和绝望的神情在提醒我,如果我不听从父亲的安排,就会给她造成的伤害。从幼时起,我就常常有这样的恐惧:如果我不听话或惹太多麻烦,就可能会伤害甚杀死她。此时,她的眼睛里失去了后一丝神采,仿佛死去了一般,她的声音里没有任何喜怒哀乐。
“医生让你留在这儿。”她说,把脸别过去,“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我停止了恳求,看着他们。
身材瘦小,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父亲不停地抽着烟。他说话轻声细语——这不是他平时的风格。他并没有表示异议,而是顺从医生对我命运的决定。但从他反常的轻柔的声音和不安的手势上,我能看出,他也很害怕。
“爸爸,求您了,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努力做后一次尝试。他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意识到,没有人会来维护我,替我说句话。巨大的恐慌不可抑制地从胸膛蔓延开来,涌向我的喉咙,从喉咙里咆哮而出。
那个男医生性格专横,瘦骨嶙峋,长着一头卷曲的红棕色头发和一张瘦长的猴脸,他身体前倾表达着他的看法。他警告我的父母,说我可能会自杀,所以不应该把我带回家去,只有他们医院的医生才有办法对我进行治疗。我的父母像是瘫痪了一般一语不发,没有表示异议。
然后我看到了使我留在这里的证据:我曾在日记里写下要淹死自己的计划,被我母亲看到了。如今我的秘密正攥在医生那双干巴、僵硬的大手里。他把日记打开,看了几页,手指在一些句子上划过。他时不时挑出一些词语,大声念出来——“危险的……坏的……肮脏的……”——曾经属于我的东西,如今却从他嘴里吐出来,这是玷污!然后他翻到后一页,念出我计划死亡的那部分。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再也听不到他说的任何东西。
“这真是个天大的误会。”我听到自己在解释,“我没病,不需要待在精神病院。”
但他们谁不听我的。我父母签了必要的文书,然后离开了。
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
入院记录
1960年5月30日
佩雷斯小姐在其父母的陪伴下,于今日从白原市家中到此入院。在住院部的接待室,她表现得很配合,但非常害羞和害怕。她不认为自己需要入院治疗,但仍然很配合地办理好了入院手续,并安静地跟随监管人员去了住院部大厅。
——瑞恩医生
在一间宿舍模样的房间里,我躺在床上,身体不住地颤抖。他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我没有精神病。我是想死,因为我是个坏人,但那跟这是不同的两回事。我也解释不清是如何知道的,但我就是确定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注意到还有其他五个女孩睡在周围几张床上。我毫无睡意。我当时的念头就是:整个经历也许是一场梦。而万一这不是梦,那我必须保持清醒,因为如果我睡着了,这场噩梦也许就成了真的。那感觉就像世界上的被颠倒了,而我手中则握着令它恢复正常的钥匙。我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当爸爸对我说再见时,他几乎要哭了,而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 南京微邮局 (微信公众号认证)
- ·爆款邮品免排队 ·海量书刊一键订 ·笔书情谊信传递 ·正品周边惠购享 操作便捷、内容丰富、风格文艺、品质保证、行动迅速的邮文化产品旗舰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