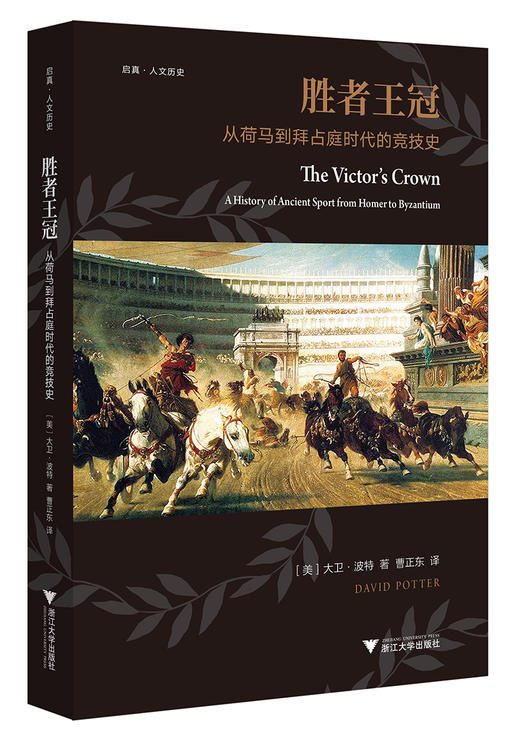胜者王冠:从荷马到拜占庭时代的竞技史/大卫·波特/译者:曹正东/浙江大学出版社
| 运费: | ¥ 3.00-18.00 |
| 库存: | 561 件 |
商品详情
【书名】胜者王冠:从荷马到拜占庭时代的竞技史
【作者】[美]大卫·波特
【译者】曹正东
【丛书】启真·人文历史
【出版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ISBN】9787308170871
【定价】52.00元
【上架建议】历史、体育、人文
【装帧】平装
![]()
【内容简介】
什么是竞技体育?我们又为什么热爱它?体育的根源在哪里,如何发展至今?
本书讲述了古代世界的体育竞技,以生动有趣的笔法向读者介绍体育,尤其是奥林匹克运动在古典时代的起源、发展以及社会作用。作者的书写横跨几个世纪,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晚期罗马以及早期拜占庭。大卫·波特写道,对古人而言体育竞技不仅关乎宗教信仰以及政治斗争,还很可能是一种社交手段与权利,展示出与现代体育竞技有所不同的竞技风貌。是一本风趣的文化读物。
【作者简介】
大卫•波特,密歇根大学历史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与罗马时代,著述众多,并多次在电视节目上为观众讲述相关古代历史。近年来的著作主要关注古希腊罗马时期与现代共通的娱乐、体育项目等,试图用较新的视角来审视古代历史。著有:《古罗马:一段新的历史》《君士坦丁大帝》《胜者王冠:从荷马到拜占庭时代的竞技史》《罗马诸王》等。
【推荐】
下笔生动,将古代竞技的细节带到读者眼前。——《独立报》
写得很好,资讯丰富。这本书把一些复杂的内容讲得很清楚。推荐阅读。
——S.A.莱西斯,《选择》
生动、权威。波特有技巧地深入古希腊生活中有关竞技的那一部分,并注意到了它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关联。当他写到罗马时期,内容更为活灵活现。他追溯了运动的起源,讲述运动怎样成为一种职业、运动员和角斗士的的生活方式等,解开了一些谜团。这本书很迷人,深具表现力。
——詹姆斯·麦康纳西,《星期天泰晤士报》
【目录】
序言 1
历史与现状 3
第一部分 尘埃、亚麻以及运动的起源 1
1. 导言 1
2. 荷马和铜器时代 9
3. 荷马与体育 17
第二部分 奥林匹亚 25
4. 从神话到历史 25
5. 公元前480 年的奥林匹亚 35
6. 公元前476 年的奥林匹亚竞技会 40
7. 盛典形态 45
8. 巅峰时刻 49
马术比赛 49
五项全能和竞走比赛 55
赤裸上阵 57
痛苦煎熬 59
9. 殊荣难忘 68
竞技英雄 71
10. 泛希腊圈的兴起 74
第三部分 竞技馆的世界 83
11. 竞技与公民道德 83
12. 贝罗亚 96
13. 身强体健职业竞技 104
第四部分 罗马竞技 125
14. 希腊遇上罗马 125
15. 国王与游戏 129
16. 罗马与意大利 137
17. 演员与角斗士 141
18. 恺撒、安东尼、奥古斯都与竞技会 157
第五部分 皇家竞技 169
19. 观赛 169
20. 观众体验 172
21. 期待 175
22. 群众的声音 177
23. 竞技之梦 180
24. 竞技图像 183
25. 女子竞技 187
26. 角斗士 192
角斗士生涯 192
训练与排名 195
死亡 196
角斗士之路 200
27. 战车英豪 204
28. 竞技者 208
竞技协会 209
自欺欺人 215
29. 好戏开场 216
行政管理 219
竞技 226
后记 尘封已久的时代 232
注释 243
索引 275
【书摘】
历史与现状
那是2006 年7 月9 日夜晚。在柏林,法比奥· 格罗索的罚球骗过了法国队守门员法比安· 巴特斯。罗马大竞技场前巨大的人群沸腾了。意大利在两亿六千万观众面前第四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全世界的观众都守候在电视机或是竞技场上大屏幕的前面,见证这一时刻的到来。之前从未有任何一次活动吸引到如此多的观众。但我们首先要谈论的正是罗马竞技场前聚集的人群。是他们将我们的世界与另一个世界连接起来,虽然那个世界早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在许多方面,它仍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建筑不仅是人们活动的场所,也是故事的载体。正是通过观察其中的故事,我们才开始发现,“iPod 与手机”的世界和“铁笔与莎草纸”的世界之间竟有那么多的共通之处。罗马竞技场的故事正是一例。就在这古代罗马竞技场之上,一千多年来,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罗马人汇聚于此,观看战车在六百米赛道绕行七圈、全程最终赛程可达四英里的比赛(这一距离让美国和英国最具挑战性的鞍马赛也望尘莫及),感受战车激烈的冲击与碰撞,欣赏那些令人窒息的竞技盛宴。
每一场在罗马竞技场举行的竞赛都会伴随自己的传说,而罗马竞技场的故事本身又是罗马传说的一个篇章,是罗马开始统治强大帝国时这座城市发展的缩影。罗马竞技场象征着凝聚人民的力量。曾几何时,它还仅是巴拉汀和阿文丁山之间山谷里的一条小道。巴拉汀曾是皇室和贵族权利的核心,俯视着一旁的政治生活心脏——罗马大广场。阿文丁山上建着一座供奉谷物女神的神庙,后来成为限制贵族权力运动的前沿阵地。坐落于两地之间的这篇伟大竞技场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于,它取代了大广场,成为人们聚集的新场所,这一点罗马人民并没有忘记。很自然地,当时会有一些贵族希望名垂青史,希望证明自己的成就不仅仅能光耀门楣(罗马贵族主要目的之一),也能造福罗马城的一方百姓。因此,到了公元前5 世纪初叶,罗马的贵族成员断定,如果能够绕着赛道设置永久的观众座席,他们的善举将更加为人传颂。这些观众座席后来成为该地区首批永久建筑物,其存在证明了体育娱乐史上的永恒主题:观众尽可能与表演融为一体,而体育将以某种方式让人们聚集在一起,这是其他活动不可能做到的。杰克· 尼科尔森和大卫· 贝克汉姆绝不是第一个在竞技场所就座的名人,在那儿,他们关注着比赛,也为人们所关注。然而,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承认,他们都体现着一种社会学现象,而这一现象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所热衷观看的比赛是一场全民盛宴。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战车比赛的盛行,竞技场逐渐被更为永固的建筑群所占领——最重要的便是那座尽善尽美、设备齐全的入场大门——它是确保所有人乘兴而来的关键。但是,一般观众只能坐在临时的小木椅上。这样做一是有现实原因——赛道需要排水,如果不先设置排水渠,就不能设置长期座椅;二是有意识形态上的考量——用石块搭建永久的建筑以供享乐,这是希腊人的做法。希腊人是“自甘堕落”的,而罗马人并非如此,他们的主要特点一直是他们的“美德”或者说是“阳刚之气”。所以罗马人认为:力量高于一切,对事物的理解可以是多角度的。
因此,在成就非凡的将军庞培于神庙旁建设剧场,从而使其威名永远铭刻在城市景观中之后,在罗马伟大的石制建筑群中,石头竞技场的出现才成为可能。庞培的劲敌、最终的胜利者尤里乌斯· 恺撒开凿了所需的下水道,并开始在赛道周围建设大理石座椅。后来恺撒决定无视“3 月15 日驾崩”的预言,大计划也因此搁浅,直到数年内战后,他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大帝才让其最终成形,并将建筑的一部分改造成胜利纪念碑。奥古斯都大帝还增设了形如海豚的全新计数器(海豚的鼻子指着比赛的起点,当竞技者飞驰而过的时候,它们会逐一下降),立起埃及的方尖碑,以提醒世人: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和她愚蠢的罗马情人马克· 安东尼是圣战最后一场战争中对抗的对象。
在大竞技场内完成剩余工程的时间可能要超过一百年,而这次的执行者是图拉真。图拉真凭借养子身份登上宝座,他的养父涅尔瓦曾被自己手下叛乱的帝国卫队所包围。因此,作为名将的养子,掌控了庞大部队后的图拉真对竞技场的修缮(他完成了用大理石改造竞技场座椅的工程),体现了对罗马人民的忠诚。他的做法不仅是在效仿奥古斯都,也是在效仿涅尔瓦的旧主韦帕芗(另一场内战中的胜利者),这位帝王拆毁了之前皇帝恢宏行宫的一部分,建造了几乎同样规模的圆形剧场,也就是现在的罗马竞技场。它也是胜利的象征,因为一部分建设费用源自韦帕芗之子提图斯在公元前70 年摧毁耶路撒冷犹太神庙时所掠夺的财富。
“当罗马竞技场矗立的时候,罗马屹立不摇;当罗马竞技场坍塌的时候,罗马也将摇摇欲坠;当罗马崩溃的时候,世界也将永无宁日。”这是拜伦勋爵引述英国清教徒的说法,这句话曾出现在一部向比德(8 世纪德高望重的学者)致敬的作品中。1954 年,当裂缝开始出现在罗马竞技场的表面时,许多人认为末日已经不远了。但我们还在,罗马竞技场还在,而且这座举办竞技的伟大场馆依旧意义非凡。对我们来说,竞技并不只是成功、失败或者比赛的刺激,它们也可以诉说我们的现在、过去或者将来。2004 年雅典奥运会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以及北京无与伦比的场馆设施是国家走入世界舞台的象征,气势非凡的开幕式是文化和荣誉的体现,运动员们也在此时熠熠生辉。
2008 年棒球赛季结束时,纽约有两座体育场永久地关闭了,接下来的赛季开始时,它们被更为现代化的场馆取代。扬基体育场关闭时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大都会(Mets)的球迷因此抱怨自己的主场谢亚球场没有得到如此郑重的告别。然而,谢亚球场不是“鲁斯之屋”,不是乔伊· 路易斯战胜马克斯· 施梅林、文明对抗希特勒“印欧意识形态”的所在,也不是全国橄榄球联盟一战成名的地方。切实地说,扬基体育场代表的不仅仅是扬基队:它代表了职业运动在美国的兴起。拆除扬基体育场的决定曾引发巨大的争议,不仅因为花费巨大(一部分要摊到纽约纳税人的头上),还在于场馆的历史地位。让扬基球迷不是滋味的是,在扬基体育场等待被拆除的时候,竞争对手波士顿红袜队却决定保留芬威公园破败的主场,而只作简单修葺(虽然门票涨价了)。
这些故事引出了体育在整个社会中发挥何种作用的核心问题:简单而言,为什么人们乐此不疲地投入到这些花费不菲的比赛中,投入到参与者各有百分之五十失败概率的游戏里?最突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那么多人如此重视体育?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除了如今,过去只有两个时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是罗马统治地中海世界的数百年间(公元前1 世纪到公元7 世纪),另一个是公元7 世纪以来的希腊和意大利。
古代竞技与当代体育之间有着直接而又特殊的联系,这一联系来自下面这三个人:埃万杰洛斯· 扎帕斯、威廉· 佩尼· 布鲁克斯博士和皮埃尔· 德· 顾拜旦男爵。诗人、新闻人士帕纳约蒂斯· 索托苏斯主张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在这一主张的启发下,扎帕斯赞助了1856 年雅典举办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这是一项创举。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项目——竞走、拳击、摔跤、战车赛等——已经不再是正规田径运动的项目。实际上,除了在学校中举行的竞赛(主要是英国学校),板球是这些年唯一有着国际影响的比赛项目。英格兰人从中世纪起就开始参与这项运动(1661 年人们会因玩板球不去教堂而被拘捕),之后开始输向英国的殖民地,在那里板球被极大程度地本地化了,以至于第一届国际板球比赛实际上是1841 年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举行的。在希腊之外,唯一一个像索托斯和扎帕斯那样对这一运动感兴趣的人是布鲁克斯博士(1809 年生于什罗普郡的马奇文洛克)。他开创了文洛克奥林匹克班,将一些古代项目和板球及新兴的足球运动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他还“提倡文洛克镇以及周边地区的居民提升自己的道德、体能以及知识水平”。布鲁克斯一直是位名副其实的翩翩绅士,在希腊项目的影响之下,他为1859 年第一届比赛设立了十英镑作为奖励资金,还将雅典的运动项目融合到自己在文洛克举办的比赛中。
扎帕斯和布鲁克斯对体育的态度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应该获准参与比赛。1859 年布鲁克斯那场开放公平的运动会引发的不满,导致了1866 年英国业余体育俱乐部(ACC)的诞生,这个俱乐部设置规定只有“业余者和绅士”才能参与到体育之中。这实际上和奥林匹克运动一样,是“希腊习惯”的复苏(虽然ACC 的成立者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古典时代,只有古代“绅士”才能参与到体育中,这些绅士期望的是风光受赏,而且当时也没有英国人所说的“业余者”这一概念。布鲁克斯继续在国内大无畏地传播体育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并在1866 年(即扎帕斯去世后第二年)成功地在水晶宫举行了一系列全国奥林匹克运动会。
1870 年,雅典的一个新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再次举办扎帕斯的运动项目,地点选在新的泛雅典娜体育馆,该馆建在古代希罗德· 阿迪库斯竞技场的旧址之上,工程开销大多来自扎帕斯的财产。但之后不久,委员会于1875 年决定停止举办这些项目,并宣称只有绅士才有资格参加比赛。1888 年,奥林匹克委员会在雅典国家花园新建成的扎皮翁宫集会,并决定再尝试一次(这一次同样也由扎帕斯遗产资助,扎帕斯的头颅即葬于扎皮翁宫)。在一系列失败之后,皮埃尔· 德· 顾拜旦开始参与进来。1870 年法国败在了德国人手里,德· 顾拜旦希望体育能够使法国的教育制度更“英国化”,从而达到重振法国士气的目的。《汤姆求学记》及布鲁克斯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激发了他的灵感,但他的社交圈子已经和先驱者的社交圈子大不相同,这些人包括一位美国学者(时为常春藤院校教工委员会的主席)、斯德哥尔摩体操协会的创始人、一位英国贵族、英国业余体育联盟的秘书,以及一名德国人、一名捷克人和一名俄国人。德· 顾拜旦的合伙人试图将教育和体育结合进行,这种做法表明他们也倾向于将参与权限定在“绅士”手中。正因如此,奥林匹克委员会才坚持参与者必须是“业余者”。基于错漏百出的调查,他们甚至坚称自己正在努力复兴的是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况。
在大量精力和金钱(这是所有工作得以开展的关键因素)的推动之下,德· 顾拜旦凭借自己的社交关系在巴黎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他的朋友们都极其支持“绅士业余体育”这一概念。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之时,顾拜旦感谢扎帕斯对于这一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还说服了希腊王储资助体育运动,并于1896年在雅典举办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
从一开始,德· 顾拜旦就做了布鲁克斯不愿做的事:他编写的参赛条款体现出他和这个时代的人对于古代希腊“业余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在美国“镀金时代”的高峰期,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那时倡导平等等同于社会主义,诸如足球这样的团体运动被看作工人阶级的游戏,是不应该被绅士们的官方机构核准的事物,绅士们只愿意为那些跟他们价值观相同的人设置奖项。1863 年英格兰足球联盟成立了,之后的第三年,业余体育俱乐部应运而生,这也许并不是偶然。布鲁克斯为了推广工人阶级的游戏而努力,他的做法似乎有点离经叛道,但是,如果不是工人阶级游戏的兴起势如破竹,布鲁克斯的做法还会引发这样强烈的反弹吗?
像德· 顾拜旦那样的成功人士也无法控制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的影响。奥林匹克的“国际性”让学校运动迅速得到了全国的追捧(例如美式足球,即橄榄球),使“工人阶级”的运动发展出了自己的职业联盟(好比欧洲的足球以及美国的棒球)。也是同样的“国际性”使得奥林匹克运动变成一些人倡导民族主义的绝佳场所,而这种民族主义是20 世纪产生的最致命的影响。从1956 年到1986 年,奥林匹克成为冷战两大阵营——苏联集团以及北约成员国——之间的临时媒介,双方都希望在运动场上一决高下来证明自己的社会制度更胜一筹。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为什么体育盛事应该成为国际政治的战场?为什么毫无运动天赋的阿道夫· 希特勒妄图把柏林奥运会变成展示雅利安人种优越性的工具呢?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再一次回顾当今体育世界和希腊罗马时期体育世界的共通之处。
问题的答案乍一看似乎特别简单,这在于关键词“athlete”(运动),它在希腊文中写作athlêtês,字面上的意思是一个人为了奖项而竞争。不像其他形式的体育活动可以当作消遣,运动是比赛,谁将是当日最终赢家的不确定性将竞技体育与其他活动区分开来。在理想世界里,参赛者要获得奖项需要挥洒汗水、付出努力、锤炼技巧,甚至可能负伤流血,结果从一开始就必须是不确定的(或者至少应该是形式上的不确定)。事前,观众根据自己的判断猜测哪位选手会胜出,观众也可以参与到比赛之中——通常情况下是通过在赛事中下注的方式。对一些人来说,这也许是他们唯一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只有观众认为胜利者实至名归的时候,他才能够获得荣誉。体育作为活动组织者和观赛人之间持续对话的一种途径而不断发展。如果比赛很无聊或者团队表现欠佳,观众完全可以起身走人。
离场的自由是一种自主选择,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自由。在古代社会,当竞技比赛开始的时候,真实的自由也遗失殆尽。具体来说,古代社会正是在这样一个不受贵族势力影响的地方才孕育出了独立的竞技文化。即使法老有观赏暴力运动作为消遣的传统,即使美索不达米亚留有记录说明体育比赛曾是统治者的娱乐项目,但“运动”的诞生地是希腊,而不是埃及。当竞技体育不断发展,统治者、独裁者、君主们就会出于各自的目的开始限制竞技体育的发展,就像希特勒举办柏林奥运会时的做法一样。但即使在那个时代,最高统治者也必须将场地让给运动员,甚至是让给观众。希特勒可以拒绝出席伟大的非裔美国籍田径明星杰西· 欧文斯的颁奖仪式,但是他不能剥夺奖牌。事实上,在参赛之间理论上的平等性、专业性(虽然和当代社会一样,古代也有一些跨界运动员,但通常并不普遍)、官僚化、详尽的规则体系以及对于体育历史的热情等方面,现代体育和古代体育都有着相通之处。
“体育的对话”一直被三个不同利益群体所推动:能够赞助体育运动,但彼此暗中较劲的金主(我们暂时称他们为“所有者”,金主间的彼此制衡是限制他们操控比赛结果的关键因素)、运动员和粉丝。因为金主间的互相较劲,所以他们愿意赞助那些让自己脸上有光的比赛项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有时候会让运动员也尝尝甜头(通常是支付更高的佣金),偶尔也会对粉丝做出让步,一般情况下是让运动员尝试一些新的、不同以往的甚至是危险的活动。这使得粉丝们觉得自己也有话语权,他们对于谁该参加比赛以及运动员应该怎样比赛的看法也越发强烈。不论运动员意愿如何,无论实际情况怎么样,运动员永远不可能只代表他们自己,这一点高尔夫运动员泰格· 伍兹深有体会,因为他的业余活动的细节就曾经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运动员往往也代表粉丝,而且必须呈现出粉丝所重视的特质。这些特质通常指正直、坚韧以及技巧,有时甚至还包括化腐朽为神奇的大无畏精神。
然而,体育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它不仅是比赛本身,而且是作为比赛使得体育场内和场外的人们融为一体,并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力量(至少能获得些许力量)的一种形式。正是体育的这一特征创造并激活了一种共存感,让人们觉得自己也是比赛中的一员。然而恰巧也是这些特性激怒了一些人,他们认为体育就是对时间和金钱的巨大浪费,不论出于何种理由,他们都感觉自己与体育绝缘。同样地,体育能够把人们团结在一起,也能够把人们分开,或者说,一个群体会因体育分裂出不同的小团体。罗马的战车赛和哑剧舞蹈引发过两方忠实粉丝之间的冲突,就像足球比赛带来了足球流氓一样。足球流氓有时将极端的政治观点和极端的粉丝结合起来,在美国橄榄球比赛中,这些人在一些大学校园周边的赛后暴乱已经常规化,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就曾经发生过类似事件。
粉丝们交谈着、欢呼着、争吵着、骚动着。他们眼前的比赛也会受到影响。粉丝们的诉求是推动古代社会不同体育运动向前发展的一股强大动力。在我们开始讨论古代社会之前,我们可以先将体育大致分为三类:运动员独立完成的体育运动(罗马统治时期女性运动员才开始引人注意,该时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 世纪);运动员需要使用器械的运动(可以是战车或者是武器);运动员需要融合多种无器械基础运动或者用特殊方式使用器械的运动。
第三类运动的产生是为了满足粉丝的需求,以罗马大竞技场战车赛为原型的“车王争霸赛”就是其中一种形式。战车选手被迫与陌生战马搭配的比赛(非常危险)以及配置超过四匹战马的比赛(极其危险)也属于这一类别。又比如,罗马的角斗士通常使用钝器进行决斗,但由于比赛的赞助者屈服于观赛人气的压力,会向王室申请特殊批文,要求他们使用利器进行决斗。这还不是最糟的,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角斗士还必须参加以生死为代价的决斗(这需要王室的特殊授权),只要赞助人保证承担葬礼的费用,角斗士们就会同意应战!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也许就是希腊的“潘克拉辛”了,这是一种集体厮杀游戏,融合了拳击和摔跤的成分,也喜欢从这两项运动的参与者中招募参赛者。某位作家曾指出,拳击手或者摔跤手所接受的“潘克拉辛”基础训练会一直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其他此类讨好粉丝的运动还包括:身穿盔甲的赛跑(没有哪个正常的运动员会设计这样一种需要扛着盾牌赛跑的比赛),以及(对我们来说)诡异的“战车跳跃赛”,在该比赛中参赛者需要在战车移动的同时,不停地上蹿下跳。
要找到愿意参加“战车跳跃赛”“盔甲赛跑”甚至是摔跤的人,都必须先设立一个奖项,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供选手争夺的只属于最终赢家的荣誉。这并不是参加比赛的佣金,而是运动员明知有可能失败却仍然要争取的东西。成功,有时甚至失败,都会让他在粉丝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运动员和粉丝们都知道,比赛并不局限在比赛当天,它也在续写着之前战绩的历史——古代运动员和当代运动员一样痴迷于自己的成绩,粉丝们对此的激情即是佐证。
总而言之,体育的发展方向就是让比赛更危险,也更昂贵。当日渐高涨的危险系数或者开销与其他社会价值发生冲突时,相较于加强管控、降低比赛难度或者削减开支的呼声,社会还是倾向于看到更精彩、更丰富的比赛项目以供消遣。直到诸如作弊、暴乱或者破产等负面消息出现,人们才会开始重视所谓“管理者”的作用。在这个时候,一些监管措施似乎变得可行,但是这一般不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古奥林匹亚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最古老的资料显示,当时禁止在摔跤中折伤对手的手指(但收效甚微),此外,降低开销以及降低角斗士死亡率的措施是否成功完全取决于罗马王室监管力度的强弱。只有当观众彻底失去兴趣,或者管理费用已经不足以支持赛事进行的时候,切实的改变才会出现。
要理解古代竞技的历史,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种为了奖励而战的比赛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运动员和观众是如何改变最初的运动形式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古代竞技的发展无法追溯到具体的历史时期,但是,通过对比现代社会的体育运动,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和整个社会的变迁一同变化的,沿着多角度的发展轨迹演变而来。希腊定期举办运动员颁奖仪式并不能说明一切,它解释不了运动员的酬劳,解释不了职业联盟产生的原因,解释不了暴乱出现的理由。但是,第一届体育盛会的举办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把人们聚集到体育之中,并且让体育成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当今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变化最初的根源。
- 浙江大学出版社微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浙江大学出版社直营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