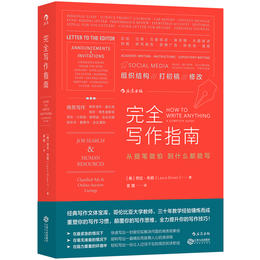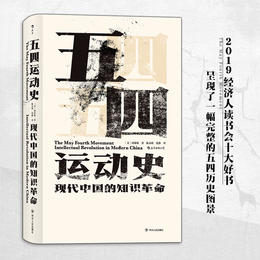商品详情
著 者:童伟格
字 数:119千
书 号:978-7-220-11463-2
页 数:200
出 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印 张:6.25
尺 寸:143毫米×210毫米
开 本:1/32
版 次:2019年09月第1版
装 帧:平装
印 次:2019年0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元
正文用纸:轻型纸60克
编辑推荐
☆ 童伟格是台湾七零后小说家中具代表性的一位,曾获台湾文学金典奖、联合报文学大奖等认可。我们能从其书写中看见魔幻写实、现代主义、内向世代等诸多风格,却无法用单一特定的词概括他,骆以军便曾言:“童伟格的可怕,在于他可以解释其他全部人,而竟无人能解释他。”
☆ 2004年夏天,童伟格开始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定名“西北雨”;历经五年书写、删减约五万字后正式出版,并表明:“初次见‘西北雨’这三个字,是在小说家袁哲生的《天顶的父》里。”一种联系由此而生,我们可能在本书窥见两位重要台湾小说家相互对照的隐秘痕迹。
☆ 在2010年“台湾文学金典奖”长篇小说决选会议上,《西北雨》不仅得到所有票数而荣获这项年度大奖,更让在场评审吴达芸盛赞:“读《西北雨》,可以说整个颠覆我原先对小说的训练或是阅读习惯。”
☆ 随着小说家操练出更繁复的时间折叠术,本书形成一个永远说不完的故事,作者长期关注的“死亡”“命运”“对乡土的困惑”等命题也都折叠其中,《西北雨》更因此被视为童伟格总结前两本小说的代表作。
名人推荐
☆ 我读童伟格,视觉上那翻动着空旷的场景如此像年轻时看的塔可夫斯基。但流动的诗意却让我想到以色列小说家奥兹,或较好时的石黑一雄……倒带、透明,那时间与命运的畸人之“我”背着快乐无害的他们在这片梦中荒原跑,从葬礼出逃,拉出这样一幅浩瀚如星河,让我们喟叹、悲不能抑、灵魂被塞满巨大风景的“赎回最初依偎时光”的梦的卷轴。
——台湾小说家 骆以军
☆ 童伟格从容谨守他在“小说的边界”的信念,不理会乡土写实,遑论家族史写作。那芜杂不文的山村、浪打菜渣坑的孤绝海港、畸零人寄居的卫星城镇,是诗的存在,抒情的存有,也是灵光的存有。米兰·昆德拉在《相遇》赞誉某书从书写形式到美学都具深刻原创力,是为“原小说”;《西北雨》同样值得如此赞美。
——台湾小说家 林俊颖
☆ 你得要够辽阔才能够深邃,《西北雨》就是这样。像大地吸收了泪水,以一种“将死之人”特有的辽阔,穿入地心,抵达文学的心脏:一种复杂无比的善良。
——台湾小说家 胡淑雯
☆ 一整座清酽悠长的宇宙:记忆中的事物在此散放着透亮光泽,并因此乾淨与确实存在着。这是一本关于阳光、微风、空气与雨雾的信仰之书,生命的永恆哀痛被安静与饱满的文字所护卫与洗涤。我们因此懂得孤身一人却盈溢各种细致的身体感受,在童伟格所许诺的魔幻乡土中,沉静等待重生,并因生命的这个恩赐而深情地微笑。
——台北艺术大学艺术跨域研究所教授 杨凯麟
获奖记录
☆ 《西北雨》荣获2010年“台湾文学奖”图书类长篇小说金典奖。
☆ 作者荣获“台北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台湾省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著者简介
童伟格(1977—),出生于新北市万里区,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硕士班,现为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讲师。
曾获1999年“台北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2000年“台湾省文学奖”短篇小说优选、“大专学生文学奖”短篇小说叁奖,2002年“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以及2010年“台湾文学奖”图书类长篇小说金典奖。著有舞台剧本《小事》、文集《童话故事》、短篇小说集《王考》与长篇小说《无伤时代》《西北雨》。
内容简介
一个家族的命运难测不可解,四代人逃离流散,死亡却始终存在。这部长篇小说被倾诉出口,却只见童伟格使用诗意轻盈的语言与多重变换的人称,让所有人回忆、想象、造梦、书写。在种种近似呓语的碎片化叙事中,亡灵复活行走,地景流转于山村、孤岛,静谧的时光迂回周折,字里行间弥漫着恍惚停滞的气息。全书仿佛一幅卷轴,或是一个莫比乌斯环,故事永不止息;所有的记忆、伤害,甚至连命运与死亡,都在小说中无尽循环。
正文赏读
卷首
别担心。如果人们再问起,我会说谎,说我还记得那天世界的样子。
阳光穿透雨后的云层,由远至近,斜斜洒落好几束光。强风起歇,分隔岛上的杂草丛,不时翻露出苍黄的肚腹。行道树的枝叶飘摇,蝉声像海潮,有时明亮,有时隐退。
那是六月里的一个星期四。下午,我跟着放学路队走出小学校门。我拉着书包的拉杆,像拖着登机箱,刻意慢吞吞磕着人行道的地砖,往路队后头蹭。经过几个十字路口,路队流散了。我收起拉杆,背上书包,开始狂奔。
那一天,我满十岁了。
我想去找我母亲。生平第一次,我主动去拜访她。
在这个世界上,我认识的第一个活人,是我的母亲。
我认识的第一个死人,也是我的母亲。
从我刚学会走路开始,每月的第二和第四个星期日,我母亲会从死里复活,到我祖父家来,把我接出门。
那些日子,我总醒得早。我躺在床上,抱着我母亲送我的一辆模型车——我记得是辆黄色的垃圾车——张着眼,看晨光亮起,等待我母亲前来,将门铃揿响。
在我身边,睡着我父亲。他喝醉了。他常常是醉的,但每个星期六晚上,他会醉得特别老实。于是在我母亲复活的那些早晨,他总睡得像一把石铸的弓,在四周被他压沉、搂紧的空气里,独自静静做着梦。
在我父亲和我的卧房外,总一同早睡、一同早起的我祖父祖母,如今一同在客厅里游走。我祖父在温吞吞做着长生操。我祖母在扫地,掸灰尘,戴上老花眼镜记账,用一个早晨清算一整个星期。
出客厅,横过走道,在另两间卧房里,分别睡着双胞胎一般的我姑姑和我叔叔。我姑姑戴着发网、眼罩,铿铿锵锵磨着牙套。我叔叔将打着石膏的左腿高高架起,以一种真空状态下才能达成的睡姿,在床上辛勤补眠。
在这间位于城市二楼的房子里,光线幽暗,一盏灯都未点亮。
因为我的家族,向来是崇尚俭省的。
我的家族,以各种自信且为人称许的方式,在这座城市里兀自繁衍多代了。偌久以前,我的一个远祖——就说是我曾曾祖母吧——死了,她的魂魄飘荡到城市的光罩下,四望,却找不到一处裂缝,找不到一个连接冥界的入口。
她无法,只好返回我的家族里来。
我的家族是如此地爱整洁,因此当我曾曾祖母飘荡回来时,她会发现她的尸体早已被我们烧除了。她最后所居住的房间,以及她生前在房里积存的一切,已经被我们谋分殆尽了。她找不到自己的躯壳,甚至找不到一套旧衣服,包裹她的魂魄,让她伪装成一个活人,行在我们之中。
我们召开家庭会议,左挪右移,好不容易腾出一弯废弃的挂钩,让我曾曾祖母的魂魄,得以像一幅壁画,镇日高挂在墙上。
日光曝伤她,夜露敷疗她。一只图谋不轨的壁虎时时跑来搔闻她。一面不停奔走的大钟刻刻以声音卡榫她。我曾曾祖母的魂魄已经不会流泪了,在她那无事可为、无路可去的漫长死期里,她只是公然对着我们,不停发放一种半似悲鸣、半似淫叫的电波。
我们再次召开家庭会议,商讨让她平静下来的办法。
我们是如此一个自信、俭省而整洁的家族,我们决议无声地、集体消化这个自我的家族逸出的亡灵。我们决定,从今以后,我们这些尚存活着的后辈,每人必须轮流让出一点时间,让出身体,借给我的曾曾祖母用,让她得以将自己化整为零,辗转流离,与我的家族共长存。
后来,当我的曾祖一辈陆续凋零后,我们也如此一一收容他们。
我们有了一项新的美德:团结。
一定是自那时起,我家族中的每个人,即令在此城中开枝散叶,分房别居后,或多或少都仍保有拼装车般的神似了。
每逢星期六,当夕阳落下,此城灯火会一一亮起,在四方天际线边,形成一个粉红色的——也就是那种曾经困住我曾曾祖母魂魄的——光罩,像是此城将自己隔离起来,不再有人可以离开了。
那时,自我祖父血脉以下的我们一家,会由我祖父领着,一起出门。
我们走下二楼,过马路,到对面王瘦子饺子馆聚餐。我们围圆桌坐定,将六份菜单全交给我祖父,由他一气点好大碗面、大盘饺子、大盆汤与大堆小菜。我们是这般一个自信、俭省、整洁且团结的家族,我们总将面饺汤菜分着吃,所有人每样都吃。唏哩呼噜,匙筷交错,像在祭飨残存在我们身体里,所有祖先的亡灵。
然后我们一起,由我祖父领着,过马路,爬上二楼,走回家。
在客厅,我们一起看完电视,一起看完我祖父层层锁好三大道钢门,然后解散,各自回去各自的房里。我们肚里胀气,一口一口各自吐出菜汤饺面杂合的气味,像是那些残缺的祖先,全都被我们释出块魂来了。
在我身边,我父亲从衣橱底挖出私藏的酒,一口一口对壁独酌。
横过走道,在另些卧房里,我祖父祖母一起爬上床,比赛谁先浅眠开来。
我姑姑上发网、上眼罩、上牙套,看能不能将青春再封存一日。
我叔叔四肢并举,像一张翻倒的神桌,由众灵庄严地扶持上床。他记不住自己此刻摔断的是哪一肢了,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了能出去游荡,让自己像头旅鼠一样,从二楼阳台跳离我们家了。
夜深了。我的家族——活的与死的都——各自静默了。
那就是在我母亲复活之前,我的家族在世界里的样子。
我们很少想起她。
我们很少特别想起任何并不在场的人。
然后,天亮了,在那三大道钢门外,门铃被轻轻揿响了。
我独自起身,穿好外出的衣物——格子短衬衫、吊带短裤、红领结、白袜子——推开门,走进幽暗的客厅里。我看见刚复活的我母亲,与我的祖父祖母,严肃地坐成一个正三角形,像陌生人一般低声交谈。
总像过了半辈子那么久,我母亲终于牵起我的手,将我领出门。
步下楼梯时我们风一般快跑,膝盖像是即刻就要化掉了。
那些星期日,无论晴天、雨天,我母亲总是特地陪我游玩。几乎就像手里有着一张城市观光地图,我母亲与我,异地来的游客般,将图上所有景点,一一地、专诚地勾销殆尽。
我们甚至曾在大雨中,转了几趟公车,去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看瓷器展。
博物院里的空调很强,瓷器很安静。我觉得既冷又闷,但我没有对我母亲说。我们彼此陪伴着,耐心看完了五百年来的各式瓷器,直到所有的花瓶,在我看来,都像是古董了。
那时,我像是七岁的样子。如果我是七岁,我母亲就是二十九岁了。
我们一起坐在博物院长廊的椅凳上歇腿,看山雨、看城市的轮廓,看比我们苍老太多了的一切事景,既不是生、也不是死地那样存在,像是一切都毫无问题,也永远不会感到疲累。
那是要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何以大多数的城市人,都认为城市里不会有鬼魂、不会有死后的居所。何以他们都认为城市里有的,就只是眼前那唯一一个现实世界——一个个互不相识的人,在街巷底错身,无语、无目光接触,如此而已。
那是要在更久以后,当我在记忆中看那个忧郁的少妇,与那个穿着得过分拘谨有礼的小孩时,我才察觉,当时我的母亲,一定也如我一般,对这城市大多数的地域,其实都陌生极了。
然而,这座城市,却是我可以与我母亲相处的唯一所在。唯一一片我们可以以各种大众运输工具,在一日之内来回的疆域。
在那之前。在我明白了,察觉了之前,在那个六月里的星期四,我出发,生平第一次自己前去拜访我母亲。
我沿着马路狂奔,向着一个我偶然听见一次,从此烙在脑里的地址接近。我低着头,很怕会遇见我所熟识的那些人脸——那些相似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所排列组合成的一张张人脸。我很害怕那张人脸会半途拦住我,将我领回我该回去的那间房子。
然而,我没有遇上任何人,轻易地抵达了。我站在一幢旧大楼底,看着一道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我很讶异我脑中的地址所指引的地方,竟就在离我的学校、离我的家族如此之近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在我母亲每月两次的复活日之外,在她漫长的死期里,她在这座城市里所寄居的地方,就是这里了。我找到了。
我步下楼梯。我踏在一道墨绿色的长廊上,长廊两侧对开着好几扇木造房门。长廊尽头,橘色的紧急照明灯亮着,像是永远没有熄灭过。
在我母亲的房门口,我找不到门铃。我敲门。片刻,我转转门把。
门上锁了。
我放下书包,靠门而坐,等我母亲的魂魄飘荡回来。
雨早就停了,但空无一人的长廊,像狗舌头一般发出一种潮暖的气味。
我睡着了。倚着门、低着头,蜷曲着身体,在等待中,我想我不知不觉睡了极久极久。夕阳应该已经下山了,我想。城市那严丝密缝的光罩应该已经又成形了,我想。我想起在那个星期天,我为了不让我母亲将我领回我祖父家,我固执地、快活地,在一座森冷的大卖场里游走。我以为我可以那样一直走下去,忽略在大卖场外,月亮已经高升了。
我母亲放弃劝止我了。即将又独自死去两星期的她,站在一个远远的地方,默默看着我。
我停下脚步。我随意从货架上取了一辆模型车,要我母亲买给我,然后我就可以再次向她告别。
过了很久,我才发觉我拿的是一辆垃圾车。
过了更久,当我与她告别后,在那间光洁的客厅里,有一颗上了发网的头对我爆笑出声,说:“她送他一台垃圾车哩。”那是我姑姑。
随后,双胞胎一般的我叔叔也跟着笑了,他对着我露出没有门牙的厚大牙龈。几天前,他又一次跳楼,摔坏了脑袋。
我想我也笑了。我想起后来垃圾车的黄色烤漆慢慢地,全部磨损掉了,也终于变成垃圾了。我猜想,等待就是这样的——有什么东西静静消失了,留下来的,全都变成垃圾了。
我在等待我母亲,一如很久以来,我的母亲在等待那些星期天一样。
我的脖子僵硬极了、酸痛极了。然而我抬不起头来。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有一双手搭在我肩上,将我唤醒过来。
- 后浪图书旗舰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后浪出版公司官方微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