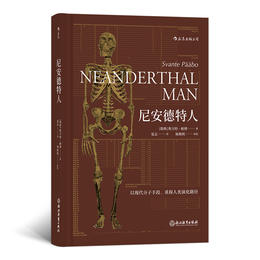无伤时代(台湾多项文学大奖得主,一种作废的小说美学 童伟格长篇小说,留住过往时光的伤悼之书)
| 运费: | ¥ 0.00-20.00 |
商品详情
著 者:童伟格
字 数:135千
书 号:978-7-220-11394-9
页 数:224
出 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印 张:7
尺 寸:143毫米×210毫米
开 本:1/32
版 次:2019年07月第1版
装 帧:平装
印 次:2019年0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元
正文用纸:轻型纸60克
编辑推荐
☆ 童伟格是台湾七零后小说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曾获台湾文学金典奖、联合报文学大奖等认可。我们能从其书写中瞥见魔幻写实、现代主义、内向世代等许多风格,却无法用一个特定的词去概括他,骆以军便曾言:“童伟格的可怕,在于他可以解释其他全部人,而竟无人能解释他。”
☆ 《无伤时代》是童伟格首部长篇小说,展示了作者从短篇到长篇的突破面向。它也是童伟格出版的第二部作品,许多存在于首部小说的隐秘痕迹,在《无伤时代》浮现得更完整,并且预先揭示第三部作品的部分轮廓。对于这部小说,张耀仁称之为“必要的过渡之书”,《无伤时代》在童伟格的创作历程中占据一个特殊位置。
☆ 童伟格的小说,人事物不时带着伤,其中以《无伤时代》最突出:主角是废人、主角母亲染病、他们生活的山村恍若被废弃,大规模的伤废败坏遍布文本,《无伤时代》仿佛一部伤痕累累的哀悼之书,并且如林俊颖所说,形成一种“作废的美学”,童伟格“以小说书写摩擦出即使作废亦有其神光”。
名人推荐
☆ 童伟格用滚滚滔滔的“败坏描写”,铺陈着一套价值——“废人”是“无伤无碍”的,“废人”不可能对这个世界有什么伤害、什么妨碍,因为他们根本不活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的“废人”身份,是以在自我想象世界里的自由决定的。
——台湾作家 杨照
☆ 童伟格似乎在重建一个品特《今之昔》《重回故里》式的慢速伤害剧场……过往时光成为一个无穷大的“微物之神”小宇宙,所有的悠然、迷糊、良善小人物慢速进行他们坏毁命运的时刻,只有作者可以任意停住画面,勘微那经常是轻暴力对峙,或一种预言式对未来灾难将临竟如此蹉跎、无知之感慨。
——台湾小说家 骆以军
☆ 未战已败的作“废”之说,恐怕大大违逆的不只是时潮,也是所谓的普世价值,童的此一背反毕竟有其悲凉。或者,他是以小说书写摩擦出即使作“废”亦有其神光。在那样敛静的文字,真正内蕴着的是稍稍有着上升出路的人子的深沉孺慕之情,父母、祖父母如同虫豸的一生,因着江以文字显象而如实存在了。
——台湾作家 林俊颖
获奖记录
☆ 作者荣获“台北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台湾文学奖图书类长篇小说金典奖”等大奖。
著者简介
童伟格(1977—),出生于新北市万里区,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硕士班,现为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讲师。
曾获1999年“台北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2000年“台湾省文学奖”短篇小说优选、“大专学生文学奖”短篇小说叁奖,2002年“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以及2010年“台湾文学奖”图书类长篇小说金典奖。著有舞台剧本《小事》、文集《童话故事》、短篇小说集《王考》与长篇小说《无伤时代》《西北雨》。
内容简介
或许是一个无法具体标示的年代,只能在一座滨海山村中,辨清一对母子的身影。儿子,自弃,始终回忆已经离开的一切事物;母亲,染病,却不断努力地自我突围。两人各自独语或彼此对话,诉说过往或虚构故事;话语不断蔓延,原本只停留一次的时间也因此漫长成永恒,让许多“伤废”的事景自由地铺陈开来,弥漫在那段曾经美好的时光里。
目 录
1 【推荐序】“废人”存有论——读童伟格的《无伤时代》 杨照
9 序章 入境
17 第一章 新生活
39 第二章 母亲
75 第三章 不在场
91 第四章 大于等待的
125 第五章 与猫演习
141 第六章 去海边
183 末章 最后与最初
195 【附录】活
正文赏读
序章 入境
她吸了三十多年粉尘,左耳后冒出两颗小小的肿瘤。她一个人背着背包——里面装着一件薄外套,和一把折起的伞——出门,骑着脚踏车去到滨海小街,然后转公车,抵达那幢大医院。那是个如常的通勤之晨,公车车厢里挤满了人。在公车每一靠站、人群更流之时,她都会踉踉跄跄,尝试着蹭移到一处自觉离人群最远的角落。所有人都健朗,所有人都神色漠然,各张着一双困眼,各自可有可无地看向车窗外。
这样很好,她想。她希望没有人注意到她。
电话声。列印声。问答声。辗轮声。她站在医院一楼的大厅里,像站在一处繁华的闹市口。
“让我想一想。”站在一长排挂号柜台前她长考着。
她要忆起昨晚独自计划好的事。她计划一次挂好三科门诊:第一诊,皮肤科;因为她发现自己耳后的肿瘤移动了位置,并且似乎变大了。“长在淋巴腺这个位置,很麻烦的。”昨晚她照着镜子,对自己这样说明。第二诊,耳鼻喉科;因为皮肤科医生大概会直接将她转到外科去动刀,到时,她一定要记得缠住医生,央求医生看仔细点。万不得已一定要转,她可以请医生帮她安排别天,自己先去耳鼻喉科看。第三诊,一般内科;因为耳鼻喉科可能还是诊不下来,她会继续央求医生,如果还是要转外科,她会说她早已经转了,然后赶去一般内科报到。
总之,她构思着:千万别一下给人推去动刀,那是最后的处置。
一直以来,她是这样相信的。
她挂好号,挤出电梯,置身在医院三楼的长廊里。
粉蓝色的工字形长廊上,一落落摆着粉红色的塑胶椅。墙上挂着好几架电视,每半小时流跑一次的新闻画面无声演着。她寸量着,挑选了两个既靠近皮肤科,又远离人群的座椅,把背包放在一个座椅上,自己坐在另一个座椅上等待。将近九点,长廊上每扇门都走出一名护士,护士挂出门后各医生的名牌。门一开一阖,送病历的手推车滚过蜡亮的地板,仿佛一病一痛都能那样准确沥干。
她一抬眼,就看见她。她看见一名老妇人,身挂着、手提着好几口塑胶袋,滴滴漏漏在长廊上滑行。老妇人望见一个人手上晃着挂号单,贴过去指引说:“你看哪科?这个单子要投进门上那个信箱,医生才知道你来了。”那人道了谢,但老妇人抓住那人的手不放,涕泪交酿对他说起一个极其复杂的故事。老妇人说她照顾一个不言不语不走不动的谁照顾到那个谁终于死了,每天每天都好辛苦啊。“怎么辛苦的我告诉你。”老妇人纷纷错错一下举了十几个例子,每一个都被那人好意的笑脸打发了。
渐渐地,那人笑脸僵结、耐心将尽。看见的人都知道。老妇人自己也知道。
老妇人一下甩开那人的手,笑着说所以说我告诉你要帮这种人洗澡的话还是要用那种不锈钢的大洗澡盆最好用了我告诉你。
那人也赔笑着,与老妇人保持融洽地各自分开。
老妇人继续滑动,继续寻觅着人们手上晃动的挂号单。“你看哪科……”老妇人贴上另一个手足失措的人说。
人声渐渐满溢长廊。在她右前方,骨科门口,一个老人坐在轮椅上,裹着石膏的左腿平举着。他不时对站在轮椅后面的年轻人高喊:“推进去。”
“还没轮到你啦。”年轻人解释着。
老人显然重听,不管年轻人说什么,老人的头总向后一仰,左腿一抬,“啊?”这样对年轻人喊。年轻人渐渐不解释了,但老人犹不时嚷着:“推进去。”片刻后,“啊?”老人独自仰头抬着腿,哀哀地自说自问。
在她左后方,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和两个母亲似乎是十分钟前初识的妇人,三人合伙用各种恐怖的话语,呵骂一个小女孩,制止她任意奔跑。她听着,苦笑了。她想着,这位母亲如果意识到“人类”是一种多么奇特的生物——一个人幼时一点点走岔的事景,都可能成为他之后六七十年咀嚼不烂的养料,她恐怕会吓得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的小孩相处。但这位母亲不知道,所以在离家庭医学科不远的地方,她紧抱一个病中的发红的婴儿,听任两个好意的陌生人帮她一起出嘴,代她照管那另一个全然健康的孩子。
这个健康的女孩,在长大以后,还会不时想起这一天吧?她想着。在一切事景淡然削弱后,长大后的女孩,会独自哀伤地记起这一切。她会记得,在那天,她的母亲,她的镇日忙碌的母亲,终于细细包好那个小婴儿,她的妹妹,像捆一个邮寄的包裹,牵着她,投进大医院。在长廊里,站在那扇仿佛是为妹妹专设的投寄门外,她的母亲紧搂着妹妹不放,笑着,配合着两个胖胖的、身上有怪味的陌生妇人,无边无际地指责她。
“母亲,”长大后的女孩会想,“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变喔,你就是这样一个总是急于讨好别人的家伙罢了。”在回忆中,她说不定会认定自己是从那天起,开始理解了母亲、开始懂得了这个世界。
空气中有一种清洁剂的味道,在密闭的长廊里无以挥发,慢慢循环。她,如今犹是一个小女孩的她,顽强地忍着泪,刻意恣意跑动,但怎样都不像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像原先初蹈一个陌生地方那样有趣而别无旁顾了。
她苦笑着,静静看着。就坐在这里,她仿佛就能透过女孩的双眼,去检视这一切。停下脚步的女孩会看见,在一道密闭长廊里,在自己正前方很远的地方,一个老人坐在轮椅上,一个年轻人站在轮椅后,歪歪垮垮背对着老人;老人不时怪异地仰头抬腿,听不清楚嘴里喊着什么。在她左前方,一个更怪异的、头发枯白蜷乱的老人——那就是此刻的她了——背对着她,呆坐着如一尊雕像。在她右后方,还有一个老妇人那样潦草凌乱地嚷着什么“不锈钢”“洗澡盆”“肉没办法一直烂下去”“半只脚粘在床垫上拔不起来”……
那多么怪诞,像是在她初识世界的那天,世界已经苍老、已在待死了一般。
总是这样的,头发枯白的她想着。她出现在一些畸零的场面里,她不由自主地成为他人记忆里的一片残影。他们看见她,在多年以后,用她来说明另一些完整的道理。他们并不需要、也无法事先经过她的同意。
他们甚至不会告诉她,透过她,他们究竟多懂得了什么。
然而,那也许,早就都不重要了,她拉拉左耳,想着。
她终于疲惫地全身退出医院。她骑着脚踏车回家。她看见她的儿子趴在书桌上熟睡了。在他身边,环伺着一堆又一堆的废纸、书籍。在书桌一角,静静站着一尊猫的骨灰坛。
她站在他身后,看了他一会。
儿子也已经年过三十了;他回来三年了,似乎还没有离开、去外面像一个正常人那样活着的打算。她不知道他这样日日坐着不动,能追回什么。
无论那是什么,那大约也已经不要紧了。
她走出儿子的房间,穿上雨鞋,去屋后洗衣服。
她慢慢洗着,刻意让天色在她眼前暗下。
她想着通勤之晨,那台挤满人的公车。她想起多年以前,在杂货店前的那支站牌下,儿子每天搭清晨五点四十五分发的公车,去港区读国中;穿回来的袜子,没有一天是干的。
有一天,天都黑了他还不回来。她撑着伞,去杂货店前等他。她想他或许是昏头昏脑在车上睡着了;或者睡到总站去了;或者下错站了;或者怎么了。她想个不停。
总算,公车来了,他下车了。她看见他怒气滔滔走下车。他说他等不到车。他大骂公车司机都是混蛋,永远打混,不肯准时开车。她看看他,想轻松说一句什么话,但找不到话。
她问:“你就不会先打个电话回家吗?”
他更生气了,一声不吭扭头就走回家。她只好跟着他。好好的房间门,他不用手,举脚一踹就把门踹开了。门上印了一个湿湿的鞋印子,她看着,心里气极了,但也实在不知道该说他什么。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时间过尽,如今,只剩下一件事了。等天完全暗了,等他完全清醒过来,等一切无可延宕的时候,她就必须对他说明这件事了。
然而,她发现,她其实早已无法对任何人,说明任何事情了。
- 后浪图书旗舰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后浪出版公司官方微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