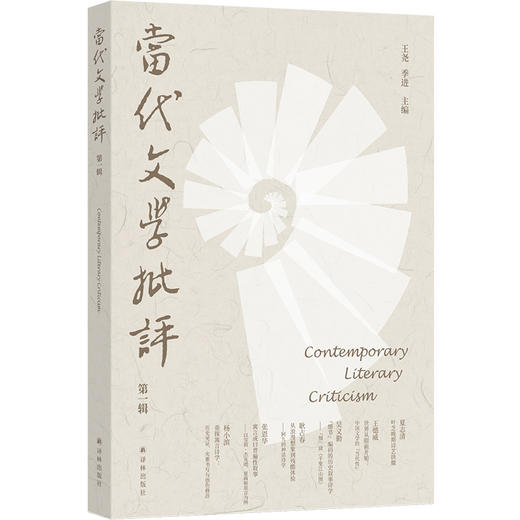商品详情
【编辑推荐】
1.本书是对人文学科边缘化焦虑与文学批评自身痼疾的深刻回应,更是把握当代文学内涵不断延展、学科亟需“外治”与“内修”双重转型的历史契机,自觉承担起作为批评转型进程中关键一环的使命。
2.定位清晰,立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融汇文学理论、比较文学与跨界视野,致力于构筑兼具思想深度、学术厚度和时代精神的批评话语体系。
3.栏目设置丰富,呈现多元思想对话,展示当代文学批评的活力与深度,力图建构面向当下的学术共同体与批评新阵地。
4.在对学术内部的反思中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把当代文学批评的“在场性”与“历史性”结合起来。
5.秉持从容与敏锐的立场,不急于否定传统,也勇于打破藩篱,努力探索兼具思想深度与方法更新的批评路径,为海内外的当代文学批评提供崭新的平台。
【内容简介】
《当代文学批评》由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与喜境(苏州)文化发展公司联合创办,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苏大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尧与苏大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季进担任主编,汇聚丁帆、吴义勤、陈晓明、南帆、程光炜、王德威、张福贵、宋明炜、张辉、张清华、黄发有等二十余位海内外著名学者组成编委会,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高度与专业品质提供坚实保障。
《当代文学批评》聚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兼顾文学理论的创新与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力图在“当代的”文学批评立场中展开对“当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第一辑包括“世界中的中国文学”“文学现场”“重审通俗文学”“科幻纵横”等多个栏目,收录夏志清、王德威、张恩华、吴义勤、杨小滨等多位学者的最新力作,兼容理论探索与个案研究,并举学术论辩与文本阐释,展现出当代文学批评应有的思想锋芒与现实关怀。
【作者简介】
主编:
王尧,苏州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思潮研究,兼及文学创作。代表作有《多维视野中的文学景观》《中国当代散文史》《乡关何处: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把吴钩看了》《“思想事件”的修辞》《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民谣》《桃花坞》等。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1949-2019)”首席专家。深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版图横跨钱锺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海外汉学三大领域,以《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另一种声音》等著作奠定学术坐标,主编的“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成为学界重要研究材料,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奖等荣誉。
【名家推荐】
【目录】
世界中的中国文学
世界从眼前开始:中国文学的“当代性” 王德威 / 3
寓言或曰普遍性叙事 ——以雪莉 · 杰克逊、夏商和莫言为例 张恩华 / 16
文学现场
“细节”编码的历史叙事诗学——“细”读《千里江山图》 吴义勤 / 33
虚构、非虚构与命运吊诡——关于董立勃长篇小说《尚青》 王春林 / 51
论胡发云小说的音乐书写与历史喻指 李 盛 / 69
重审通俗文学
鸳鸯蝴蝶派:中国现代小说抒情传统的开端 张 蕾 / 91
网生性、经典化、学科归属与网络文学的本土经验:当下网络文学研究的问题困境及突围 房 伟 / 108
科幻纵横
晚清时期科幻小说源文本与中译本的文化互涉——以《回头看纪略》为例 李培涵 姜智芹 / 123
当下的诱惑:当代海外中国科幻文学研究的三种方法 胡星灿 / 138
重绘城市
“慢下来”与城市文学新文法 ——谈《玄鸟传》《不舍昼夜》《撞空》的游荡叙事 唐诗人 / 155
不存在的城市与家宅——卡尔维诺、王苏辛与一种可能的城市悲苦剧 林云柯 / 169
新诗新论
从“否定之否定”到“亲切叙事”:兼论韩东四十年新诗创作的启示价值 陈义海 / 187
从浪漫想象到残酷体验 ——阿九的神话诗学 耿占春 / 208
重探寓言诗学:历史见证、灾难书写与创伤修辞 杨小滨 / 227
比较视域 · 夏志清小辑
叶芝晚期诗艺抉微 夏志清 / 239
弥尔顿的“音乐性” 夏志清 / 249
博论选刊
“压抑”的功效——重读《看虹录》与《摘星录(绿的梦)》 牛 煜 / 261
年谱
钱锺书文学创作年谱简编 余承法 / 277
【相关图书推荐】
(编辑不填)
【前言】
卷首语
从夏天到夏天,经过一年时间筹备,《当代文学批评》辑刊第一期终于付梓。 这一年正是人文学科危机被聚焦的一年,因“危机”而来的焦虑和缓解焦虑的努力也就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胎记。在此意义上,辑刊是当代文学批评转型中的一个环节。考察学术史我们会发现,学科的危机固然因外部变化而生,相当程度上也是内部困顿使然。“当代文学批评”因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外部变化会迅即成为学科的遭遇,这常常会转移学科内部的问题而把重点只放在如何应对外部之变层面。其实正是这种外部与内部的复杂纠结生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内驱力,生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当代性。“外治”与“内修”兼顾的当代文学批评,需要从容和敏锐地在历史变革中重建。所谓从容,是不必惊慌失措推倒一切;所谓敏锐,是拆除藩篱方可移步换景。本刊主要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问题,兼顾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视野,以“当代的”文学批评立场研究“当代文学”。虽有栏目之分,但具有“当代性”的文学问题均在研究之域,在学理之中,可标新立异,可删繁就简,可老生常谈,可童言无忌。既是新生媒介,便无门户之见,四海之内大凡认真问学者,皆为同道中人。若说本刊理想,我们期待:当代文学批评是“历史的”,也是“在场的”;是“学术的”,也是“思想的”;是“问题的”,也是“方法的”;是“审美的”,也是“文化的”。
【文摘】
世界从眼前开始:中国文学的“当代性” 王德威
这一主题与苏州大学召开的“世界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会议(2024年6月19—21日)的核心议题紧密相连。我首先从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进行剖析。随后,我将以一种对话方式分享个人在阅读当代文学过程中的体会和心得。同时,我也思考这些文学作品如何在全球视野下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它们可能产生的启示和影响。
一、 重述文学史的关键词:“世界”与“当代”
首先,我们可以思考一些关键词,比如“世界”与“当代”。“世界”,它实在是一个外来的词语;原本就是一个在世界语言以及文化文明流动的过程中,进入中国语境的词汇。它源自梵语(lokadhātu),从佛经汉语翻译来,由“世”(时间)和“界”(空间)组合而成,这个翻译本身的意义对于我们文学的理解至关重要。世界的“世”原本指的是时间。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晚清到民国文化剧烈变动中,“世界”这个词经由日文翻译后再度引入中文语境,有了新意:引入了全球或全球化的内涵,并涵盖国家的流通,以及文明交融互动的线索。
苏州大学的前身东吴大学,在最初的中国文学命名与发生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回溯至1904年,时任东吴大学教师的黄人写出第一本现代中国文学史;同时,北大的林传甲也制作了一份中国文学史的文稿。这两部文学史写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语境中首次对由西方构思发展而来的“世界”“文学”“历史”的叙事框架做出因应。
至于“世界中”—“worlding”这一概念,则源自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提出的术语。它将名词转变为动词,意在提醒我们:世界并非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一种被召唤、揭示的存在方式,即“being-in-the-world”。
在当今的语境中,我们所欲探讨的“世界”观念与全球、国家之间的关系依然深远,但其定义并不仅限于全球化、国家等层面,甚至及于星球。
在我个人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我曾介绍过这一概念,并借鉴了海德格尔关于“世界”的观念,将其动词化,意在提醒我们,“世界”并非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一个充满动态性的过程与进程。世界是一种召唤,一种变化的状态,它不断促使我们在生存的情境中思考、摸索、揭示那些我们未曾思考或发现的现象。因此,“世界中”是一种机制,一种动态的思维方式,它不断地重新发现我们之间的各种关联。这或许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讨论“世界中”的起点。
接下来我们探讨“当代”这两个字,尤其是它与“中国”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诸多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解读中,从文学史的视角、世界文学的维度以及文学理论的立场出发,涌现出了各异的诠释。其中,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对于世界文学背景下的当代文学有着独到的见解。在洪子诚的观点中,当代文学在时间上主要指的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0年前后的中国文学。性质上,它的“主导形态”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形态。因此,这个时期的台港澳文学就不包括在内。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当代文学”并不包括同一时期的台港澳文学。由此可见,洪子诚教授在界定当代文学时,将时间范围的上限定为1949年,而下限则大致划定在1980年前后。这种界定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当代文学的视角。洪老师指出,当代文学的内部矛盾冲突性质及其展开方式,与冷战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国际形势变动的过程中。“当代”一词所承载的战略性乃至策略性意义得以凸显。
而苏州大学王尧老师在两三年前提出了另一种基于发生论视角的当代观。他提及20世纪50年代周扬至邵荃麟关于方向方针、领导性质、任务、成就和经验的论述,这些论述不仅是对当代的建构,同时也涉及了当代文学的论述。这些最初的建构和论述,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框架、脉络和基本理论。因此,从发生论或起源的角度来看,当代文学经过不断的论述和不同时期的演化,逐渐发展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当代”。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文学“时间性”的角度来审视当代,顾名思义,“当代”即意味着当下此刻,这是我们普遍认可的一种定义。如果“现代”已经暗示着时间的瞬息流变,“当代”更指向一种与时俱进、日新又“新”的机动性。也因此,当代文学理应首尾相应,相互开放,展现历史进程中每一个稍纵即逝的刹那,所以当代文学有一个特别敏锐的时间感受,向着过去,向着未来,感受到当下此刻的对瞬息万变的一种机动性,甚至某一种危机感。
然而现代中国文学史里的“当代”却另有诉求。倘若“现代”指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国共分裂的三十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即成为“当代”的开端。倏忽七十年过去,“当代”的跨度不断延伸,不但超过“现代”,甚至已然要成为天长地久的“历史”了。原本,“当代”一词应指代当下、此刻,然而如今它似乎已演化为一种象征永恒、天长地久的概念。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对文学历史的深深眷恋,更是对崇高理念的一种坚定追随和确认。从刹那到永恒,这种文学史观的转变无疑反映了多年来政治实践与文化传承之间的紧密关系。
因此,对于“当代”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诠释,我们需要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出发,将其视为一种既包含历史深度又具备现实意义的时代标签。这种理解方式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代中国的发展脉络,也能为我们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思考空间。
关于“当代”的解读,我们还可以参考台湾省学者王智明博士的观点。他强调,在探讨“当代”的意义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审视、把握与深思。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当代”的意义远超出当代中国的疆域范围。换言之,对于这一命名及其所蕴含的预期视野,我们不应仅局限于地理坐标的考量,而应拓宽我们的视野,进行全球的思考。
我们提出这一命题,旨在通过以下两方面来深化对当代的认识:一方面,我们借助“中国”这一关键词来拓展当代的意义,进而探索其内部结构。如果当代具有世界性的意义,那么属于中国的当代性又是如何与中国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的呢?王智明提醒我们关注当代的空间观念,以进一步丰富我们的理解。另一方面,我们运用“当代”这一概念来丰富对中国的意识和想象,使之不再局限于政治形态。尽管政治进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仍有诸多不同的时间维度值得我们思考与追踪。在当下此刻,我们有能力从一个世界性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当代观念,这构成了我们探讨的重要命题。
二、 从无明中“看见”世界:当代文学可畏的想象力
除了中文语境下对当代进行思考的批评者们的贡献外,我还想特别提及意大利著名当代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观点。在座诸位也许对这位曾访问过中国的学者有所了解。阿甘本在《什么是当代人》(“What Is the Contemporary?”)一文中明确地写道:“当代人就是那些直观此刻当下的人,他们如此专注,以至于看到的不是光明,而是黑暗。”这种对当代的独特定义,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而深刻的思考角度。
那些既不同时存在又相互矛盾的元素,它们如同时间进程中的不同段落,相互交织而又参差不齐。作为当代具备辨识力与判断力的学者或文学工作者,他们有能力在这些纷繁复杂的时间碎片中,展现非凡的洞见。面对世界,他们不仅看到光明的一面,也洞察到黑暗的存在。因此,他们得以感知过去,影响当下,既关注现实中的阴暗面,又从历史中汲取灵感与启示,从而推动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
那么,现状究竟如何呢?我们又是如何从历史的长河中一路走来的?当代社会所展现的积极介入与能动性,使得真正的学者与作家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属于他们时代的独特光芒,即便在黑暗中,也能发现那一抹幽暗之光。这种光束以其独特的方式穿越层层迷雾,向我们传递着深刻的信息。
因此,所谓的“当代性”就是自己与置身的时间处于一种独特的关系中,这关系在依循“此刻当下”时间的同时,也与之保持距离。更精确地说,它就是透过断裂及时间错乱感来定位(自身所处)时间的那种关系。所谓当代人,就是知道如何看见、如何能够书写“现在”的蒙昧之处。一个优秀的读者、评论者或作者,往往能够对这种期许产生深刻共鸣。他们将自己置于与时间独特的关系点上,让不同时间维度的元素相互交织、相互映照。在这样的时空交错中,他们既能看到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也能预见到未来的可能性。他们知道如何洞察并书写现在,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与缝隙。
在这个历史的当代关键点上,我们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洞察力,以更好地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方面面。这种洞察力不仅关乎我们如何看待周围的事物,更关乎我们如何审时度势、把握时代的脉搏。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锻炼这种洞察力并不需要完全依赖西方的理论框架,而是应该结合本土文化和实际情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视觉感、判断力和洞察力。
鲁迅在1933年的作品《夜颂》中曾写道:“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他们自如地在黑暗之中洞察世间万象,不应将眼前那漆黑一片的夜幕视作混沌不清的虚无。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思考者、评论者或作家,往往能在这样的黑暗环境中,洞悉出层次丰富的黑色。这些黑色进而汇聚成一道别具一格的光线,从中,他们得以窥见所谓的“黑暗之光”,即隐藏在黑夜中的深刻真理与无尽奥秘。
因此,我认为,鲁迅早在1930年代便已然展现出了一位“当代”作家的风范。这里所指的“当代”,并非仅限于30年代,它同样可以指向我们的当下,乃至遥远的未来。鲁迅对于黑暗的探索与解读,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我们期待更多人能够像鲁迅一样,具备看见——并诉说——黑暗之“美”的能力。
在此,我还想引用另一位知名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她曾深入探讨了在公民社会中,公共性的培养与塑造问题。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培养和提升我们的公共意识与责任感。
对于阿伦特而言,公共性实际上是一种“说故事”的纽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断裂。她坚信,人间的公共性及关联性有赖叙事—说故事—的发生性(natality)和现场性证成。正是这种叙事能量所引发的发生性和现场性,使我们得以对公共性有一种尤为敏锐的感知。借由故事,我们相互言说与倾听,产生交锋或对话,公民社会的意义因此敞开。在阿伦特看来,现代之“恶”最诡谲的形式在于,它以最平庸无感的形式渗透于日常生活,并被视为当然,甚至膜之拜之。
但是,阿伦特认为,只有那些幸免于肉身凌辱,尚未因种种劫难而成为行尸走肉的人,才得以在见证不义之余,有能力想象种种恐怖,并运用这可畏的想象力。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叙事者,即便未曾亲身遭遇现场性的灾难,也能在避免成为行尸走肉之前,凭借其对公共性和叙事能量的自信,以及通过故事传达意义的互信,来开启一个新的社会脉络。因此,在见证不易的同时,我们必须发挥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可谓是一种深刻的、具有洞察力的想象力。换言之,作家们以其卓越的笔触描绘出我们普通读者能够想到或感受到但难以言表的各种情境和问题。
在这样的沟通中,我们的故事变得更加丰富,对当代公民社会的信念也因故事的关联性而得到更深一层的确认和加强。因此,从理论层面来看,这些关于当代世界、叙事以及文学能量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发。
我们所强调的,乃是虚构的力量,叙事的力量。通过文学,我们得以在无明中“看见”世界的全貌。历史经验千头万绪,我们其实无从以先验或后设方法化约其动因和结果。当此之际,文学以虚构力量揭露理性不可思议的背反,理想始料未及的虚妄,从而见证历史俱分进化的现象。这一虚构力量所激发的“幽暗意识”起自个别的想象,异端的洞察力,却成为文学批判现实、想象未来的重要契机。
而今日所探讨的“文学”,并非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戏曲、散文、诗歌等形式。我们所谓的文学,实则是对中国传统文明中“文”与“学”这两个关键词深入骨髓的浸润与认知的再度领悟。在影视作品、大众传媒乃至各种数字化社交、游戏平台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运用着对文字的敏锐感知力,试图与世界进行沟通交流。这种努力,正是对传统的延续与传承。因此,我们应当勤于思考,深入探索文学的本质,才能真正展现其无所不在的渲染力与认知能量。至于历史经验的纷繁复杂,我们无法仅凭先验或后设的方法加以展现和认知。此时,借助虚构的力量,我们能够揭露理性所无法解释的背反理想以及始料未及的虚妄,从而见证历史进程中善恶并存的现象。这种虚构力量所激发的幽暗意识,正如先前所提及的鲁迅所给予我们的深刻教训。
在探讨看到黑暗中的光束这一现象时,我们不得不提及个别想象异端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已成为文学感知现代与当代社会,进而批判现实的重要方式之一,得以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亦是我们共同的期许。
三、 重新思索“世界”:以十位当代作家为例
接下来,我将通过最近阅读的当代作品来阐述我们对“世界”的定义,以及文学阅读所展现的广阔视野。
邱华栋先生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新作《哈瓦那波浪》便是一部具有游记性质的半虚构式作品,由九篇故事组成。这部作品跨越了太平洋、澳大利亚、中亚、古巴、俄罗斯和冰岛等地,通过不同华人的经验,重新思考了在全球格局下华人居住、漂流和行走所形成的共同体理念及其相互间由文字和想象所构筑的关联性。
此外,我还阅读了年轻作家石一枫的作品《漂洋过海来送你》。这部作品回溯了战争期间华工对世界各地政治和军事事务的贡献,以及他们的后代为将葬身海外的亲人骨灰带回故土所付出的努力。故事从美国延伸至阿尔巴尼亚,再次提醒我们那段战争年代不同世界之间的紧密联系。
还有当代青年作家陈济舟的作品《我走遍所有的南方寻找你》。这部作品以一位在海外成长,具有中国血缘和家族背景的青年为主角,讲述了他在古巴旅行的经历以及由此引发的浪漫传奇。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主人公与古巴文化的交融,还隐晦地探讨了革命起源的复杂性和难以言喻的想象。
这些当代作品通过不同的视角和叙述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多元而丰富的世界图景。它们不仅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和理解现代社会中人类共同的经历和命运。
我们的文学领域再次拓展了边界,触及了更为遥远的世界角落。以当代科幻作家陈楸帆为例,他的作品引领我们深入中国南方的潮汕地区,那片曾经的电子废弃物聚集地—硅岛。这里不仅是一个实体存在的地方,更是一个虚拟的、由网络通信硬件废料构筑的世界。在这片独特的土地上,我们见证了各种废弃物交织成的不可思议的机器人冒险故事。这既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当代关系的独特特征,也展现了作家们对于人与环境、科技与废弃物的深刻思考。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女性作家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文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她们的作品,如林棹《潮汐图》将人与动物、各种事物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交错叠映的观点。
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则以其惊人的才情展示了中国作家在古典与现代、旧山河与新世界接轨方面的卓越才华。一段段神秘的冒险故事,跨文化的想象和交融,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文学世界。
最后,必须提及定居台湾的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张贵兴。他的作品《鳄眼晨曦》(即将在中国大陆出版)无疑将为我们的文学领域带来新的震撼和思考。张贵兴来自婆罗洲,尽管定居于台湾,他的心灵却总飘向遥远的家乡。婆罗洲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19世纪末,华人在婆罗洲的殖民经历,不仅使他们接触到了多种殖民势力,更深化了他们与土著民族的交往。这些经历,以及婆罗洲独特的动植物生态和自然风貌,共同塑造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华语叙述世界。在这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里,距今三万年前的人类形象玛丽引发了关于人类学的深刻想象。这位形似猴子的女性角色,穿越时空来到1970年代的婆罗洲,与一位年轻的华裔男子展开了一段跨越三万年的传奇恋情。这种跨越时空的想象力,无疑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加广阔而深邃的世界。
近年来,海峡两岸作家的交流日益频繁,为我们带来了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台湾著名作家骆以军在2019年受到刘慈欣《三体》的启发,创作出了一部独具特色的科幻古典小说《明朝》。这部小说的关键词“明朝”既指代历史上的明朝时期,也寓意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小说中,当一切价值体系崩塌之后,有人将明朝文明的精华全部储存于一个巨大的数据之中,并通过卫星发射至遥远的宇宙深处。这种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叙事方式,既展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深情回顾,又融入了刘慈欣《流浪地球》中科幻元素的精髓。在宇宙的彼端回眸,曾经那个短暂而绚烂的南朝风光,个人的命运与台湾当前政治局势的错综复杂,在在令人瞩目。
提及此,不得不提我特别尊敬的作家韩松,他创作了许多引人入胜的作品。近年的杰作“医院三部曲”中,他再次展现了对宇宙黑暗力量的探索与敬畏之心。小说强调人生而有病,世界就是我们的医院。这部作品以其近五十万字的宏大篇幅,构建了一个变化莫测、诡谲万端的世界。韩松无畏地直面恐惧,在作品中呈现了我们所渴望窥见的,以及那些我们畏惧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各种现象。这些现象构成了他对亡灵的召唤,以及驱魔仪式的深刻描绘,体现了他作为作家对写作艺术的精湛运用。
以上所述的这些作家,他们的视野已拓展至全球乃至宇宙星辰,展现了建筑世界中的宏大格局。然而,也有另一些作家将目光聚焦于眼前,关注生命之间最真实、最及时的互动与体验。我们不妨借用佛家的一句箴言“世间无常,国土危脆”来纵论这些作家的个人关怀。需澄清的是,此处的“国土”并非指主权国家的疆域,而是泛指我们所生存的生命空间。时间流转,世间万物瞬息万变,而我们生活的世界亦充满了各种看不见的挑战、潜在的威胁。我们或许以为身处安逸之境,然而谁又能预知生命的无常与旦夕祸福呢。
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所处理的,正是韩松以其无限虚构所构筑的那座“医院”,而毕飞宇则凭借我们刚刚历经的疫情经验,细腻描绘出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所展现的生老病死,都是人们最切身的课题;日常生活中也暗藏惊心动魄的细节,带给我们启悟或无明。
我们也想到贾平凹的《老生》和《山本》。贾平凹描绘故乡陕西南部秦岭一带的农村,那里的风土人情、传说故事,构筑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共同体。秦岭是贾平凹的根本,而他的叙事既绵密又松散。经过了大风大浪的作家回看世间无常、国土危脆的时候,产生体悟。
格非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先锋作家曾经倾倒多少读者?多年之后,他写出“江南三部曲”(“乌托邦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以一贯忧郁抒情的语调,遥想革命的伤痕,启蒙的蒙昧;直视我们自己置身的时代各种自然灾害与人为祸端导致的生态裂变。格非以诗意的方式承载了暴力的主题,成为介入当代的一种独特表达。
迟子建的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恰好契合了我们的两个关键词。一位女性叙事者幽幽叙述着东北凋零矿区小镇的沧桑变迁、神秘的命案,以及一位心碎女子如何在这个小镇上直面自己生命的巨大伤痛,最终达成和解。《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讲述一则又一则无法救赎却必须救赎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东北故事集》更将视野拉回到20世纪40年代甚至清末民初。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再次见证了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以及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从南北宋到海兰泡事件,再到伪满洲国,不同时代的交错穿插。如同贾平凹《山本》一样,迟子建的东北故事说不尽、讲不完。这些“故”事必须不断地被继续叙述、诉说与呈现。
在我们探讨左翼文学往何处去之际,香港女作家李维怡以其实际行动为香港底层社会以及底层文学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她以《行路难》和《鬼母双身记》等作品,深刻剖析了阶级不平等、性别差异以及世代冲突等社会问题。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香港社会的现实,也展现了香港文学的独特魅力。
来自四川嘉绒藏族的作家阿来,以其优美的笔触描绘了川藏地区的独特风貌。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不同的文明传统,还深入挖掘了四川阿坝地区藏族自治州的历史与文化。从《尘埃落定》到神话史小说再到最近的《云中记》,阿来的作品展现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与独特见解。
我们特别向阎连科先生致敬。他早期作品如《坚硬如水》《日光流年》曾经引起极大反响,至今仍为读者传颂。这些作品更因翻译而走向世界文学舞台,成为不可忽视的中国软实力。面对“世界”就在“眼前”这一话题,阎连科2014年在卡夫卡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值得我们再次回味:
我想到了我们村庄那个活了70岁的盲人,每天太阳出来的时候,他都会面对东山,望着朝日,默默自语地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日光原来是黑色的——倒也好!”
更为奇异的事情是,这位我同村的盲人,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有几个不同的手电筒,每走夜路,都要在手里拿着打开的手电筒,天色愈黑,他手里的手电筒愈长,灯光也愈发明亮。于是,他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着,人们很远就看见了他,就不会撞在他的身上。而且,在我们与他擦肩而过时,他还会用手电筒照着你前边的道路,让你顺利地走出很远、很远。
为了感念这位盲人和他手里的灯光,在他死去之后,他的家人和我们村人,去为他致哀送礼时,都给他送了装满电池的各种手电筒。在他入殓下葬的棺材里,几乎全部都是人们送的可以发光的手电筒。
从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种写作—它愈是黑暗,也愈为光明;愈是寒凉,也愈为温暖。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让人们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写作,就是那个在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着黑暗,尽量让人们看见黑暗而有目标和目的闪开和躲避。
这种以故事形式表达的深刻内涵,既体现了阎连科先生对文学的独到见解,也展现了他对人生和世界的深刻洞察,更是他对自己心目中当代文学与作家的期许。
总结报告,我以两位作者的话语,对“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再做定义。顾城在1979年发表《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若以洪子诚老师的定义来看,也许1980年代前夕是以冷战为坐标的当代文学的终结,然而,这恰恰是我们所定义的“世界中”的当代文学的重新辨识与开始。
通过这一解读,我们深刻领悟到历史其实包含众多不同的脉络,时间的进程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各种色彩迥异的黑暗与光明相互交织,共同等待着我们作家的寻觅与揭示。无论是诗人、散文家还是剧作家,他们都在黑夜中,用他们那深邃的黑色眼睛,为我们探寻并照亮前行的道路。
我们再次回顾鲁迅在1933年所给予的深刻教诲:“自在暗中,看一切暗。”这句话提醒我们,应当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批判精神,以理性的态度审视并应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同样赋予我们思考能量的,是鲁迅的《影的告别》:“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鲁迅既不愿在虚无的天堂里苟且偷安,亦不愿沉沦于地底的深渊。他所追求的是那充满无限可能与发展的黄金世界,然而如果这一世界非他所愿,他亦不肯轻易涉足。这一表述不仅揭示了“当代”这一词汇本身的深刻内涵与复杂性,更指明了世界发展的多元方向与挑战。我们立足当下,从眼前的实际出发,展开思考、阅读与写作,不断探索并拓展我们继续创造新世界的方法与路径。
[作者单位: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
- 译林出版社旗舰店
- 本店铺为译林出版社自营店铺,正品保障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