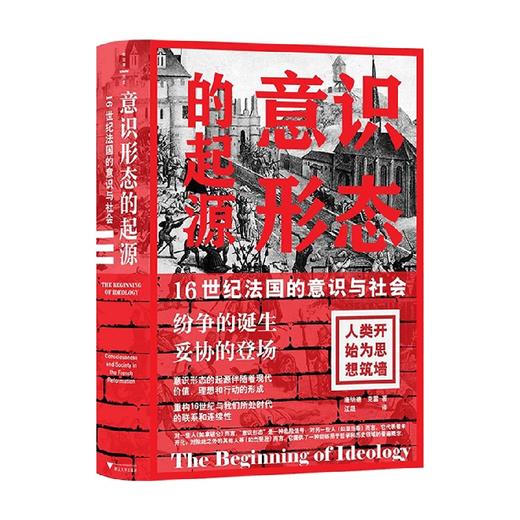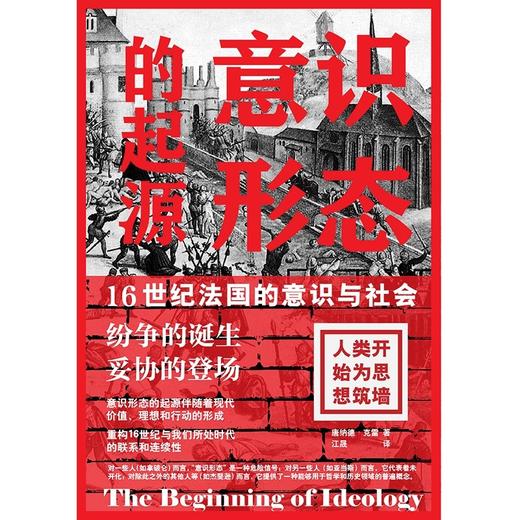商品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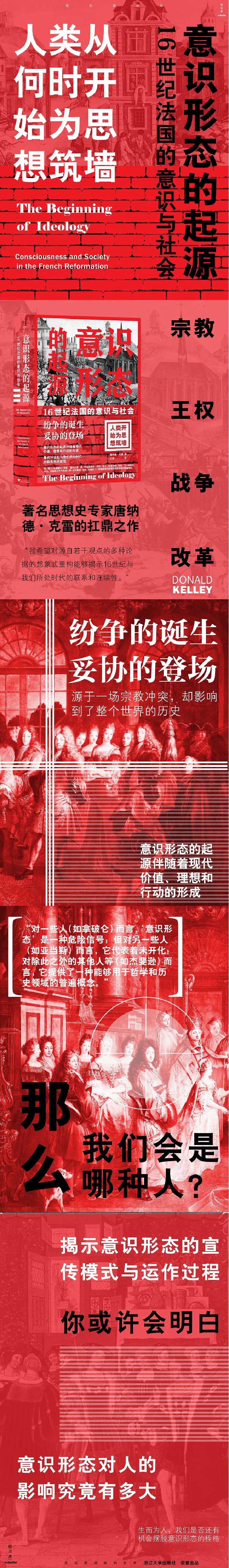

书名: 意识形态的起源 16世纪法国的意识与社会
定价: 88
ISBN: 9787308235334
作者: 唐纳德•克雷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3-05
用纸: 胶版纸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本书完整剖析意识形态的来龙去脉,为人们理解左右自己行为和思想的这种集体性观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还提出具有争议性的观点,将宗教改革时期定为人类意识形态的诞生期,能够引发大量争鸣。并且从内容上来说,也符合当下人们的阅读趣味,通过大量生动有趣的历史珍闻深入浅出地揭开真相。

当代世界俨然成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战场,不同阵营的人们为了各自的理念争论不休,甚至兵戎相见,既创造了各自辉煌的文化,也导致了一个个可怕的悲剧。那么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从哪里诞生的呢?
本书检视了奠定一种深刻的智识的和社会的变化之基础的情感、价值观、理想、正义感和行为等的产生过程,即意识形态的诞生史。在16世纪的法国,宗教冲突发展到社会分裂,进而演变成政治进化,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和群体意识、组织和行为都发生了变化。于是,这样一种典型的深刻的智识和社会变化就发生了。本书充分运用了各种宏微观史料,尤其是16世纪法语世界流传的大量小册子,剖析了这个阶段反映在思想和行为中的私人和公共意识,并且对现代欧洲的一个革命时代进行多层次的解析,终对意识形态的诞生过程及其影响做出了威的判断。本书立论严谨,史料丰富、具启发性,是思想史不可多得的典之作。

001 序章:意识形态问题与历史进程
013 一章 背景:路德孵化之卵
013 序言:布告事件(1534年)
021 改革的观念
029 马丁•路德的七头
038 宗教改革的维度
048 人的境况和意识形态的起源
058 第二章 家庭:宗教经验与意识形态信念
058 序言:泰奥多尔•贝扎得见光明(1548年)
064 良知的自责
071 通往大马士革之路
081 要辩证法
094 从血亲到宗派
103 第三章 信众群体:培育信仰
103 序言:圣雅克街事件(1557年)
108 从信仰到事业
118 由听道而生的信仰
127 福音革命
138 教会的种子
151 第四章 学院:教化与辩论
151 序言:彼得•拉米斯及其讯息(1543年)
156 传统教育与新学
165 是与非
174 新教教育
184 学术战争
195 第五章 法庭:法律职业与政治家
195 序言:巴黎高等法院中的对抗(1559年)
202 第四等级
211 真正的哲学与人的境况
222 王之所好
234 政治家
245 第六章 宣传:信仰的传播
245 序言:艾蒂安•多莱的火刑(1546年)
252 印刷术与原始新闻业
265 书卷弥满的世界
275 禁书与焚书
283 宣传的模式
293 第七章 派系:对事业的定义
293 序言:孔代亲王制定契约(1562年)
300 界线的划定
311 理性与非理性之声
321 血与墨
336 事业的奉献者
350 第八章 意识形态:社会思想的剖析
350 序言:警报声起
357 意识形态的形态
367 意识形态的要素
376 意识形态的层次
384 意识形态的终结
395 结语: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405 姓名索引

唐纳德•克雷
现任罗格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及《思想史》期刊的执行主编。他常年专研思想史与观念史,在业界具有重要影响力,其著作主要包括《人类的尺度:西方社会思想和法律传统》等。

禁书与焚书
或者说,书籍(与《圣经》不同)是魔鬼的发明?当然,它来自德意志地区,具备“浮士德式”的内涵,而且似乎频频成为违禁知识的提供者。对于印刷机的个形象描绘出现在1499年,图画中描绘了它的两名操作员被拖走的场景,此二人大概是被拖进了地狱。如历史学家所指,如果说一本希伯来文书籍在1475年面世,那么一本反犹出版物也是出现在这一年。如若印刷书籍能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给良善公民带来启迪,那么它也可能点燃那些忠诚度不甚高者的怒火。在法国,路易十二世确实宣称过“印刷术”是一项神赐的发明,但不到一代人之后,他的继任者弗朗索瓦一世(尽管被冠以了“文学之父”的头衔)对此的期望却已经彻底幻灭(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试图彻底压制印刷术的发展。这正是“印刷革命”的悖论之一,它不仅为近代这一宣传时代奠定了基础,也为其意识形态上的正面的、预防性的审查奠定了基础。
审查制度以及控制思想的尝试也是缮写传统——特别是大学纪律的组成部分,它在传统上要求“理性”须服从于“威”,尽管这种威的定义在几代人的历程中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在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亚里士多德哲学从智识激进主义的化身转变为为顽固的正统信仰的象征。整个基督教哲学史和神学史的一个侧面便是关于谬误的记载,这些谬误或被调和,或遭到了多多少少的压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有其异端历史撰述[比如布林格包罗万象的《谬误之源》(Origins of Errors)],并企图采取类似的方式压制它们。从15世纪晚期开始,无论是帝国还是教皇都试图审查印刷书籍——1501年,一项为此目的而出台的帝国敕令便被辩称为“良知之职责”——而在路德出现之前,“罗伊希林事件”已经成为这项政策的可耻焦点,该政策的目的即在于没收罗伊希林派系所撰写的书册。11515年,教皇利奥十世(Leo X)颁布了一项“关于书籍印刷”的重要法令,因此就总体而言,制度上的防卫措施已准备好了应对让“罗伊希林事件”迅即相形见绌的路德教派的攻击。
尽管我们论及了路德的“新谬误”,但他的学说实际上与胡斯、威克里夫或任何过往改革者的学说并无二致,因为路德的“新”对于大多数批评家而言仍然归属于一个非常传统的类型。他们的反应也偏于传统。路德接受了问询,他的著作被分析并简化为一些有争议的命题,他遭到了学术威和教会威的评判,后又为世俗权力所谴责。年轻的皇帝查理五世在德意志地区的一项公开法令(它用法文撰写,于1521年在安特卫普刊布)便是针对路德之谬误与“愚蠢”思想的抨击。八年后,他又继续展开行动,基于一份著名的“布告”建立起了永久性的审查制度,遵从端但又因循守旧的惩罚措施,比如火刑、刺穿舌头和没收财产。作为典型,路德被与胡斯、威克里夫、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和扬•普珀尔•冯•戈赫(Jan Pupper von Goch)相提并论,其中,戈赫关于“基督徒自由”的著作虽然与路德的观点不同,但似乎也支持了后者。
在某些领域,这项立法颇见成效。根据法雷尔的一个朋友的说法,在1525年,梅茨驱逐了两名书商;而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从1527年至1550年期间,在印刷业曾于1521年得到蓬勃发展的洛林地区,“宗教改革的声音遭到了压制”。帝国的政策此后没有发生改变,1550年它又颁布了一项针对“由马丁•路德、约翰•厄科兰帕迪乌斯、乌尔里希•慈温利、马丁•布策尔、让•加尔文或其他异端魁首以及彼等之教派成员制作或编写的书籍”的敕令。鲁汶大学在1550年发布的禁书目录中警告读者:“勿要对这份目录包含了这么多不被认可的《圣经》和《新约》文本感到惊讶,因为异端魁首就从中产生。”
在法国,官方的反应如出一辙,而且同样迅速。在那里,审查制度也已成为一种传统的做法。1514年,巴黎大学对镇压罗伊希林的帝国运动表示了支持,在两年之内,诺埃尔•贝达就开始攻击各种异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和福音派人士。根据德•图的说法,诸如比萨大公会议,特别是1516年《宗教协定》的议题,促成了“大量著作”的面世,以及试图阻止其传播的官方行动。那么,路德的思想会受到何等的欢迎就变得毫无疑问了。人们对它的反应始于1521年春巴黎大学一份颇具针对性的“决议”,其中为“经院哲学”进行了辩护,并重申了圣礼的价值,以驳斥路德的谬误。至6月,世俗权力当局,即巴黎高等法院紧随其后,它首先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若无神学院的批准,任何书籍均不得出版,而后(在查理五世之法令颁布前几周)又通过了禁止印刷出版路德教派文本的法令。8月1日,这一法令在“号角声中”被宣读,有这类书籍都被下令上交给政府当局。这是专门针对路德教派、旨在压制印刷文本宣传的一系列法令中的一部。
在某种意义上,攻击性文本的风格是由路德自己决定采用的,因为他正是那个在1520年为了庆祝其对于天主教教义的摒弃而把教皇传统在书本中的化身——教会法合集扔进火中之人。他认为,数个世纪以来,圣人们亦是如此对待邪恶之书籍——事实上,古典时代和教会都为这种做法提供了先例,包括阿伯拉尔之著作在内的大量卷帙都曾被付之一炬。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路德本人的许多出版物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1521年,400册书籍在安特卫普遭焚毁,次年在根特被投入火海的书籍数量更众,而在1523年8月的巴黎,路易•贝尔坎充满了诸多谬误和可恶的异端思想的著作也遭到了所谓的“公开焚烧”(publica combustio)。遭到焚烧的出版物包括了标题为“论弥撒的废除”“虔诚和迷信之间的辩论”等等的书籍,一份针对亨利八世对路德之批判的回应,以及(伊拉斯谟匿名创作的)《儒略二世被拦于天堂之外》(“Julius Excluded”)的印刷副本。恰如伊拉斯谟本人曾对贝达说过的,继书册之后,活人辄受火刑之苦;事实上,一个星期后,法国的一位路德教派殉道者让•瓦利埃就因为“渎神谬论”而紧随贝尔坎的书卷之后被烧死。六年后,桀骜不驯的贝尔坎本人也加入了此君的行列。
自1534年布告事件后,对异端出版物的搜查变得越来越严格。次年6月,弗朗索瓦一世成立了一个高等法院特别委员会来监督针对书籍的审查工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比代在他于当年出版的一篇抨击圣礼主义新教神学家的文章中为这一政策进行了辩护;至少部分是为了回应这一言论,加尔文在其一年后出版的《基督教要义》初版中加入了致弗朗索瓦一世的书信。审查运动变得愈加激烈,在这种激烈的气氛中,加尔文和拉米斯都受到了来自立法机构的攻击。1542年,高等法院在一项实际上是反新教宣传的开创性法令中指出:《基督教要义》及其作者“阿尔昆”(加尔文之名的拉丁文变形词)是其有害的谬误来源。这本书受到了谴责,任何收到通知24小时之后还继续出售它的书商也会被定罪。事实上,他们被禁止出售任何此类书籍——“无论是法文的还是拉丁文的,无论大小”——而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的任务则是审查新的出版物(即使在语法方面)是否存在异端的迹象。根据1543年2月14日的一份高等法院判决结果,伊拉斯谟、梅兰希通、路德和加尔文的书籍被要求在巴黎圣母院前伴随着号角之声和大教堂钟声予以焚烧。这场运动的高潮是巴黎大学在次年开始出版的《禁书目录》(Catalogue of Censured Books),它的一系列续编成为新教文本的畅销书清单。在有关“邪恶教义”的作品中,不仅包括了已知的异端书籍,还包括拉伯雷和多雷的著作,而在其后的扩展版本中,甚至还出现了罗贝尔•艾蒂安《新约》译本的身影。
当然,这些管控公众舆论的努力并不囿于直接审查;它们只是对这一蓬勃发展的行业施加控制的更广泛尝试的组成部分。就像对其他有行会一样,这是通过制定针对印刷匠师和印刷工人的一系列立法而实现的。总而言之,其目的在于维护文字商品的标准,并让出版商对其产品负责。从1539年开始,印刷商就被禁止发行匿名的或使用笔名的书册,而从1537年开始,他们还要将印刷副本寄往位于布洛瓦的国王图书馆。除了各种法令之外,书籍只能在大学城出售。1551年著名的《夏多布里昂敕令》还要求印刷商保留底稿,并在每一版印刷书籍上标注其真实姓名。此类立法还涵盖了诽谤和渎神之问题,从而加强了审查制度。当然,这些尝试基本上是徒劳无功的。“火焰法庭”在宣传异端文本方面做得比压制异端文本更为成功。试图阻止移民流动和境外书籍涌入的1551年敕令也承认:“这些谬误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瘟疫,已经污染了我们王国的许多市镇和领土,甚至包括孩童。”由于图书贸易的存在,意识形态的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印刷业本身也遭逢困境,虽然这些困难肯定不是独立于宗教动荡之外的,但其确切的联系并非始终是显而易见的。主要问题来自学徒、书贩与底层劳动力难以操纵的力量;而他们也成为立法机关所关注的对象。从1539年开始,巴黎和里昂的印刷匠师们就遭遇了工人罢工,工人们对微薄的工资其缓慢的(或未尝有过的)增长感到不满。两年后,弗朗索瓦一世颁行一项法令,禁止了这种行为,甚至禁止了五人以上的集会。在贯穿这个世纪的劳工纷争中,印刷工人被发现或怀疑与流浪汉、乞丐以及更为不堪者相勾结。无照书贩普遍被贱视为小偷、酒鬼和“拈花惹草之徒”,他们的宗教和政治观点也因此受到了怀疑。为了达成某种程度的控制,后来的立法文件要求这些人充当学徒并具备低标准的识字能力,而渎神者以及其他顽固分子则可以被赓即解雇。
新教徒并没有否认印刷术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威胁,胡格诺派历史学家道比涅(D’Aubigne)就曾自豪地指出:“大批书籍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殉道者流传开来的。”印刷商始终陷于麻烦之中。在这个世纪里,法国至少有12名印刷商被处决,当然还有更多人受到了较轻的惩罚,或遭到流放。巴黎印刷商马丁•洛梅正是其中的一名受害者,他参与了1560年夏昂布瓦斯阴谋之后胡格诺派的一波宣传。在调查一起谋杀案时,闯入其宅舍的巴黎治安官发现了一些在巴黎流传的反吉斯家族著作,其中就包括了抨击洛林枢机主教的、后来被认为是由弗朗索瓦•奥特芒创作的著名作品《法国之虎》(Tiger of France)。一个月后,洛梅在大学城的一个传统行刑地——莫贝尔广场被处死。3其他类似事件比比皆是,例如同样在这几年里,里昂有三名书贩遭遇到了类似的命运——而这些事件又继续演变成为宗教战争中规模更大的暴力事件。当然,立法机关也试图控制印刷行。事实上,这场书籍之战的战场正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政府越发需要保护自己免受来自外国印刷中心的走私文本的困扰。1548年,来自日内瓦的书册遭到了禁止,但是收效甚微。与审查制度一样,16世纪60年代的抄没和焚书也无法阻止宣传的浪潮。
这一总体模式在欧洲各地重复出现,不仅在诸如神圣罗马帝国和萨瓦这样的天主教地区,亦包括了信奉新教的诸侯国与城市。例如,在宗教改革后的日内瓦,一部“印刷商敕令”就在1539年5月“伴随着号角之声”对外宣布;其市政议会对外来文本的评判也同样严厉。遭禁的作品包括了拉伯雷和波焦等“不信教者”的作品,以及在萨瓦发布的将日内瓦称为“异端巢穴”的“天主教徒”作品。然而,不同于法国的是,此地的出版许可有时只附带了一个条件,即这座城市的名称或作者的名字不得出现在书籍之中。在宗教战争伊始,为孔代亲王制作的一些宣传文本即是如此。无论如何,无许可印刷书籍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市政府官员们的标准非常之高,或者更准确地说,委员会非常谨慎,以至于连加尔文教派的宣传作品——比如贝扎的《论行政长官的权利》——有时都被拒绝出版,乃至在关键时期,奥特芒的《法兰克高卢》(Francogallia)的印刷副本也遭没收。对于像贝扎的著作以及(在日内瓦秘密印刷出版的)《警钟》这样的政治煽动性书籍而言,让城市当局担忧的并非出版物本身,而是它所要承担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内瓦是16世纪早期兴起的秘密印刷业的组成部分,尽管身居自己的领土之内,但这座城市的政府依然像其他国家一样谨慎而自私。
宗教战争的爆发并没有改变法国的审查制度,反而是加剧和规范化了它。曾经在一代人当中招惹众多是非的布告的散播至今仍然是一个中心问题,伴随阴谋而来的宣传本身也被谴责为暴乱的主因。1560年5月《罗莫朗坦敕令》(Edict of Romorantin)的谴责对象包括了未经当局许可的布道者与只会煽动人们发动叛乱的“布告、大报和诽谤性书籍,以及这些印刷品的印刷商、销售者和散播者,此辈皆吾等与公众之敌,犯有叛逆罪……”。在宗教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胡格诺派仍在四处张贴他们的布告,天主教徒也在出版其回击声明,并收到了回应,如此循环往复——后诉诸战争。一次宗教战争之后,审查制度得到了加强。没有高等法院签发的“特权”和财政大臣的许可,任何书籍、诗歌或散文皆不得出版,二十四位宣誓书商(libraries jurés)中的两位被任命为督察。当然,这种自我调节也无补于事。就像宗教战争本身一样,书籍之战也无法通过立法的手段来终结:宣传册和刀剑继续共同挥舞,它们各自的受害者都在不断增加。
- 中信书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美好的思想和生活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