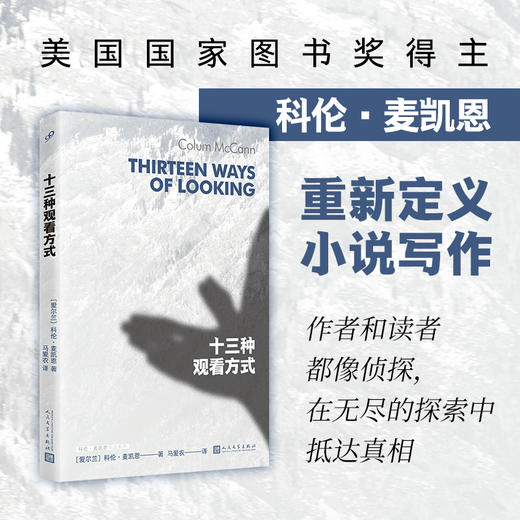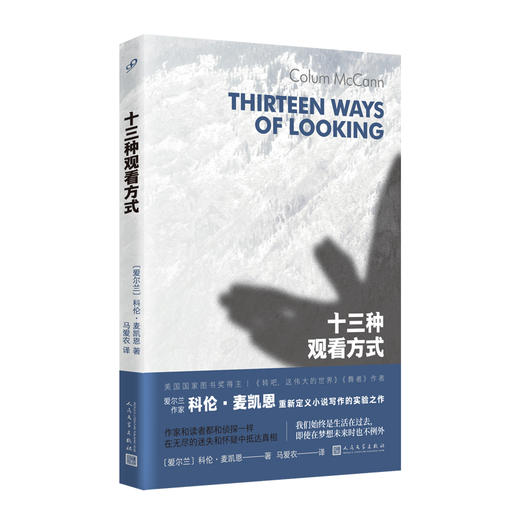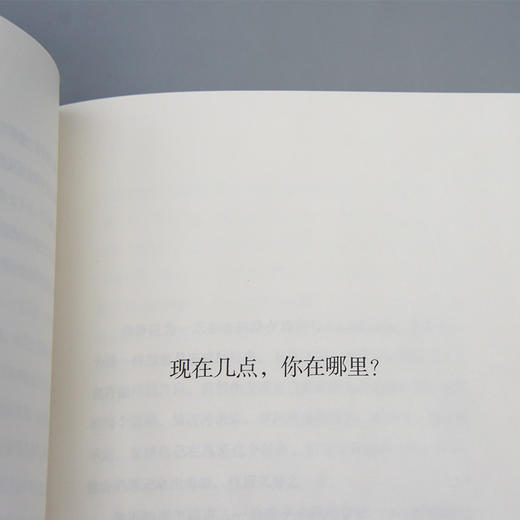十三种观看方式 科伦麦凯恩作品系列讲述日常生活中改变命运的偶然瞬间 马爱农翻译版外国经典文艺小说3000856
| 运费: | ¥ 5.00-15.00 |
| 库存: | 20 件 |
商品详情




作者简介:
科伦•麦凯恩,1965年生于爱尔兰都柏林, 1986年为小说创作来到美国,之后的一年半里,他骑车穿越了北美,为其之后的小说累积了大量素材。1988年至1991年,他旅居德克萨斯州,在德克萨斯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目前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教授创意写作课程。 自199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黑河钓事》起,麦凯恩已出版七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短篇小说集,包括《佐利姑娘》《舞者》《转吧,这伟大的世界》《隧道尽头的光明》《飞越大西洋》等。其中,《转吧,这伟大的世界》获2009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2011年度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其作品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
他最近的一部作品为长篇小说《无极形》(2020)。

内容简介:
《十三种观看方式》(2015)是爱尔兰作家科伦•麦凯恩实验性较强的短篇小说集,由一个中篇和三个短篇构成,故事的主题均和伤害、真相与和解有关。
本书同名中篇《十三种观看方式》,巧妙地以史蒂文森的同名诗歌中的句子作为每章的引子,作家用不同的视角、风格和素材去抵达发生在纽约的一桩命案,故事一直在不幸遇害的主人公门德尔松法官的主观叙述和叙述者的第三人称视角巧妙切换;《现在几点,你在哪里?》则接近元小说,小说中的一位作家受杂志邀约创作以圣诞节为主题的故事,他虚构了一个在中东战场上渴望与家人联系的女兵,她最终能否顺利打通那个电话,成为小说中被无限延宕悬置的问题; 《sh'khol》描述了一个中年离异的爱尔兰母亲遭受的意外,传递了形容丧子之痛的希伯来语单词sh'khol的微妙寓意;《协议》一篇中,即将抵达生命终点的贝弗里修女隐居长岛,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多年前曾虐待自己的人多年之后变成了走红的政客,她多年来建立的心理平衡瞬间瓦解……

媒体评论或名家推荐
麦凯恩的小说力量惊人,细腻和优美兼备。《十三种观看方式》这篇会一直在你脑海里萦绕不去。——《纽约时报》
催眠般的美妙阅读体验……那些不明白历史小说写作意义的读者,将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房间》作者 爱玛•多诺霍
麦凯恩是那种情感炽热的作家,他无时无刻不在试图更完整地理解他笔下所有的人物。——《华尔街日报》
麦凯恩继续淋漓尽致展现了他在《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中施展的魔法—— 写作的行为本身逐渐内化成小说的一部分。——《赫芬顿邮报》

精彩内容节选
维多利亚车站。拥挤的面孔。马哈鱼般密集的游客。她的长裙擦着地面。她的箱子没有轱辘,而且把手坏了,不得不拽着走,费力,笨拙。她很想休息一会儿。坐下来,让两条腿松快松快。找个避难所。游客礼拜堂,或小咖啡馆里一个安静的角落。
一只鸽子扑啦啦地飞过一架钢琴,把她吓了一跳。那架钢琴似乎是个艺术项目,放在火车站里,谁都可以去弹。
鸽子盘旋着,落在琴盖上,顺着斜边往前走。
在一个小食摊上,贝弗利给自己买了个羊角面包和用纸杯盛着的一杯茶。从纸杯里喝茶真别扭,茶包上的小纸片挂下来。没有地方坐,她慢慢溜达到钢琴旁,坐在琴凳的边缘。
后腰一跳一跳地疼。这趟旅行很艰苦,在肯尼迪机场延误两小时,在希思罗机场遭遇跑道事故,在帕丁顿坐地铁弄错了方向——到了终点站她才被叫醒。
鸽子飞回来,啄她的脚。她注意到它胖得出奇,是一种仿佛没有颜色的颜色。想想多么奇怪,它竟然住在车站里,在房梁上做窝,一辈子没见过任何一种树。
她把脑袋贴在钢琴喷漆的边缘,片刻后,被一个脸色苍白的小男孩摇醒,男孩想要弹琴,他的妈妈站在一旁,略含歉意。一时间,她恍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记得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别忘了你的茶,夫人。
她拍了拍小男孩的头。对他的一种祝福。以前是这样,很久以前,我们可以画十字。一去不返了,那些日子。或许这样也好:如果她想给孩子祝福,谁知道那母亲会说什么呢?
外面,天光洒下来,坚硬,清冽,微微泛黄。茶已变得温吞,但她还是喝光了最后一口。看不见垃圾桶。她把纸杯捏扁,塞进羊毛开衫的口袋,然后推着箱子,朝出租车候车点走去。
她相信自己远远地听见了模糊的钢琴声:男孩的自信和灵敏超出他的年龄。
她挤上前去排队,拍拍羊毛开衫的口袋,翻翻护照,寻找弟弟的地址。一张票根,几张收据,没有别的。上帝,快帮帮我。我必须找到他的地址。就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我记得的。
她把箱子平放在地上,用拇指打开钢锁。三条连衣裙,一件外套,一双换穿的鞋子,一本托马斯•莫顿写的书,一本新教皇的传记。强烈的绝望袭上她的心头,恶心的感觉从腹部深处开始,上升,蔓延。
——你没事吧?
出租车司机的衬衫领口处露出纹身,是某种蔓生的藤或荆棘。她盖上箱子,扣上锁,然后按住箱盖,不让自己向前摔倒,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他略感惊恐地抬头看着她。她比他高出整整一个头和肩膀。如果她摔下来,可能会把他也带倒。
——我丢了地址。我弟弟的。本来写下来的。是……我脑子不灵了。一阵阵犯迷糊。
——对不起,亲爱的,他说,这我可帮不了你。
她眼巴巴看着司机为另一位乘客打开车门。一根藤蔓。墨绿色。树丛里的电话线。无线电的声音。门上的一个小钢锁。逃跑。竹子很容易割断:一次是用磨尖了的衣架,一次是用一片波纹金属。她从缝隙间挤出来,穿着橡胶底的鞋子悄悄往前走。她一直走到河边,可是下雨后河水暴涨,把她吓坏了:她扑通跪倒,颓然靠在一个树桩上,等待着。他们找到了她,从头到脚都是蚂蚁叮出的包。恢复过来后,她挨了打。他用兜帽蒙住她的头。黑暗层层叠叠把她包围。布料散发出烂水果的气味。她吐了,他把她憋在兜帽里几分钟。后来,她喃喃地念祷文。一段接一段的祷文。她的身体在痛。她在流血。血渗透她的衣服。卡洛斯允许她清洗。那种可怕的尴尬。纵使她转过身,弓着背,遮挡住她的乳房、她的腹股沟,看到有阴影的地方就弯腰躲进去。有人在远处监视她。她不知道如果怀上孩子会怎么样。一次,她例假停了两个月。她吓得半死,还好后来又流血了。她没有被遗弃。她把自己洗干净。**不管在哪里,都要潜心祷告。**
贝弗利拖着脚离开出租车停靠点,回到火车站的遮篷下。脑子在跟她玩捉迷藏。她变得连自己也无法信赖。这些曲里拐弯,这些悄悄移位。远处仍传来钢琴声。也许是车站大喇叭里的音乐?伊恩住的那条街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我在机场时还有他的地址。在火车上也有。在地铁里也有。也许不小心掉到地上了。
一时间,她希望回到休斯敦,和那些女孩在一起。凭空变出一个安全的地方。回到熟悉、亲切、轻松的环境里。和她们一起站在后门口。高挑姐妹。坐在后门台阶上,抽烟。和其他姐妹并排跪在地下室小礼拜堂里。或者,哪怕就在长岛简陋的修道院里。走在海滩上,注视着海鸥在晨曦中飞过。安妮姐妹。卡米尔姐妹。还有另一个姐妹,阿根廷的,她想不起她的名字了,叫什么来着?
在沃克斯豪尔桥路的红绿灯路口,她停住脚。脑海里灵光一现,她想起来了:约翰•艾斯利普街。
* * *
他有了小肚腩,眼睛肿着,像是有一阵没睡好觉了,但他依旧高大、体面、满头银发,是那种傍晚独自在家也坚持打领带的男人。
——贝弗,他说。
她小时候的名字。这使她想起奥特拉河上的石桥,桥下的河水又急又浅,有浅浅的细纹。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他立刻伸手来拿她的箱子。她在公寓套房的悬崖上站立片刻。河水湍急地西流。夏天是红铜色。钓鱼的渔夫,站在河道拐弯处的歪脖子大橡树那儿。上面是低矮的红色天空。
他扶住她的胳膊,领她朝客厅走去。几面墙上都是书,显得很古雅:小说,影集,提前阅读本,诗歌。地板上也到处堆着书。
他把笨重的褐色长沙发上的五六本书扫到一边。书落在地毯上,与它们的同伴为伍。
——碰撞,她说。
伊恩握住她的手。他的手指冰凉。他现在用什么填满日子?他因什么而踌躇?除了书,还有什么霸占着他的思想?即使在很小的时候,他就不太相信上帝,不相信贫困、纯洁、虔诚的理念。最近几年,他在电话里责骂天主教。弊端。丑闻。玛德莲洗衣店。虚伪的官僚主义泥沼。他说,买者在无知中购得生命。她知道那些缺陷,可怕的耻辱,明目张胆的贪婪。她不需要反驳,为其辩护。她对教会也有过怀疑——也许比她弟弟知道的更深的怀疑。不是在丛林里的时候,而是后来,在圣路易斯医院的清爽的被褥里,她承认了恐惧,似乎此事被设定了延迟。她自己曾有过什么欲望?上帝塞给她一面什么镜子?那些日子里,谴责排山倒海向她袭来,她几乎无力招架。她告诉自己那是她的过错:她的身体,她的思想,她的失败。她引诱了他。她自找的。她活该。日子保留了它们的亮光。她的心灵是一粒空瘪的种子。绝望弥漫在黑暗的壳里。
——你还好吧?出什么事了?贝弗?你刚才说了碰撞。
——是吗?
——我去沏茶。我给你端一杯茶来。
——太好了。
茶杯咔哒响。他从拐角处探出头。
——我马上就来,他说,你别睡着了。
接着,她听见茶壶刺耳的哨音和冰箱门的一声轻叹。
一个书架上,放着他们父母的一张照片,他们坐在一辆老爷车的前保险杠上,车子有很大的白车灯,弧形的面板,空气喇叭。一个不可能的时代。他们在距她很远的地方,不在记忆中,而更多是在照片里。在公寓深处的什么地方,她听见某人的话音,接着突然响起古典音乐。收音机里的钢琴曲。
伊恩走进房间,小心地把托盘放在桌上。两个瓷茶杯,一盘饼干,一个带保温罩的茶壶。他仍是一个老派的男人。很久以前,他结过一次婚,娶了个苏格兰女人,但两人没有孩子。那女人短头发,戴眼镜。一位语言心理学家。他们离婚了。伊恩起初不敢告诉贝弗利。那女人叫什么名字来着?这些词总是偷偷跑掉,就像空气从她肺里慢慢溜走。
他用一个小金属过滤器倒茶,然后举起牛奶壶,似乎不仅在权衡她的口味,还在评估她的举止。
——我觉得我现在很健忘,伊恩。
——哦,上帝,不会吧。
——不是阿尔茨海默症,不是那个。
她把茶杯举到唇边,停住了:准确地说,不是健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应该说是一种记忆复苏。
——你究竟想说什么?
——知道吗,他回来了。
——谁回来了,贝弗?
随着她的讲述,她弟弟脸上如同幕布拉开:在休斯敦心力交瘁,迁至长岛,电视上那人再次露面,困惑,怀疑,深夜在楼梯上与安妮姐妹谈话,在海滩漫步时卡洛斯的脸不断闪现,他如今成了一个和平人士,这令她惊慌,令她无法释怀,她必须过来看到他,她必须看看这是不是真的,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摧毁和平的人是否可能找到和平,一个人怎么可能改变得这么彻底,他内在的变化是在哪里发生的,她正在寻找的那个词是什么,和解?
——目前他在参加某个和平会议?
——是的,一个机构。
——你想见到他?
——我甚至不敢确定那是不是他。
伊恩的眼睛里快速闪过一道光:绿眼睛,跟她自己的一样。所以,是一个兄弟。也许是这么回事?也许卡洛斯有个兄弟?一个表兄弟?她从来都没想到过这点。甚至是孪生兄弟。紧张感钳住她的喉咙。如果她犯了个最简单的错误,那只是个长相酷似的人呢?相貌完全一样,本质却截然相反?
伊恩从盘子里拿起一块饼干,轻轻咬下去,让它在舌尖融化。
——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天,没错。
她不由得发出刺耳的喘息声:哦,我错过了弥撒。有生以来第一次。我错过了弥撒,伊恩。真不敢相信我错过了弥撒。
——你在旅行。
——我很疲倦,伊恩。非常、非常疲倦。
她把托盘举到茶杯下,稳住自己颤抖的双手。
——我相信会有某种豁免,对吗?是不是有一个天主教的词?
他用脚趾拨拉他的书,似乎能在地板上散乱的书中找到那个词。
——赎罪,他说,打了个响指。对吗?赎罪?
- 99读书人 (微信公众号认证)
- 外国文学出版品牌·99读书人微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