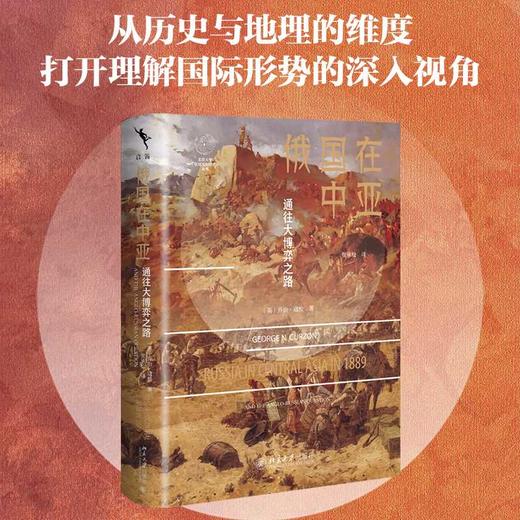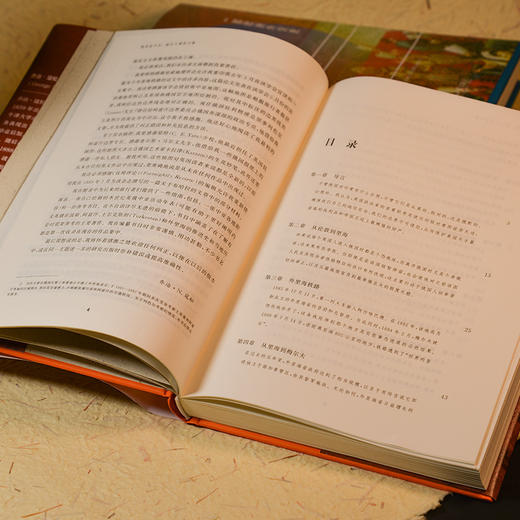商品详情

【英国】乔治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乔治寇松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1859年出生于英国的贵族家庭。他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对英国的中亚和印度事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在1885年毕业后加入保守党担任索尔兹伯里的秘书,之后成为下议院议员。1888年,寇松以议员身份前往中亚、波斯和中国进行考察,先后出版了三部相关的著作。此后寇松先后担任印度事务部次长(1891_1892)、英属印度总督(1899_1905)、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1911_1914)和英国外交大臣(1919_1924),并在1921年授勋为侯爵,他对英国印度事务和外交政策的制定曾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贺承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贺承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边疆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兰州大学上合中心;有恒欧亚编译团队成员。
第一章
导言 3
第二章 从伦敦到里海 13
第三章 外里海铁路 25
第四章 从里海到梅尔夫 43
第五章 从梅尔夫到阿姆河 67
第六章 高贵的布哈拉 97
第七章 撒马尔罕和塔什干 131
第八章 外里海铁路的延伸和影响 167
第九章 英俄问题 197
第十章 俄国在中亚的统治 235
附录一 1889年外里海铁路车站及里程表 252
附录二 中亚地区距离表 255
附录三 中亚事件年表(18001889) 261
附录四 外里海行人指南 270
附录五 1873年俄国和布哈拉条约 273
附录六 1881年俄国和波斯条约(关于阿哈尔_呼罗珊边界) 276
附录七 中亚参考书目 279
注释 316
第九章英俄问题
也许可以说,无论是外里海铁路的修建,还是某些人对其的敌意,都不能用作证明英俄在东方关系值得真正警惕的证据,有关于目前危险或未来冲突的理论只是教条主义者的梦想。因此,我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英俄问题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我将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英俄问题、指出英俄问题确实存在的理由并解释英俄问题的现状及其在不久的将来可能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我将从自己在该国的观察、历史教训以及俄国军官和政治家发表的意见中寻找证据。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准备对亲俄假说做出很大的、也许是不寻常的让步,这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而是因为这是真理使然,而真理往往被冲突双方的文字所歪曲或忽视。我不认为俄国的政策在一个世纪、半个世纪或更短的时期内都被一个坚定不移的、马基雅维利式的目标所驱使,这个目标就是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俄国每一个前进的行动都严格服从于这个目标。我在圣彼得堡时,英国《标准报》(Standard)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把俄国报纸气得火冒三丈。这篇文章把俄国在亚洲的推进比作一条巨大的冰川,无情地碾压着面前的一切,尽管它的前锋可能会被冲散和摧毁,但在后面的雪(即俄国外交部)不可抗拒的压力下,永远向前推进。我认为没有比这更错误的想法了。我不认为俄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贯的、无情的或深刻的,我认为它是一种;见风使舵(hand_to_mouth)式的政策,是一种等待事态发展、从别人的错误中获利的政策,而她自己也时常犯下同样的错误。例如,她对保加利亚和对根据《柏林条约》获得解放的基督教民族的态度,就是一长串无法弥补、几乎难以想象的错误。迄今为止,她从她当时同意的东南欧和解中获得的唯一好处,就是保加利亚的亚历山大和塞尔维亚的米兰这两位君主的退位。
我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统一意见或行动计划的政权还能有什么其他政策。这个政权下的各个将军或总督的独立性只能通过皇帝的个人权威来改变,而皇帝的意志可以凌驾于大臣会议的一致表决之上,他不负责任的独断专行非但不能保证行为的稳定性,反而常常导致政策的不协调。一个具有强大人格魅力的君主可能会给国家政策带来特殊的偏向,或者给它打上自己个性的烙印。但是,在这巨大的独立性中,也存在着巨大的失误空间。而一个软弱的或者一个容易受他人影响的人则受这种天性影响,在一连串谋士的影响下可能会制定出一种虚夸与空洞交替、强势与低能混杂的政策。俄国政府经常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惊讶,就像对手国家对自己的成功感到震惊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1885年的库什卡事件绝非像英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精心策划的一部分,而是科马洛夫和阿里汉诺夫的即兴之作,它在圣彼得堡外交部和白厅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俄国大臣们向来精通的一个领域就是将自己拥护者出乎意料的决策和对手意料之外的失误转化为有利的结果。如果俄国边防军官员擅自行动,破坏了某些外交协议,但却取得了成功,那么他的罪行就会得到宽恕和原谅,如果失败了,他就会被轻易地否定。很难高估俄国统治范围的扩张,特别是由个人野心在轻率地独立于国内命令的情况下造成的向中亚扩张。当侵略已经发生,征服已经完成,俄国人对东方政治的方方面面有了足够的认识时(这是英国人长期的经验无法获得的),他们不会从已经占据的地位或已经获得的优势中退缩。1866年,切尔尼亚耶夫因越权而被召回。但他的继任者罗曼诺夫斯基却将他的措施推得更远,而将军本人最终被派回他曾任总司令的省份担任总督。而对成功者更常见的情况则是会马上得到圣彼得堡的饰品和宝剑。每一个这样的皇室认可标志都是对那些毫不掩饰行动的一种激励。
我所描述的状况与这样一种制度密不可分:在这种制度下,军事组织处处取代了民事组织,需要政治家天才的工作却被委托给军人锤炼。而奇怪的是,违反外交惯例或国际义务的情况却没有变得频繁。关于这些事件的发生以及据此对俄国人两面三刀和恶意行为的合理指控,我唯一惊讶的不是俄国人编造了一些辩解,也不是他们接纳了那些辩解,而是英国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一次又一次地认可,被同样透明的手段蒙骗。我们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现在伦敦外交部传统的咆哮更不体面或暴躁的了,但这种咆哮只需通过外交保证来平息,从来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我们不得不抱怨自己受到侮辱或愚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能归咎于自辱。希瓦、浩罕、阿什哈巴德、梅尔夫和潘杰德: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对吞并的前景发出可怜的呼声,而一旦吞并成功,我们都会服帖地坐下来接受事实。半个世纪以来,英国人士一直宣称赫拉特的失守将为印度敲响丧钟。而当这一打击真的落下时,我确信英国人的鹅毛笔将造出成堆的傻瓜纸(fools_cap),但我不太确定英国人的剑是否会从剑鞘中抽出来。
我的这次行程使我在另一个方面改变了英国人对俄国前进动机的普遍看法。虽然俄国从里海向东出发并向土库曼尼亚进攻时只能远眺英国和阿富汗的情况可能是事实而且我马上会引用一位俄国政治家的最重要的电报来证明这一点但同样清楚的是,一旦开始了征服外里海的事业,她就不可能只在盖奥克泰佩、巴巴杜尔马兹、萨拉赫斯或梅尔夫停留。正如从奥伦堡向草原的第一次进军注定会以占领塔什干为终点,不管俄国书信体大师戈尔恰科夫亲王会做出怎样相反的保证,洛马金在外里海的第一次混战也必然会成为俄国人的梅尔夫兵营和阿姆河桥梁的先驱。援引地缘原则还是种族原则并不重要,二者都可用于开脱罪责。事实是,在没有任何有形障碍的情况下,在一个以掠夺为生活准则的敌人面前,在一个只懂失败而不懂外交逻辑的敌人面前,俄国就像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不得不前进。如果有人有合法权利抱怨她的前进,那肯定不是那个有能力阻止却故意拒绝行使权力的人。
不过我承认,我认为俄国进入中亚并不是出于深谋远虑的政策,而主要是受自然力量的驱使。但我也同样相信,她在那里的存在对印度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而且她出于自己的目的准备把那里变成对自己有利可图的宝库。她就像一个自然而然却出乎意料地继承了一个富有亲戚遗产的人,她从未听说过这个亲戚,但却是这个亲戚不为人知的继承人。俄国发现自己在中亚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她既可以通过开发一个大陆的物质和工业资源来为自己谋利,又可以在其最脆弱的地方攻击强大的对手,而这个对手的传统政策是敌视俄国在欧洲实现其所谓民族愿望的。我想在俄国,除了少数的投机理论家和时不时冒出来的无脑狗才之外,没有一个人真正梦想着征服印度。不管是俄国人还是英国人,只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浅显的研究,就会觉得这个计划太荒谬了。这将是一项成就,与之相比,一家贸易公司获得印度(这本身就是历史现实)将沦为儿戏。这将涉及世界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持久的战争,它会造成一种损失虽然这种损失几乎不可能发生其影响并非局限在印度而是覆盖全人类,那就是英国人纺织品的
丧失。对于那些追求更多实际考量的人来说,我们可以指出,尽管俄国现在拥有运输方面的所有优势,但它仍然面临着补给方面的困难,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即使在阿富汗冲突的早期阶段,这个困难已是很大的,而随着它向巴尔赫或赫拉特以外的地方每推进一公里,这个困难就会以几何级数增加。而且英国最近在比欣和俾路支斯坦边防线的扩展和加固,让她在涉足印度斯坦的丰饶果实之前还有不少开胃菜要破解。当一支俄国军队从巴尔赫出发前往兴都库什山口,或从赫拉特南向坎大哈进军时,英国指挥官可能会有底气重复克伦威尔(根据伯内特主教的说法)在邓巴(Dun bar)发出的胜利感叹:;上帝现在将他们交到我手中了!
虽然俄国的政治家和将军们都不会愚蠢到梦想征服印度,但他们确实在认真考虑入侵印度,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坦率地承认,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帕提亚人(Parthian)后退、战斗,眼睛向后看;俄国人前进、战斗,目光也转向同样的方向。他的目标不是加尔各答,而是君士坦丁堡;不是恒河,而是金角湾。他相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钥匙在赫尔曼德河畔比在普列夫纳(Plevna)高地更有可能赢得。简而言之,让英国在亚洲被牵制,使其在欧洲保持沉默,这就是俄国政策的主旨和实质。英国必须尽快介入,挫败另一个《圣斯特凡诺(SanStefano)条约》,或再次用她的枪炮保护被打败的伊斯坦布尔。赫拉特一定会被一场事变夺去,安年科夫将军的车厢里正满装武装人员。我曾问过一位杰出的俄国外交官,在什么情况下俄国政府会认为自己有理由侵犯一年半前已经严正确定的阿富汗边界,并在东方与英国发生冲突。他的回答十分明确,他说:;如果出现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你们篡夺阿姆河以北的俄国领地,或者你们干涉我们在欧洲实现国家目标。这次不需要但以理就能解读墙上的字迹。
进一步证明这一意图的证据可以从每一位在中亚服役的俄国军官的坦率供词中找到,例如斯科别列夫的权威言论。通常斯科别列夫在几年前说过的话在几年后就会被军队实现。他在信中曾两次说过鞭笞亚洲的名言。1877年,他写道:
通过对此地及其资源的了解,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解决东方问题对我们有利的前提下,我们以俄国利益的名义在土尔克斯坦的存在才是合理的。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必须解决东方问题。否则,亚洲就不值得被鞭笞,我们在土尔克斯坦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利用我们在中亚新的强大战略地位,以及我们对路线和手段的熟知,对我们真正的敌人进行致命一击,岂不是很好? 除非(这一点很值得怀疑)我们决心打击他最脆弱处的策略本身就会让他完全让步。
此外,1881年他从盖奥克泰佩回来后,又写道:
在我看来,整个中亚问题就像白日一样清晰。如果它不能使我们在较短时间内认真处理东方问题,换句话说,不能使我们主宰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么这里就不值得被鞭笞。俄国的政治家们迟早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俄国必须统治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不仅关系到俄国作为第一强国的伟大,而且关系到俄国的防御安全,以及俄国制造业和贸易的相应发展。如果不在印度方向(很可能在坎大哈一边)认真展示,就不要考虑巴尔干半岛战争。在中亚,在相应战区的大门口,必须保持一支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强大军队。
历史事实可以证明,整整一个世纪以来,俄国政治家的头脑中一直存在着通过中亚打击印度的可能性。这些想法并不是一个人头脑中的产物,也不是中亚政策的附带结果,它们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尽管这种可能性既不是前进的最初动机,也不是后来吞并的诱因,但它一直在他们的耳边响起挑衅的号角,鼓励着许多危险的冒险,也缓和了许多暂时的失败。
也许可以说,无论是外里海铁路的修建,还是某些人对其的敌意,都不能用作证明英俄在东方关系值得真正警惕的证据,有关于目前危险或未来冲突的理论只是教条主义者的梦想。因此,我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英俄问题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我将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英俄问题、指出英俄问题确实存在的理由并解释英俄问题的现状及其在不久的将来可能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我将从自己在该国的观察、历史教训以及俄国军官和政治家发表的意见中寻找证据。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准备对亲俄假说做出很大的、也许是不寻常的让步,这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而是因为这是真理使然,而真理往往被冲突双方的文字所歪曲或忽视。我不认为俄国的政策在一个世纪、半个世纪或更短的时期内都被一个坚定不移的、马基雅维利式的目标所驱使,这个目标就是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俄国每一个前进的行动都严格服从于这个目标。我在圣彼得堡时,英国《标准报》(Standard)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把俄国报纸气得火冒三丈。这篇文章把俄国在亚洲的推进比作一条巨大的冰川,无情地碾压着面前的一切,尽管它的前锋可能会被冲散和摧毁,但在后面的雪(即俄国外交部)不可抗拒的压力下,永远向前推进。我认为没有比这更错误的想法了。我不认为俄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贯的、无情的或深刻的,我认为它是一种“见风使舵”(hand_to_mouth)式的政策,是一种等待事态发展、从别人的错误中获利的政策,而她自己也时常犯下同样的错误。例如,她对保加利亚和对根据《柏林条约》获得解放的基督教民族的态度,就是一长串无法弥补、几乎难以想象的错误。迄今为止,她从她当时同意的东南欧和解中获得的唯一好处,就是保加利亚的亚历山大和塞尔维亚的米兰这两位君主的退位。我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统一意见或行动计划的政权还能有什么其他政策。这个政权下的各个将军或总督的独立性只能通过皇帝的个人权威来改变,而皇帝的意志可以凌驾于大臣会议的一致表决之上,他不负责任的独断专行非但不能保证行为的稳定性,反而常常导致政策的不协调。一个具有强大人格魅力的君主可能会给国家政策带来特殊的偏向,或者给它打上自己个性的烙印。但是,在这巨大的独立性中,也存在着巨大的失误空间。而一个软弱的或者一个容易受他人影响的人则受这种天性影响,在一连串谋士的影响下可能会制定出一种虚夸与空洞交替、强势与低能混杂的政策。俄国政府经常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惊讶,就像对手国家对自己的成功感到震惊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1885年的库什卡事件绝非像英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精心策划的一部分,而是科马洛夫和阿里汉诺夫的即兴之作,它在圣彼得堡外交部和白厅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俄国大臣们向来精通的一个领域就是将自己拥护者出乎意料的决策和对手意料之外的失误转化为有利的结果。如果俄国边防军官员擅自行动,破坏了某些外交协议,但却取得了成功,那么他的罪行就会得到宽恕和原谅,如果失败了,他就会被轻易地否定。很难高估俄国统治范围的扩张,特别是由个人野心在轻率地独立于国内命令的情况下造成的向中亚扩张。当侵略已经发生,征服已经完成,俄国人对东方政治的方方面面有了足够的认识时(这是英国人长期的经验无法获得的),他们不会从已经占据的地位或已经获得的优势中退缩。1866年,切尔尼亚耶夫因越权而被召回。但他的继任者罗曼诺夫斯基却将他的措施推得更远,而将军本人最终被派回他曾任总司令的省份担任总督。而对成功者更常见的情况则是会马上得到圣彼得堡的饰品和宝剑。每一个这样的皇室认可标志都是对那些毫不掩饰行动的一种激励。我所描述的状况与这样一种制度密不可分:在这种制度下,军事组织处处取代了民事组织,需要政治家天才的工作却被委托给军人锤炼。而奇怪的是,违反外交惯例或国际义务的情况却没有变得频繁。关于这些事件的发生以及据此对俄国人两面三刀和恶意行为的合理指控,我唯一惊讶的不是俄国人编造了一些辩解,也不是他们接纳了那些辩解,而是英国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一次又一次地认可,被同样透明的手段蒙骗。我们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现在伦敦外交部传统的咆哮更不体面或暴躁的了,但这种咆哮只需通过外交保证来平息,从来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我们不得不抱怨自己受到侮辱或愚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能归咎于自辱。希瓦、浩罕、阿什哈巴德、梅尔夫和潘杰德: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对吞并的前景发出可怜的呼声,而一旦吞并成功,我们都会服帖地坐下来接受事实。半个世纪以来,英国人士一直宣称赫拉特的失守将为印度敲响丧钟。而当这一打击真的落下时,我确信英国人的鹅毛笔将造出成堆的傻瓜纸(fools_cap),但我不太确定英国人的剑是否会从剑鞘中抽出来。我的这次行程使我在另一个方面改变了英国人对俄国前进动机的普遍看法。虽然俄国从里海向东出发并向土库曼尼亚进攻时只能远眺英国和阿富汗的情况可能是事实———而且我马上会引用一位俄国政治家的最重要的电报来证明这一点———但同样清楚的是,一旦开始了征服外里海的事业,她就不可能只在盖奥克泰佩、巴巴杜尔马兹、萨拉赫斯或梅尔夫停留。正如从奥伦堡向草原的第一次进军注定会以占领塔什干为终点,不管俄国书信体大师戈尔恰科夫亲王会做出怎样相反的保证,洛马金在外里海的第一次混战也必然会成为俄国人的梅尔夫兵营和阿姆河桥梁的先驱。援引地缘原则还是种族原则并不重要,二者都可用于开脱罪责。事实是,在没有任何有形障碍的情况下,在一个以掠夺为生活准则的敌人面前,在一个只懂失败而不懂外交逻辑的敌人面前,俄国就像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不得不前进。如果有人有合法权利抱怨她的前进,那肯定不是那个有能力阻止却故意拒绝行使权力的人。不过我承认,我认为俄国进入中亚并不是出于深谋远虑的政策,而主要是受自然力量的驱使。但我也同样相信,她在那里的存在对印度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而且她出于自己的目的准备把那里变成对自己有利可图的宝库。她就像一个自然而然却出乎意料地继承了一个富有亲戚遗产的人,她从未听说过这个亲戚,但却是这个亲戚不为人知的继承人。俄国发现自己在中亚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她既可以通过开发一个大陆的物质和工业资源来为自己谋利,又可以在其最脆弱的地方攻击强大的对手,而这个对手的传统政策是敌视俄国在欧洲实现其所谓民族愿望的。我想在俄国,除了少数的投机理论家和时不时冒出来的无脑狗才之外,没有一个人真正梦想着征服印度。不管是俄国人还是英国人,只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浅显的研究,就会觉得这个计划太荒谬了。这将是一项成就,与之相比,一家贸易公司获得印度(这本身就是历史现实)将沦为儿戏。这将涉及世界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持久的战争,它会造成一种损失———虽然这种损失几乎不可能发生———其影响并非局限在印度而是覆盖全人类,那就是英国人纺织品的丧失。对于那些追求更多实际考量的人来说,我们可以指出,尽管俄国现在拥有运输方面的所有优势,但它仍然面临着补给方面的困难,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即使在阿富汗冲突的早期阶段,这个困难已是很大的,而随着它向巴尔赫或赫拉特以外的地方每推进一公里,这个困难就会以几何级数增加。而且英国最近在比欣和俾路支斯坦边防线的扩展和加固,让她在涉足印度斯坦的丰饶果实之前还有不少开胃菜要破解。当一支俄国军队从巴尔赫出发前往兴都库什山口,或从赫拉特南向坎大哈进军时,英国指挥官可能会有底气重复克伦威尔(根据伯内特主教的说法)在邓巴(Dun bar)发出的胜利感叹:“上帝现在将他们交到我手中了!”虽然俄国的政治家和将军们都不会愚蠢到梦想征服印度,但他们确实在认真考虑入侵印度,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坦率地承认,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帕提亚人(Parthian)后退、战斗,眼睛向后看;俄国人前进、战斗,目光也转向同样的方向。他的目标不是加尔各答,而是君士坦丁堡;不是恒河,而是金角湾。他相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钥匙在赫尔曼德河畔比在普列夫纳(Plevna)高地更有可能赢得。简而言之,让英国在亚洲被牵制,使其在欧洲保持沉默,这就是俄国政策的主旨和实质。英国必须尽快介入,挫败另一个《圣斯特凡诺(SanStefano)条约》,或再次用她的枪炮保护被打败的伊斯坦布尔。赫拉特一定会被一场事变夺去,安年科夫将军的车厢里正满装武装人员。我曾问过一位杰出的俄国外交官,在什么情况下俄国政府会认为自己有理由侵犯一年半前已经严正确定的阿富汗边界,并在东方与英国发生冲突。他的回答十分明确,他说:“如果出现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你们篡夺阿姆河以北的俄国领地,或者你们干涉我们在欧洲实现国家目标。”这次不需要但以理就能解读墙上的字迹。进一步证明这一意图的证据可以从每一位在中亚服役的俄国军官的坦率供词中找到,例如斯科别列夫的权威言论。通常斯科别列夫在几年前说过的话在几年后就会被军队实现。他在信中曾两次说过鞭笞亚洲的名言。1877年,他写道:通过对此地及其资源的了解,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解决东方问题对我们有利的前提下,我们以俄国利益的名义在土尔克斯坦的存在才是合理的。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必须解决东方问题。否则,亚洲就不值得被鞭笞,我们在土尔克斯坦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利用我们在中亚新的强大战略地位,以及我们对路线和手段的熟知,对我们真正的敌人进行致命一击,岂不是很好? 除非(这一点很值得怀疑)我们决心打击他最脆弱处的策略本身就会让他完全让步。此外,1881年他从盖奥克泰佩回来后,又写道:在我看来,整个中亚问题就像白日一样清晰。如果它不能使我们在较短时间内认真处理东方问题,换句话说,不能使我们主宰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么这里就不值得被鞭笞。俄国的政治家们迟早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俄国必须统治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不仅关系到俄国作为第一强国的伟大,而且关系到俄国的防御安全,以及俄国制造业和贸易的相应发展。如果不在印度方向(很可能在坎大哈一边)认真展示,就不要考虑巴尔干半岛战争。在中亚,在相应战区的大门口,必须保持一支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强大军队。历史事实可以证明,整整一个世纪以来,俄国政治家的头脑中一直存在着通过中亚打击印度的可能性。这些想法并不是一个人头脑中的产物,也不是中亚政策的附带结果,它们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尽管这种可能性既不是前进的最初动机,也不是后来吞并的诱因,但它一直在他们的耳边响起挑衅的号角,鼓励着许多危险的冒险,也缓和了许多暂时的失败。- 新华一城书集 (微信公众号认证)
- 上海新华书店官方微信书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