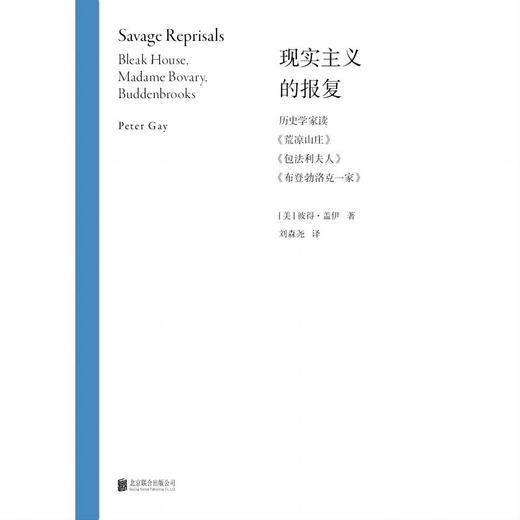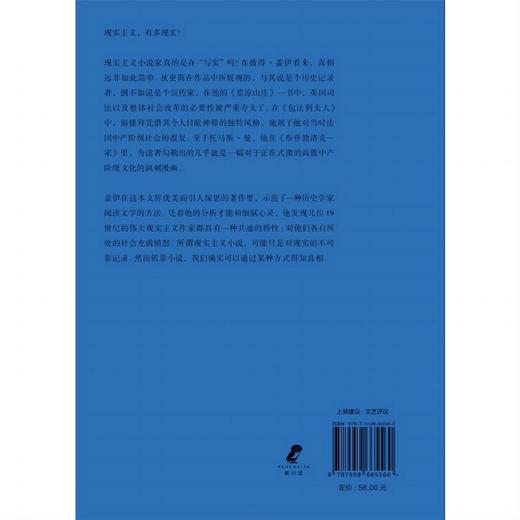商品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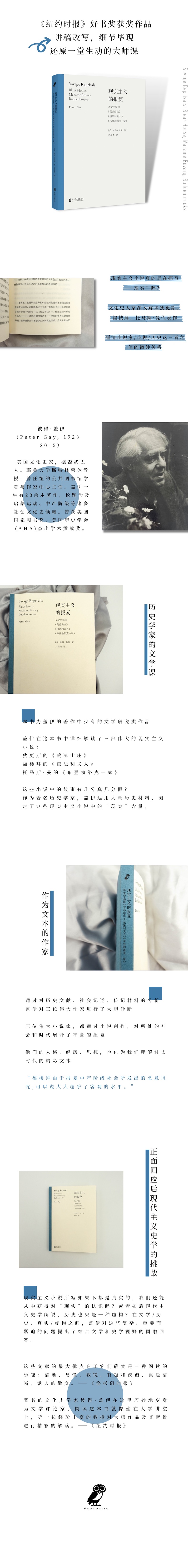 【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1.结合史实读小说,知人论世测量文本“现实”含量
狄更斯、福楼拜、托马斯·曼,这三位伟大小说家似乎都通过小说创作对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展开了率意的报复。《荒凉山庄》《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这些小说中的故事有几分真几分假?解答此类问题恰恰是历史学家的专长。作者运用大量历史材料,测定了这些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现实”含量。
2.给大作家做一次精神分析,以意逆志深入作品底层
这些伟大小说家如此书写的原因何在?熟悉精神分析的盖伊结合他们在小说和传记材料中的表现,对他们进行了大胆的诊断。透过有趣有料的八卦轶事,带领读者抵达名著和小说家本人的隐秘内面。
3.历史也是一种虚构吗?作者正面回应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挑战
现实主义小说所写如果不都是真实的,我们还能从中获得对“现实”的认识吗?或者如后现代主义史学所说,历史也只是一种虚构?在文学/历史、真实/虚构之间,盖伊对这些复杂、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提出了结合文学和史学视野的圆融回答。
【内容简介】
现实主义小说真的是在描写“现实”吗?
盖伊在这本书中详细解读了三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狄更斯的《荒凉山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位历史学家认为,这三位作家通过小说对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展开了报复。盖伊在这本书中结合历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分析了小说家、小说、历史之间的关系。本书为文学爱好者和历史研究者提供了结合两种学科之优势的小说阅读方法,让小说成为发现历史真相的辅助媒介。
【作者简介】
彼得·盖伊(Peter Gay, 1923—2015)
美国文化史家,德裔犹太人。耶鲁大学斯特林荣休教授,曾任纽约公共图书馆学者与作家中心主任。盖伊一生有20余本著作,论题涉及启蒙运动、中产阶级等诸多社会文化史领域。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历史学会(AHA)杰出学术贡献奖。
【目录】
序言:超越现实原则
1. 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狄更斯的《荒凉山庄》
2. 患有恐惧症的解剖师:福楼拜的 《包法利夫人》
3. 叛逆的贵族: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结语:小说的真相
引文出处
参考文献简述
致谢
【精彩书摘】
序言:超越现实原则
Ⅰ
在19 世纪, 文学的现实主义最为风行的时候, 这种风格备受赞誉, 其中以诗人惠特曼所说的一句话最为剀切中肯:“只要适当说出事实, 则一切罗曼司立即黯然失色。 ” 巴尔扎克曾经把自己看成是 “历史的抄写员” (the amanuensis of history) , 这样的论调将是本书要深入研究探索的一个主题,不过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小说家的强烈现实感。 1863 年2月, 屠格涅夫有一次在巴黎的一次晚餐聚会中———福楼拜、法国当时的批评泰斗圣伯夫 (Sainte-Beuve) 以及日记撰写者和小说家龚古尔兄弟 (Goncourt brothers) 等这些文学界名流都在场———这样说, 俄国的作家们, 虽然迟了些, 也都已经加入了现实主义的行列。
事实上, 即使进入了20 世纪之后, 欧美许多小说家仍然坚定奉行 “现实原则” (Reality Principle) , 他们和读者之间业已形成一种默契, 即作家有义务贴近个人和社会的真相,只创造 “真实的” 人物和环境。 简言之, 他们的小说必须呈现出日常生活的真实面。 至于描写英勇骑士和华丽冒险以及妖艳女色和不幸恋人这一类的浪漫传奇, 在他们而言是格格不入的。 相反, 这些现实主义者会在他们的资产阶级读者的生活情境中, 比如他们说话或生活的真实方式中, 去寻找写作的素材。 即使是经典的现代主义作家, 像普鲁斯特或乔伊斯, 他们在小说中所创造的人物都一样坚持遵循人类本性的法则; 事实上,《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这样的小说作品企图伸入人类内在的生活核心, 前者以细腻分析的手法著称, 后者则充满语言学方面的实验, 他们的方法比同时代的许多更墨守成规的小说家更有效。 无论是前卫还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们都在不断努力描绘具有可信度的故事背景和人物。
我在本书中预备要探讨的三位作家都是现实主义作家,只是他们各有不同风格。 他们的作品都一致指向对世俗生活的忠实描写。 以狄更斯而言, 他的小说充满对异常行为的描写, 甚至轻易把好人和坏人截然两分, 但他坚持———特别是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一书中———他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想象的场景, 都是符合自然和科学的法则的。 托马斯· 曼在撰写《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一书时, 他所依据的是他个人对吕贝克 (Lübeck) 早年生活的记忆, 他在书中所塑造的人物大都以家族中的成员或以前的旧识或甚至他自己的哥哥亨利希 (Heinrich) 为原型, 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让他的小说读起来逼真而具有可信度。 即使像福楼拜这样的作家, 那么鄙夷当时流行的所谓 “现实主义”, 甚至斥之为暧昧和粗俗的代名词, 然而他自己在写作《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一书之时, 还是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现实主义, 以不厌其烦且彻底的执着姿态去塑造他小说中的人物,让他们看起来就像现实世界中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栩栩如生。所谓的 “现实主义”, 不管作家、 批评家或读者如何定义, 他们都会一致同意, 一个严肃的小说家必须把自己严格限制在仅描写有可信度的人物, 生活在有可信度的环境之中, 然后参与有可信度的 (有趣的是, 它应该是人们所期望的) 事件。
然而, 随着小说家地位的不断提升, 这种情形遂把现实主义的领导者推向了现实原则之外。 他们不单只是平凡生活的摄影师和抄写员, 他们更是文学的创造者。 他们超凡的想象力使他们以社会科学家被禁止的方式获得了解放———所谓的社会科学家指的乃是社会学家、 政治学家、 人类学家及历史学家等 (本书下面的篇幅我将以 “历史学家” 统称上述的这些社会科学家, 以求简便) ———对历史学家而言, 首要之务乃是追求事实并给予理性的诠释。 因此之故, 19 世纪的作家们沉浸于不受陈腐观念束缚的权利中———当然一切仍得维持在理性的范围之内。 19 世纪中叶, 正当福楼拜在从事《包法利夫人》的写作之时, 曾经给他的女友路易丝 · 科莱(Louise Colet) 写过好几封很精彩的情书, 这些情书今天看来实在无异于美学论文, 他在信中反复强调: “首要之务: 对艺术的热爱。 ”
托马斯· 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出版之后, 曾经在他的家乡吕贝克造成不小轰动, 同时还招来许多恶意的批评,他感到很讶异, 因为他并未想到他的同乡会以 “对号入座”的心态来看待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他带着抗议的不悦口吻这样说: “一个作家企图面对的现实, 可能是他自己日常生活的世界, 可能是他最熟悉、 最热爱的人物。 他可以尽其所能将自己依附于这个现实世界所提供的一切细节, 也可以贪婪地、 顺从地利用现实中最深层的特质来表现他的文本; 但对他而言———对全世界亦然! ———在现实世界和他所完成的作品之间, 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换句话说, 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此两者之间永远会因为这本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
这种现实主义的策略可说相当富于说服力, 无须多加评论。 我们不必过分要求现实主义的现实程度。 诚然, 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和读者都很清楚, 现实主义并不等同于现实。 在《布登勃洛克一家》这部小说之中, 托马斯· 曼在推动故事进行之际, 有时会在叙述中间写上一句简单交代, 比如 “两年半过去了”, 借此提醒读者, 小说中时间会如杂技般飞跃。 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一书的后面部分用短短几个字 “他去旅行” 打断了男主角生活的连续性, 然后也一样用很简短的描述来交代男主角从1848 年到1867 年之间的所有行动。 现实主义小说把世界切开, 然后用特殊手法将其重新组合。 这是一个风格化的现实世界———经过推动和扭曲———完全为了作者描述情节和人物的发展之必要而设计。 甚至当小说家诉诸巧合事件的发生或 “神从天降” (deusex machina) 之类偷懒的设计时, 他们也声称, 他们所刻画的世界是真实的。
现实主义小说是文学, 而不是社会学或历史, 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的小说会允许类似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之中所出现的愉快或令人惊异的怪诞情节之发生, 也可以接受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之中对法国外省地区一位带有忧郁气质的美女之解剖式的描绘, 还可以欣赏托马斯· 曼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之中描写最具颠覆性的家族故事时所频频使用的反讽笔调, 这些都可以为读者带来许多阅读上的乐趣。 我并不反对文学批评家把小说家, 包括现实主义小说家, 看成是懂得把琐碎平凡的日常生活转化成艺术之黄金的炼金术士。我在这几页所说的任何内容都无意阻挠读者将小说视为具有自己的标准、 自己的圆满, 以及自己的胜利的一种美学产物。
毕竟小说实在是现代文明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成就。当然, 阅读小说的方式绝对不会只有一种: 可以把它当作文明的乐趣之泉源, 也可以当作是寻求自我精进的教育工具, 同时也可看成是进入某种文化的门户。 我已经指出其中第一种并加以赞扬, 至于第二种, 连同其善意和诚挚, 我预备留给精神的教育家和推销员。 在本书下面的篇章之中, 我想尝试去探索第三种: 把小说看成是知识宝库来研究 (不过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宝库) 。 在我看来这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因为如何从小说中提炼出真相来绝非不言自明。
和一般小说读者一样, 许多历史学家经常会忽略上述这层困难, 不加批判地把小说看成提供某种社会性和文化性信息的档案性资料。 当然, 一个有头脑的学者绝对不会把卡夫卡的《审判》看成是奥匈帝国时代有关司法体制的直接报道,同样的, 他也不会从《城堡》中考察土地测量员的职责。 然而, 19 世纪的小说家, 特别是大多数现实主义小说家———例如葡萄牙的克罗玆 (Eça de Queiroz) 、 法国的龚古尔兄弟、美国的豪威尔斯 (William Dean Howells) ———经常被当作时代特定信息的可靠提供者, 无论是法律规定, 或是社会习俗,像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以及妇女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是婚姻嫁娶中经济因素所占的比例, 或是一般公职人员的薪俸平均数额, 甚至称呼主教的正确方式, 所有这些都成为了学者们趋之若鹜的重要研究资料。
我们在此不妨看一下19 世纪西班牙小说家加尔多斯(Perez Galdós) 令人难忘的小说《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Fortunataand Jacinta ) , 小说的背景设定在1870 年左右,历史学家可以从中得到大量可靠的历史信息, 例如当时马德里的中产阶级婚姻是什么样子, 大学里的知识风尚如何, 以及商业交易和地方性政治怎样运作等等。 同样, 对百货公司的历史感兴趣的学者在左拉写于1883 年的《妇女乐园》 (Aubonheur des dames ) 中会有所收获, 只是要接受其中一些夸张和过度简化。 上述现象说明了为什么一本小说可以成为一份不可逾越的指南。 它处于文化和个人、 大与小的战略交汇点上, 在一个亲密的设定中操演政治、 社会及宗教等观念和实际运作的问题, 发展的预兆和时代的冲突等等。 如果我们阅读方式正确的话, 一本小说会是一种绝佳的启发性档案。
现实主义小说之所以具有如此丰富的综合意义, 正是因为它让其人物经历特定的时空考验, 好像这些人物都是作为其文化和历史缩影的真实的个人, 他们稳固地扎根于他们所生存的世界之中。 他们会有这样的成长过程: 起先当他们五六岁的时候, 就像是他们所生存的社会之小型综合缩影, 他们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长辈和师友———父母、 兄弟姊妹、 保姆以及仆人、 老师、 教士、 学校同学———那里学得行为的准则、 品位的标准和宗教信仰等等。 因此, 一个生长在意大利的小孩会讲意大利语或圣公会的小孩会依附圣公会的信仰,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样的小孩在经历了早年的家庭和学校生活之后, 便学会如何应对自己的兄弟姊妹、 学校同学以及权威人物, 有时会成功, 但有时会失败, 成功时获得奖赏, 失败时则是惩罚, 而且学到生存所需的一些小虚伪。 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必然要让其小说中的人物符合这样的基本生活事实。
小孩子在早年所习得的教训, 不管是轻易学来的还是顽固抵抗的, 总是会不断持续下去。 这在维多利亚时代不新鲜,在古希腊时代亦然, 从柏拉图的时代以至19 世纪初瑞士的教育改革者裴斯泰洛齐 (Pestalozzi) 的时代, 情况都是一样的。 早在弗洛伊德提出这一理论的一百年前,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就说过这样有名的话: 小孩乃人类之父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 。 1850 年, 福楼拜去近东旅行时, 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 “最初的印象总是无法磨灭, 您知道得很清楚。 我们总是带着自己的过去往前生活, 在我们一生的历程当中, 总会时时感觉到奶妈的存在。 ” 总之, 一个在家庭的茧中成长起来的人, 很难脱离小时候家庭生活强加给他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经常抱怨说: “资产阶级” 现实主义小说总是无法充分描绘出其人物所生存和活动的社会背景。 他们当中一位重要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认为, 资产阶级小说的批判性读者应该把艺术的语言转译成社会学的语言。但是我们不必去学习辩证唯物论即可认出我前面说过的, 大与小之间不断而紧密的互相作用现象。 霍桑在《红字》 一书中大肆发扬美国的清教徒精神, 他并没有凭借任何的文学理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卡拉马佐夫兄弟》 时, 并未得助于弗洛依德关于家庭三角关系、 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我在本书中将阐明, 想象的人物如何通过 (或通不过)这个世界加诸他们身上的各种试炼, 在最私密的领域里, 在内心中———比如在《荒凉山庄》 里主角对早期受虐的反应,在《包法利夫人》 里女主角对婚姻的幻灭, 在 《布登勃洛克一家》 里一个商业家族家道衰落的过程。 所有这些人物的反应都离不开文化上的因素, 但感知的唯一中心始终是个人,他们企图试探其中之缘由, 估量其所引发之结果。 因此, 我的读法不但可行, 甚至还会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对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生而言, 读小说时就像摆荡在大与小之间,然后探索其交互作用的道理。 简而言之, 小说就像是反映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
- 联合天畅 (微信公众号认证)
- 为了每一本书的抵达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