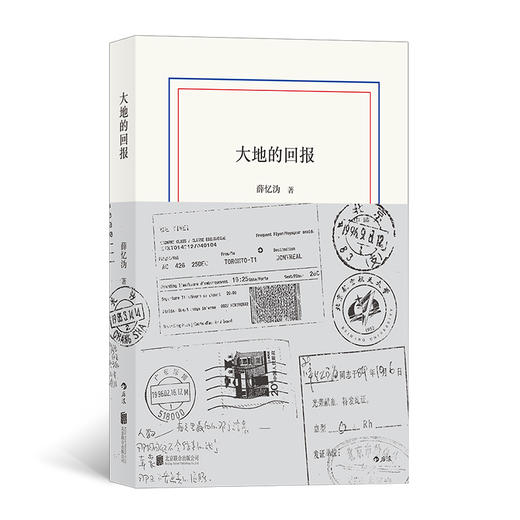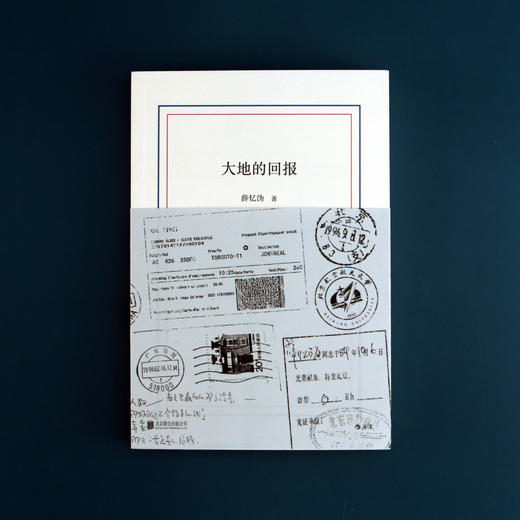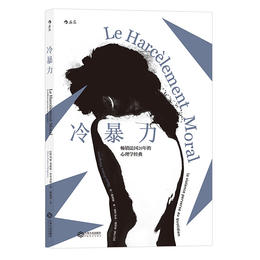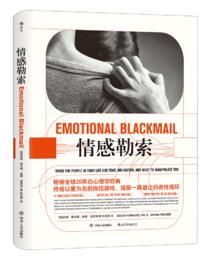大地的回报(被视为“中国文学秘密”的薛忆沩“文学三十年”作品集; 周国平、何怀宏、刘再复、哈金等名家推荐;)
| 运费: | ¥ 0.00-20.00 |
商品详情
作 者:薛忆沩
字 数:232千
书 号:978-7-5596-3316-3
页 数:384
出 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后浪出版公司
印 张:12
尺 寸:143毫米×210毫米
开 本:1/32
版 次:2019年7月第1版
装 帧:平装
印 次: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00元
正文用纸:75g书纸
编辑推荐
◎ 薛忆沩“文学三十年”自选虚构、非虚构作品集各一册,此为非虚构卷。
◎ 作品在国际引起关注,鹤立于国内文学界和知识界,无论何种形式、文体,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 连续荣获十大好书奖,进入各种年度书单,获得国际奖项。
◎ 周国平、何怀宏、刘再复、哈金等名家推荐。
名人推荐
他不属于文学界,因为他只属于文学:薛忆沩就是这样的经典作家。
——周国平
美丽、干净、温暖,是文学的祖国,也是思想的家园。
——何怀宏
愿更多的读者,与薛忆沩金子般的文字共鸣。
——刘再复
作为薛忆沩的欣赏者,我向他的勇气、耐力以及他对孤独的爱致敬!
——哈金
媒体推荐
被“翻译”发现的中国小说家。
——《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文学的秘密。
——《蒙特利尔报》 The Montreal Gazette
精细地呈现人的孤独是《深圳人》的成功之处。
——《责任》 Le Devoir
这位生活的极简主义者在语言里寻找自己的天堂。
——《新京报》
获奖记录
《遗弃》获2012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2014年第三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优秀作品奖;
《出租车司机——“深圳人”系列小说》获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2014年第二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2017年蒙特利尔的“蓝色都市”国际文学节(Blue Metropolis Festival)“多元文化奖”(Diversity Prize);
《首战告捷》获《南方都市报》2013年度“十大中文小说”;
《空巢》获2014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南方都市报》2014年度“十大中文小说”。
著者简介
薛忆沩,工学学士、文学硕士、语言学博士。出版过近 30 部文学作品。当代中国文学界罕见的同时精于“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家之一。作品近年被译成英、法、德、意、瑞典及保加利亚等多国语言,获大量国际关注。
内容简介
《大地的回报》为薛忆沩“文学三十年(1988-2018)”非虚构作品集,篇目、装帧设计皆由作者自选自定,具有纪念意义。
这本随笔选集包括薛忆沩曾被《读者》和几乎所有文摘类杂志转载的散文《外婆的〈长恨歌〉》《献给孤独的挽歌》《面对卑微的生命》,广受好评的《读〈看不见的城市〉》(节选),长篇随笔《异域的迷宫》等作品,充分展现了作者独特的思想境界和文学风格。
正文赏读
文学的祖国
如果我能够从一本书里面引出如下的一些句子,我引用的是哪一本书?
我深信,语言是我周围的世界混乱的根源。
口语好像是暴雨,书面语言则似乎是缓慢移动的白云。
人们以死亡来雕琢历史。
时间将我分析成一些基本的元素。我用这些元素组织起一个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中有一颗骚动不安的心。我假定那是我的心。
在我感到寂寞的时候,我进而感到自己是唯一的实在。
我无时无刻不在犹豫。我就是犹豫。
每个人都是死亡的候选人,而且都是一定能够最终获胜的候选人。
如果我能够从一本书里面引出如下的一些句子,我引用的会不会是同一本书?
去思想就是去毁灭。
我靠近的每一个柔软的事物都用锋利的刀刃刺伤我。
我已经悄悄地见证了我生命的逐渐瓦解,见证了我想成就的一切缓慢的隐没。
我写作就像我记账一样,细心又冷漠。
对我来说,世俗的爱是平淡的,它只能提醒我失去了什么。
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写的作品。我将自己在句子和段落中展开,我给自己加上标点。
我感觉如此无聊,我的泪水几乎都要涌出来了:不是那种会流下来的眼泪,是那种会留在内心深处的泪水。那种泪水起因于灵魂的病症,而不是肉体的疼痛。
这两组引文来自两本不同的书。其中第二本书的主体是一部由481个片段组成的“没有事实的自传”。作者将这部作品的著作权转让给了里斯本的一位助理簿记员。这个虚构的人物用作品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他“出生在一个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信仰上帝的时代”。而第一本书的作者称他的作品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愿失业的“业余哲学家”留下的日记。这位“业余哲学家”的一封短信出现在作品的开始。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一个例外,我只有在消失中才能够感到完美。”这个“虚构地”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人与那个“虚构地”生活在二十世纪初期的葡萄牙人在性格和思想上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翻读佩索阿的《惶然录》(The Book of Disquiet),我想起了我的《遗弃》。佩索阿曾经借用他的虚构人物的名字发表自己的一些诗作,而我也将自己在1988年前后写下的那些没有人能够理解的短篇小说慷慨地转让给了虚构的“业余哲学家”。这种转让使我不得不在一篇文章中佩服我的虚构人物比我自己“更高的”文学才能。看到这虚构的人物将我疯狂地写下的那些作品冷漠地安插在自己的日记里,我感到过难忍的嫉妒。我的这种感觉显示出我并没有能够借助写作来完全忘记自己。而《惶然录》的英译者在他漂亮的导言里告诉我们:最早忘记了佩索阿的是佩索阿自己。
但是,我们不能够像佩索阿一样忘记佩索阿。这个孤独的葡萄牙人靠翻译商业文件维持他简单而短暂的生活。他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对世俗的“爱情”更是或许从来没有过“体”验。像同时代的卡夫卡一样,他生活在灵魂的“城堡”里。这“城堡”的遗迹被语言保存下来。当我们以阅读的名义闯入这神秘的世界,我们会看到无数的镜子,我们会从这无数的镜子里看到无数的自己。
“我的祖国是葡萄牙语!”里斯本的那位助理簿记员这样写道。这显然也是佩索阿自己的声音。
语言是文学的祖国。这祖国蔑视阶级的薄利、集团的短见以及版图的局限。这是最辽阔的祖国。这是最富饶的祖国。
写作者的“分身术”
写作者是魔法师,这近乎常识的隐喻凸显了写作的“非凡”特质。以“变性术”为例:人类历史上第一例成功的变性手术完成于1952年,而对文学史稍有知识的读者都知道,早在1856年,也就是这医学奇迹发生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变性的壮举就已经在写作中实现。“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福楼拜这样说。这惊世骇俗的爆料扫除了比原罪还要原始的男女界限,确保了文学想象的自由。
与“变性术”相比,“分身术”的难度就更高了。能否成功地将连体的婴儿或者成人分开,医学至今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而要将正常的人体一分为二,让它们各行其是,不仅是技术上永远的难题,也应该是道德和法律上永远的禁区,医学专家们不会敢想,更不会敢做。但是,对于喜欢犯忌的文学家,“分身”只不过是“可能世界”中的一种普通的“可能”。他们不仅早已经“心想”,而且早已经“事成”。前者的例子在孩提时代第一次听到马雅可夫斯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说:激情的诗人在题为《列宁》的长诗中对伟大导师的工作压力充满了忧虑,想到了要用“分身术”来为他减负。而后者的例子以卡尔维诺的小说《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最为张扬。在那部建立在“分身”基础上的作品中,生活原本平淡无奇的子爵被炮弹一轰为二。平分的两半分别代表对立的善恶。它们在小说中短兵相接,你死我活。
这些都还只是有形的“分身”。写作者更依赖和更擅长的其实还是无形的“分身”。最伟大的文学家早已经用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实践了这一魔法。《哈姆莱特》是以父子关系为基石的悲剧。与它相关的一个经典问题也与父子关系相关:莎士比亚本人到底是哪个角色的原型,是那个一直犹犹豫豫的儿子(复仇者),还是那个始终忽隐忽现的父亲(受害者)?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地认定是前者,因为他是悲剧中的主角。而在小说《尤利西斯》中,以乔伊斯本人为原型的斯蒂芬却相信是后者。他提出了两点理由:从创作背景上说,这“国殇”似的悲剧来源于作者生活中的“家丑”(莎士比亚的妻子与他兄弟之间的暧昧关系);从文本本身来看,悲剧和悲剧主角的名字(Hamlet)与莎士比亚唯一的儿子的名字(Hamnet)仅一字母之差(对很多人而言,这还是发音很容易混淆的字母)。我的看法是以上两种看法的对立统一。我认为,死于悲剧之前的父亲和死于悲剧最后的儿子都以莎士比亚本人为原型,因为“to be,or not to be”显然是困扰莎士比亚自己的问题,而向兄弟复仇也出自莎士比亚本人的义愤。毫无疑问,支撑了整个西方文学正典的大师在悲剧的写作过程中对自己施行了“分身术”。
父子关系同样也是《尤利西斯》的基石。乔伊斯用这现代派文学的“镇店之宝”继续先师的“分身”魔法。整个小说的时间设定在“六月十六日”。这是乔伊斯与他的妻子第一次约会的日子(现在也成了爱尔兰和全世界“乔”粉们的法定节日)。这一路标说明男主人公(也是小说中的“父亲”)布鲁姆的原型就是乔伊斯本人。但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主人公斯蒂芬也以“儿子”的形象出现在这部小说之中。而斯蒂芬更是以乔伊斯为原型的人物,这几乎是现代派文学的常识。很明显,乔伊斯在写作过程中也同样对自己施行了“分身术”。
“分身术”在我自己的写作过程中也很重要。以两部在台湾发表的长篇小说为例。《白求恩的孩子们》的叙述者是一位居住在蒙特利尔的中年中国学者。他的许多特征让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读者都将我“对号入座”。而我曾经在一次访谈中宣称自己是他的朋友扬扬——那个十三岁自杀身亡的孩子的原型。我甚至提醒说,在“扬扬的妹妹”身上也可以看到我个人生活的影子。事实上,小说中这三个“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典型人物都是从“我”这个原型中“分身”出来的。
而《一个影子的告别》中那个形联神散的家庭里也有三个性格迥异的孩子:主人公X,他内向的哥哥W以及他外向的妹妹Y。细心的读者会发现,XYW正好是我名字汉语拼音的简写。这好像又是关于“分身术”的提示。
变化莫测的“分身术”就如同魔幻的时空一样,为写作者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是这精神的自由让语言能够乘着想象的翅膀在“可能的世界”中自由地翱翔。
语言、蝴蝶和彩色的螺旋
文学本来是与家园和母语密不可分的事业。但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质疑作家身份的20世纪不仅让历史悠久的“流放”继续成为一些作家别无选择的厄运,同时让名噪一时的“流亡”成为了不少作家义无反顾的归宿。这被迫与自愿的人才流动造就了一个以母语之外的语言写作的作家群体,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留下了特殊而醒目的痕迹。在这个群体中,由波兰语转道法语抵达英语的康拉德,由英语直达法语的贝克特以及由俄语同时向英语和法语挺进最后雄踞英语的纳博科夫表现最为突出,他们通过语言的“变节”而成为了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大家。
在他著名的随笔《为了取悦一个影子》的最开始,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总结了这三位文学巨匠“求助于母语之外的语言”写作的不同理由。在他看来,康拉德这样做是出于“需要”,贝克特这样做是想寻求与现实之间“更大的疏离”,而纳博科夫的理由则是出于“燃烧的野心”。根据这种总结,纳博科夫的“变节”显然最为奢侈。
(附带说一句,纳博科夫的同胞及同乡布罗茨基本人可以算是这个“变节”者名单上的第四号人物。在32岁刚被驱逐到西方世界来的时候,他的英语水平还只是斑驳的皮毛,而到47岁那年站立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的时候,他那高傲而深邃的随笔已经成为英语文学中深受同行尊敬的品牌。在那篇随笔里,布罗茨基宣称自己的“变节”仅仅是为了取悦一个影子:他心目中20世纪最伟大的哲人和诗人奥登的影子。)
事实上,英语并不能完全说是纳博科夫“母语之外的语言”。在1964年的一次访谈中,纳博科夫将自己定义为是“拥有一个巨大书房的家庭中的讲三种语言的极为正常的孩子”。(这句话像他的许多话一样也自相矛盾,因为能够流利地“讲三种语言”的孩子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年代都不应该算是“极为正常”。)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曾经对纳博科夫的语言进行了市场细分,称他“在餐桌上讲法语,在儿童室里讲英语,而在其他的场所讲俄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像俄语一样,英语和法语都可以视为是纳博科夫的母语。他的父母用这三种语言与他交谈。在他的回忆录《说吧,记忆》的第十章里,纳博科夫用一段特殊的“记忆”来说明自己成长于其中的特殊的语言环境。那发生在他11岁在柏林治病的时候。当时他的父母从圣彼得堡赶来看他。一天晚上,纳博科夫与他的父亲谈起自己对女性的感觉,他问父亲为什么自己一想到女性的形体就会有躁动不安的感觉。他的父亲正在翻读“德语”的报纸,他用“英语”向自己的孩子解释说,这不过是自然界里无数正常的因果关系之中的一种,就像羞耻会导致脸红,悲伤会引起眼泪一样。说到这里,他转而用“法语”对自己的妻子说:“托尔斯泰去世了。”这显然是他刚从“德语”报纸上读到的消息。听到这消息,纳博科夫的母亲好像感觉到世界末日已经迫在眉睫,她用“俄语”惊叫道:“天啊,我们该回家了。”
九十年代初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纳博科夫传记分《俄国岁月》和《美国岁月》两大卷。它内容一丝不苟,论断通情达理,文笔沁人心脾,被公认是纳博科夫最权威的传记。传记作者波依德提到了11岁的纳博科夫另外一段与语言和异性有关的经历。纳博科夫当时已经在翻译一部英文小说,那部小说中有不少关于女性身体的详细描写。而纳博科夫不仅不是将小说翻译成他的母语,也不是将小说翻译成小说,而是将这部英文小说翻译成“法文诗歌”。(这种语言的天赋让我想起与纳博科夫同年出生的博尔赫斯,他鲜为人知的处女作是他7岁那年用英文写的一份希腊神话的提要,而他的“作品二号”是他8岁那年翻译的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三种语言于一身的纳博科夫经常在中学时代的俄语作文中加入英语和法语的词句,因此得到了“好卖弄”的坏名声。
纳博科夫出生于1899年4月22日。他的家庭是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最显赫的家庭之一。他的爷爷是两位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三世)期间的司法部长。他的父亲也是著名的政治家,最后也在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推翻的临时政府中担任过司法部长(他特别为托洛茨基所不齿)。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纳博科夫的父亲同情贫困、向往正义,并曾因参与“反政府”示威而遭沙皇的监禁。不过,他却终身执迷于贵族的生活习气,据说他连自己的衬衫都要专门送到伦敦去洗熨。纳博科夫的母亲也同样出自名门。他的外祖父通过开矿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他的外祖母与知识界的权威有血缘上的联系。这样一个显赫的家庭自然会有许多枝节的故事。在六十年代中的一天(也是他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向对家庭的隐私讳莫如深的纳博科夫突然对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费尔德严肃地说道:“是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身体里流淌着彼得大帝的血。”这著名的“肺腑之言”暗示他的父亲可能有更为高贵的出处,也为纳博科夫的血统布下了不解之谜。
充实的精神和奢侈的物质的完美结合是纳博科夫一生中长达20年的“俄国时期”的特色。在父亲巨大的书房里,纳博科夫邂逅过无数名垂青史的先贤;而通过社会通达的网络,纳博科夫又亲历过不少货真价实的圣哲。托尔斯泰抚摸过他的头发。曼德尔施塔姆毕业于他就读的中学,并且为他们朗读过诗歌。传记作家格蕾逊将“语言的丰富”和“视觉的敏感”归结为纳博科夫为自己打开文学圣殿的两把钥匙。这后一把钥匙也与他的“社会存在”难舍难分:纳博科夫的母亲不仅在他的睡床旁用英语为他读故事,还经常让年幼的纳博科夫观赏和摆弄自己琳琅满目的首饰。纳博科夫自信是这后一种别有用心的熏陶成就了他“视觉的敏感”。(事实上,这些首饰不仅有虚幻的美感,还有实际的功用。纳博科夫在1919年7月写给他的一位家庭教师的信中说,是他母亲用首饰支付了他在剑桥读书那三年的昂贵学费。)
“视觉的敏感”与纳博科夫除语言之外的另一种“至爱”也应该有密切的关系。纳博科夫7岁那年在百忙的父亲的引导下迷上了蝴蝶。1908年,他父亲在被监禁的期间曾经收到过一封偷偷带进监狱的家信,里面有9岁的纳博科夫最新采集的蝴蝶标本以及他对父亲最新采集的询问。在偷偷带出监狱的便条中,深受感动的父亲用事实打破了儿子的幻想:“监狱的院子里没有蝴蝶。”追寻蝴蝶不仅成为纳博科夫终生不渝的迷恋,还一度成为他赖以为生的职业。他刚到美国的第二年就被聘为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博物馆的昆虫学研究员。在49岁那年成为康奈尔大学正式的文学教授之前,纳博科夫也兼有科学家、作家及教师三重身份(靠这三份微薄的收入他才足以养家糊口)。而他晚年未酬的壮志是编写一部关于欧洲蝴蝶的大作。在1963年的一次采访中,谈及他与蝴蝶的关系,纳博科夫又一次抛出了耸人听闻的语句:“是它们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它们。”这就是说,蝴蝶是他的宿命的一部分。就像琳琅满目的首饰一样,五彩缤纷的蝴蝶也宿命地雕琢和满足了纳博科夫“视觉的敏感”。
在他养尊处优的“俄国时期”,除了经常在欧洲度假之外,纳博科夫主要的生存空间是他们家在圣彼得堡市中心的豪宅以及他们家在圣彼得堡郊外的别墅。这豪宅和别墅与当今房地产广告“隆重推出”的品种不可同日而语。纳博科夫5岁那年,沙皇时代著名的首届全国行政代表大会(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前身)的闭幕式就在他们家的豪宅里举行。而他们家的别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被德军用来做东部前线的总指挥部。更重要的是,纳博科夫本人17岁那年从他的舅舅那里继承了包括一座豪宅,一座两千公顷的庄园以及一大笔现金在内的巨额遗产,未到法定的年纪就已经成了法定的巨富。当时,他正在初恋和热恋。他用自己的钱将自己的情诗印制出来(印了500册)在亲友中散发。那当然是纳博科夫最早的出版物。
但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结束了纳博科夫不劳而获的“俄国时期”。1919年3月,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在克里米亚被彻底挫败。绝望的纳博科夫一家在著名的塞波斯托港口挤上了一艘名为“希望”号的货轮,在接踵而至的红军的子弹的“护送”下踏上了不归之路。如果不是求助于差不多40年之后纳博科夫用母语之外的语言虚构的那个12岁的美国少女,这显赫的家世大概从此就变成了如烟的往事。是名垂青史的“洛丽塔”在苏联解体之后将纳博科夫一家带回了他们在圣彼得堡的故居。那里的一个很小的角落现在变成了名为“纳博科夫博物馆”的旅游景点。
2001年出版的《怀旧的未来》一书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中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在这本从“怀旧”的角度讨论文学作品的书中有关于纳博科夫的专门一章(题为“纳博科夫的假护照”)。作者是纳博科夫的同胞,哈佛大学斯拉夫语和比较文学的教授。她在这一章中提到了纳博科夫家的门房。在《说吧,记忆》一书中那门房是纳博科夫初恋时的信使。后来,他成了带领红军找到他们家保险柜的向导。门房的后人近年与博物馆联系,想将他们占有的纳博科夫家的物品卖回原处,但是博物馆却没有能力做成这笔怀旧的买卖。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对纳博科夫的创作有深远影响的初恋情人有点反讽的下落:她留在了红色的祖国,并且嫁给了一名“契卡”(克格勃的前身)的干部。
1919年5月,纳博科夫一家逃到了伦敦。他们离父亲从前的洗衣店近了,却离他们习惯的安逸和奢侈远了。纳博科夫长达20年的第一次“欧洲时期”从他的三年剑桥生活开始。据博伊姆的记载,纳博科夫在剑桥的生活仍然比较舒适。他住在剑桥三一学院著名的公寓里。他隔壁的房间里住的是电子的发现者汤姆逊,而斜对面的房间是四百年前牛顿的住处。他在求学的同时也积攒了更多的恋爱经验。可是,这舒适和平静被另一场悲剧打破。在纳博科夫毕业的前夕,他们家已经迁居俄国流亡者云集的柏林。他的父亲仍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一次由他主持的政治集会上,他用身体挡住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射向自己的政敌的子弹,从而结束了他向往自由的一生。
毕业之后,纳博科夫也回到了柏林。他靠教授英语、俄语、网球和拳击为生,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1925年,这个30年后将用“母语之外的语言”冲击人们的性观念的破落贵族青年走进了他自己的婚姻。经历过少数证据确凿和少数查无实据的绯闻之后,这婚姻并无大恙,它一直陪护着纳博科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就是在这个时期,纳博科夫第一次获得了他向往已久的作家身份。他开始用俄语写作,很快以“希睿”(Sirin)的笔名成了俄国流亡文学的名家。
但是,苏维埃的日渐强大极大地限制了俄国难民的文化扩张。而因为他的妻子是犹太人,法西斯的猖獗更是直接威胁到了纳博科夫的生存空间。在两股对立势力的共同挤压之下,纳博科夫终于不得不带着妻儿离开柏林。他们在巴黎暂住了一段,等待他们的“假护照”。最后在纳粹的铁蹄接近凯旋门的时候,纳博科夫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逃亡。
与20年前的那一次逃亡不同,这一次,他已经是丈夫和父亲;这一次,他已经在俄罗斯的流亡文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一次,他几乎是身无分文;这一次,他的行李中装有自己的两部俄文小说以及他的回忆录《这是我》(《说吧,记忆》最初的版本)的英文译稿……更重要的,这一次,他携带着一笔奇特的精神财富:一年前(1939年),纳博科夫的头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古怪的构思。他想用俄语写一部关于道德和欲望相冲突的中篇小说,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结婚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他妻子的女儿的继父,因为他对那个少女充满了幻想。
同样长达20年的“美国时期”使纳博科夫成为了我们所熟悉的纳博科夫。但是,要成为我们所熟悉的纳博科夫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方面,为了养家糊口,纳博科夫必须用极度的耐心来压制“燃烧的野心”;而另一方面,刚刚登上“新大陆”的纳博科夫又一次遇到了与“身份”有关的老问题:他的身上背负着俄罗斯文学的伟大成就,但是这昨天的荣耀却很容易变成今天的负担。他自己也已经通过写作在欧洲的俄国流亡者中建立起了响亮的名声,但是这旧世界的资本却无法兑换成新大陆的通货。他到底要用什么以及怎样去征服那些对俄罗斯文学和他自己的光荣一无所知的美国读者呢?
他首先必须果断地完成一次文学的自杀,一次痛苦的“破”,然后他又不得不顺利地完成一次语言的“宫外孕”,一次同样痛苦的“立”。于是,那个名为“希睿”的著名俄语流亡作家从此销声匿迹了,而中年的英语作家“纳博科夫”开始崭露头角。万幸的是,1950年,在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活基本上安定下来之后,纳博科夫想到了10年前他已经用俄语写出的那部构思古怪的中篇小说的提纲。“燃烧的野心”让他决定用英语将它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很快完成的第一稿令纳博科夫极度失望,几乎被他付之一炬。而他于1953年完成的定稿,不仅没有能够如他所愿在《纽约客》上连载,直接在美国出版单行本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1955年,《洛丽塔》的初版在法国出版。市场最初的反应几乎是悄无声息。但是,小说很快被英国大作家格林发现,他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将它列为1955年最好的三本书之一。这重大的发现将《洛丽塔》推上了登峰造极之路。三年之后,《洛丽塔》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在美国正式出版。50年代后期的美国,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令知识界诚惶诚恐的麦卡锡主义也已经降温。在艾森豪威尔治下,人民正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突然,从一位俄裔教授写的小说里走出了一个12岁的小精灵和一个因她犯罪、对她犯罪又为她犯罪的老继父。所有人都有点沉不住气了。《洛丽塔》的出版抢走了已经在《纽约时报》畅销书版上雄踞近30个星期的《日瓦戈医生》的风头。它成为了1958年美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它成为了影响20世纪下半页美国社会的“历史事件”。
- 后浪图书旗舰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后浪出版公司官方微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