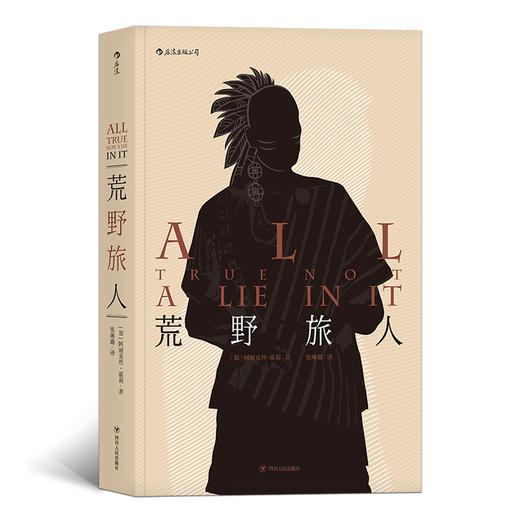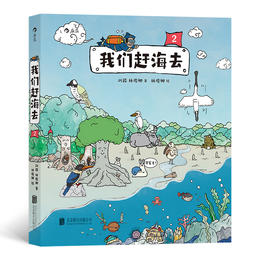商品详情

著 者:[加]阿丽克丝·霍莉(Alix Hawley)
译 者:张琳璐
字 数:324千
书 号:978-7-220-10432-9
页 数:376
出 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印 张:11.75
尺 寸:143毫米×210毫米
开 本:1/32
版 次:2018年2月第1版
装 帧:平装
印 次: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编辑推荐
◎ 加拿大文坛新星阿丽克丝·霍莉的扛鼎之作,入围多项文学奖项。
◎ 以主人公视角再现美国拓荒先驱丹尼尔·布恩的传奇人生,有血有肉,充满回味,亦充满张力。
名人推荐
看来阿丽克丝·霍莉对这位美国史上的草莽英雄着实下了一番力气。凭借其细致入微的描摹与想象,慢慢掸去历史的尘埃,勾勒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丹尼尔·布恩,以及他桀骜不羁的自由天性。可谓匠心独运,文采斐然。
——《戴珍珠耳环的女孩》(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作者特蕾茜·希瓦利埃(Tracy Chevalier)
我觉得自己几乎爱上了阿丽克丝·霍莉笔端的丹尼尔·布恩——怀着对荒野世界的永恒向往,永远热血,永远一往无前,永远为自由而不顾一切。
——《庇护》(Shelter)作者弗朗西斯·格林 斯莱德(Frances Greenslade)
书中山峦叠嶂,层林掩映,引人入胜,作者阿丽克丝·霍莉以天资与自信跨越风俗、年代与性别的障碍,重新赋予丹尼尔·布恩血肉之躯,以生动的口吻讲述时代背景之下的人物悲欢,既是声色享受,亦是情致体验。
——《奇迹时代》(The Age of Wonder)作者理查德·霍姆斯(Richard Holmes)
获奖记录
获2015年加拿大Amazon.ca First Novel Award
获2015年加拿大BC Book Prize for Fiction
获2016年加拿大Ethel Wilson Fiction Prize
著者简介
阿丽克丝·霍莉(Alix Hawley),1975年生于加拿大,曾先后就读于牛津大学、东英吉利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文学与写作。2008年发表首部小说集《习以为常》(The Old Familiar),先后于2012年、2014年两次荣获CBC文学奖第二名,并于2014年在加拿大世系文学大赛中拔得头筹。霍莉与家人现居加拿大基洛纳市,并在当地的大学执教。
内容简介
《荒野旅人》以主人公视角再现美国拓荒先驱丹尼尔·布恩的传奇人生。他是漂洋过海的移民之后,自幼在贵格殖民地长大,值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肯塔基州拓荒垦殖,两度被印第安人俘获。
他是闻名在外的神枪手,人送绰号“白皮肤的印第安人”。在肯塔基被俘期间,发现真我,成为反抗白人入侵的印第安酋长的寄子。
他是声名远播的探险家,与妻子丽贝卡爱情缱绻,然而却耽湎于开拓美好新世界的个人臆想,不断给自己以及身边至亲带来纷扰,甚至招致死亡。
他是丹尼尔·布恩,一个北美文学史上无出其右的传奇角色。阿丽克丝·霍莉以娴熟的叙事技巧和丰沛的情感笔触,以本书故事,首度为主人公塑像。
简 目
作者题记
上卷 执 迷
1. 宾州娼妇
2. 日渐疏离
3. 互生牵绊
4. 卡罗莱纳
5. 费城娼妇
6. 接连受伏
7. 樱桃在口
8. 面朝红土
9. 应许之地
10. 人间天堂
11. 有待发现
12. 大开狮口
13. 荒野之舞
14. 流连忘返
15. 总角晏晏
16. 侏儒矮人
17. 日出田野
18. 北而西往
19. 故地重回
下卷 不 悔
1. 若有天堂
2. 生死离散
3. 盐如风雪
4. 或赦或杀
5. 漫漫长路
6. 奇利科西
7. 洗肠涤胃
8. 人尽可夫
9. 飞短流长
10. 再踏征程
11. 特洛伊城
12. 法国王后
13. 宝马良驹
14. 吾父吾儿
15. 平白无辜
16. 阶下之囚
17. 肉食者鄙
18. 谢尔托易
19. 昔日重现
20. 情归何处
作者致谢
正文赏读
上卷 执 迷
“你姐姐是个不要脸的娼妇!”
“你姐姐不要脸!”
“不要脸!不要脸!”
他们伏在水河大桥下嘶声怪叫,简直像一窝卡在栏圈里的猪。这种滥调我打七岁起就听得多了。
“别惹我,我就是个不要命的莽夫!”我朝着大桥的方向吼回去。
木板缝之间眼光一闪,一块石头直冲我脑门,幸而被我闪身避开。另一个混小子不服气地继续添油加醋:
“他爷爷养的小娼妓,那可是艳名远播!”
“那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闻名丧胆——”
我跟他们就势扭成一团,一脚正中一个人的小腿,回肘砸烂了另一个的下巴,顾不得自己脸上也吃了一记重拳,抄起打鸟棍连连反击。混乱中只见威廉·希尔咧着嘴站在一旁,一只手捏着鼻头试图止血。哈哈。他退了两退,想挡一挡脸上的狼狈。我抽身便跑,边跑边骂,屎娘养的!—— 这句可是我自己的发明创造。不管怎么说,都是我赢了,我刚刚说什么来的,我可不好惹!
只剩希尔还在我身后一路穷追不舍,“小丹……小丹”地乱叫。我回过头骂他:
“你们知道个屁!我两岁的时候,德拉瓦尔人的族领还来过我家,向我爷爷讨了块蛋糕吃 — 我爷爷那时可有的是老婆,他老人家真该宰了你们这些混蛋 ——对,那可是堂堂萨萨诺恩王,我亲眼所见,虽说我那个时候才两岁。”
希尔停住脚,兴奋地呼喊:
“总有一天,你会立身扬名的,小丹!到那时,我要为你著本书!”
我知道他此刻一定在抹着嘴笑着,血糊了一脸,头发像蓬草一样遮在眼前。我知道他追不上了。我知道他一定也告诉了其他人,那些从他父亲嘴里听来的飞短流长,那些在埃克赛特被盖棺定论的风言风语:布恩一家简直寡廉鲜耻。你爷爷在英格兰蓄娼养妓!刚才桥下那个没错准是他,一开口简直跟他父亲在主持贵格会时的腔调如出一辙。尽管希尔总是胡诌八扯,但这次倒是所言非虚。
“小丹,我看到你了!我来了!”
我加快脚步,仍感到希尔那双充满好奇的明亮的灰色眼睛就在我背后。我俩也算是旧相识了,好像打一出生就相互认识了一样,以至于每每看到他,总觉得我俩就像耕牛离不开犁杖,被命数绑在一起,连同这个鬼地方一块绑在一起。我俩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敦实健壮,一样有点小聪明。只不过希尔的聪明仍有机会在詹姆斯叔叔的课堂上抖一抖,而我则早就受够了学校,乐得逍遥自在。我们两人的父辈也有诸多相似——都算得上是纺织业的同行,只不过希尔的爸爸早年做羊毛生意从英格兰发家,富庶有余,而我的爸爸只能日复一日守着仓棚里区区几台破织布机和同样派不上什么用场的锻铁炉。在我看来,我和希尔有的时候的确亲如伙伴,不过绝大多数时候则形同路人。倒是他单方面地一直密切关注我的一言一行,甚至试图模仿我的一举一动,好比说我是怎么把鸟棍掷出去的,或者一开始,我是怎么预备和瞄准的。他的这种一厢情愿倒显得他对自己本来的生活并无兴致,一心只想抓住我的生活。总之,希尔就是不肯放我一个人静静待着。
我撒开双腿,像是要甩开我的生活,甩开一直束缚我的所谓命数——
“你姐姐是个不要脸的娼妇!”
“你爸爸也有个不要脸的姐姐!”
大概已经跑出距奥瓦汀桥和小镇很远了,脚下的路渐渐收拢,变窄。一枝树杈划破了我的耳朵。又有两个混蛋边喊边追了上来,不过可惜没一个跑得过我。我感到手肘生疼,脚也是。该死的鞋。
“小丹,小丹!”
又是希尔,他大概以为我要翻到山另一侧的牧场去。他知道个屁,他什么都不知道。
好容易钻出了冬青丛,奋力跑上了小路,那帮混蛋肯定早就找不见我了。顺着这条路再往前就是祖父的石头房子,我没怎么去过,也没什么别人去过。那是一幢用深色石头砌起来的方形房子,和镇上的议事大楼差不多,只是看上去更残破些,像是位病怏怏的表亲。祖父养的猎犬都被拴在木屋边的链子上,吠声四起——他居然还没把那些破木头拆了!我的心怦怦直跳,闪身溜进菜园,闻到一股洋葱混合了坟墓的阴郁味道。
终于进了院子,我踏上石板阶来到门前狠命拍门。这还是我第一次不经爸妈陪同,单独一个人来这儿,紧张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门没锁,房子里弥漫着诡异的静谧和湿旧的霉气。
“有人在吗?”
没有回应。萨拉姑妈,哦,就是刚刚提到的“不要脸”中的一位,肯定正在屋后洗衣服呢,不然还能在哪儿。自打被逐出教友会,她就只有常伴祖父,伺候榻前了。也许此刻她正坐在草地上呼吸着这坟墓的气息,从中分辨着她丈夫的味道。那个搭上了别的女人而抛弃了她的男人,在死前又拖着病体回到了她身边。我想象着他作为一个死人,此刻被独自埋在土里的孤寂。父亲是决不能容许一个外人在死后葬进教友会的墓园的。被贵格会的长老们委派守陵,于父亲而言算是荣膺重任,再没见他对别的什么事这么上心了。你时常能看到他在新填的坟头上跩着两条罗圈腿反反复复地趟来趟去,居然是为了确保地面绝对平整如初。
我学着长兄伊斯雷尔的样子,哼着《我谁也不在意》,他最喜欢的小调,边走边掂着手里的打鸟棍,一路进了门厅。想想看,当时德拉瓦尔族长就站在那儿,对,就是那个位置,由妻妾们拥着,我也有幸陪站在侧。可惜年纪尚小,亲历的盛况如今只剩下记忆里的一条红色的披毯斗篷和纷至沓来的一双双鹿皮软底便靴。我像一个印第安人一样悄无声息地滑过地板,整幢房子安静极了,莫不是祖父已经死了?
我停在右手边第一扇门口,面前屋子里窗帘拉着,昏晦不明。我知道,祖父的卧榻就支在暗处,他和他的一把骨头就蜷在里面。我斗胆走进去,盯着他,看了又看,确信还有呼吸。唤他,他费劲抬起眼皮,扬起脸,那眼神大概以为我是某个贵格会的长老,又或者以为萨萨诺恩王的灵魂穿墙而入,披着他猩红色的毯子和羽毛发饰一起附到了我身上。
“你能看见我吗,爷爷?”我犹豫不决。他眯着眼睛,眼神混沌而黯淡。嘴和涎水耷拉着挂在左脸。我保持不动。他胸腔起伏。父亲曾给我讲述过祖父一生中的荣耀时刻,从1666 年出生于余焰未烬的伦敦开始。看着他如今垂垂老矣,尚存一息,想着他曾为了落脚他乡,在贵格派教友会面前坦言过往,他的放荡,他的不羁,他在登上开往宾夕法尼亚的渡轮前的种种。他以匠心营建新的议事大楼忏洗前尘,新大楼端立小镇中心,街衢自此四通八达。他给这座小镇取名埃克赛特,以此怀念英格兰的故土。但在我看来,这也许并非明智之举,那里的埃克赛特并不是他的幸运福地,那里不过是他的风流过往。
提起祖父,大家莞尔,心照不宣地相互点点头,就像提起任何一位睿智的长者,表面的恭敬实则未必出自真心。原本一切都好,直到萨拉姑妈外嫁,人们开始对这个家族的血统贵贱说长道短。我看着祖父伸出手,用右手那根掰不直的拇指在被子上划来划去,像是在操控着他的梭织机,像是他还在努力经营着他的老本行,像是他还未在风流场里散尽家财,像是他还年富力强,像是他还风度翩翩,任何一个看上眼的姑娘都手到擒来,像是他此刻就身在至乐天堂,也许这些正是他最初来到这里时怀揣的梦想。我不禁感到一阵晕眩,道了别正想转身离开,祖父忽然咳起来,挥挥手指向床边的尿壶。
“拿!”
尿壶放在黑色的雕花大木柜下面,庆幸里边是空的。他坐起身,在睡衣上一阵摩挲。
“你养过婊子。”我小声咕哝。
“什么?”
祖父散发着婴儿般的味道,确切说是奶味混合着尿味,可能比婴儿更臊一点。他手臂发抖。我深吸一口气接着说:
“但是,你也打过仗,还曾经从一帮坏人手上救了两个印第安女孩。”
也是我父亲讲给我们的。故事发生在议事大楼落成以前,那个时候的德拉瓦尔人和卡托巴人常常来此集市。一次,几个白人里的败类掳了两个女孩,祖父仗义执言,出手相助,给了钱,救了人。我试图想象年轻的祖父骁勇善战的形象。
“我也打了一架,就在刚刚。你看!”
我把受伤的手肘擎得高高的。祖父顾自尿得很响。他半张脸已经瘫了,另半张上的一只眼睛盯着我,像是盯着一个满嘴大话的骗子。我偷瞥他的尿具,了无生气,临了,淅淅沥沥溺在床单上,另一只手还瑟瑟地扶着尿壶。“会翻的,”我心里默念,“肯定会打翻的。”
“你来这干什么,嗯?你是,哪个?”
我感到自己的胃简直要从喉咙里蹦出来,冲着他近乎喊道:“我才不要变老,才不要变成跟你一样老得没人理的模样!我要打赢所有的人,要守住所有的秘密,不要像你,烂在这儿,不要!我要找到真正的伊甸园,要完成你没做到的事!”
走道里响起萨拉姑妈咯噔咯噔的木鞋跟的声音。祖父蹙着眉,颤抖着,循声摆过头去。他曾在贵格会上为她与外人通婚而跪求宽恕。我又想起那个如今埋在冰冷泥土间的死人,生前是非曲直,死后尽归骸骨。我再道了别,一路冲出大门。外面,草地上,阳光下,新浣的床单闪闪发亮。
我又跑回山上,跑进林子里,用手里的棍子从一株不起眼的大榆树上打下一只松鼠—— 红色的,拖着不大不小的尾巴。我坐在树枝上,要是能给妈妈猎回一头野猪就好了,我还从没打到过野猪——一头野猪,想想也诱人啊。待我想再往丛林深处去的时候,夜幕已经拉开,于是我就这么坐着,一直坐到影子斜长才起身回家,顺着山谷和溪边的滩涂,穿过两个叔伯的农场,再穿过自家的农场,拖着不知道是打架还是打猎留下的擦伤和瘀青,向家门口走去。
不等我绕到房前,妈妈已经提着灯迎了出来,灯下的她看上去脸色愈显苍白。她抚过我酸涩的面颊,并不开口问我因由。我给她看松鼠的尾巴,她笑了,扭过脸,那张苍白的脸随即陷入黑暗。我把松鼠尾巴收进马裤口袋时,又想起了祖父和他的尿具。他老了,就这么老了,父亲有天也会老吧。老了的人,会慢慢腐烂吧,像一枚放陈了的鸡蛋。
亲爱的妈妈,还有我可爱的亲人们,如今你们都已一一弃我而去,长眠地下。然而曾经天真而美好的我,还有曾经烂漫而温暖的过往,你们是见过的。
1. 宾州娼妇
我姐姐,萨莉,那个他们嘴里的娼妇,被丢在贵格会的教众们面前,像一条被铁锹从泥土中掘出来暴露在光天下的蛆虫,一个人站在议事大厅的正中,其余人则一个个坐在她四周的条凳上。看来她已经准备好了她的告解辞,端着那张纸,平举到脸前,声音中没有一丝起伏,含混得像是嘴里还嚼着没咽下的土豆。萨莉平时说话可没这么无聊,如果她乐意,绝对够资格开一所专教人嚼舌的语言学校。小伙子们看见她,总是说,抬一抬你的高跟鞋啊,萨莉。他们轻叩手指,她就咯噔咯噔应声而来,然后,总是最晚一个在夜色里起身,离开篝火堆,或者谁家新搭的谷仓。
我看着她此时无措地踮着她那双昭著的高跟鞋,帽子歪在一边,露出遮耳的卷发,抬起眼皮,想看看谁也在看她。她的那个相好此刻就站在几步远的地方,扭身望着窗外。我试图从她的忏悔中听出些兴致,不过也只听得一二,什么“私交过甚”和“通奸”之类的,看来她对自己的过失供认不讳。任何人只消从旁看看她隆起的腹部,一切就都再明白不过了。何况现在,除了她自己,所有的人都在看。
这不是一次通常的例会。空气凝滞,仿佛刚刚划过一颗子弹。长老们召集了所有的教友会成员,条凳上挤满了人,有些甚至开车从乡下的农场远道赶来。
父亲难过得不停发汗,汗水蒸腾起一股属于他的味道,面包的味道。正当他想起身走掉,看见妈妈伸手轻轻拍了拍小内迪的头,于是他敛了敛下巴,又坐回她身边。我用脚在地上划着圈圈,想笑,妹妹贝茨捏着鼻子模仿狐狸,而长兄伊斯雷尔真的在笑。
“……这就是我的忏悔。”
终于念完了。一个靠门坐着的寡妇忽然猛捶自己的腰,抱怨都是穿堂风闹的。
“小丹尼,你也受风了吗?”贝茨咽了笑,学妈妈的样子问我。
我戳了她一下算是回敬。希尔的父亲接着萨莉以及她的相好说:
“是的,在今天以前,你们实在私交过甚。”
真是一个听上去就腰缠万贯的男性嗓音,掷地有声,像袋子里哐啷哐啷作响的钱币声。希尔的父亲总是像现在这样面色红润,这会儿,他的脸好像为接下来的措辞陷入了思索。我也陷入了我的思索。除了家里养的牛,到那会儿为止,我还没真的见过什么私相授受的过甚之举,但是畜生们在干那种事情的时候总是太过直截了当,毫无情致可言。是的,尽管我什么都不懂,但这不妨碍我对很多事感兴趣。我回过神来,听见希尔的父亲问萨莉,是否愿意在众位教友的见证下缔结神圣的婚约。萨莉说她愿意。旁边的那位闻言倒吸了口气,也说愿娶她为妻。礼成,万事大吉。萨莉瞄向我们,她大概在想,这下好了,皆大欢喜。我看见她眼睛里的光亮,我听见她指关节的脆响。今此以后,谁还能说三道四,就像变了个戏法,从婊子到为人妇。看来连上帝有时候也忍不住耍点小把戏,打个响指什么的。
“至于你的忏悔,”希尔的父亲转向旁边的年轻人,声音慈爱而和缓,“别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在他看来,我们大可以花上一整天时间坐在这儿,幸好萨莉的新婚丈夫婉拒了当众告解的提议。这个年轻人不是贵格派的教友,也是个“外人”,在我看来也许他尚未搞清楚自己的意愿,就糊里糊涂地成了布恩家的一员,当然现在说起来已然为时晚矣。他睨着眼,稀稀拉拉的胡子捻在一起,好像灯芯,我知道他不是眼斜,不过是想尽量忽视新婚妻子的肚子,尽管其他人都在看。
希尔的父亲只好穿过大厅,寄希望于父亲:
“我们终此一生探寻真理。我们因忏悔而重获新生。教友布恩,是该你告解的时候了。”
父亲站起身,正如当年祖父也曾为了他的女儿站在这里:
“我的女儿,确实,错不该与人私交过甚,为此,我感到万分惭愧。”
有那么一刻,父亲抻了抻脖子,做出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只敢低头看着希尔父亲的腿,颤抖的手指仿佛想亲自捻一捻对方昂贵的衣料。这个十足的穷织工,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何沦落至此,倒还分得清眼前的上等套装用料。不得不承认,单看这身行头,就知道眼前这位教友会的元老一生顺顺当当。
“以,以后,会,会,会更留心的。”
也许就是那身灰黑色衣料散发的深邃色泽最终击溃了他,父亲一时口吃。闲谈的时候,偶尔他也会这样,但这次不合时宜的口吃令他的脸色多少有点难堪,他伸手摸摸谢了顶的脑壳,不知道是想遁土而逃,还是想发火。曾几何时,渡轮轰隆隆驶离英格兰灰黑色的海岸时,年轻的父亲把下巴架在船首的斜桅杆上,憧憬着离开熟悉的人和事,离开熟悉的教区,跟自己的父亲、姐妹、兄弟一起,开往陌生之地,寻找安身之所。那个当初陌生的这里,本该一切美好而安然。
伊斯雷尔忽然放声大笑。妈妈两眼放空,失去焦距的瞳仁像两片易碎的玻璃。她紧了紧怀里的小斯夸尔,这令小家伙皱起了眉头。父亲重重坐回凳子上,攥着拳头,大口呼吸。妈妈,这位一生忠贞追随上帝的信徒,望着萨莉,后者正努力堆出温良恭顺的表情,尽管其实她已经被调教成一个邋遢的婆娘。贝茨把脸埋进胳膊,假装在咳嗽,我知道她是在偷笑。
我也学那个人睨着眼,仰起脸,这样一来,其他人的脸就在视线中消失不见了。真是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的聚会,教友们排成排,分坐两边,中间专为萨莉和她的相好留出空,供人观赏。还有这冗长的沉默,只听得到彼此的鼻息。贝茨小声地哼着调调,屁在肠子里钻来啊 ——钻去,又捅了我一下,我故意视而不见。我想我大概是整间屋子里最先注意到那只鸟的吧。一只深色的紫崖燕,落在最高的窗子上。它直愣愣地飞进来,只在窗台上停了片刻,跟着双翼一剪,上了房梁。我观察它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展翅,每一根羽毛,还有它那双黑亮的小眼睛。
很多人也看到了,举着手指指点点。燕子在这番静默的观赏中慌不择路,徒劳地拍打着天花板,像埋在胸中的不安分的心脏。
“它会把屎屙在萨莉身上的。”伊斯雷尔说。
我觉得他说得对,我总是觉得他说得对,说什么都对。伊斯雷尔才十六岁,两颊已经蓄须,总让我忍不住多看两眼,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长出那样的胡子。伊斯雷尔抱着手臂,挑着眉蔑然一笑——这还是他今天第一次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流露出一丝兴致。我合上嘴,仰起头。轮到贝茨放肆大笑:
“会的,会的!或者尿上一泡!”
父亲瞪了她一眼,贝茨把帽带咬在嘴里在牙齿间磨来磨去。我依旧注视着那只燕子,体会到伊斯雷尔无聊的趣味,他也在注视着它,其实他可以轻易地把它打下来。
燕子绕着房梁前前后后,一匝一匝,像是要衔着一根线把梁架缝缀起来,最后气喘吁吁地落在其中一扇窗框上,张开尖尖的喙,却并没发出什么声响。如果我今天随身带着打鸟棍,肯定能轻易把它打下来。或者给我支箭,一根木棍什么的也好。我可以就坐在这发力,保准一击命中,也好让伊斯雷尔瞧瞧我的能耐。
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咳了一声。这只紫崖燕笔直地跌落下来,又翻身冲上房顶,奋不顾身地一次次用头撞向天花板,惊出一声一声闷雷。我希望它能看到我,看到我眼里对它的惋惜。如果父亲肯给我一把枪,我一定能一枪打穿它的小脑瓜,一举结束它这无休止的自我折磨。我用棍子打死过太多鸟了。我知道它们总是睁着眼死去,然后眼神慢慢涣散失焦,再然后羽毛慢慢褪去光泽。我曾就那样握着它们的尸体,直到它们变凉,凉透,只不过整个过程需要的时间比你认为的更久。
燕子还在无谓挣扎。希尔的父亲明白,在这种时候,谁也不会再在意他在讲什么。于是,他合十双手,宣布散会。接下来是寒暄,握手,道别,轻松和友好的神情重新回到每个人脸上。婚礼结束了。面对教友们的点头致意,妈妈满眼宽慰,而父亲依旧一脸冷峻。正当我想趁机跟父亲再提提枪的事,一根恼人的手指插进了我的耳孔。
又是威廉·希尔,我把脚伸到后面猛踩他的脚趾。他抽出手,一边兴奋地大嚷:
“你姐姐要生小宝宝啦!”
“是的,看她那大屁股,简直像只母鸡。是吧,希尔,我知道你最喜欢看母鸡屁股了。”
希尔咧开大嘴,我赶紧拉着贝茨追上家人。才一出门,伊斯雷尔就扭头冲着父亲吼道:“你怎么能袖着手看她就那么走了?你怎么能不说点什么、做点什么?什么所谓的婚礼,简直就是放屁!没人有权评判我们家的对错!”
嘘,妈妈像对待小斯夸尔一样叫他噤声。父亲只是摇头,不发一言。伊斯雷尔扬长而去。我知道他一定回去取他的猎枪了,他一定又会带着枪抛开这一切跑进山里,也许要到明天早上他才会回来。
我正想追上去,被妈妈一把拽住:“看着小内迪。别让他闯到马路上去。”
低头,内迪笑着望着我。我的乖乖小弟,你总是这样一副笑颜。我把他抱起来,他和祖父一样,臭臭的。
“快看!”
我举着内迪,彼时,萨莉正费劲地把她的大屁股挪上一辆货车,那辆车将载着她,前往她的新家。在那儿,她将生下她的宝宝,并自此全然成为一个“外人”,和她的斜眼丈夫一同过活。
“走了,走了。”内迪叫着。
“是的,都走了。”
我把他放下来,他满眼困惑,但忍着没哭。妈妈和父亲呆呆地站在那,望着货车离开的方向,茫然不知所措,仿佛除此之外再没别的可做。他们站着,望着,像是在等一个答案。我转过身,那只紫崖燕终于冲出了议事大楼的大门,门槛上一摊紫色的鸟粪清晰可见,这大概是我们今天唯一能得到的答案了。
“贝茨,贝茨?”
婚礼结束后的晚上,我难以成眠,尽管屋子很静,妈妈和父亲安静地睡在阁楼,我、内迪和贝茨并排睡在楼下。我试图把贝茨唤醒,只怪她睡得太沉,翻了个身又不动了。上次我俩去夜钓,她还把鲱鱼肠子甩到了我脸上,想到这,我扯了条被单蒙在她脸上,一个人走了,由她像具尸体一样挺在那儿。
我趴在地板上匍匐前行,爬过萨莉的空床,一想到这张床就永远这么空下去了,感到有点钻心。我继续向前爬,伊斯雷尔的床上也没人,真令人沮丧,他果然还没回来,不过转念一想,也许我可以出去找他。
终于爬出了房子,我提着桶翻过菜园的篱笆,准备先弄几条虫子。月朗星稀。我快步穿过奥瓦汀桥,跑向河边,渐渐能听见湍急的流——清冽的声音让人分外愉悦。
我刚要下水,忽然一阵异响。
“是你吗,伊斯雷尔?”
一条黑影从桦木林里飞出来,抓住我的胳膊。愉悦之情瞬间一扫而空。
“你在钓鱼吗,小丹?我就猜你会溜出来。带我一个。”
当然不是伊斯雷尔。威廉·希尔嘴里的锈涩味道并不怡人,虽然夜色浓密,但不用看我也知道,他一定又咧着嘴在笑,活像是我刚刚的愉悦被他一股脑吞进了肚子。希尔只比我大一岁,以前同在詹姆斯叔叔的学校里时,他坐我前排,经常回过头来喷我一脸口臭。有的时候,他也会小声把答案告诉我。但我从不听他的,我情愿蒙着眼睛坐在角落里,一个人待在那把瘸腿的破椅子上,也不愿意听他的。詹姆斯叔叔总是为在课堂上罚我感到抱歉,于是回到家偷偷塞给我糖吃。
不过希尔不一样,他有零花钱,时不时就有一两枚硬币从他的口袋里落出来,掉在地上,他则显得不很计较。有的时候,他付钱给我,向我讨一两只死松鼠,或者让我带着他溯溪而上,觅个钓鱼的好去处。所以我也就有幸经常会在篱笆后面看见他那张开心的脸,或者猛一抬头,发现他就扒在门边。
“你不知道我要去哪。”我说。
“去你爷爷那?没关系的,我不介意。我也想看看那幢房子里到底什么样。他真的在每个房间里都养了个小老婆吗?”
于是我只有跑,他只有追。他以为他知道我要去哪,怎么可能呢,我故意在田野里绕圈,不想去爷爷那儿,也想不出还能去哪儿。我只想跟希尔兜兜圈子,直到他累了放过我。我跑进牧草深深的田野,穿过玉米地和亚麻园,乌云遮月,我只能凭着记忆在田野里奔跑,因为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在没膝的草地里跑了一阵子,手背触到了篱笆栅粗糙而稀疏的栏杆。这应该是到了布莱克家了。听说他们全家都染上了暑热症,这成了妈妈少有的可与人闲谈的话题。我不关心什么疾病,只是对威廉·希尔深恶痛绝。
我沿着篱笆墙走进布莱克家的院子。一匹从厩棚中溜出来的马立在门前的台阶上,我摸了摸它软腻的鼻子,从它身旁走过,它在我的掌心留下一团潮湿的热气。我原本是打算在藏萝卜的菜窖里躲一躲就好了,可听见希尔笨重的脚步已经追进了院子,只好一不做二不休上了台阶。布莱克家的大门上拦着根破绳子,以示警戒,我正在门口犹豫,听得希尔对着马在问,你在哪儿啊,于是干脆猫腰钻了进去。
我发现自己僵立在浑厚的黑暗中。我可不害怕,我一向什么都不害怕——一边给自己壮胆,一边让自己尽量保持呼吸。地板的一端咯吱作响。我向后面的墙边跑去,感到希尔的呼吸已经到了脖子后面,停了脚。
“接着跑啊。”他说。
“你就不怕也染上暑热?”
“不怕吗?”
布莱克一家都是女眷。最小的女儿躺在一扇打开的窗户底下,烧得像只烤熟的苹果派。她把自己的牙齿咬得咯吱作响,眼睛上蒙着退烧用的白布。我俯下身看她。希尔揿着我的肩膀,把她的一缕头发和我的搅在一起,用跟他父亲如出一辙的慈爱的主持腔宣布,我将和莫莉·布莱克结为夫妇,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现在,亲吻她,给她一个拥抱。”
伊斯雷尔曾经告诫过我,病人的头发会触及霉运,不知道真的假的。那绺头发的确扎人,但我可不想在希尔面前认怂。我于是弯下腰,把嘴唇印上莫莉滚烫的脸颊,感觉到她的牙齿在打战,大笑着滚到一边。希尔又接着说了句似乎很合情合理的话:
“现在,跟她做爱,让我看看。”
“不!”
“来吧,小丹。我这是在帮你。你总不能等着去嫖吧,人是需要老婆的。”
“不!”
“小丹!”
我一把把他推开。
“绝不!”
莫莉的牙抖得更凶了,我伸手捂住她的嘴,希尔腆着那张大宽脸凑上来:
“ 我倒想看看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把希尔锈涩的口臭气甩在身后,径直跑向门外。这回,他并没有追过来。我就这样在星光下一路跑,一路跑,不想停下,不想再停下。
我感到胸腔在着火,但并没有慢下脚步。月亮又出来了。在顺着另一条小道回到河边的时候,途经几间属于印第安人的棚屋。他们皈依了贵格派,也参加了白天的聚会。木屋前的草地上拴着两只灰白色的小马驹,隐约还能闻见炉火的味道。大概是听见了我的动静,我听到背后一扇门开了,但我没回头,脚下也丝毫没慢半分。我绕开田野,向着河的方向一路跑,一路跑,感觉自己从没跑出过这么远,也许没谁跑出过这么远吧。
直到又听见了湍急的流水,我才蹲下身子,停在岸边大口喘歇。忽而一个低回急促的声音。应该不是鸟吧?
我沿河而上,听见上游水花飞溅,有人在踏水。一个颀长的身影,深色的头发隐匿在夜色和斑驳的树影之间,但白皙的大腿暴露了他。他没穿马裤,敞着怀,拾起地上的一根树杈,把其中一端撅下来,转过脸。
是伊斯雷尔。我想他肯定早就看到我了,不过这时,他紧盯着身后的河滩,一串轻巧的脚步声跃进了树丛。
“是鹿吗?”我压低声音,“你要动手吗?”
我想只要他想,一只鹿还不是手到擒来。有好几次,我大清早爬起来偷偷跟着他,看着他漫不经心地环顾破晓时分的苍穹,临要扣动扳机前的一瞬间,忽然目光如炬。他总能猎到些松鸡、乌鸦什么的,有的时候则是鹿。并不是每一次他都能察觉我的存在,但有的时候,他会把我揪出来,教我指认草地上的蹄印、粪便,或是勾在树杈上的鹿鬃。晚上回到家里,他准许我帮他配火药。我还帮他刮过鹿皮,四次;用他的猎枪打松鼠,两次。他给了我一条空枪管,现在就藏在我的床板下面。我有次梦到过这条枪管,尽管不是什么好梦。我梦想着成为伊斯雷尔那样的好猎手。父亲很喜欢他,准许他一个人独自外出打猎。伊斯雷尔不喜欢锻铁,也不喜欢做纺织的活儿,总是自由散漫,我行我素,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他教我如何屏息静气悄声行走。伊斯雷尔总能找到别人看不到的鹿蹄印,而我能找到伊斯雷尔看不到的鹿蹄印。但我依旧不知道他晚上都干什么去了。
河水从他的两腿间滑过。“那不是鹿,小丹。这么晚,你去哪儿了?”他声音和缓。
我不想提起希尔或者莫莉·布莱克,只好敷衍说:
“我打猎去了。那么,那是什么,那个声音?”
他仰起头,手里举着一只鱼,用刚撅断的树枝叉着。鱼鳞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他的声音平静一如夜色:
“真的吗?这里可只有你和鱼,两手空空你拿什么打的猎啊?”
我噎在那说不出话。他了解每一种动物的习性,它们藏在哪儿,怎么找到它们。凡此于他而言都轻而易举。
“你呢,你去哪了?你才抓到一条鱼,肯定也刚到这不久。你是不是白天已经进了山打过猎回来了?快给我讲讲。”轮到我反问他。
他转过身去,月色将他的面庞镀上一层浅金。我追问:
“怎么你下午才出去,半夜又跑出来了?你总是不好好睡觉,还总是一个人跑出来。怎么样,算上我一个,我们去猎一条鹿,我能帮你忙!”
伊斯雷尔没有理我。他把叉在木棍上的鲱鱼取下来,继续捕鱼,视我不见。
“喂,伊斯雷尔!”
“回家吧,小丹。”
他赤着脚,逆着流水向上游走去。我急得大喊:
“我恨这个鬼地方,恨埃克赛特!打猎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人也行,用不着靠你!”
- 后浪图书旗舰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后浪出版公司官方微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