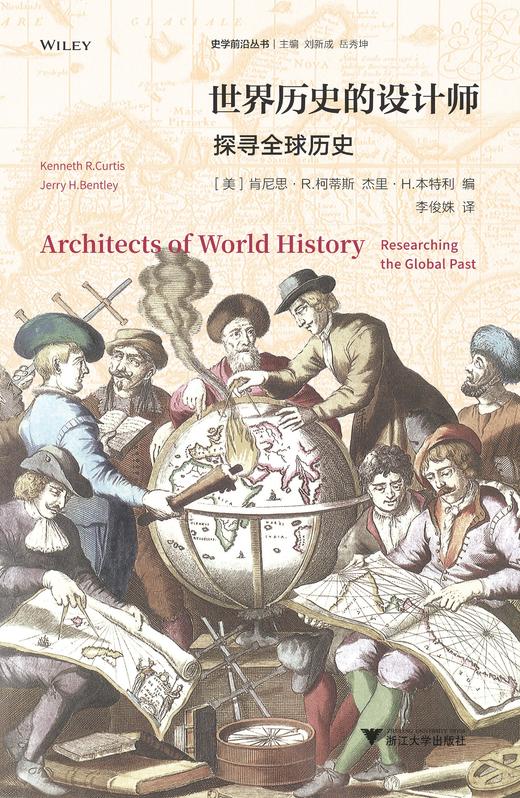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史学前沿丛书/肯尼思·柯蒂斯/杰里·H.本特利/总主编:刘新成/浙江大学出版社
| 运费: | 免运费 |
| 库存: | 780 件 |
商品详情
【书名】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
【编者】【美】肯尼斯•R. 柯蒂斯、杰里•H. 本特利
【作者】【美】肯尼斯•R. 柯蒂斯、杰里•H. 本特利、彭慕兰 等
【译者】李俊姝
【出版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丛书】史学前沿丛书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ISBN】9787308178105
【定价】52.00元
【上架建议】历史
【装帧】平装
【页数】261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富有启发性的作品集,同时呈现了世界史领域的一流声音和一些重要的主题研究方法。这部作品集清晰地描绘出方法论和史学轨迹,赋予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世界史以连贯性。不同学者的文稿使得宽泛的探究模式人性化,并提供了新鲜的、独创性的研究方法。
【相关推荐】
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九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因为不满意国别史的苛刻限制,寻找他们到达彼此以及更广泛的志趣相投的职业史家网络的路,这经常是偶然发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世界历史建设为一个肥沃的研究和教学领域。
——罗斯•邓恩,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该书是一部富有启发性的作品集,呈现了世界历史领域之内的一流声音和一些重要的研究方法。吸引并引导学生朝着如何研究世界历史的更大感觉的方向发展,这个目标特别有吸引力。
——彼得•斯特恩斯,乔治梅森大学
这部作品集清晰地描绘出方法论和史学轨迹,赋予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世界历史以连贯性。来自许多不同学者的文稿使得宽泛的探究模式人性化,并提供了新鲜的、独创性的研究方法。如果想要把握这个生机勃勃的领域的历史和范围,《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是各个层次的学者和教师的必备读物。
——劳拉•J.米切尔,加利福尼亚大学
每一位作者都是名副其实的设计师和世界历史领域内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他们共同给当前的教学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内容丰富的介绍,同时展示了把他们带到世界历史前沿的个人独有的、通常是不同寻常的学术历程。
——克雷格•本杰明,世界历史学会主席
【编者简介】
肯尼思•R. 柯蒂斯(Kenneth R.Curtis),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历史学教授,他承担现代非洲和当代世界历史的教学工作。他最近的出版作品是与瓦莱丽•汉森合著的《世界历史上的航行》第二版(2013)。他当前研究的项目涉及到通过旅行者的叙述重新评价20 世纪历史。
杰里•H. 本特利(Jerry H.Bentley),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历史学教授,世界历史学会的创建成员之一,担任《世界历史杂志》编辑长达22年。除了早期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著作和文章,他在世界历史理论、分期、和前现代跨文化相遇的著述颇多,主编作品多种,合著广受欢迎的教科书《传统与相遇》(中文版译名为《新全球史》)。
【作者简介】
杰里•H. 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是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历史学教授,世界历史学会的创建成员之一,担任《世界历史杂志》主编长达22年。除了早期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著作和文章,他就世界历史理论、分期和前现代跨文化相遇的著述颇多,并编辑了大量书籍,且合著了广受欢迎的教科书《传统与相遇》(Traditions and Encanters, 中文版译名为《新全球史》)。
劳伦•本顿(Lauren Benton)是纽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和法学兼职教授。她关于比较法律史的出版作品包括《寻找主权》(A Search for Sovereignty, 2010) 和《法律和殖民文化》(Law and Colonial Culture, 2002)。本顿的博士学位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取得,研究方向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她的学士学位是在哈佛大学攻读。
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是接受俄国和苏联史训练的历史学家。他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供职于位于悉尼的麦考瑞大学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1989 年他在麦考瑞大学开始讲授大历史的课程。2004年,他出版了《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2010年,他与比尔•盖茨一起创立了“大历史项目”,这个项目要建设免费的在线高中大历史课程,计划于2013年底发布。大卫•克里斯蒂安是国际大历史学会的创始人兼主席。
肯尼思•R. 柯蒂斯(Kenneth R. Curtis)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历史学教授,他承担现代非洲和当代世界历史的教学工作。他最近的出版作品是与瓦莱丽•汉森(Valerie Hansen)合著的《世界历史上的航行》(Voyages in World History, 2013第二版)。他当前研究的项目涉及通过旅行者的叙述重新评价20世纪历史。
凯伦•路易丝•乔莉(Karen Louise Jolly)是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历史学教授,是研究中世纪欧洲的文化史学家。她著有《撒克逊英格兰晚期的流行宗教》(Popular Religion in Late Saxon England),内容涉及中世纪的巫术概念,世界语境内的基督教历史(《传统和多样性》)。她最近的著作《10世纪晚期的圣卡斯伯特社群》(The Community of St. Cuthbert in the Late Tenth)透过一件手抄本挖掘了一个诺森伯兰郡宗教社群。
J. R. 麦克尼尔(J. R. McNeill)是乔治城大学的校级教授,也供职于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他的著作包括《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获得了三种图书奖,被译为九种语言;《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与威廉•麦克尼尔合著,被译为七种语言;《蚊子帝国:大加勒比地区的生态与战争,1620—1914》(Mosquito Empires: Ecology and War in the Greater Carribbean,1620–1914),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的贝弗里奇奖。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是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之前曾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教。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不过他也对比较历史和世界历史非常感兴趣。他的大部分研究属于社会史、经济史和环境史,不过他也关注国家形成、帝国主义、宗教、性别和其他话题。出版作品包括《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2000),该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并分享了世界历史学会的著作奖。他是《全球历史杂志》的创始编辑之一。他当前的研究项目包括从17 世纪到现在的中国政治经济史和一本名为《为什么中国如此大?》(Why Is China So Big ?)的专著,尝试从各种角度解释当代中国的庞大地区和人口如何且为什么最终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他于2013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
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是德国不来梅雅各布斯大学现代亚洲历史系的教授。在此之前,他曾经在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担任教职。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和西方的全球史/ 世界史研究方法、17世纪中西文化关系以及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全球趋向。
克里•沃德(Kerry Ward)是莱斯大学世界历史方向的助理教授。她著有《帝国网络: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强制移民》(Networksof Empire: Forced Migration in the Duth East India Company,Cambridge, 2009)和关于南非、东南亚和印度洋史的若干文章和章节。她于2009—2013期间担任世界历史学会的秘书。在2013—2014年她是耶鲁大学吉尔德莱尔曼奴隶制、抵制和废除研究中心(Gilder Lehrm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lavery, Resistance, and Abolition)的人口贩卖和现代奴隶制协会的会员。
梅里• 威斯纳–汉克斯(Merry E. Wiesner-Hanks) 是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历史系的特聘教授和系主任。她是《16世纪杂志》(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的资深编辑,《全球历史杂志》的编辑之一,并且写作或编辑了20本著作和很多文章,以英语、德国、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中文、土耳其语和韩语的形式出现在读者眼前。她的研究得到了来自富布莱特和古根海姆基金会等的资助。她也写了很多用于大学课堂的资料集和教科书、一本给青年人看的书和一本给普通读者看的书:《了不起的多毛女孩:冈萨雷斯姐妹和她们的世界》(The Marvelous Hairy Girls : The Gonzales Sisters and Their Worlds, Yale, 2009),讲述了生活在16世纪晚期欧洲的极其多毛的一家人的故事。目前她担任即将出版的九卷本《剑桥世界史》的主编。
【目录】
作者简介 1
1 世界历史的设计师(肯尼思•R. 柯蒂斯) 1
2 通往世界环境史的道路(J. R. 麦克尼尔) 33
3 性别交汇(梅里•威斯纳–汉克斯) 62
4 没有大分流?通过东亚研究抵达世界历史(彭慕兰) 88
5 文化与宗教交流(夏德明) 118
6 法律和世界历史(劳伦•本顿) 143
7 世界上的非洲:从国别史到全球联系(克里•沃德) 170
8 大历史(大卫•克里斯蒂安) 204
9 探索全球文化史(杰里•H. 本特利、凯伦•路易丝•乔莉) 231
索引 255
【书摘】
1 世界历史的设计师
肯尼思•R. 柯蒂斯
世界历史是什么?像很多教授一样,比起在理论上,我开始更多地从实践角度思考这个问题。那是在威斯康星的一个阴冷的早晨,当时我正在为上午八点半的“现代世界历史”讲座做准备。仍然在完善我的关于殖民地坦桑尼亚咖啡产销的政治驱动力的博士论文,我如何才能说服一屋子年轻人,让他们相信我能帮助他们了解16 世纪奥斯曼帝国?除了阅读的教科书与学生的不同,我确实有一些工具来帮助自己。一位有经验的同事曾经非常热心地给了我他的课堂讲义(使用的是1989 年最新的电子存储技术:一套“软盘”),里面存有优秀的学术资料和一手资料引文。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东非学家,我牢固地掌握了关于伊斯兰教的基础信仰和实践行为,如果没有这些知识背景,我的学生不可能理解奥斯曼历史。最后,我阅读过大量的比较历史资料,所以我了解如何把历史节点连接起来以揭示更大的图景。但是,接着我心里闪过一丝惊慌:“苏莱曼(Süleyman)”的标准土耳其语发音是什么?求助于互联网是几年后的事情;当时我没有途径来求证。我只能下定决心尽我所能从经验中学习。
我觉得我的很多世界历史同事能够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一点自己的影子(如Getz, 2012)。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日子里(至今情况没有太大变化),我们关注研究、关注梳理所有潜在的复杂线索,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些可能看似是平直的故事(比如非洲人种植和售卖咖啡)。我们很少花费时间思考教学,教学需要的技巧几乎完全相反:能够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为非专业人士呈现复杂性。所隐含的预设是最终就职于一家大型研究机构会容许我们关注自己的专业,把一些粗线条的入门课程留给别人。(更不用说实际上现有工作机会多在教学居于首要地位的地方:文科院校,很少有研究资助的州立大学、社区学院。)虽然从未接受过如何教学的训练,我们开始了教学工作。
当我的本科母校——劳伦斯大学——提供给我一份短期教学合约的时候,真是天赐良机,不仅帮助我偿还了在完成论文时所欠的账单,而且在后来的终身教职职位申请过程中给了我可以援引的教学经验。在劳伦斯大学,我得以有机会继续研究非洲历史;事实上,我自愿讲授了一部分世界历史,因为我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这会给我的简历增色。的确,如果第二年我不能说服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我“能够讲授世界历史”,我怀疑自己是否会被他们考虑。
一旦得到了终身教职,我本可能会希望避免更多的世界历史教学任务。但是在20 世纪90 年代早期,全球范围内有重大关系的历史似乎太重要了,无法视而不见。柏林墙的倒塌、纳尔逊• 曼德拉出狱、冷战终结、“全球化”的修辞和现实,这些都伴随着我从威斯康星过渡到加利福尼亚。那时,我开始更加尽责地考察世界历史,逐渐地(就像本书中其他学者一样)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独立且有活力的分支(关于世界历史的制度发展,参见Pomeranz and Segal, 2012 ;关于当代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历史,参见Bright and Geyer, 2012)。
随着我开始更加深入地探究世界历史,我逐渐区分出该领域的学者们所具有的两种“思维习惯”特点(援引原世界历史预修课程[APWH] 的描述):“跨越时空看待全球各种模式和进程,同时把地区发展与全球发展联系起来”,和“在社会内部和各社会之间进行比较,包括比较各社会对全球进程产生的反应”。就像很多其他世界历史学家,我对帮助连接起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书写形式感兴趣,在甄别跨越民族的或者全球的模式并进行适当比较的过程中会在心智上得到满足。
例如,随着我在现代世界历史考察方面的经验增多,我开始把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看作更宽泛模式的一部分:基于陆地的旧式社会和帝国(也包括中国清王朝、日本德川幕府、俄罗斯帝国)的领袖们面临着努力适应工业时代新的经济和军事现状。在所有地方,保守派和改革派互相斗争以扩大影响力,并使世界发生了改变。我发现,挖掘这些联系和可比之处既有挑战性也有启发性。
通过实践逐渐靠近了世界历史,理论上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在关于什么构成了“世界历史”这个问题上,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有时是分歧的意见。有些分歧反映出了国家多样性,如夏德明(2011)所示:例如,比起北美的同行,德国和中国的历史学家带来了对“世界历史”的不同概念性理解。尽管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基于美国的历史学家主导着定义性对话。
作为一个起始点,帕特里克• 曼宁(Patrick Manning, 2003)提供了一个适用范围广的世界历史定义,其特点是关注“人类社群内部互相联系的故事”,这些故事“描绘人类历史上如何跨越边界和链接体制”。杰里• 本特利给出了更加精确的陈述(2002),他提到:
明确地跨越各社会的边界线比较各种经历, 或者考察不同社会人们之间的互动,或者分析超越个体社会的大范围历史模式和进程的历史学。该类型的世界历史所处理的历史进程不受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边界线的限制,但在跨区域、大陆、半球和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影响(第393 页)。
本特利继续列举世界历史所特有的历史进程,如“气候变化、生物扩散、感染和接触传染病的传播、大规模迁移、技术的传输、帝国扩张活动、跨文化贸易、想法和理念的传播、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展”。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在这张覆盖范围如此广的列表上发现不了一些切题的事件,这几乎无法想象,但是,关键在于这些话题看起来要求跨区域或者全球范围的考察。
1992 年,在费城参加世界历史学会(WHA)的一场会议时,我有机会与志趣相投的历史学家继续这样的对话。现在我发现,我对全球和比较历史的热情在来自全美和一些国外的历史教育者同行身上也存在着。我马上意识到世界历史学会的文化包含了来自各类机构的历史教育者,其中大量中学教师的参与是一大特色。
此外,世界历史学会的成员共同分享着使命感。20 世纪90 年代早期,世界历史还在为得到职业史学的认可而奋争。特别是在一些非常精英的研究型大学,世界历史可能仍然被看作只适合高中学生或者大一新生的素材,肯定不属于严肃学者的主题(Weinstein,2012)。甚至在学院调查中,其角色仍然在遭受已有“西方文明”研究方法的传统主义支持者的质疑(Levine, 2000)。在政治领域,对人类历史进行全球思考被一些美国保守派指责为“识时务”,陷于贬低“西方”独特成就的文化相对主义(参见Nash, Crabtree,and Dunn, 200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历史学会里的很多高中和大学教师是理想主义者,相信全球知识、全球理解与全球和平、公正的可能性之间存在联系(Allardyce, 2000)。
这就是世界历史学会具有的意气相投的氛围,在这里进入世界历史领域的新人(比如我)可以很容易地与该领域的重要人物(如杰里• 本特利)交往并向他们学习。本特利博士,作为《世界历史杂志》的创办主编,曾在他的家乡夏威夷组织了1993 年的世界历史学会会议。他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后来被一些人称为“新世界历史”领域的一位开拓者,在教学、学术性出版物以及教科书编纂方面的创新者;而对于非常多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也是一位导师,包括本书中的每一位学者,他们都曾从本特利的建议中获益。2012 年夏天,本特利与癌症抗争失败去世,留下了一个巨大空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以收录杰里的最后一篇文章,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思考他作为现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领域的设计师之一所产生的影响。
世界历史的“设计师”
如何把建筑学的比喻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我们的标题所蕴含的意思是建设之前的远见。让我们想想建造一座砖结构的大厦。供应充足结实的砖块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原材料不足,修建不能完工;如果砖块的质量不好,大厦就会坍塌。在这个类比中,砖块相当于历史事实:除非事实证据在数量与质量上充足,否则无法做出有效的史学论证。然而成堆的坚实砖块无法自己聚集成大厦。与之类似,仅仅有关于过去的数据无法构成历史。
为了建造一座牢固的大厦,也需要泥瓦匠的技巧,这是把砖块连接成一面耐久的墙所必须的专业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也是“泥瓦匠”,他们接受的训练是把史学证据连接成因果关系的墙。正如本特利所指出的,“历史不是一箱子混杂的细节或者一盒子数据,历史学家简单地从中扯出信息片段,然后试图将之加工成某种故事。事实上,历史代表了历史学家为洞察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做出的创造性努力”(第217 页)。但是,一面墙仍然不是一座完工的大楼,最多算是因果关系解释构成了一次完整的史学论证。
这时,作为建筑师的历史学家所具备的远见最为关键。在选择砖块之前、在计划装配材料之前,建筑师眼里有大厦的最终模样。当然,为了保证她的蓝图愿景能够实现,她必须拥有扎实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基本功;但是如果没有她最初的远见,任何漂亮的、牢固的或者耐久的建筑都无法建造出来。
这样,历史学家联合起了所有这些技巧。他们像烧砖的工人,搜寻出历史的原材料,为了寻求证据经常在档案室和图书馆里默默而勤奋地工作。历史学家也像泥瓦匠,娴熟地把原材料证据连接成可理解叙事的实心墙。真正产生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也像建筑师,以原创性的方式展望史学构建的愿景,然后加工成创造性论证的叙事。在本书中,你会看到八位这样的历史学家。他们已经做出了显著贡献,被选出来以凸显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节点,他们都很快地指出相互协作是不可缺少的:“我想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建造的房子里,都不会发现这么多世界历史,”彭慕兰写道,“像在成排房子所形成的邻里社区里那样。”( 第103 页)
促使产生《世界历史的设计师》的对话是从特莎• 哈维开始的,他是威利– 布莱克韦尔(一家备受推崇的学术书籍出版商)的编辑。特莎当时的首要任务是编辑一本《威利– 布莱克韦尔世界历史研究指南》(Wiley Blackwell Compation to World History,Northrop, 2012,包括Pomeranz、Sachsenmaiaer 和Ward 的文章),对于试图沿着本书中出现的问题线索继续探寻下去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理想的补充读物。诺斯罗普的书与杰里• 本特利编辑的《牛津世界历史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2011)、罗斯• 邓恩的《新世界史:教师用书》(The New World History: A Teacher’s Companion, 2000)一起成为基础参考书目。就长期从事世界历史研究的单个作者而言,帕特里克• 曼宁的《全球史导航:历史学家创造世界历史》(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2003)仍然未被超越。
诺斯罗普、本特利、邓恩、曼宁的著作和《世界历史的设计师》之间的差异在于目标读者。那些书是由历史学家为历史学家书写的;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历史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初始方向(尽管我们也希望本书同样能为其他读者提供帮助,比如有助于没有太多训练或者背景的教师完成世界历史领域的任务)。
事实上,迄今为止本领域的可用资源多少有些失衡,要么目标读者是富有经验的学者,要么是为了指导基础概况课程。在历史连续统一体的一端,实在的研究已经开始,并产生了对类似《威利–布莱克韦尔世界历史手册》和《牛津世界历史手册》资源的需求。从另一方面看,概况课程现在成为美国大学课程的主要组成部分,推动产生了质量较好的资源支持世界历史的推介。我曾经为这类文献资料撰稿,比如合著教科书《世界历史上的航行》(Voyage in World History)2013 年版、文献选读《发现全球历史:审视证据》(Discovery of Global Past)2011 年版。但是,基础历史学里强烈的存在主义和新兴研究领域的力量,使得世界历史看似“缺失的中间地带”,本科生阶段的高年级课程和研究生阶段的初期课程在这里都能找到。《世界历史的设计师》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帮助弥合这个缺口,帮助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新生理解该领域的架构,在通往他们也许愿意去追求的研究领域的道路上为他们提供一些路标。
本书的理念已经酝酿了一些年头,然而我总是分心于行政事务。那时我做了一件事,任何理解世界历史概念的人都会这么做:我与杰里• 本特利进行了商讨。杰里怀旧地想起了与本书相似的《历史学家工作坊》(The Historian’s Workshop),他在本科时曾经阅读和欣赏过(Curtis, 1970), 当时我们在伦敦会面,都是由欧洲普世史和全球史网络(European Network in Global and Universal History)主办的会议参会人员,他同意担任《世界历史的设计师》一书的合作编辑。我们这些作者的“学术轨迹”将成为本书的主题,关注他们在朝着世界历史研究方向发展时所曾经走过的各种各样的道路。
通往世界历史的道路
我自己通往世界历史的道路源于最初接受的非洲学训练向外扩展,以及与教学相关的训练。2003 年春天,这些经历使我得到邀请去参加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资助的“佛罗里达大学的全球化历史: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坊”(Globallizing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A Workshop for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World History)。我演讲的题目是“自下而上的改变:世界历史和美国公共教育(Change from Below: World History and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尽管广受好评,我认为我对全球历史视角从美国中学向上流动到大学的解释没有产生太大影响。这是一个传统的、以研究为导向的历史系,参会的研究生中只有一位表达了对教学的关注。学术历史和更广泛的历史教育潮流之间明显缺乏联系,这没有让我觉得很惊讶,即使这种情况与我自己在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经历差异很大。
当我1990 年进入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历史系时,该系已经有着深厚的致力于K-12 教学的传统。这里是历史教育学会(Society for History Education)的所在地,其备受推崇的杂志《历史教师》(The History Teacher)上刊登由学校教师和专业学者写作的关于历史教学法的文章(Weber, 2012)。那种共同目标和缺乏等级制度的感觉吸引了我的民主教育本能(为当时学术界影响力渐长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所存在的种种困惑提供了矫正方法)。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我了解我的很多学生想着得到在初中或高中讲授历史的资格证书。长滩分校的很多学生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个进入大学的孩子;很多学生是移民的孩子。考虑到我妻子本身是七年级世界历史教师,而且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与长滩联合学区(以及长滩城市学院,作为长滩教育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培育了紧密联系,我面前的道路很清晰:积极致力于公共历史教育(Houck, 2004)。
与讲授非洲历史的教师们一起工作是清晰的起始点。如同克里• 沃德所说,非洲学家总是因为对非洲历史和地理根深蒂固地忽视而感到受挫。我发现很少有当地教师能够在非洲研究领域享有学术上优先知名的情况,随之而来的担忧是不正确的刻板印象会传给下一代人。幸运的是,20 世纪90 年代晚期关于历史/ 社会科学的新州立标准实施了,规定了干预范围(和资金):学生在世界历史的语境内学习关于非洲的历史,现在成为必修内容。但是,新的加利福尼亚标准有利也有弊。在新标准的形成过程中没有咨询过世界历史学家,新标准与丰富的对人类历史的联系和比较研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在后来的大学世界历史预修课程项目中通过对比得以发现。例如,在加利福尼亚新标准为十年级学生规定的现代世界历史部分,美国和西欧例外主义依然被编织进了课程结构。
加利福尼亚州的历史学科标准是20 世纪90 年代全国范围内更大趋势的一部分,当时提出了更加严谨的标准,以解决美国长期以来教育成果不令人满意的问题。在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的赞助下,来自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背景的一大群有名望的历史教育家协调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对话,讨论制定美国的国家历史学科标准以及世界历史。从教育和教学法的角度来看产生了极好的结果,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是灾难性的。被提议的标准受到了保守派攻击,说是对传统历史进行了“政治上正确”的歪曲,随后美国参议院以99:1 的投票将之废除(Symcox, 2002)。
但是,将眼花缭乱的国家政治搁在一边,一群想法超前的世界历史学家对大学理事会进行游说,希望在有着良好声誉且飞速发展的大学预修课程(AP)项目中纳入他们的科目。通过大学预修课程和考试,高中学生能够学习大学层次的课程,并有可能得到大学录取和学分。游说成功了,2002 年大学理事会公开了其最新大学世界历史预修课程设置,这个课程设置确实反映了“新世界历史”的“架构”,强调联系、比较和全球语境的主题(披露一下:我参与了课程的设计与实施,现在仍作为大学理事会历史学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担任监管的角色)。不仅从学术内容的角度来看,而且从数字上看,该项目的发展势头良好。在2013 年参加了大学预修课程考试的100 万高中学生里(大部分在美国,但是国际范围内的数目在增加),超过22 万人尝试了大学预修世界历史课程的测试,其中大约一半人的成绩足够取得大学学分。正是通过大学预修课程项目,由世界历史学会培育出来的中学和大学历史教育者联盟产生了最广泛的公共影响。
这些在学校里建立世界历史学习标准的尝试——在国家层面上产生了混合性的结果,在全国范围内的结果令人极度失望,而在大学预修课程项目中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指向了一个重要现象:美国教育中世界历史所占的空间实质上并非从上而下、从学术贵族向普通教室里的教师“向外延伸”的结果,而是得益于教室里的教师(在各个层次上)在他们尝试全球化历史教育的过程中寻求学术指导的“向上延伸”。大卫• 克里斯蒂安如此有前瞻性地热衷于调整他的“大历史”项目,以在学校能够广泛运用,其直接原因是——我希望他会同意——世界历史现在已建立了教育层级之间可以自由跨越开展工作的传统;另一个显著例子是“我们所有人的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 For Us All)在线项目的开发,这是由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罗斯• 邓恩(Ross Dunn)所构思的。
正如教学,地区研究也如此:我在长滩分校体制内的职位帮助我在我原有训练之外扩展了专业知识。事实上,大学教职员工如果没有资源良好的地区研究项目,通常会发现自己在原先领域之外开展教学,尤其是那些专业知识属于曾经被称为“第三世界”地区的教员。对于很多人来说,世界历史成为从菲利普• 柯廷(Philip Curtin, 2005)所谓的“边缘”过渡到历史学科“中心”的学术道路的主要方式。尽管倡导了几十年的地区研究给美国大部分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带来了意义非凡的更加多样化的地理知识,但是传统欧洲中心主义的残留效应仍然存在,有时美国和欧洲之外各社会的历史仍然在残留的“其他”或者“非西方”范畴之下被堆积在一起。世界历史,更加平衡地纳入了全球各区域,为课程设置所面临的僵局提供了一条出路。
尽管致力于非洲,我记得在到达麦迪逊之前看过历史系的课程,并曾经想象所有我在学习巴西历史、土耳其历史或者南亚历史时有可能会遇到的有趣课程。事实上,我的研究稳固地定位于非洲:我有价值相当于一个大陆的知识去学习(超越一生的学习!),需要快速开始学习斯瓦希里语,浪费时间是说不通的,我的教授们也不会允许我这么做。同时,非洲研究项目有跨学科的极好优势,促进了来自社会学、政治科学、人类学以及非洲语言和文学等领域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尽管我仍然对没能学习的其他很棒的历史课程感到遗憾,但是学生需要打好关于特定空间、时间和语言的基础(我的要求:东非、英国殖民时期和斯瓦希里语),这依然是研究生训练的标准,甚至在考虑向更广泛的比较研究扩展之前就得做到(Steets-Salter, 2012)。
美国的非洲研究和其他地区研究项目最初在冷战语境内表现为公共机构形式。1958 年国防教育法为不常讲授的语言(包括俄语和中文)提供培训资助,并给全国范围内的跨学科学习中心奠定了基础,每个中心关注不同的地区。随着新成立的主权国家浪潮般地敲开了联合国大门,新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即将开设,美国需要自己的地区研究专家。半个世纪后,这些地区研究项目的产物及其仍在持续的生产力对世界历史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三代地区研究学者的学术工作,大部分全球和比较历史工作的原材料就不会存在,也无法得到合适的语言训练。我是一名接受联邦资助的斯瓦希里语研究者,并且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对坦桑尼亚研究和德国国际教育工作的赞助,我能很好地证明政府部门对地区研究的支持非常重要。
但是,地区研究的学者们会被困在区域泡沫里。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时很少意识到“世界历史”是一种学术选择,这让人觉得讽刺,因为十年前麦迪逊的历史系已经靠着比较历史这个强项而闻名(Lockard, 2000)。这主要归功于菲利普• 柯廷博士,他从一名加勒比海的专家转向非洲研究,再转成世界历史学家,他在1956—1975 年间是麦迪逊的教员(在去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之前,影响了很多人的学术道路,包括劳伦• 本顿和J.R. 麦克尼尔)。在柯廷离开之后和我到来之前那段时期,比较历史和地区研究之间的鸿沟再一次扩大了。(不过,在由斯蒂文• 斯特恩[Dr. Steven Stern]博士成功主持的关于奴隶历史的比较研究研讨会上,参加者包括同等数量的非洲学家和拉丁美洲学家,我确实经历了该项目强有力的回应。)
所以像很多其他来自地区研究背景的学者一样,引领我认真对待世界历史的是教学责任而不是研究议程。我是“从下而上”靠近世界历史的——从课堂教学开始——“从边缘到中心”——从曾经被称为“第三世界”研究的背景开始,这种方向远非是独一无二的。我自己的故事,就像梅里• 威斯纳– 汉克斯在本书中的其他部分所说,“偶然性、机会和运气的作用像理性、计划和准备一样重要”( 第61 页)。
但是,尽管我自己和其他人是被运气推向了世界历史研究的轨道,我们似乎都分享着一些“思维习惯”,比如渴求像伞兵一样看待历史。这个类比由埃马纽埃尔• 勒华拉迪里提出,他对从一定高度考察宽广过去的历史学家进行了对比,这些历史学家带着“嗅块菌的鼻子(truffle snufflers)”深入钻研到历史学非常具体的方面(以当地或者国家为界)。本书中所有的历史学家——无论他们的兴趣最初是由课程改革和创新引发,还是求知欲带来了学术研究议程,或者甚至是国际旅行经历——都从高于平地的高度看待跨越区域或者全球历史的宽泛模式。
地理位置在决定通往世界历史的道路上也非常重要。杰里• 本特利来自檀香山,与我有着共同的经验,即每天向太平洋注视。正如凯伦• 乔利所解释,本特利调整学术关注点以适应他位于岛屿上的新家,占了这位年轻教授从文艺复兴历史到世界历史研究转变过程的一大部分。就我的情况来看,在一所拉美文化和亚洲文化交汇的美国大学工作(长滩分校有大约35% 的学生是拉美裔,25% 是亚裔),“我们”分享的历史故事有必要是“世界历史”。人口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正在并将会使得全球和跨区域历史对于世界上更多的人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意义。
基础文本
来到世界历史领域的新人现在可以得到对这个领域的很多指
导,包括本书。然而,就像《设计师》的其他编著者一样,我自己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开始熟悉该领域的基础文本。一天,我在图书馆的开放书架徘徊时,一本书的标题一下子吸引住了我:埃里克• 沃尔夫(Eric Wolf)的《欧洲和没有历史的人民》(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1982)。沃尔夫是一位人类学家,专门研究中美洲的人民,我本科时曾经阅读过他的关于阿兹特克人历史的经典作品《颤动地球的儿子们》(Sons of the Shaking Earth,1959)。沃尔夫解释道,现代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们已经被双重边缘化了:他们不仅被剥夺了政治主权和经济资源,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剥夺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作为一名非洲学的新手,我看到沃尔夫的全球观点如何进一步支持了沃尔特• 罗德尼(Walter Rodney)的观点,罗德尼的《欧洲如何阻碍了非洲的发展》(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1974)自从其1972 年首次出版就是学习现代非洲的学生的必读书目。我清楚地记得罗德尼这本书的最初封面形象:一双巨大的白人的手把非洲大陆撕成了两半。论点是清晰的,正如埃里克• 沃尔夫的书所指出的,历史和当代社会公正问题之间存在确凿无疑的联系。就像大部分历史学家,我随后逐渐看到这两部作品有着说教目的和缺少精确分析的局限性。但是,它们仍然在我的书架上,作为我通往非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道路指示标。
本书中的其他作者有着自己的“正好在合适的时间被合适的书”所影响的故事。我们所有人都在20 世纪70 年代到90 年代之间接受教育,发现我们共同分享着某种基准文本,某种历史分析的基准概念,这并不出乎意料。尽管提供一份全面的书目指南不在《世界历史的设计师》的范围之内,在这里列举一些曾经产生过宽泛影响的奠基性学术作品也许会有用。
“欠发达”、“依附理论”、“核心—边缘关系”这些术语是通往沃尔夫和罗德尼的书中所蕴含的全球历史分析类型的起始点。在一门“政治现代化”的本科课程上,保守的教员让我们阅读了一本激进的书:《拉丁美洲的依附和发展》(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Cardoso and Enzo, 1979)。拒绝了“现代化”理论家关于开放市场是通往广泛繁荣的最可靠道路的承诺,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事实上资本主义是拉丁美洲长期以来欠发达的源头:资本主义是拉丁美洲贫穷的历史原因,而不是其解决方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多索后来成为巴西总统,在变化的全球条件下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改革。)该书提出的道路指向了被高度肯定的安德烈• 冈德•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经济分析及其经典构想《欠发达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1966)。这些作品是更多文献(如Amin, 1977,2010)的一部分,把全球无产阶级的角色给了“第三世界”被压迫的人民:正是他们(不是像马克思所预示的西方的产业工人)的革命行为将改变世界。
研究欠发达理论的专家们主要从社会学和经济学得到了深刻见解。他们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是通过伊曼努尔•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terstein)的作品产生的(在本书中被本顿、沃德和彭慕兰援引)。沃勒斯坦所接受的训练是社会学的,不是历史学的,他在其里程碑式的《现代世界体系:16 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974)里对全球结构比起人类活动更感兴趣。在该书及随后的作品中,沃勒斯坦描述了早期现代西方建立的全球经济“核心”与其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边缘地区”的掠夺性关系之间的关联,“边缘地区”为“核心”提供市场和原材料,并且是“核心”过剩资本和过剩人口的输出地。通过这些历史进程(复杂但是没有被否定为“半边缘”案例),世界大多数人的贫困被创造出来,这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Chase-Dunn and Hall, 2012)。
作为一位历史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强调结构而不是人民,强调“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家”。他的“降落伞”视角有利于构建现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语境,不太利于勾勒植根于历史资料的实际研究安排。也许有人会说,世界体系分析都是关于建筑架构的视角,很少从砖和灰浆的角度看问题。
20 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的很多历史学家发现,在费尔南•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作品中可以得到更多合适的灵感;事实上,“布罗代尔式的(Braudelian)”这个词很久之前就进入了词汇表,所指代的作品特点是长时段历史(the longue durée),同时关注地理和历史、陆地场景和变化、持续的长期力量之间的相互交叉。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的领头人(其代表杂志也是如此命名),布罗代尔对战后的史学书写有着显著影响:J.R. 麦克尼尔和劳伦• 本顿在阅读他的三卷本《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Braudel, 1972) 时都受到了极大影响。他后来的作品《文明和资本主义》(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977)把看待欧洲和世界经济中的长期结构变化与研读文本、详细考察文化充分联系起来。对于对宽广历史框架中人类代理和人类行为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来说,布罗代尔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在这些影响的基础上,我发展了一种特殊兴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官僚体制国家的兴起,特别是与农业社会的关系。在我所发现的有启发性的透彻思考这些进程的比较历史作品中(克里• 沃德也这样援引)是巴林顿• 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966)。在考察民主、法西斯主义等政治形态产生的各种结果时,摩尔关注在一系列欧洲和亚洲社会内农民、拥有土地的精英和城市商人阶层之间的阶级关系。而摩尔的作品(就像沃勒斯坦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历史社会学”模式,成为一个研究模版,有利于强化乡村人口在塑造现代历史过程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这个基本事实。
另外一条前进道路是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新社会历史兴起,关注“从下至上”的历史和普通人的故事。在我自己的经历中,两部作品非常重要。第一部是E.P. 汤普森(E.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6)。当我阅读这部厚重且论证严密的关于英国农民转型为产业工人的描述时,感到很震惊,发现与我最初研究非洲殖民历史时有很多相似点;例如,18 世纪英格兰描述阶级差异的辞汇与20 世纪时东非描写种族差异的语言区别不大。有着类似影响的是尤金• 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的《奔腾吧,约旦河:奴隶创造的世界》(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1976),该书仔细考察美国南北战争前奴隶的生活、思想和经历,就像汤普森研究英国工人阶级一样。吉诺维斯使用了“文化霸权”的概念,这个概念最初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 葛兰西提出,以精确地描述对奴隶身份的抵制和认同这两种模式,另外一个引起历史学强烈共鸣的话题是从被殖民群体的视角出发,后来称为“ 底层”视角。
试图“从下而上”看待历史使得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和直接来源于此的出版作品(Curtis, 1992, 1994, 2003)严密地从地理角度关注这段有着细微线索的历史,探讨全球商品市场和国家干预如何开始影响坦桑尼亚西北部村民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方式。这就是“嗅块菌”的历史,使用的是保存较差的殖民记录;有一些记录几乎因时间、无知和潮湿毁坏了。此外,与“降落伞”视角相关的工作展现在,例如,詹姆斯• 斯科特(James Scott)关于农民道德经济及其与官僚政权之间关系的研究中(1977,1987)。无可否认的是,如果我当时知道现在所具备的知识,我会更加明确地梳理这些全球—地方的联系。这样的研究确实存在完美的题目,不过已经被唐纳德• 怀特(Donald Wright)为其关于一个冈比亚小社群的作品采用了:《世界和非洲的一个弹丸之地》(The World and a Very Small Place in Africa, 2010)。在怀特的书中,全球大变化的结构与植根于当地语言、文化、经历和感知的微小细节联系起来,这种方法能够被广泛地模仿(Gerritsen, 2012)。
在完成我的博士论文之后,加入了学术工作群体,发现了世界历史学会和《世界历史杂志》,然后我开始弥补已失去的时间,努力追赶着世界历史的“经典作品”,其中许多在本书内多篇文章中有提及。
实际上, 我的书架上已经有一本威廉• 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Rise of the West, 1963 ;曾经的书店定价是1.25 美元,足见其老旧的年代),并且在他到访长滩的时候通读了他的其他作品,比如《瘟疫和人》(Plagues and Peoples,1976)。在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变得越来越狭窄和专业化之后,麦克尼尔多年间呼吁回归世界历史大框架的声音显得孤立无援。尽管书名《西方的兴起》听起来有胜利主义的色彩,实际上该书通过把西欧历史稳固地置于麦克尼尔所谓的亚欧共生圈(oikumene, 相互联系的世界)语境内从而把西欧历史融入了背景。然后,他展示了中世纪晚期和早期现代欧洲的知识和技术发展如何由跨区域迁移产生。《瘟疫和人》也是一部极其有影响力的作品,研究明显是跨区域的主题疾病史,再一次提供了必要框架以合适地考察如黑死病等形式的流行病,这明显是涵盖亚非欧大陆的现象,而不仅仅是欧洲现象。
长滩分校的另一位演讲者,我对他的作品已经非常熟悉,是阿尔弗雷德• 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他于1992 年到访,当时正值纪念哥伦布首次美洲航行五百周年。他是研究世界历史上生物交换的一位先锋人物,我清楚地记得克罗斯比告诉我们:“是科尔特斯在天花的帮助下征服了阿兹特克人,还是天花在科尔特斯的帮助下征服了阿兹特克人,我不太确定哪一种说法更加真实!”当然,克罗斯比是在启发人思考,但他所强调的是人类事件经常受到环境和疾病因素的驱动。这在20 世纪70 年代是一个新鲜的角度,之后引发了很多创新性的研究,包括J. R. 麦克尼尔的《蚊子帝国》(Mosquito Empires, 2010)。正是阿尔弗雷德• 克罗斯比第一次创造了“哥伦布交换”(1972)这个术语,描述在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疾病、饲养的动物和食用作物的迁移,这个进程显示出,想要探求这些话题的历史学家必须让自己具备跨学科研究能力。他后来的作品《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 1986)解释了世界上的植物群如何被欧洲帝国主义者重造(有时带着人的主观意愿,通常是偶然情况),对每个大陆上的人们产生了大范围的环境影响(并可以解释在我加利福尼亚办公室之外生长的澳大利亚树种)。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持续出现的另外一个名字是菲利普• 柯廷。就像杰里• 本特利,柯廷在该领域的重要性既源自其对年轻学者的导师作用,也来自自己的作品,尽管就他的情况而言,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牢固联系。柯廷的研究方法是把一群年轻聪明的学者召集起来,设定一个讨论会话题,然后让他们去研究该话题的各个具体方面。通过这种归纳和合作的方法(与历史社会学强调推理正好相反),柯廷的作品深深地植根于砖和灰浆般的历史细节当中。最终成果是被广泛引用的作品,如《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1984)和《种植园复合体的兴衰:大西洋历史论文集》(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 1988)。
马歇尔• 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是在《设计师》的几篇文章中屡被提及的另外一个名字。作为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霍奇森的影响通过其逝世后出版的《伊斯兰世界的历程:一种世界文明的良知和历史》(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1974)传递出来。霍奇森保持了“文明”范式,这随后被很多世界历史学家超越了,但是在这个框架内他强调历史推动力和创新(Burke, 2000)。他强调伊斯兰社会(如他所命名的Islamicate societies)内以及这些社会和相邻文明之间理念在流动,这违反了早期的静态模式。与之相似,列夫顿• 斯塔夫里阿诺斯反驳“东方学家”对奥斯曼帝国和社会的构想,他的方法是强调奥斯曼帝国和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及其与北非、欧洲中部和伊朗不断发展的邻里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另请参阅Islamoğlu,2012)。霍奇森和斯塔夫里阿诺斯都预示了爱德华• 萨义德在他影响力巨大的《东方学》(Orientalism, 1979)中提出文学批判,批判西方人对“东方他者”进行静止和异域的比喻。萨义德的作品成为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和底层研究的一个支柱,这些领域与世界历史有重合之处,但是各自发端的修辞和研究出发点却大相径庭。(关于这些学术事业之间的交叉和分离,参见Bentley, 2005 和Sachsenmaier, 2011。)
《设计师》和世界历史学术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世界历史”,我告诉学生,我们当然不能把之想象为“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人中曾经发生的一切事情”。那将会是一项过于大胆和野心勃勃的事业。难道不是吗?大卫• 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2011)事实上确实把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作为其领域。对于胆小的人来说,对于那些认为星球历史太遥远的人来说,克里斯蒂安的《这个飞逝的世界》(This Fleeting World, 2007)仅限于不过25 万年的智人(Homo sapiens)历史。克里斯蒂安的大胆主动推动产生了大历史协会和许多文章、书籍(Spier, 2012), 尽管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他的扩张性研究方法仍然处于主流之外。
对于世界历史学家来说,更常见的是通过时间、空间、主题或三者结合起来限制他们的探究领域。如同亚当• 麦基翁(Adam Mckeown, 2012)所强调,世界历史学家必须特别注意地理和时间维度,选择最适合他们所框定问题的年代和空间参数:“每个维度,”正如他写道,“照亮不同的进程。”这样,菲利普• 柯廷在他关于“种植园复合体”的文章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地中海的起源和非洲、欧洲和美洲在三个多世纪期间的事件。费尔南• 布罗代尔把地中海海岸描述为长时段内一片连贯的历史研究地区,而威廉• 麦克尼尔关于瘟疫和流行病的历史把欧亚大陆作为出发点(正如其他历史学家把他的深刻见解延伸到了非洲、美洲和波利尼西亚)。一些学者如唐纳德• 怀特关注长时期内一个小的区域(2010),其他学者会选择从小的时段考察整个世界,如约翰• 威尔斯(John Wills)的《1688 年的全球史》(1688: A Global History, 2002)。
我们援引了杰里• 本特利的话题列表作为世界历史的最明显特征,但是他没有明确提出与我自己的研究联系最密切的主题区域:现代世界历史中的商品链研究(Levi, 2012)。一些经济和社会历史学家发现通过关注单一商品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他们能够梳理出有意义的历史学关联。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尽管是由一位人类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书写的,是西敏司(Sidney Mintz)的《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1986)。除了对劳伦• 本顿产生了影响,西敏司的书也对我构思《发现全球历史》的章节很有启发,使用一手材料讲述“甜蜜联结:糖和现代世界的起源”(2011)。另外一本我曾经撰稿的书以咖啡为出发点分析现代经济中生产商、商业中介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全球咖啡经济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1500—1989》(The Global Coffee Economy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1500 –1989,Clarence Smith and Topik, 2003)。其他世界历史研究关注了橡胶(Tully, 2011)、盐(Kurlansky, 2003)和棉花(Roelly, 2013)。与之类似,环境世界历史学家有时关注单一疾病,如疟疾(Webb, 2008 ;Pernick, 2012 的著作更具有概括性)。
在接下来的八篇文章,你会看到过去十年期间世界历史学术上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主题发展,作者们使用了多样化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当然,不是世界历史研究的每一个重要地区都被纳入进来:例如,重新思考帝国和帝国主义历史的学术(如Sinha, 2012)不是任何一篇文章的直接关注点。即使与研究趋势并驾齐驱的目标变得令人不可企及,读者仍然能够通过接触《世界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全球史杂志》(Th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和《世界历史连线》(World History Connected, 一种免费在线杂志,主要强调教学法)上出版的目录和评论文章获得一个良好的开端。新上线的《世界历史信息杂志》(Journal of World-Historical Information)和由匹兹堡大学的帕特里克• 曼宁世界历史中心归档的世界历史数据平台(World-Historical Dataverse)也很有吸引力。当然,世界历史学会成员之间的网络、全球和世界历史组织网络(Network of Global and World History Organizations)也形成一个区域性联合组织、通过订阅人文– 世界(H-World)研讨网可以每天获得关于世界历史的对话,这些都是无可替代的。
《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意欲让读者能够全面欣赏世界历史领域及其一些主要研究点;也许也可以促进他们深入思考自己的“学术轨迹”,以及联系和比较全球历史在其中的位置。强烈鼓励读者更加深入地研究其中一位学者的作品及其所代表的子领域,也许读者可以给这个混合体添加上他们自己的地理或者时段专长。也就是说:历史系的学生们借助于本书这个降落伞从一定的高度形成对世界历史学术的看法,最终必须向大地降落,并把自己放在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一旦你彻底想清楚大的语境、联系和比较,你的视角或许将不再保持不变。
尽管我们这些作者研究世界历史的方法有很大差异,J.R. 麦克尼尔和梅里• 威斯纳– 汉克斯有着一些共同点。他们俩所在的历史研究领域在40 年前几乎不存在——麦克尼尔的环境史、威斯纳–汉克斯的性别史。威斯纳– 汉克斯试图回答为什么性别史和世界历史之间相互作用了几十年才开始结出成果;另一方面,从环境史的角度看,跨越这些学科区分形成的聚合不太存在问题。从而麦克尼尔和威斯纳– 汉克斯提醒我们:“世界历史”不是一个被隔离的专业,而是一个与历史学科的其他发展共同成长和成熟的专业。
彭慕兰和夏德明分享着一些共同的经验,他们分析了孟德卫(D.E. Mungello)所谓的中国和西方之间“大相遇”的不同侧面(2005)。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2001)引发了一场激烈和持续的论辩,给为什么英国在19 世纪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清王朝落后了这个问题带来了新鲜的研究。同时,从社会和学术角度来看,夏德明的贡献是重新评价了早期现代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他的研究用语言技能和新的档案资源改写了这个曾经以欧洲为中心视角的研究领域。此外,夏德明凭借独特的经历,从三个差异很大的国家出发(德国、美国和中国)看待历史的发展,并出版了首次全面研究世界历史全球化的著作(2011,另请参阅Zhang, 2012 和Neumann,2012)。
劳伦• 本顿和克里• 沃德之间的学术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沃德明确认识到本顿的《法律和殖民文化》(Law and Colonial Cultures, 2001)对她自己的专著《帝国网络》(Networks of Empire,2009)产生了影响。这是世界历史学家在法律史和帝国史领域发现新资料和对传统话题发展新阐释的两个例子。比较法律史是一个成熟的领域,但是在过去,法律历史学家倾向于对比较法律体系进行规范性描述,社会要求人们应该怎么做,而不是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本顿表明,首先就法律史而言,然后扩展到“主权”方面,司法程序不能仅从立法章程上读出来,即便是被征服的人民或者臣民也有一些关于法律实践的话要说。在这些深刻见解的基础之上,沃德从事的研究跨越印度洋,与非洲和亚洲历史联系起来追踪罪犯的迁移,在此帝国史、法律史、宗教史、社会史和传记相互交叉。如果我们说世界历史作为一个领域,其特征之一是优先考察“运动”的故事(Ward, 2012),那么她的研究就是一个完美案例。
到此,本书读者的视角也许已经充分地延伸,为大卫• 克里斯蒂安关于“大历史”起源和发展的想法做好了准备。不仅仅是伞兵,克里斯蒂安是历史学宇航员。如果研究世界历史经常会给传统历史学领域(法律或者帝国史)带来耳目一新的总体洞察力,或者全球史与其他浮现的话题(环境或者性别史) 像燕尾榫一样接合起来,那么克里斯蒂安是一个例外。他朝着“大历史”富有想象力的飞跃使得他和志同道合的同事超越了历史学家通常工作的领域边界,进入与天体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的对话。
最后,从浩瀚的宇宙回到相对亲密的人类文化和文化互动,我们以杰里• 本特利最后的文章结束。我和杰里最后一次谈话时,他的语言间洋溢着他朝着全球文化历史方向发展的学术轨迹,但是听起来他非常虚弱。一个月之后,他过世了,我了解到他曾经在最后的日子里还在写作他的《设计师》文章,他的遗孀卡罗尔• 蒙• 李(Carol Mon Lee)认为这篇文章值得出版。在与我们共同的朋友阿兰• 卡拉斯(Alan Karras)交流时,我也发现,夏威夷大学的一个同事凯伦• 乔利(Karen Jolly)在杰里弥留之际与他见了面,并精心准备了学术讣告。这样,我们在此按照原样出版了杰里的文章段落,在结尾部分乔利以第三人称叙述了杰里成熟的作品和思想。为了纪念杰里• 本特利对世界历史领域的持久影响,我们将此书献给他。
- 浙江大学出版社微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浙江大学出版社直营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