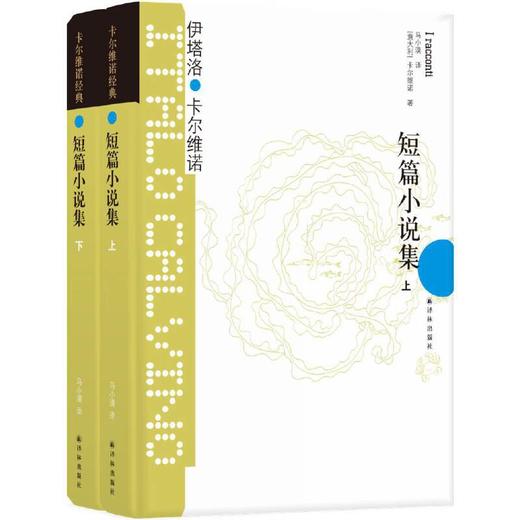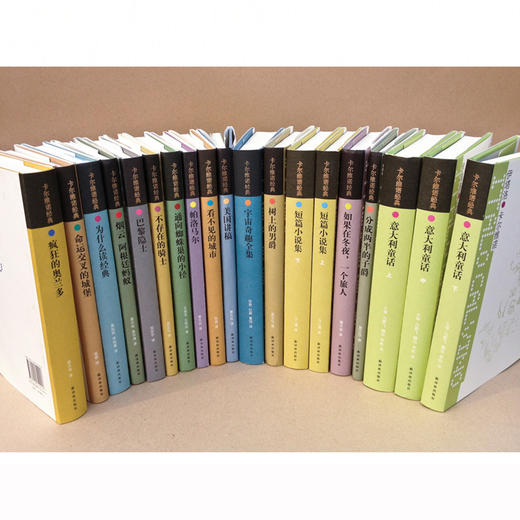商品详情
卡尔维诺因为听厌了人们总说他写的东西“容易”“愉悦”,成心写一些 “艰难”的东西。 这些“田园诗”、“记忆”、“爱情”“生活”轻盈短小,却让人体味到困窘、苦恼、无法沟通的艰难和沉重。

【内容简介】
一首艰难的田园诗,一段艰难的记忆,一份艰难的爱情,一种艰难的生活。在这四卷《短篇小说集》里,卡尔维诺把贫瘠、困窘、苦恼、无法沟通的爱这些艰难沉重的东西,都写成了普通人的瞬间,变成了“一种味道、一道闪光、一声吱嘎响、一种生命的调子”。在小小的快乐、扭捏的困境里,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小说中的人物怀着自欺欺人的侥幸,带着“不得不如此也就算了”的无奈接受了现实状况。
【作者简介】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意大利当代*有世界影响的作家。1923年生于古巴,1985年在滨海别墅猝然离世,而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其人其作早已在意大利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卡尔维诺从事文学创作40年,一直尝试着用各种手法表现当代人的生活和心灵。他的作品以丰富的手法、奇特的角度构造超乎想象的、富有浓厚童话意味的故事,深为当代作家推崇,并给他们带来深刻影响。“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命运交叉的城堡》、《帕洛马尔》等达到惊人的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意大利童话》*限度地保持了意大利民间口头故事的原貌,再现了意大利“民族记忆”之深厚积淀。《美国讲稿》是卡尔维诺对自己近40年小说创作实践的丰富经验进行的系统回顾和理论上的总结与阐发。他的作品以特有的方式反映了时代,更超越了时代。
【媒体评论】
我不能强求大家喜欢他(卡尔维诺)的每一本书,但是我觉得必须喜欢他的主意:小说艺术有无限种可能性.——作家 王小波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三人同样为我们做着完美的梦,三人之中,卡尔维诺*温暖明亮。——约翰?厄普代克
【目录】
*卷 艰难的田园诗
大鱼,小鱼(1950)
一个下午,亚当(1947)
装螃蟹的船(1947)
被施了魔的花园(1948)
人们中没有一个知道这事(1950)
好游戏玩不长(1952)
去指挥部(1945)
乌鸦*后来(1946)
在路上的害怕(1946)
雷区(1946)
三个人中的一个仍活着(1947)
牲口林(1948)
不可信的村庄(1953)
一家糕点店的盗窃案(1946)
像狗一样睡觉(1947)
你这样下去就不错(1947)
美元和老妓女(1947)
一张过渡床(1949)
猫和警察(1948)
城市里的蘑菇(1952)
市政府的鸽子(1952)
饭盒(1952)
黄蜂疗法(1953)
高速公路上的森林(1953)
好空气(1953)
毒兔子(1954)
和奶牛们的旅行(1954)
长椅(1955)
月亮与Gnac(1956)
车间里的母鸡(1954)
数字之夜(1958)
帕乌拉提姆太太(1958)
第二卷 艰难的记忆
荒地上的男人(1946)
巴尼亚思科兄弟(1946)
主人的眼睛(1947)
懒汉儿子(1948)
与一个牧羊人共进午餐(1948)
进入战争(1953)
青年先锋队员在芒通(1953)
国家防空联合会的晚上(1953)
第三卷 艰难的爱情
一个士兵的奇遇(1949)
一个海水浴者的奇遇(1951)
一个职员的奇遇(1953)
一个近视眼的奇遇(1958)
一个读者的奇遇(1958)
一个妻子的奇遇(1958)
一个旅客的奇遇(1957)
一对夫妻的奇遇(1958)
一个诗人的奇遇(1958)
第四卷 艰难的生活
阿根廷蚂蚁(1952)
房产投机(1957)
烟云(1958)
【前言】
我没写过的短篇小说
对于自己的作品,本是什么都无需说的。让它们自己说,就够了。把若干短篇小说凑成一本书,给它们理个顺序,再归个类,在它们的排列中找出个意义,寻出标题和一些总括性的定义,就已经是对原作品的声音(不管这声音是强是弱)外加了另一种声音,一种解释性的不同意图,就已经是对读者的自由使用了暴力,就已经是去完成那些属于评论家职业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则已彻底地超出了作者的任务。妙的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如果作者抢了评论家的活,如果作者想定义自己的作品,评论一点都不反对;人们本来指望着评论会赶紧提出其他的阅读指导、其他的定义、其他的作品和作品间的关系,来加以反驳,然而评论却接受了它被给予的*个借口,仅仅满足于解述作者的痕迹。比如:在我把我的这本书分成的所有四个部分的标题中,都用上了“艰难的”这个形容词。为什么?因为我早就听倦了人们对我以前写的那些东西说“容易”,说“愉悦”,说“愉悦的容易”,说“容易的愉悦”。于是,我就到处写下了“艰难的”这个到目前为止人们感觉与我的文章相去甚远的形容词,这种性质,这种生活的意义于我曾显得遥不可及。好吧:行了。几乎所有的评论,都不眨眼地一致主张,艰难的意义一直就是我小说主要和永恒的特点。我本该为此而高兴,但我存了个疑,如果在这些标题中,我不是用“艰难的”这个形容词,而是用了“容易的”这个形容词,是不是什么都不会改变,所有人仍会同样地完全赞同。于是,我就留在了原地;我对于世界,对于与世界关系的犹疑,如果一切都是艰难的,不管是使人强健的或是使人丧失能力的艰难,又或一切都是容易的,不管是热情的或是失望的容易,我那个犹疑都没有解决,我这种对于世间万象缘由的普遍质问,并没有得到回答。而这些,都是徒劳的,需要知道如何靠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应该是永远无需对自己的作品说些什么的,不能比它们被数出来的词多说一个词,也不能比它们必不可少的词多说一个词,这些词是一个也不能添,一个也不能减。这些东西早在隐逸派时代就已明晓于世了。蒙塔莱的Occasioni里的注释,你们还记得吗?从孩童时候起,每读完一首貌似十分难懂的诗,我就会跑去看书本末尾那少许几页的注释能否提供什么帮助,什么鼓励。然而没有,都是一些吝啬得叫人失望的注释,简洁,患了失语症一般,对那些我们期待的东西是什么都不说,但这正是教给了我们正确的一课,这里也是如此:你要自己去解决它,也许这是我们学会的*好一课。
现在我们属于一个不同文学的时代,现在的文学更轻率,更倾向于评论文学,谈文学,把文学当作一种话题。
可文学的话题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有关世界现实,有关隐秘规律、图案、生命节奏的话题,一个从也没有结束过的话题,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感到有必要反复重新提起的话题,因为我们与现实产生联系的方式在不断改变。
你们将要好心地加以关注的这本小说书,只是想成为一种证据,证明在那些于一九四五年开始自己文学实验的人中,他们中的一个,从其时到如今,是如何追随那个去捕捉一种味道、一道闪光、一声吱嘎响、一种生命的调子的幻想的。那是些对于世界的伟大哲学解释并不适合的时代,同样对于伟大的小说也是不适合的;我们尝试过在好比蚂蚁一只眼睛的无数刻面中,在人们企图据以重建整座庞大恐龙骨架的化石脊柱中,去捕捉宇宙的秘密。
当我刚开始的时候,写作是容易的。在词语和东西之间,在事实的力量和风格之间,在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之间,是没有差别的。生活在用我们周边的故事迅速繁殖。我和其他人写的很多小说,都是在游击队员的露营地中,在一战后的三等车厢里的tales of hearsay,听别人讲出来的故事。那时,有种要诉说,也要选择那些诉说方式和形态的集体驱动力。当然,我再也写不出来当时是怎么样的了,不只是因为我那时还年轻,所以事情于我看来都很容易。那种允许用相当有限的方式来表现事实的张力,是一种历史的张力,是早在个人的写作艺术之前,就存在于事物和时间之中的。我很快就发现,那是一种易逝的财产,我不久就能将其掠劫一空、消耗尽的财产。那个时候,我仍能相信这种财富是与“经验”相符的:游击队时期的经历被剥削完了,我们还能用什么来滋补我们的叙述?曾经有一个学派,也就是我们后来定义为叙事学的美国学派,提出一种能肯定获得成功的方法:丰富经验,旅行,亲临正在发生动荡事件的地方;那么写作就会成为一种必然。在我开始写作的年代里,这种思维形态正值其*。那么,既然战争已然结束,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如果我们还想写作的话?追随已经迫在眉睫的新冲突爆发,去西西里参军、和朱里阿诺的独立主义分子混在一起,或者是去巴勒斯坦跟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作战?可对于既不是西西里人也不是以色列人的我们,那只会是种纯粹的冒险。而在全世界乱转的毫无理由的冒险,并不是我寻找的现实。如果这我不是自己明白的,还有切萨雷•帕维泽反复对我们说,只有从那些不带着文学动机而经历的东西中,才能生出诗来,只有那拥有真正根系的地方,才能冒出树叶与果实。
另一条路是求助于现实的宝藏,这种现实是由自己的地域,由地方的、通俗的、取之不竭的场景构成的:正是在那些年里,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有回归地区唯真主义的明显倾向。但地区唯真主义并不是我寻找的现实。地方主义永远要晚于历史一拍,而我感兴趣的是那些与历史同步的东西,但同时也要从自己的根源出发,立足于一片土地,拥有一种经历。
我曾参与的政治一派,企图在文学中描写出一种人民,这种描写会把纪实性的客观与积极情绪的富足和说教的热情混淆起来。但是社会现实主义并不是我寻找的现实:在革命运动中,我对一种早已众所周知的道德的解释从来也不曾感过兴趣,也不会感兴趣,但我感兴趣的是那种历史逻辑的荒谬机制。我在政治报刊上登载的小说在慢慢地失去现实的体积,但增添了叙述的线性成分,增添了能够获得一致的对称,增添了像寓言或童话般精准的几何学,而这正好发生在——您请注意好了——其时的政治理念*能来滋养我那些小说的时候。直到如今,我仍以为,如果不是想像的,讽刺的,乌托邦的文学,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文学,我仍以为,“现实主义”经常携带着一种不信任历史进程的因素,携带着一种对过往的偏爱,这种偏爱但愿是高贵地反动的,并且即使在保守这个词的*积极的意义上也是保守的。
所以,是那种加强小说中理性的和故意的因素,加强秩序与几何学的需要,把我推向童话的。童话和想像叙述的那条道路,并不是一条任性与简单的路途:如果太过偏向纯粹的超现实无理由,可就糟了,如果不得不遵循一种局限于体现狭义道德历史的准则,那也很糟。为了避免成为一场纸做的舞台背景,想像必须要充满了回忆、必要性,总之,充满了现实性。
现实,于是——在我的*早的那些短篇小说的时期,现实好像如此简单和直接——就越来越成为一条不可捉摸的白鲸。如果我想抓住它的骨架,则必须要感到现实在越来越稀薄,直到它变成童话或是芭蕾舞蹈,而如果我想抓住它无限庞杂的整体,则需要对准一种在空间和时间里尽可能确定的叙述,一种麇集、细致、密布的叙述,就像用极细的针脚织成的网。而这里,我不得不去面对自己过去的一切;因为刚从浸满了直接经验的亲身经历中脱离出来,这网的针脚会扩张,缺口和脱漏也会打开,而现实的意义就会缺失。我寻找的现实也不存在于自传主义和心理反省中。对于人类灵魂的自传和描述会偏向于不定形,偏向于无限的接近,偏向于每一个人类存在的内心混乱;而我却总是偏向于构建一种有意义、有矢量线条图解的故事,偏向于把现实的刀片往每次选择出来的不同方向磨尖。
当然,只有从记忆,还有从我们曾直接卷入其中的经验出发,才能获得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描写,一种不冷也不假的描写。但我寻找的现实,也肯定不存在于对意大利社会描写的现象学中,也不存在于对习俗的记录和批判中。当没有别的形式来了解,来表现这些事实的秩序时,文学有这种功用是合理的;而现在,我们有相当活跃的新闻业,也有在环境和现象方面都颇具实况效果的电影艺术。文学于是就有了另一项任务:揭示历史转折点,揭示重要时刻,揭示钟表结构上将来未知的一步跳跃,而不是今天那种滴答声。
我看到,我能向你们说出的,不是我已经写出的那些小说的故事,而是我慢慢地拒绝写出的那些小说的故事。至于那些我写过的小说,它们在那里,在书中,我希望,它们的故事能由它们自己讲述出来。
【免费在线读】
*卷 艰难的田园诗
大鱼,小鱼
泽费利诺的父亲从来不穿游泳衣。他总是穿着卷着裤脚的裤子,套着短袖衫,戴着顶白布料的帽子,从来不离开礁石群。他的爱好是帽贝,那种扁平的、贴在礁石上的软体动物,它们硬极了的介壳和石头几乎浑然一体。为了把它们拿下来,泽费利诺的父亲得使上刀,每个星期天他都用自己那戴着眼镜的目光检阅海岬上的每一块石头。他能一直这样继续下去,直到他的小筐子里装满帽贝;有几个是刚摘下就吃掉了,他吸着帽贝那湿润而发酸的贝肉,就像从调羹里吸出来一样;其他的帽贝他则放进篮子。他不时地抬起眼睛,并把这有些茫然的眼睛转向平滑的大海,喊道:“泽费利诺!你在哪里?”
泽费利诺整个下午都待在水里。他们两个一起来到海岬,随后父亲就把他丢在那里,赶紧去跟在他的帽贝后面了。帽贝这么坚定固执,不可能吸引泽费利诺的注意力;首先吸引他的是螃蟹,然后是章鱼,再有就是水母,接着是各种各样的鱼。入夏以来,他这个猎打得是越来越复杂和巧妙了:现在跟他一般大、持着水下猎枪能把猎打得像他这么好的小伙子,是一个也没有。水下功夫上乘一些的要数有点矮胖的家伙,耐力好,肌肉足;泽费利诺正在往这个样子长。在地面上,他那样牵着父亲的手,看起来就是一个那种剃着光头,张大嘴巴,需要让人拍着脑袋才能往前走的小伙子,在水上,他可是比谁都要强;潜在水下还要厉害。
那一天,泽费利诺为了水下狩猎把所有器械都准备齐全了。潜水面具他是去年就有的,那是他奶奶的礼物;一个表姐妹的脚小,就把她的脚蹼借给了他;猎枪他是从舅伯家里拿来的,他拿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却跟父亲说是他们借给他的。再说他是个小心的孩子,既会耍枪,处事又周全,大家把东西借给他都很放心。
大海很美,很清澈。泽费利诺对所有的嘱咐都说:“好的,爸爸,”然后就下水了。他那样顶着插上通气管的玻璃脸罩,蹬着双鱼尾一样的腿,手里还操着那既像长矛,又像步枪,也像鱼叉的工具,都不再像人类了。然而,一下海,尽管他是半埋在水中地游弋,还是很快就能认出来那是他:从他拍脚蹼的模样,从他把枪夹在腋下举向前方的方式,从他把头浮在水面向前行进的那个势头。
海底起初是沙子,然后是石头,有些石头表面给侵蚀了,光秃秃的,另一些上面则是长胡子般布满了密匝的褐色海带。在礁石的每一处褶缝里,或是翱翔在水流中那颤抖的须根之间,都有可能突然出现一条大鱼,玻璃面罩后,泽费利诺全神贯注地转动着不安的眼睛。
*次发现海底时,会觉得它很美:不过就像其他每一件东西,*美的,还在后头,要通过一次次的划臂才能完全了解它。就好像是在喝这些水下景色:走啊走,永远也走不到头。面罩的玻璃是一只巨大的单眼,吞食着这些阴影与色彩。现在阴暗结束了,他已经远离了那片礁石的海域;在海底的沙子上,能辨认出来被海水流动勾勒出的纤细波纹。太阳的光芒一直到达这底下,摇曳着闪烁不停,成群的追饵鱼也跟极小的鱼群笔直地疾行着,然后突然又一齐来个直角转弯。
突然升腾起来一片沙云,那是海底的一条金鲷鱼拍了一下尾巴。它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对准了那个鱼叉。泽费利诺已经在潜游了;而金鲷鱼呢,那生着条条线纹的两侧漫不经心地摆动几下后,猛的一跳就溜走直冲到水面去了。这鱼和捕鱼人一直游到了一片小海湾里,周围尽是些竖着刺海胆的礁石,那里的石头多孔,光溜溜的。“在这里它可就逃不掉了,”泽费利诺想;就在那一刻,金鲷鱼失踪了。从一些洞穴和凹槽里,冒出一串小泡,然后很快就止住了,然后在另一处又冒起泡来;海葵不停地发着光。金鲷鱼从一个穴口中探出身来,随即消失在另一口洞穴中,很快又从极远的一个孔里钻出来。它沿着一块山嘴般的礁石,朝底下游去,泽费利诺看见在海底有一处地方绿得发光。这鱼在那片光亮中迷失了方向,泽费利诺紧随它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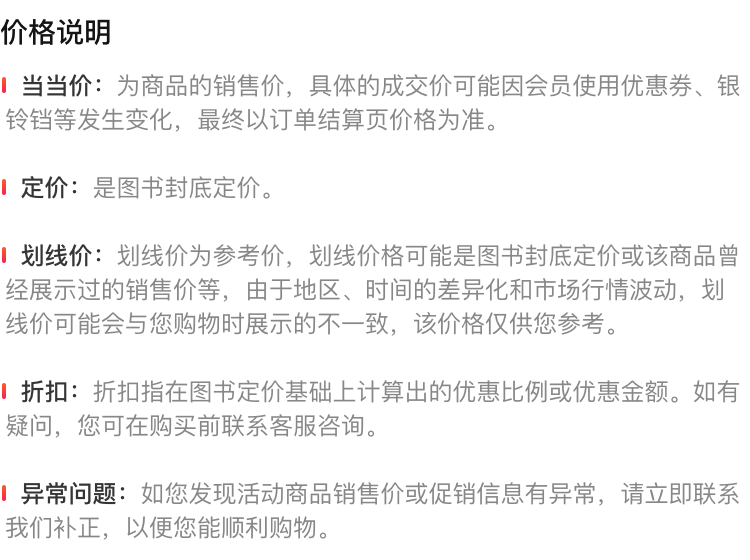
- 译林出版社旗舰店
- 本店铺为译林出版社自营店铺,正品保障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