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详情


书名:《月亮与六便士》
主编/作者: [英]威廉•萨姆塞特•毛姆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75-4292-1
版次/印次 :2016年1月
定价 :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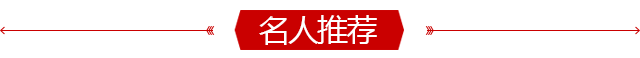
这是一本关于梦想与追寻的书,“月亮”是美好而遥远的,就像人们追寻的梦想,但追寻的过程也许孤苦,甚至最后会一无所得;“六便士”象征着世俗、琐碎的生活,但也有其存在价值。你的手中究竟是“月亮”还是“六便士”,看完之后也许你会陷入沉思。
——范冰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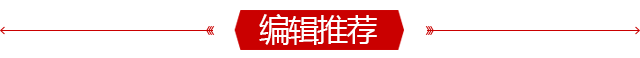
毛姆三大代表作之一,20世纪风靡全球;
马尔克斯、奥威尔、格雷勒姆•格林、奈保尔、伍尔美、张爱玲、村上春树、王安忆、刘瑜、毛尖、董桥、冯唐、曹文轩等人一致推荐;
以高更生平为题材的经典之作,书中收录30幅高更的代表画作;
《送你一颗子弹》《民主的细节》作者刘瑜作序推荐;
陈逸轩译作,全新台译本,更优美更流畅的全彩印刷,精装典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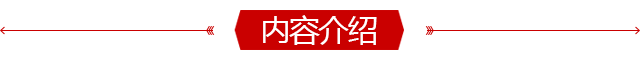
作品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
“我”是一名作家,认识了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一家。这个家庭看上去美满幸福,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先生总是显得缺乏活力。不久之后思特里克兰德离开了家庭,去了巴黎,决心寻找自己的“艺术”。
“我”找到思特里克兰德,他决心挣扎出这种生活。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后来找到了谋生的技能,过得很好。五年之后“我”在巴黎见到了思特里克兰德,他过得穷困潦倒,但是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中,从未觉得后悔。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他的才能也渐渐得到认可。
后来思特里克兰德决定抛弃文明生活,来到了接近原始的南太平洋群岛的塔希提岛,与“我”偶然相逢。思特里克兰德娶了一名土著姑娘,并且生了三个孩子,度过了三年短暂的幸福时光。
后来孩子们死了,他也得了麻风病。最后在失明的时候在墙上完成了一幅力作。土著妻子埋葬了他,并且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遗作予以销毁。尽管“我”惋惜不已,但也在他的绘画中理解了他的追求。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1874.1.25-1965.12.15)英国小说家、戏剧家。十岁之前都住在法国巴黎,因父母先后去世,他被送回英国由叔叔抚养。
毛姆先后就读于坎特伯雷皇家公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孤寂凄清的童年生活和因身材矮小、严重口吃遭受歧视的学生时代,在毛姆的心灵上投下了痛苦的阴影,养成他孤僻、敏感、内向的性格,也对他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92年进入伦敦圣托马斯医学院学医。学医使他学会用解剖刀一样冷峻、犀利的目光来剖视人生和社会。他的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莉莎》(1897),正是根据他从医实习期间的所见所闻写成的,从此弃医从文。
接下来的几年,毛姆写了若干部小说,但是没有一部能够“使泰晤士河起火”,遂转向戏剧创作,获得成功,成了红极一时的剧作家。代表剧作《弗雷德里克夫人》(1907),连续上演达一年之久。
在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决定暂时中断戏剧创作,用两年时间潜心写作酝酿已久的小说《人性的枷锁》(1915)。1919年发表的《月亮与六便士》更加巩固了他作为小说家的地位。
为了收集素材,毛姆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因此不少作品有浓郁的异国情调。1920年毛姆到了中国,写了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1922),并以中国为背景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面纱》(1925)。
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期,是毛姆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代表作有刻画当时文坛上可笑可鄙的现象的《寻欢作乐》(1930)和充满异国情调的短篇集《叶之震颤》(1921)等。
第二次大战期间,毛姆到了美国。1944年发表长篇小说《刀锋》。此后,他回到早年定居的法国里维埃拉,直至1965年溘然长逝。
译者陈逸轩,台湾高雄人,资深外国文学译者,接生过很多流离失所的文字,专长是成为陌生人。其代表译作包括《变色龙》《月亮与六便士》《青年狄更斯:伟大小说家的诞生》《二次性的建筑》《菲洛梅娜》等。

那个时段的克利希大道人潮汹涌,你若有生动的想象力,或许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可以瞥见许多不伦恋情的主角。里头有公司职员和女店员;有如从巴尔扎克书中走出来的老人家;靠人类弱点赚钱的行业的男女从业人员。巴黎较为贫穷的区域里,街上有种摩肩接踵的活力,让人热血沸腾,期待迎接未知的事物。
“你对巴黎熟吗?”我问。
“不熟。我们度蜜月时来过。之后就没来过了。”
“你到底是怎么找到你住的旅舍的?”
“有人推荐给我的。我想找便宜的地方。”
苦艾酒来了,我们煞有介事地把水浇在融化的方糖上。
“我想我最好开门见山告诉你我的来意。”我稍微有点尴尬地说。
他眼中闪烁着光辉。“我就想迟早会有人来。我收到一堆艾美寄来的信。”
“那么你很清楚我要说什么了。”
“我一封都没读。”
我点了根烟沉淀思绪。我自己也不大清楚该怎么着手此行任务。我事先想好的动人台词,不论诉诸怜悯或表达愤慨,在克利希大道上似乎都格格不入。他忽然低声窃笑。
“你担上了个苦差事,是不是?”
“喔,这我不晓得。”我这样回答。
“好吧,听我说,你把事情赶快解决,咱们晚上就有乐子了。”
我迟疑了一下。
“你可曾想过,你妻子有多不快乐?”
“她会平复过来的。”
我无法形容他这样回答时有多麻木无情。我感到仓皇失措,但尽量不显露出来。我端出自己当牧师的亨利叔叔会用的语气,他每次要亲戚捐献助理牧师候选人协会时都会这样说。
“你不介意我老实跟你说吧?”
他微笑着摇头。
“她做了什么让你这样对待她?”
“没有。”
“你对她有什么怨言吗?”
“没有。”
“那么这样离开她岂不恶劣?你们都十七年的夫妻了,她也毫无毛病可挑。”
“确实很恶劣。”
我惊讶地瞟了他一眼。他对我说的每句话皆表示由衷赞同,这让我站不住脚。我的立场因此变得很复杂,更别说可笑了。我本来准备好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忠告、训诫和规劝齐发,必要的话甚至可以谩骂、愤怒且讥讽;但罪人毫不犹疑地坦承罪过时,“心灵导师”能怎么办?我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因为我自己总是习惯否认一切。
“然后呢?”思特里克兰德问。
我用嘴角试着装出轻蔑之意。
“既然你都承认了,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想应该是没了。”
我觉得自己此行任务执行得并不漂亮。我真的恼火了。
“去你的,你不能抛弃女人,让她身无分文。”
“为什么不行?”
“她要怎样过活?”
“我已经养了她十七年,为何她就不该养活自己试试看?”
“她没办法的。”
“让她试试。”
当然我有许多可以回应这句话的答案。我或许可以提起女性的经济地位,男人缔结婚姻时立下的契约——不论是默认或明文规定的,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但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仅有一点。
“你不再爱她了吗?”
“一点儿也不。”他这样回答。
对所有人来说这件事极其严肃,但他回答的方式厚颜无耻到欢快的地步,我必须咬着嘴唇才不会笑出来。我提醒自己,他的行为可恶至极。我努力让自己处于义愤填膺的状态。
“真该死,你得想想你的孩子。他们不曾伤害过你。被生下来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你要是像这样抛弃一切,他们会流落街头。”
“他们已经养尊处优好几年,远超过大部分小孩子所拥有的一切。何况会有人照顾他们。说到这个,麦克安德鲁夫妇会支付他们的教育费。”
“可是你不喜欢他们吗?他们是很乖巧的小孩。你真的想说自己不想再和他们有任何关联?”
“他们还小的时候我的确喜欢他们,不过他们现在大了,我对他们没特别的感觉。”
“你好无情。”
“我敢说是这样。”
“你看起来一点儿都不觉得羞愧。”
“的确不。”
我改变方针。
“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个畜生。”
“随便他们。”
“知道别人厌恶鄙视你,你也没事?”
“没事。”
他简短的回答极其轻蔑,我的问题相形之下虽然再自然不过却感觉荒谬。我思索了一会儿。
“我不晓得人要怎样安心过日子,假如他心里明白别人对他的非难。你确定自己不会哪天开始担忧了起来?每个人多少都有点儿良心,迟早会找上门来的。假设你妻子死了,难道你不会悔恨当初?”
他没回答,我等着他开口应声。最后我还是自己来打破僵局。
“这你要怎么说呢?”
“我只想说你蠢到家了。”
“无论如何,你都可能被迫抚养妻小。我想他们可以寻求法律保护。”我有点儿不悦地回嘴。
“法律能从石头身上榨出血来吗?我没有钱,身上只剩一百英镑左右。”
我愈来愈摸不着头绪。他住的旅舍的确显示他的处境拮据。
“钱花光你打算怎么办?”
“再赚。”
他的态度十分冷静,眼神中保持着嘲讽的笑意,让我所说的一切相形之下都显得愚蠢。我安静了一会儿,思索接下来该说什么好。他倒是先开口了。
“艾美为什么不改嫁?她还算年轻,也不是没有姿色。我可以推荐她的确是优秀的妻子。她想跟我离婚的话,我不介意提供必要的理由。”
这下轮到我窃喜了。他很精明,这显然是他锁定的目标。他不晓得为了什么理由,隐瞒他和女子私奔的事实,他小心翼翼隐藏她的下落。我断然回答:
“你妻子说,不管你怎么做,她都不会跟你离婚。她已经铁了心。这条路你可以不必再想了。”
他惊讶地看着我,那神情绝对不是装出来的。他收起嘴边的笑意,很认真地说:
“可是朋友啊,我不在乎。不管离不离,我半点都不在乎。”
我笑了出来。“噢,拜托,你别以为我们都是笨蛋。我们恰巧就是知道你和别的女人私奔了。”
他愣了一下,接着蓦地放声大笑,笑声震耳欲聋,引得坐在附近的人回头侧目,有些也笑了起来。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
“可怜的艾美。”他咧嘴而笑。
然后他脸色变得鄙夷不屑。
“女人的头脑真可悲!爱。老是爱。她们以为男人离开,只可能是移情别恋。你觉得我这么做会是傻到因为一个女人吗?”
“你的意思是说,你并非为了别的女人而离开妻子?”
“当然不是。”
“你以人格担保?”
我不晓得自己怎会这样要求。我真是太过天真。
“我以人格担保。”
“那么,老天爷啊,你究竟为了什么离开她?”
“我想画画。”
我细细端详他良久。我不懂。我觉得他疯了。别忘了当时我很年轻,在我眼里他是中年男子。我只记得自己当时的讶异。
“可是你四十岁了。”
“正因如此我才认为是时候了。”
“你画过画吗?”
“我小时候很想当画家,但我父亲逼我从商,因为他说搞艺术没钱赚。我一年前开始尝试画。过去一年我晚上都去上课。”
“思特里克兰德夫人以为你去俱乐部打桥牌时,你都是去上课?”
“没错。”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
“我宁可保守秘密。”
“你会画了吗?”
“还不行。但我会成功的。所以我才来到这里。我在伦敦无法达成目标。在这里或许可以。”
“你觉得像你这样的年纪才开始,会有任何成就吗?大部分的人十八岁就开始画了。”
“我可以比十八岁时学得更快。”
“你凭什么觉得你有天分?”
他没马上回答,眼神驻留在路过的人群身上,但我并不觉得他真的在看他们。他的回答等于没回答。
“我就是得画。”
“你这岂不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他注视着我,眼里闪着异光,我被他看得很不自在。
“你多大年纪了?二十三?”
我觉得他问这个岔题了。我去冒险那是很自然的事,但他早已青春不在,他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证券经纪人,家有贤妻和一双子女。对我来说再自然不过的道路,对他而言却荒诞不经。但我还想对他公道一些。
“当然奇迹有可能发生,你可能成为伟大的画家,不过你也得承认这只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假如到头来你必须承认自己搞得一团糟,那就难看了。”
“我就是得画。”他又重复了一次。
“假如你顶多只能成为三流画家,你觉得因此放弃一切值得吗?毕竟对其他任何行业来说,你不特别杰出也没关系,你只要还过得去就能过得很舒适,不过艺术家就不一样了。”
“你这该死的蠢蛋。”他说。
“我不懂你为何这样说,除非把显而易见的道理说出来也算是蠢事。”
“我就跟你说了我得画。我也没办法克制自己。一个人掉进水里的时候,他游得好不好并不重要,他就是得游出来,不然就等着溺水。”
他的声音中带着真正的热情,我不由自主受到感动。我仿佛感受到一股激昂的力量在他体内挣扎:感觉就好像他不情愿地被某种十分强烈、压倒性的东西给控制住了。我没办法理解。他似乎被魔鬼附身,我觉得他随时都可能被撕成两半。然而他看起来正常极了。我眼睛好奇地盯着他看,他丝毫不以为意。他就穿着他那件旧的诺福克外套、头戴着单面绒的圆顶礼帽坐在那儿,真不晓得陌生人会怎样看他。他的裤子太过宽松,双手也不干净;而他那张脸,下巴上长满没刮的红色胡碴,小小的眼睛和张扬的大鼻子,看起来粗鲁鄙俗。他有张大嘴巴,嘴唇厚而肉感。不,我没办法帮他定位。
“你不会回到你妻子身边?”我终于这样说道。
“绝对不会。”
“她愿意忘记发生的一切从头开始。她甚至完全不会责怪你。”
“叫她去死吧。”
“你不在乎别人觉得你是无耻之徒?也不在乎她和你的孩子们得乞讨为生?”
“一点儿也不。”
我沉默了一会儿,酝酿开口说出下一句话的气势。我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吐了出来。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无赖。”
“这下你已经一吐为快了,咱们去吃晚餐吧。”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认证)
- 本店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官方直营旗舰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