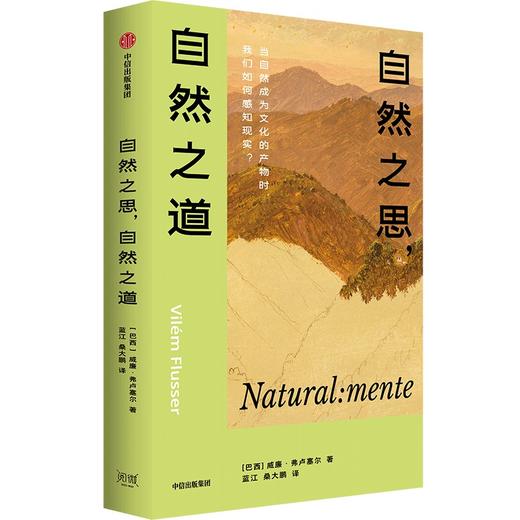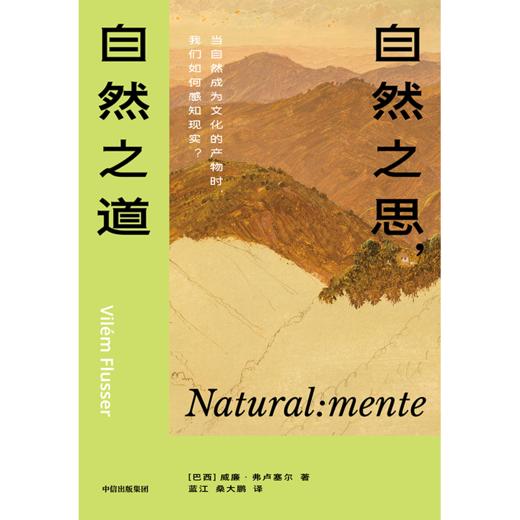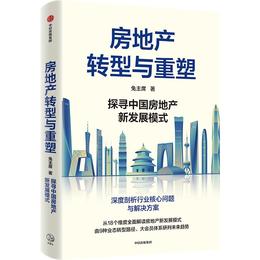商品详情

书名: 自然之思,自然之道
定价: 58.00
作者: 威廉·弗卢塞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 2025-12-02
页码: 176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ISBN: 9787521772388
 (1)预见“人造自然”时代的前瞻性视野,为技术裹挟中的认知提供哲学指南
(1)预见“人造自然”时代的前瞻性视野,为技术裹挟中的认知提供哲学指南早在全球生态意识开始觉醒、信息技术逐渐兴起的20世纪70年代,弗卢塞尔已敏锐意识到技术媒介对“自然”概念的深刻改写,堪称“数字时代的哲学先知”。本书不仅回应了当时的生态思潮,更精准预见了当今由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定义,以及深受技术规训的“人造自然”世界。书中对技术重塑现实与人类感知的剖析,在科技狂飙的当下尤显深刻。
(2)唤醒清醒的生存姿态和科学观,倡导以思考和行动关切、塑造我们共同的世界
本书通过对“自然”概念的解构超前地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然”与“文化”深度纠缠的混合现实。弗卢塞尔由此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鼓励我们夺回对所创造世界的理解权和定义权。既然我们无法脱离自己创造的、由技术和文化塑造的自然,那么一的出路就是清醒地认识它,批判地介入它,并主动地为其承担责任。
(3)媒介哲学家弗卢塞尔的思想成熟之作,设定其后续哲学探索的关键议题
弗卢塞尔是一位凭借前沿思考在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思想家。作为开启其思想成熟期的关键之作,本书以对“自然”与“文化”(特别是由技术媒介构成的环境)之间辩证关系的根本性思考,为他此后关于技术、图像、媒介与人类生存状况的研究定下基调。其学术体系的诸多重要议题已在本书中萌发,使得本书成为理解其思想脉络不可绕过的源头性文本。
(4)以诗意思辨打破学科壁垒,中文译本由业内专家精心译校打磨
本书以独特的诗化语言融合哲学、媒介理论、生态学与语言学,开启了弗卢塞尔对技术文明的前瞻性反思,典型地体现了其跨学科写作风格。中文译本由知名欧陆哲学研究者蓝江教授主译,经青年葡萄牙语译者桑大鹏校译,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的思辨密度与文学质感。
 我们是否生活在纯粹的自然中?还是说,它是人类心灵借由文化呈现的造物?当技术图像等文化产物日益覆盖我们的认知并逐渐成为“第二自然”时,那个曾作为人类思想源头的自然,将走向何方?
我们是否生活在纯粹的自然中?还是说,它是人类心灵借由文化呈现的造物?当技术图像等文化产物日益覆盖我们的认知并逐渐成为“第二自然”时,那个曾作为人类思想源头的自然,将走向何方?在这部次出版于1979年的哲学随笔中,威廉·弗卢塞尔运用现象学方法,对谷地、奶牛、月亮、草场等15个自然之物进行细致的观察与思考,揭示出一条通往自然真谛的道路:所谓“自然”,从来都是经过文化、技术与语言等媒介编码的文本。我们永远无法“自然而然地”思考自然,因为人类心灵始终是介入它的一工具。
由此,自然与文化并非截然对立。在如今被技术图像规训的“后客观时代”,弗卢塞尔倡导一种科学的姿态:认识到自然与文化彼此交织的辩证本性,承认我们深陷于认识对象的纠缠,却依然寻求一种广阔而无成见的视角,并以此实现真正自由的思考与行动。
 引言 道路
引言 道路谷地
鸟
雨
公园里的雪松
奶牛
草
手指
月亮
山
假的春天
草场
风
奇迹
萌芽
迷雾
结语 自然之思
 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1920—1991)
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1920—1991)哲学家、媒介理论家。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移居巴西,晚年定居法国。曾任巴西哲学研究院成员、圣保罗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精通德语、葡萄牙语、英语与法语,其写作游刃于多种语言与文化语境之间,其前瞻性思考至今仍持续激发读者对技术、媒介和人类处境的反思。
主要著作有《摄影哲学的思考》(1983)、《技术图像的宇宙》(1985)、《书写还有未来吗?》(1987)等,以跨学科视野探讨技术、图像与文化的根本性变革,被译为多种语言,影响深远。
 引言 道路
引言 道路人生的两段经历交汇,令我得以罔顾后文即将细述之思绪的反复拉扯。一段经历是笔者上一次穿越奥芬山口,该山口将恩加丁谷地与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交界处的特伦蒂诺–上阿迪杰的诸多河谷连接起来。第二段经历是笔者近游览布列塔尼的卡尔纳克巨石阵。在这两段经历交汇前,笔者须首先把它们分别讲述。
奥芬山口处有一条沥青公路。它不太宽,因为交通流量并不大,该公路所连接的两个地区人口也不多。一些重要公路会在冬季封闭,而奥芬山口的公路却能在整个冬季保持无积雪的路况,因为它是所连接的两个地区之间一的公路。奥芬山口的公路是一条主干道的辅路,主干道始于库尔,沿着马洛亚山口通向米兰,成为中欧地区的南北通道之一。奥芬山口处的公路在恩加丁谷地的采尔内茨(距离美国石油大亨和百万富翁云集的城市圣莫里茨不太远,距离哲人尼采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所在的城市锡尔斯–玛丽亚也不太远)脱离主干道,沿着恩加丁国家公园上升到大约2 300米的高度,再沿着韦诺斯塔河谷的拉定人村庄和哥特式、伦巴第式城堡及特伦蒂诺—上阿迪杰的诸多河谷下降,在此汇入古罗马将军德鲁苏斯为打败雷蒂亚人而修建的道路,并在博尔扎诺(即古“德鲁西桥”)抵达慕尼黑—罗马高速公路,即古代的弗拉米尼亚大道——日耳曼尼库斯曾以罗马帝国的名义沿此大道穿越条顿人的森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曾为了向罗马教皇屈服,在忏悔中逆向穿越此大道,前往卡诺莎交还皇权。奥芬山口(其拉定语名称意为“烤炉通道”)由于横贯两条要道,似乎应是晚近的工程杰作,以便缓解中欧和亚平宁半岛之间川流不息的重型卡车带来的交通问题。这一项晚近而大胆的工程杰作需要采用先的技术方法。
笔者曾数次途经奥芬山口,不仅赞叹其山峰、冰川景致之雄伟,也钦慕其公路曲线之俊美。人类精神为科学工具所武装,便能凿穿自然的秘密,将其展露并供人欣赏。不仅如此,这一创举还兼顾美观。直到笔者在一本古人类学书籍里读到:在数万年里,奥芬山口处曾有马群、牛群和驯鹿通行的小径,旧石器时代的猎人们——我们的祖先追随它们的足迹将其捕获。当今公路的路线正是由这些动物“踏出”的。马群、牛群和驯鹿规划了这条公路,只有被执行的规划——无论是当今还是曾经无数次的施工——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如果把规划和想法视为相似的概念,那么造出道路的想法应属于苔原上的动物。它们才是勇敢的开拓者,而我们乘车从博尔扎诺到采尔内茨,不过是追随它们的足迹,正如猎人们(我们的祖先)一样。
同笔者上个星期所经历的一样,去布列塔尼旅行的人大都出于多重原因穿越这个神秘的区域:因为布列塔尼标志性的奇特建筑“受难碑”(calvários);因为圣米歇尔山这座庞大的修道院,这座山被称为“西方的阿索斯山”;因为布列塔尼人的伪基督教传说,他们在被盎格鲁–撒克逊人从“大”不列颠驱逐后迁徙至此,至今仍在延续“布列塔尼化”的进程,尽管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很早以前就在英国本土消失了;因为稀奇极的凯尔特人——也就是所谓的阿摩里卡人,即“海的子民”——从未真正被罗马人统治过,也没有被高卢人、布列塔尼人或法兰克人统治过。顺带一提,他们也未被正在“阿摩里卡”海滩上建造公寓楼的巴黎资产阶级同化过。(但是,他们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正在被大众文化支配,因而如今从“阿摩里卡人”变成了美国人。)
然而,这个地区之所以神秘,主要是因为早于阿摩里卡人之前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人们对其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在公元前6000—前4000年之间建造了(如果“建造”一词合适的话)那些惊为天人的卡尔纳克巨石阵,以及海峡对岸的英格兰史前巨石阵。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在一座埃及金字塔建立的两千多年前,他们就不可思议地竖立起数千块尖锐而不规则的石头,其中数百块石头的重量相当于协和广场卢克索方尖碑的数倍,而竖立方尖碑本已要求人们大度地付出启蒙时期的技术手段,以及法兰西共和国浪漫的革命热情。直到如今,笔者在所查阅的文献里也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满意答案,只找到《魔法师的黎明》(O despertar dos mágicos)中的那种奇幻解释,或是弗洛伊德式阳具(phallus)那样的庸俗解释。文献中还有其他类似的解释,但它们都无法令人满意,因为在任何人类杰作面前,关于作品动机和意图的问题都会油然而生。这就是文化与自然的区别:文化作品有含义,可以被解码。卡尔纳克巨石阵是荒谬而神秘的,因为我们业已失去解开赋予其含义的符码之钥。我们不再知道前人是因为什么、出于什么目的而竖立巨石阵,我们不得不“解读它”,因为无法“阅读它”。
数千块岩石遍布于渔民村庄和“贝隆”牡蛎养殖场周围的平原上。村庄名为“卡尔纳克”[Carnac,该名称匪夷所思地暗示埃及的凯尔奈克(Al Karnak),还因其后缀-ac之故,也暗示青铜时代之前的过往]。乍一看来,这些岩石似乎混乱地分布在一片废墟上,有如一座超人类规模的建筑在地震里倒塌的遗迹。然而,观察者会慢慢发现貌似混乱的偶然实则是尤为复杂的秩序。再仔细观察,人们会发现这些岩石不是“天然艺术品”(objets trouvés)或巨型“极简艺术”(minimal art)雕塑,而是不可见栅栏或消失栅栏的组成元素。
当这些超级栅栏在精神上被重建时,数百条纵横交错成高度复杂几何图形的道路便浮现出来。心灵之眼仿佛窥见庞大林荫道和大道的集合,而单独的岩石尽管巨大,在集合里不过是路线的一个元素。在这样的迷宫里,连岩石自身都变成了小矮人,那么我们人类又是什么呢?我们变成了蚂蚁,在为与我们大小不同的巨大生命而建的大道和林荫道上茫然乱窜,试图用我们的精神触角触摸各块岩石,以发现昔日沿着这些大道行走的是怎样的活物。毫无疑问,岩石是由像我们一样的人放置在相应位置上的,尽管我们难以想象他们付出了怎样的艰辛、采用了什么方法。然而,这个建筑规划不可能清晰地诞生于这些人的大脑中。该规划没有满足他们的任何需求,它应该有着另外的起源,应该是建造者脑中的某种“灵光乍现”。在建造卡尔纳克巨石阵时,被忽视的民族,即金字塔建成以前的布列塔尼先民,应该遵循的是无意识的规划,为着不明所以的目的开辟道路。
前文讲述的两段经历交汇于一点:道路规划。围绕这一点的思考迅速回旋成离心圆,因为“规划”和“道路”是富有含义的用语,然而,如果能够仅仅抓住一个方面不放而进行思考(具体而言就是两段经历交汇而出现的问题——人类道路的规划并不一定源自人类),那么这种离心力便可以得到约束。就奥芬山口的公路而言,该规划似乎发生在前人类(pré-humano)时期;就卡尔纳克巨石阵而言,它的建筑规划似乎是超人类的(extra-humano)。如果我们的思维能够聚焦于此,便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道路:一种是通过清晰、明确、刻意精心规划出来的道路,或者想象和编排的道路;另一种则是其他道路。前者的例子是巴西利亚的纪念轴公路和泛亚马孙公路,后者的例子是奥芬山口的公路和卡尔纳克巨石阵。这种区分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自然和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们不禁断言:刻意规划出的道路和其他道路之间的差别在于各自的“路龄”。古老的道路、史前的道路是没有计划和实施方案的,因此在我们这些后世的观察者看来,它们似乎没有经过精心规划。然而,现象无法证实这种断言。穿越欧洲的“盐之路”和“琥珀之路”其古老,却是经过精心规划的项目,而奥芬山口是阿尔卑斯山晚近通道中的一条。于是,想要断言道路越古老,人为参与就越少,因此就越“自然”,是站不住脚的。一条道路的自然性或人工性并不取决于其“路龄”。不可能如此,因为历史不是简单递增的人工化过程,而是周期性地返回其初始自然之源的过程。我们应该尝试以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两种道路的区别。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做:前文提及的四条道路的例子可以被重新分组,分组标准不是它们的规划,而是它们的功能。奥芬山口的公路和泛亚马孙公路用于货运和客运,卡尔纳克巨石阵和纪念轴公路则作为传达信息的象征。当然,分组标准并不是非此即彼。纪念轴公路也是多个政府部门职员开车上班的通勤路,而卡尔纳克巨石阵的林荫道也可以被“德鲁伊”当作通行之路,奥芬山口的公路和泛亚马孙公路同样可以作为某种象征(前者也许是欧洲共同市场的象征,后者当然是“伟大巴西”政治理念的象征)。象征功能在上述道路的其中一组占主导地位,而经济功能则在另一组占主导地位。因此,如果我们从功能标准出发,精心规划的道路和其他道路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更加清楚。
在技术层面,奥芬山口的公路比泛亚马孙公路先进得多,后者的大部分路段都还是土路。在此意义上,奥芬山口的公路更加“人工”,更富有“文化”,没有那么“自然”。然而,泛亚马孙公路对它周边的景观影响更大。它不仅穿过景观,而且还与景观“作对”。泛亚马孙公路吞噬森林,而奥芬山口的公路则凸显森林。在此意义上,泛亚马孙公路反而“人工”得多、“文化”得多:它代表人类规划对于制约人类的自然条件的胜利。作为象征(比如飞向光明未来、晨曦宫和“伟大巴西”的飞机)的纪念轴公路,其符码的外延性比卡尔纳克巨石阵强得多,清晰明确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业已失去卡尔纳克巨石阵符码的解密之钥。卡尔纳克的符码应该向来是晦涩难懂、极富内涵的。因此,在解读纪念轴公路传达的信息时,我们需要采用与解读卡尔纳克巨石阵传达的信息不同的方法:以理智而非直觉来解读。在这个意义上,纪念轴公路比卡尔纳克巨石阵“人工”得多、“文化”得多:它更能代表赋予世界意义的人类意志。于是,一条道路的人工性似乎并不取决于它的规划,也不取决于它的功能,而是取决于它周围的存在主义氛围(clima existencial)。沿着“人工”和“文化”的道路,人类昂首挺胸向自己规划的命运前进。沿着神秘和“自然”的道路,人类追随被忽视或被模糊感知的活物的足迹,向被忽视或被模糊感知的命运前进。或者就像身处卡尔纳克巨石阵那样,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前进路线。既然有这两种类型的道路,便有两种类型的“旅人”(Homo viator)。
然而,如此区分“自然的”和“人工的”道路而引出的“艺术”和“文化”观念,乍一看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按此标准,“文化”会是一个过程,它将某种人类意义刻意强加于名为“自然”的无意义元素集合,而“艺术”则是人类精神将自身意志强行施加于自然时所用的方法。尽管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受到很多人支持,但是它完站不住脚,审视奥芬山口的公路和卡尔纳克巨石阵便可以证明这一点。假如这样的观点令人满意,那么与奥芬山口的公路相比,泛亚马孙公路将会是文化进步,而纪念轴公路则会是比卡尔纳克巨石阵更有意义的艺术品,因为在泛亚马孙公路和纪念轴公路上,人类精神更为清晰地影响高原和森林的自然。实际上,奥芬山口由于(通过展露“现实的视野”)提供强烈的体验而被视为艺术品;卡尔纳克巨石阵则被作为一种文化遗迹而呈现,该文化业已失落、被人遗忘,却与我们的文化一样重要和“正当”。因此,反自然的道路不一定是更“先进”艺术的成果,而文化也不一定就是反自然的。
这两种类型的道路恰恰表明有两种类型的文化,它们发扬着不同的艺术。一种类型的文化致力于规划自然的本质并使其发扬光大,该文化的艺术就是揭示自然本质的方法。奥芬山口的公路和卡尔纳克巨石阵便是这种文化的产物。第二种类型的文化实际上致力于刻意将人类规划强加于自然,使人类精神的本质发扬光大,该文化的艺术则是揭示人类精神本质的方法。泛亚马孙公路和纪念轴公路就是这种文化的产物。然而,这样的划分简化了问题。也许这两种类型的艺术和文化都无法以纯态(estado puro)存在,也从未以纯态存在过。有具体的文化和艺术都是上述两种类型的混合物或综合体。这就使得想要在本体论层面区分多种文化,以及在文化和自然之间建立严格的辩证关系困难重重。
这意味着“旅人”不是可以在规划的道路和神秘的道路之间选择的人,也不是可以刻意或者随意选择的人。恰恰相反,这意味着“旅人”是时而沿着规划的道路行走、时而沿着神秘的道路行走的人。他的行走时而刻意,时而随意,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半刻意半随意地沿着部分是规划、部分是神秘的道路行走。因为一边是奥芬山口的公路和卡尔纳克巨石阵,另一边是泛亚马孙公路和纪念轴公路,它们都是边界情境(“端案例”)。大多数道路就像意大利的太阳高速公路和巴西的杜特拉公路,或者像法国的塞纳路和巴西的迪雷塔街,多多少少都是规划得不完善的道路,因为人类精神无法控制一切。通常来说,我们都是沿着这样的道路行走的。
- 中信出版社
- 中信出版社坚持“我们提供知识,以应对变化的世界”的出版理念,以高端优质的内容服务,多样化的内容展现形式,为读者提供高品质阅读与视听内容,满足大众多样化的知识与文化需求。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