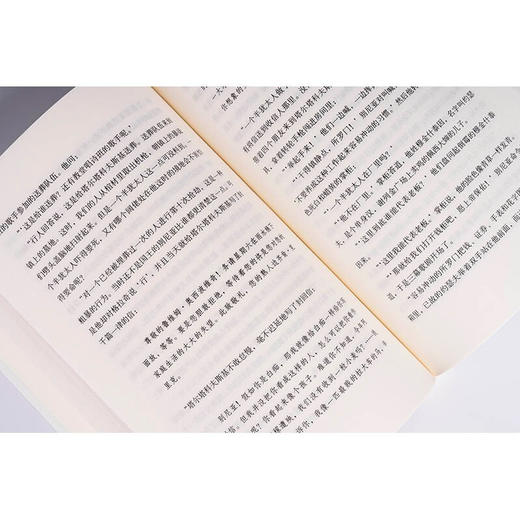商品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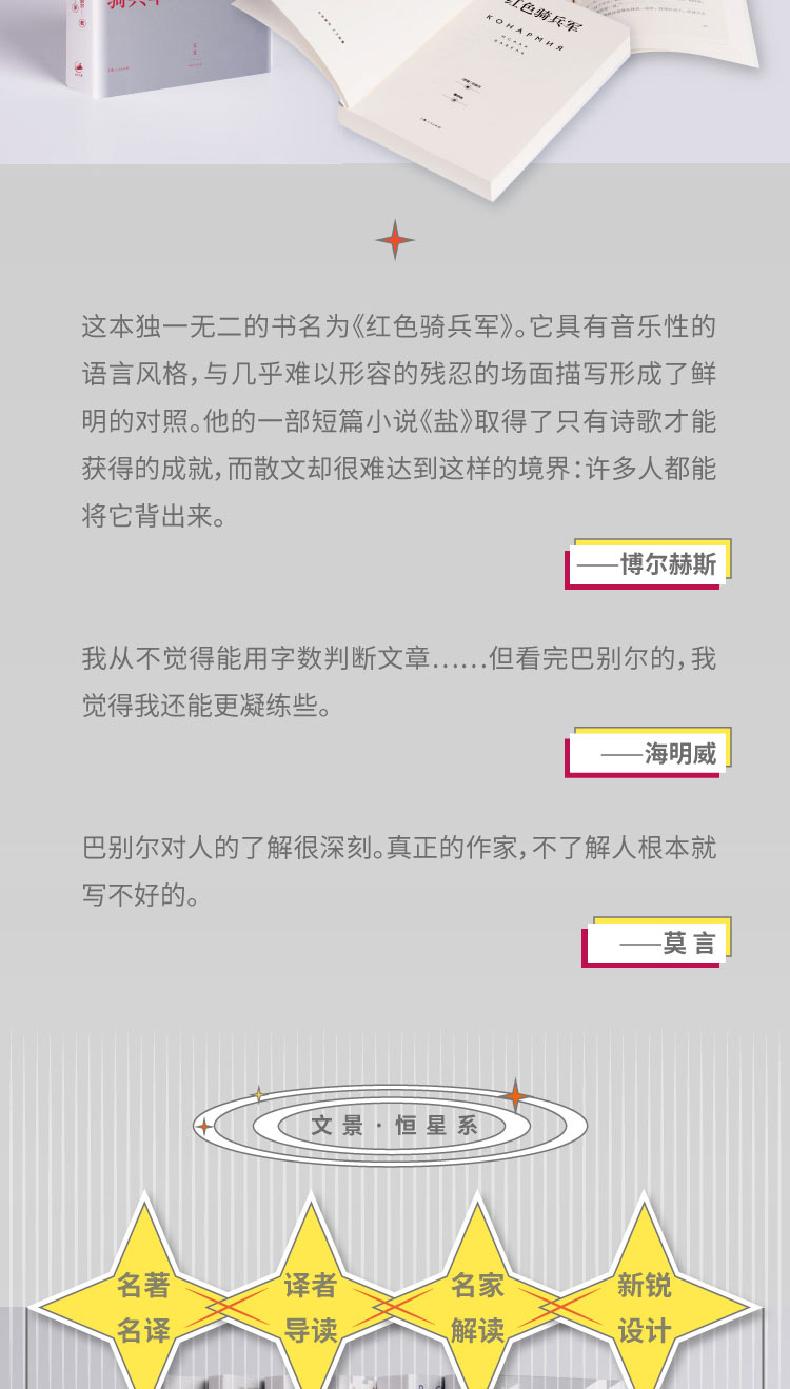



书名: 红色骑兵军
定价: 59
ISBN: 9787208173002
作者: 伊萨克·巴别尔,傅仲选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1
装帧: 平装
开本: 32

❈位居世界佳一百位小说家首的巴别尔代表作。本书采用傅仲选先生译本,其译文贴合巴别尔华丽而敏锐、新鲜而强劲的文风。译者根据巴别尔获得平反后在苏联出版的一个巴别尔作品集翻译,包含原版书中的爱伦堡序言。书中选入《红色骑兵军》《敖德萨的故事》《故事集》,凝集了巴别尔小说艺术的精华。
❈鲁迅、莫言、博尔赫斯、海明威都喜爱的作家!“任何一种钢铁钻进人的心脏都不如恰当地打上句号那样令人胆寒。”巴别尔以此为写作信条,崇尚简约和精确,将极简的现代品质和古典的寓言风格融合在一起,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讲述炽烈的爱情和死亡,在对人生片刻的描写中把握时代全貌!巴别尔擅长描写军队生活及底层民众的悲欢,其书写对象在大与小、远与近、暴力与温柔之间来回穿梭。他撕碎叙事的礼仪,将有细节都糅合进一个姿势、一种心绪、一个震撼人心的启示。

《红色骑兵军》这本书包含《红色骑兵军》、《敖德萨的故事》和《故事集》三个部分,它们展现了作为“世界一百位佳小说家”首的巴别尔的精华之作。这些短篇小说的主题与素材有两大来源,一是军队战斗生活和一个个具有鲜明性格的军中人物,二是作者故乡敖德萨的众多人物(也包括作者自己),特别是底层和贫困民众及其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巴别尔善于捕捉强烈、生动的细节,以一个具体的动作、事件或汇集众多戏剧性要素的画面,来展现复杂的社会面貌、不同群体相互较量的势能和无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导读:非常的小说,非常的小说家江弱水……1
译者前言:任何诋毁攻击都无法消灭真正的艺术……6
伊·埃·巴别尔伊利亚·爱伦堡……11
自传……19
红色骑兵军……21
横渡兹布鲁奇河……23
新城的天主教堂……26
家信……30
军马储备局局长……36
阿波列克先生……39
意大利的太阳……48
格达利……53
我的一只鹅……57
拉比……62
通往布罗德之路……66
闲话敞篷马车……69
多尔古绍夫之死……73
第二旅旅长……78
萨什卡基督……81
帕夫利琴科,马特维·罗季奥内奇传……87
科津墓地……94
普里谢帕……96
一匹马的故事……98
休息地……103
别列斯捷奇科……108
盐……112
傍晩……117
阿丰卡·比达……120
在圣徒瓦连特圣骨匣旁……128
骑兵连长特鲁诺夫……133
两个伊万……142
续一匹马的故事……150
寡妇……152
扎莫希奇……158
叛变……163
切斯尼基村……168
战斗之后……173
歌曲……178
拉比之子……182
阿尔加马克……185
吻……192
敖德萨的故事……199
国王……201
在敖德萨这是怎样发生的……209
父亲……221
柳布卡哥萨克……232
我的鸽子窝的故事—献给马·高尔基……240
初恋……253
你错了,船长!……262
养老院的末日……264
卡尔-扬克利……275
在地下室里……285
觉醒……297
迪·格拉索……306
弗罗伊姆·格拉奇……311
故事集……319
埃利亚·伊萨科维奇和玛加丽塔·普罗科菲耶夫娜……321
妈妈,里玛和阿拉……326
兴奋……338
沙博斯-纳赫穆……342
卡莫号和邵武勉号……351
在女皇王宫度过的一晚……355
耶稣的罪过……358
圣伊帕季的末日……364
线条和色彩……368
道路……372
居伊·德·莫泊桑……380
石油……390
但丁大街……397
审判……404
答复……407
蝴蝶花号轮船……412
苏拉克……426

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苏联作家、短篇小说家。1894年7月13日生于敖德萨。他有名的作品是1926年出版的小说集《红色骑兵军》和1931年出版的小说集《敖德萨故事》。1939年被捕入狱,1940年被枪杀,1954年被苏联当局平反。1986年,《欧洲人》杂志选出世界一百位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一。

一匹马的故事
有一天,我们的师长萨维茨基牵走了一骑兵连连长赫列布尼科夫的一匹白牡马。这匹马看上去滚圆发胖,实际上是虚胖,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笨重迟钝。赫列布尼科夫换得了一匹步子平稳的黑色良种母马。但是他虐待这匹母马,渴望报仇,等待时机,而且终于等到了。
七月打了几次败仗之后,萨维茨基被免了职,并被送往后方预备队,这时赫列布尼科夫给军部递了个呈文,请求把马归还给他。军参谋长在呈文上批示,“所述公马还归原主”,于是赫列布尼科夫兴高采烈地赶了一百俄里,去找那时住在拉济维洛夫城的萨维茨基。这是一座遭到严重破坏的小城,像一个衣衫破烂的女叫花子。这位被免职的师长独自一人住在那里,各级司令部的那帮马屁精再也认不得他了。那帮马屁精在军长的微笑中钓到烤鸡,他们这伙势利眼不再理睬赫赫有名的师长了。
他身上洒了香水,很像彼得大帝。失宠之后,便和一位哥萨克女子帕芙拉住在一起。这女子连同二十匹良种马是他从一个犹太军官手里夺过来的,我们都把这二十匹马当成是他个人的财产。他院子里的太阳火辣辣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他院子里的小马驹拼命地吮吸母马的奶,饲养员们汗流浃背地在旧风车上筛燕麦。怀着被伤害的心情和渴望复仇的愿望,赫列布尼科夫径直朝栅栏围住的院子走去。
“您认得我吗?”他问躺在干草上的萨维茨基。
“我似乎见过你。”萨维茨基答道,同时打了个哈欠。
“那就请看参谋长的批示,”赫列布尼科夫语气强硬地说,“请您,预备队的同志,正眼看着我……”
“可以。”萨维茨基心平气和地嘟囔道。他接过文件,读了很久,随后突然叫唤在遮阳下阴凉处梳头的哥萨克女子。
“帕芙拉,”他说,“从一大早起,谢天谢地,你就在梳头……去把茶炊生好吧……”
哥萨克女子放下梳子,双手拢住头发,把它甩到背后。
“您今天怎么啦,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老找碴儿,”她懒洋洋地说道,同时傲然一笑,“不是这不合您的意,就是那……”
她走到师长跟前,胸脯架在两只高筒靴上,两个奶头颤动着,像袋子里的两只小兔子。
“老找碴儿。”女子兴高采烈地重复说,并给师长扣上胸前的衬衫纽扣。
“不是这不合我意,就是那不合我意。”师长笑了起来,他起身接住帕夫林娜顺从的肩膀,突然把苍白的脸转向赫列布尼科夫。
“我还没有死,赫列布尼科夫,”他说,同时和哥萨克女子搂抱在一起,“我的腿还能走路,我的马还能奔跑,我的手还能捉到你,我的炮还在我身体附近发热……”
他掏出挂在他光肚皮上的左轮手枪,走到一骑兵连连长跟前。
后者脚跟一旋,转过身去,马刺吱吱地响了起来,他像一个拿着急件的传令兵走出院子,又跑了一百俄里去找参谋长。这次参谋长却把赫列布尼科夫赶了出去。
“你的问题,连长,已经解决了,”参谋长说,“马我已批还给你了,没有你麻烦事我也够多的了……”
他不再听赫列布尼科夫说话,干脆把这个离队的连长遣送回一骑兵连。赫列布尼科夫离开连队整整一个星期。在这期间,我们被赶到杜宾斯基森林的一处驻扎地。我们在那里搭了帐篷,过得挺好。我记得,赫列布尼科夫是在十二号,即星期天早晨回来的。他向我要了一刀[1]多纸和墨水。哥萨克们给他刨平一个树墩,他把左轮手枪和纸放在树墩上,一直写到傍晚,糟蹋了好多张纸。
“你可真像卡尔·马克思,”傍晚时骑兵连政委问他,“你在写什么?算了吧。”
“我在对照誓言写各种想法。”赫列布尼科夫回答说,并把一份退出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声明书递给政委。声明书说:
我认为,共产党是为了快乐和坚定的真理而建立的,应注意到小事情。现在我谈一匹白牡马的事。这匹马是我从一伙异常反动的农民那里夺来的,十分瘦弱,许多同志肆无忌惮地嘲笑它的模样,但是我顶住了这类尖刻的讥笑,为了共同的事业咬紧牙关,把马调养得十分称心如意。因为,同志们,我是一个喜欢灰马的人,肯把从帝国主义和国内战争中所剩下来的有限精力花在它们身上。而这些马善解人意,我也能感觉到这些不会说话的动物的需要和要求。但是不公正换给我的黑母马我不需要,我猜不透它,也讨厌它。这一点同志们都能证明,但愿事情别发展到不幸的地步。可是,党却不能根据批文把我心爱的东西归还给我,因此我别无他法,只好含着眼泪写下这份声明书,尽管战士不兴流眼泪,但是我的泪水却流个不停,似万箭穿心,刺得心里流血……
以上就是赫列布尼科夫声明书的内容,另外还有许多话略去没有抄录。他整整写了一天,声明书很长。我和政委折腾了将近一小时,才总算弄清了它的意思。
“真是个傻瓜,”政委说,并把声明书撕掉,“晚饭后来一下,我们谈谈。”
“我不要和你谈,”赫列布尼科夫回答说,他哆嗦了一下,“你耍弄我,政委。”
他垂着两只手站在那里,浑身发抖,一动不动,两只眼向四周张望,仿佛在打量从哪儿逃跑。政委走到他跟前,但没有看住。赫列布尼科夫猛力一冲,拼命跑了起来。
“耍弄我!”他疯狂地叫了起来。他爬上树墩,又是撕身上的衣服,又是抓胸脯。
“打吧,萨维茨基,”他跌倒在地上叫道,“你一枪打死我吧!”
我们把他拖到帐篷里,哥萨克们也来帮忙。我们给他煮好茶,卷好烟。他抽着烟,但仍一直发抖。我们的连长直到傍晚时才安静下来。他不再提那份荒唐的声明书,不过一周后去了罗夫诺,经过医务委员会的身体检查,作为一个六次负伤的废而复员了。
就这样,我们失去了赫列布尼科夫。我为此十分悲痛,因为赫列布尼科夫是一个温和的人,性格像我。骑兵连里只他一人有茶炊。在无战事的日子里,我们一块喝热茶。我们有共同的嗜好。我们俩人都把世界看成是五月的草地,是妇女在其上嬉戏、马儿在其上奔驰的草地。
别列斯捷奇科
我们从霍京出发开往别列斯捷奇科。战士们坐在高高的马鞍上打瞌睡。歌声低微,宛如行将干涸的小溪发出的潺潺声。在千年的古坟丘群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具具可怕的尸体。穿白衬衫的庄稼汉们向我们脱帽致敬。师长帕夫利琴科的斗篷在司令部上空飘动,像一面阴森的旗帜。他的绒毛围巾帽搭在斗篷上,弯马刀挂在腰间。
我们驰过一个个哥萨克坟丘和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塔楼。从墓石后面爬出一位老大爷,他弹着班杜拉琴,用童声唱了一首歌颂哥萨克昔日的荣誉的歌。我们默默地听着他唱,然后打开军旗,在响亮的进行曲中冲进了别列斯捷奇科。居民们用铁棍闩上栅栏门,于是寂静,无比威严的寂静登上了这个小城镇的宝座。
我的住处安顿在一个受尽寡居之苦的棕红头发的寡妇家。我洗干净旅途的尘土后走上大街。柱子上贴着布告说,师政委维诺格拉多夫晚上将做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就在我的窗下,几个哥萨克在处决一名搞间谍活动的银胡子犹太老头。老头子尖叫着、挣扎着。这时机枪队的库德里亚捉住他的头,把它夹到腋下。这个犹太人不吱声了,两条腿叉了开来。库德里亚右手拔出匕首,小心翼翼地杀着老头,不让血溅得到处都是。随后他敲了敲关着的窗框。
“谁要是感兴趣,”他说,“就来收尸吧。这可没有任何限制……”
说罢哥萨克们拐过街角走了。我跟在他们后面,在别列斯捷奇科逛了起来。这里的居民多为犹太人,而在郊区则住着俄罗斯小市民——皮革商。俄罗斯人住在带绿色栅栏门的白色房子里,居住的环境清洁。这些小市民不喝伏特加,而是喝啤酒或蜂蜜,在房前小花园里种烟草,像加里西亚农民那样用弯弯的长烟袋抽烟。
风习在别列斯捷奇科已经淡化,但在这里依然经久不变。已逾三百年的枝芽又在沃伦的古老、暖和的腐殖土上长出了新绿。犹太人在这里用生财之线把俄罗斯的庄稼汉和波兰的地主、捷克的移民和罗兹的工厂联系起来。这是些走私贩子,国境线上的亡命之徒,而且几乎总是为信仰而大打出手的好斗分子。哈西德教派令人窒息地左右了这群由小酒店主人、叫卖小贩和经纪人构成的终日忙碌的居民。穿宽大外衣的男孩们仍然踏着古老的路前往哈西德教派的小学,而老太婆们照旧把儿媳妇带到长老那里苦苦地祈求多多生子。
这里的犹太人居住在刷成白色或淡蓝色的宽敞房子里。这种建筑式样的传统缺陷已存在好多世纪了。在房子后面还搭着两层或者三层板棚,棚内从来不见阳光。这些异常昏暗的板棚相当于我们家乡的棚舍。有暗道通往地窖和马厩。战争期间,人们在这些地下走廊里可以躲过子弹和抢劫。日积月累,这里积存了许多垃圾和人畜粪便。忧郁和恐惧又为地下走廊增添了刺鼻的臭气和粪便的腐酸臭味。
别列斯捷奇科未受触动地发臭一直发到现在,有的人都散发出腐烂的鲱鱼气味。这座小城发着臭味等待新时代的到来,可是遍及城市各处的不是人,而是褪了色的边境不幸事件的示意图。天黑前它们已使我厌倦了。我出了城,登上山坡,钻进拉齐博尔斯基伯爵家空空荡荡的城堡。这个家族不久前还主宰着别列斯捷奇科。
落日柔和的余晖给城堡前的草地染上一层幽蓝。像蜥蜴那样青绿的月亮升起在水塘上面。透过窗户,我看到了拉齐博尔斯基伯爵家的领地——覆盖着暮色波纹绸带的草地和葎草种
植场。
城堡里过去住着疯癫的九十岁的伯爵夫人和她的儿子。她恨儿子没有给日益衰落的家族增添继承人,因此,——庄稼汉们告诉我——常用马鞭抽打儿子。
下面的场地上在举行群众大会。来参加大会的有农民、犹太人和郊区的皮革商。维诺格拉多夫充满激情的声音和他的马刺的声音在他们头顶上空激荡。他在讲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而我却沿着围墙闲步,围墙上绘着一群眼睛被刺破的自然神跳古老的轮舞的图像。后来在拐角处,在踩脏的地面上,我发现了一片发黄的信纸。信纸上墨水的颜色完全褪掉了,上面写着:
别列斯捷奇科,一八二〇年,波尔,我亲爱的,传说拿破仑皇帝驾崩了,这是真的吗?我感觉良好,分娩顺利,我们的小英雄快满七周了……
在下面,师政委的声音还没有停息。他热情地向那些疑惑不解的小市民和被抢光的犹太人说明:
“你们就是政权。这里的一切都是你们的。老爷没有了。我正在着手准备革命委员会的选举……”
盐
亲爱的编辑同志。我想向您讲讲那些对我们有害的妇女的不自觉的行为。希望你们在访问做有标记的内战前线时,不要错过积习很深的法斯托夫车站。它在非常遥远的地方,位于某个国家,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我当然去过那里,在那里喝过家酿啤酒,不过只沾湿了胡子,并没有灌进嘴里。关于上面提到的那个车站,说起来可就话长了。但是正如我们那里有句俗话说的,眼见为实,所以,我只把我亲眼看到的一些事情讲给您听。
七天前的一个宁静、美好的夜晚,我们骑兵军使用多年的列车停在那里,车上坐满战士。我们大家都渴望干一番共同的事业,这次的目的地是别尔季切夫。可是我们发现,列车怎么也不开动。我们的加夫里尔卡没有转动。干吗要停车不动呢?停车不动对于共同事业来说的确是非同小可的,因为来了一群背袋贩子,这是些狠毒的敌人,其中还有不可估计的女人的力量,他们对铁路当局耍无赖。这些狠毒的敌人,毫无顾忌地抓住扶手,在铁皮棚顶上乱跑,踩得棚顶嘭嘭响,搅得人心烦,每个人手里都有颇有名气的盐,一袋达五普特重。但背袋贩子的资本并没有猖狂多久。战士们发扬主动精神,一个接一个地从车厢里爬出来,让受凌辱的铁路员工当局缓了一口气。只有妇女带着袋子留在周围。出于怜悯,战士们把一些妇女安置在取暖货车上,有的妇女则没有安置。我们第二排的车厢里也来了两个少女,一次铃声响过之后,一个体面的妇女抱着一个娃娃走到我们跟前说:
“让我上车吧,亲爱的哥萨克们!整个战争期间,我手里抱着个吃奶的娃娃跑火车站受罪,现在想去看望丈夫。但是由于乘火车难,怎么也没有去成。难道我不配乘你们哥萨克的车?”
“且慢,大嫂,”我对她说,“是否让你们上车,得看全排是否同意。”接着我转向全排,告诉他们说,这位体面的妇女请求让她搭车去她丈夫工作的地方,她确实抱着个娃娃。我问他们有什么意见——让她搭车呢或是不让?
“让她搭车,”小伙子们嚷道,“跟我们待过后,她就不会想要丈夫了!……”
“不行,”我相当有礼貌地对小伙子们说,“我向你们,向全排鞠躬致敬。不过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你们竟说出如此轻佻的话。小伙子们,请回想一下你们的生活,你们也曾经是母亲怀抱中的娃娃,这样你们就会感到,你们这样说似乎不恰当……”
于是,哥萨克们交头接耳说了一阵,认为我巴尔马舍夫的话在理,便让那个妇女进了车厢,她怀着感激的心情钻进了车厢。战士们被我的真理所打动,抢着搀扶她,争先恐后地说:
“大嫂,请坐,到这个角落里来,像妈妈们惯常那样逗弄您的娃娃吧。在这个角落里,谁也不会伤害您的,您会像您所希望的那样,平平安安地去到您丈夫的身边。我们也相信您有良心,会培养出我们的接班人。因为,您瞧,老的老,小的小。我们吃过苦,大嫂,不管是现役军人还是超役军人,都挨过饿,受过冻。您请坐在这里,大嫂,别担心……”
铃声响了第三遍,列车开动了。美好的夜幕笼罩着大地。星星宛如盏盏油灯挂在夜幕上。战士们想起了库班的夜晚和绿色的库班的星星。思绪似鸟儿般飞翔起来。车轮发出哐啷啷、哐啷啷的声音……
时光流逝,黑夜被换下岗来,红色鼓手们在自己的红鼓上打起了点名鼓。这时哥萨克们见我干坐着不睡觉,百无聊赖,就走到我跟前。
“巴尔马舍夫,”哥萨克们对我说,“你干吗这么闷闷不乐,干坐着不睡觉?”
“我向你们,战士们,深深地鞠躬,并请你们多多原谅,请允许我和这个女公民说两句话……”
说罢,我浑身哆嗦着从卧铺上爬起来,睡意也随之而跑掉了,就像一只狼见到一群凶狠的公狗跑掉一样。我走到她跟前,从她手里把娃娃抱过来,扯掉娃娃身上的包布,原来包布里包着一大袋盐。
“好一个有趣的娃娃,同志们,不要吃奶,不会撒尿,也不打扰人们睡觉……”
“请原谅,亲爱的哥萨克们,”妇女十分冷静地插话说,“骗人的不是我,而是我身上的邪恶……”
“巴尔马舍夫原谅你的邪恶,”我回答妇人说,“对巴尔马舍夫说来,它算不了什么,巴尔马舍夫怎么买的也就怎么卖。但是大嫂,你看看哥萨克们,他们可把你奉为共和国劳动人民的母亲。你看看这两个姑娘,现在还在哭,今晚她们遭受了多大的损害啊。你再看看麦浪滚滚的库班河一带我们的妻子,丈夫不在家,她们耗尽了女人的力气。而那些也是单身汉的人,他们出于罪恶的天性,强奸撞进他们生活中的姑娘……但却没有动你,尽管应该动你这个没有道德的人。你再看看俄罗斯,她在痛苦呻吟……”
而她却对我说:
“我失掉的是自己的盐,我不怕真理。您没有替俄罗斯着想,您在拯救犹太人……”
“现在不是谈犹太人,有害的女公民。犹太人与此无关。而你们,卑鄙的女公民,比那个挥舞锋利的军刀、骑在价值上千卢布的马上威胁我们的白军将军更加反革命……他是公开的,那个白匪将军,劳动人民都琢磨着干掉他,而你们,数也数不清的女公民,和你们那些不吃不喝、不拉屎不拉尿的娃娃们,是隐秘的,像一窝跳蚤,在暗中咬啊,咬啊,咬啊……”
- 中信书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美好的思想和生活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