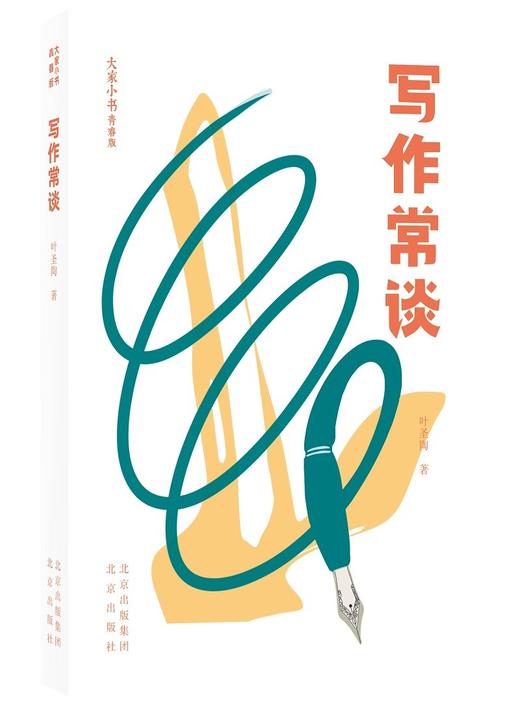商品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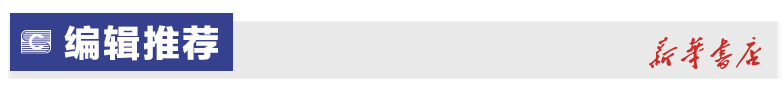
叶圣陶先生当过语文老师,当过编辑,编杂志、编书籍、编教科书,可以说叶老一生都在与文字打交道。然而在叶老眼里,“写作并不是了不起的事,是人人办得到的事”,因此他乐于普及写作知识,提倡人人写作。相信当你读毕叶老的经验之谈,能够打消对写作的顾虑,甚至开始享受写作带来的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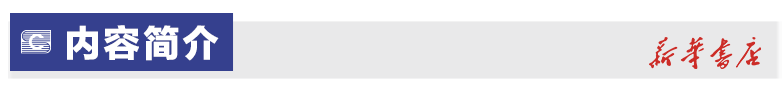
本书遴选叶圣陶先生谈写作的文章二十余篇,其中绝大多数写于上世纪前叶。作者以其深厚的生活和文学功底现身说法,从日常阅读、生活经验的点滴积累以及人生观、世界观的养成,到叙事、写景、抒情、反衬等技巧的训练,一篇文章如何开头结尾,如何运用想象与联想,如何锤炼语言和训练语感,如何从前人及现代经典作家鲁迅、徐志摩、朱自清、顾颉刚等人的笔下汲取营养,乃至最终形成个人的文风及艺术性,如此等等,叶老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提高的方案。正如书中所言,文章写作亦如人生修炼,一蹴而就的秘诀是没有的;倘若认定目标,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则又是人人都可办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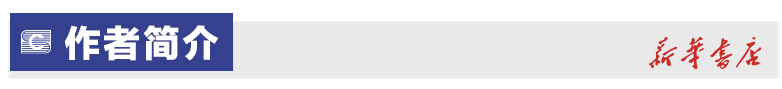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苏州人,作家、语文学家和教育家。早年在乡镇小学任教,1916年进入尚公学校执教,着手编写国文教材;后加入北京大学春潮社,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文学研究会,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小说、诗歌和评论文章,有童话《稻草人》和长篇小说《倪焕之》等。1949年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叶老一生从事语文教育和教材编写工作,是著名的文章家和文体鉴赏家,他与夏丏尊、陈望道、朱自清等有关阅读和写作技法的探讨曾在青少年读者中间产生广泛影响。叶老为文素以平易谨严著称,说理透辟,语言凝练,可以说每篇皆是现代语体的典范之作。

略谈学习国文
写话
写文章跟说话
漫谈写作
一、用笔说话
二、照着话写
三、写加了工的话
四、写作要有中心
五、用全国人通用的话写
和教师谈写作
一、想清楚然后写
二、修改是怎么一回事
三、把稿子念几遍
四、平时的积累
五、写东西有所为
六、准确;鲜明;生动
七、写什么
八、挑能写的题目写
学习写作的方法
拿起笔来之前
开头和结尾
谈叙事
木炭习作跟短小文字
临摹和写生
依靠口耳
关于使用语言
学点语法
谈文章的修改
从梦说起
要做杂家
文艺谈
我如果是一个作者
第一口的蜜
文艺作品的鉴赏
一 要认真阅读
二 驱遣我们的想象
三 训练语感
四 不妨听听别人的话
揣摩
杂谈我的写作
写话
“作文”,现在有的语文老师改称“写话”。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
其实,三十年前,大家放弃文言改写白话文,目标就在写话。不过当时没有经过好好讨论,大家在实践上又没有多多注意,以致三十年过去了,还没有做到真正的写话。
写话是为了求浅近,求通俗吗?
如果说写话是为了求浅近,那就必须承认咱们说的话只能表达一些浅近的意思,而高深的意思得用另外一套语言来表达,例如文言。实际上随你怎样高深的意思都可以用话说出来,只要你想得清楚,说得明白。所以写话跟意思的浅近高深没有关系,好比写文言跟意思的浅近高深没有关系一样。
至于通俗,那是当然的效果。你写的是大家说惯听惯的话,就读者的范围说,当然比较广。
那么写话是为什么呢?
写话是要用现代的活的语言写文章,不用古代的书面的语言写文章——是要用一套更好使的、更有效的语言。用现代的活的语言,只要会写字,能说就能写。写出来又最亲切。
写话是要写成的文章句句上口,在纸面上是一篇文章,照着念出来就是一番话。上口,这是个必要条件。上不得口,还能算话吗?通篇上口的文章不但可以念,而且可以听,听起来跟看起来念起来一样清楚明白,不发生误会。
有人说,话是话,文章是文章,难道一点距离也没有?距离是有的。话不免啰嗦,文章可要干净。话说错了只好重说,文章写错了可以修改。说话可以靠身势跟面部表情的帮助,文章可以没有这种帮助。这些都是话跟文章的距离。假如有一个人,说话一向很精,又干净又不说错,也不用靠身势跟面部表情的帮助,单凭说话就能够通情达意,那么照他的话记下来就是文章,他的话跟文章没有距离。不如他的人呢,就有距离,写文章就得努力消除这种距离。可是距离消除之后,并不是写成另外一套语言,他的文章还是话,不过是比平常说得更精的话。
又有人说,什么语言都上得来口,只要你去念,辞赋体的语言像《离骚》,人工制造的语言像骈文,不是都念得出来吗?这样问的人显然误会了。所谓上口,并不是说照文章逐字逐句念出来,是说念出来跟咱们平常说话没有什么差别,非常顺,叫听的人听起来没有什么障碍,好像听平常说话一样。这得就两项来检查:一项是语言的材料——语汇,一项是语言的组织形式——语法。这两项跟现代的活的语言一致,就上口,不然就不上口。我随便翻看一本小册子,看见这样的语句,是讲美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支配的几种刊物的:“……在不重要的地方,大资产阶级让他们发点牢骚,点缀点‘民主’风光,在重要的地方,则用不登广告……的办法,使他们就范。”不说旁的,单说一个“则”,就不是现代语言的语汇,是上不得口,说不来的。就在那本小册子里,又看见这样的语句,是讲美国司法界的黑暗的:“有好多人,未等到释放,便冤死狱中。”不说旁的,单说按照现代语言的组织形式,“冤死”跟“狱中”中间得加个“在”,说成“冤死狱中”是文言的组织形式,不是现代语言的组织形式,是上不得口,说不来的。
或许有人想,这样说未免太机械了,语言是发展的,在现代的语言里来个“则”,来个“冤死狱中”,只要大家通用,约定俗成,正是语言的发展。我想所谓语言的发展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实际生活里有那样一种需要,可是现代的语言里没有那样一种说法,只好向古代的语言讨救兵,这就来了个“咱们得好好酝酿一下”,来了个“以某某为首”。“酝酿”本来是个古代语言里的语汇,“以……为……”本来是文言的组织形式,现在参加到现代的语言里来了,说起来也顺,听起来也清。这是一种发展情形。“则”跟“冤死狱中”可不能够同这个相提并论。现在在文章里用“则”的人很多,但是说话谁也不说“则”,可见这个“则”上不得口,又可见非“则”不可的情形是没有的。“冤死狱中”如果可以承认它是现代的语言组织形式,那么咱们也得承认“养病医院里”“被压迫帝国主义势力之下”是现代的语言组织形式,但是谁也知道“养病”跟“被压迫”底下非加个“在”不可,不然就不成话。
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想。既然“则”可以用,那么该说“了”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写成“矣”吗?该说“所以”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写成“是故”吗?诸如此类,不用现代语言的语汇也可以写话了。既然“冤死狱中”可以用,那么该说“没有知道这回事”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写成“未可知”吗?该说“难道是这样吗”的地方不是也可以写成“岂其然乎”吗?诸如此类,不照现代的语言组织形式也可以写话了。如果这样漫无限制,咱们就会发现自己回到三十年以前去了,咱们写的原来是文言。所以限制是不能没有的,哪一些是现代语言的词汇跟组织形式,哪一些不是,是不能不辨的。不然,写成的文章上不得口,不像现代的语言,那是当然的事。咱们看《镜花缘》,看到淑士国里那些人物的对话觉得滑稽,忍不住要笑,就因为他们硬把上不得口的语言当话说。咱们既要写话,不该竭力避免做淑士国的人物吗?
不愿意做淑士国的人物,最有效的办法是养成好的语言习惯。语言习惯好,写起文章来也错不到哪儿去,只要你不做作,不把写文章看成稀奇古怪的另外一套。
把写成的文章念一遍是个好办法,可以检查是不是通篇上口。不要把它当文章念,要把它当话说,看说下去有没有不上口的地方,有没有违反现代语言规律的地方,如果它不是写在纸面的文章,是你口头说的话,是不是也那样说。
还可以换个立场,站在听话的人的立场,你自己听听,那样一番话是不是句句听得清,是不是没有一点儿障碍,是不是不发生看了淑士国里那些人物的对话那样的感觉。
还有个检查的办法。你不防想一想,你那篇文章如果不用汉字写,用拼音文字写,成不成。有人说,咱们还在用汉字,还没有用拼音文字,所以做不到真正的写话。这个话也有道理。但是,为了检查写话,就把汉字当拼音文字用,也不见得不可以。一个语词有一个或者几个音,尽可以按着音写上适当的汉字。这样把汉字当拼音文字用,你对语言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你会发觉有些话绝对不应该那样说,有些话只能够写在纸面,不能够放到口里。经过这样的检查,再加上修正,距离真正的写话就不远了。
(原载1951年1月10日《新观察》第二卷第一期)
写作是人人办得到的事
叶小沫
我的爷爷叶圣陶先生曾经说:我当过教师也做过编辑,当编辑的年头比当教师长,如果别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说是编辑。爷爷当教师的时候教的主要是语文,当编辑的时候为青少年编杂志、编书籍、编教科书,比较起来其中涉及语文知识方面的相对要多一些,因此无论是在做教师的时候,还是在做编辑的时候,无论是讲课,还是写文章,写作都是爷爷经常要提起的一个重要话题。最近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系列,把爷爷一些有关谈写作的文章编成一集,书名定为《写作常谈》,我觉得这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
写作看起来是个挺大的题目。从古至今,有关写作的专著从来就不少。那些专著里,写作还是个让很多人都望而生畏的词儿,以为那是只有文人才能做的事儿,轻易不敢动笔。爷爷偏不把写作看成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他的教学经验和编辑经验告诉他,在和同学,和老师,和编辑出版界同人说写作的时候,最先要打消的就是大家对写作的顾虑。爷爷说:“这是一道关,学习写作的人首先要打破它,打破它实在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它只是思想上的一个小疙瘩。咱们只要在思想上认清,小疙瘩就解除了,关就打破了。”至于怎么打破它,爷爷说:“习作的目的不在学习写文章,预备做文人。”因为,“无论什么人都生活在人群中间,随时有把意思情感发表出来的需要。发表可以用口,可以用笔,比较起来,用笔的效果更大。因此,人人都要学习用笔发表,人人都要习作”,而且,“写作并不是了不起的事,是人人办得到的事”。
都说爷爷是语文大家,这位语文大家在和大家谈写作的时候,却写了很多小文章,说的也大多是一些极平常的话。咱们不妨选一些文章的题目来看看。为了让大家放下包袱,他写了“写作是极平常的事”;为了教大家怎么开始动笔,他写了“写文章跟说话”“写话”“照着话写”“写加了工的话”;为的是让大家知道,写作无非就是把要说的话写下来。至于应该怎么写,他又告诉大家“写作要有中心”,在“拿起笔来之前”,要“想清楚后再写”。然后告诉大家怎么“开头和结尾”,怎么“安排句子”,文字要“准确;鲜明;生动”。在你按照他教的步骤把文章写好了后,他还要你“把稿子念几遍”,告诉你“修改是怎么回事”,和你说说“文章的修改”。上面提到的这些文章,只是爷爷和初学者谈写作中的几篇,少则几百字,多也不过千把字,他把道理和大家说得清清楚楚,把方法和大家讲得明明白白。只要照着去做,多多练习,相信就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的人,也会渐渐有了自信,慢慢地学会写作,而这些文章中所说的,就是这位语文大家一生都在做的事情:普及写作知识,提倡人人写作。
关于写作,爷爷写的当然不止我这里说的这些短文,在父亲叶至善先生编的《叶圣陶集》的文学评论卷里,就收录和集成了第九卷《论创作》《文艺丛谈》《时挂心间》,第十卷《揣摩集》《读后集》《文章例话》等。其实爷爷写的还远远不止这些,他写过《这样写作》,和外公夏丏尊先生一起合作过《文章讲话》《文化七十二讲》《文心》,这些书至今都被语文老师看作是经典的必读书。《文心》这本书是夏丏尊和叶圣陶两位老人家专门为中学生写的,他们用孩子乐于接受的形式,用三十二个故事述说了关于写作的基本知识,这种教授作文的方法在当年是一个创举,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一版再版,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突破它。我上面提到的这几本书,大多是爷爷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的,如果哪位朋友在看了这本《写作常谈》之后,还想了解爷爷关于写作的更多论述,市场上应该还可以买得到,因为这些年来这些书没有断过档,一直有各出版社再版。
我出生在一个编辑家庭,爷爷做了七十三年的编辑,父亲做编辑也有六十一个年头。他们父子两个对编辑工作的热爱、执着和精益求精,称得上是为编辑的一生,编辑就是他们的生命。说来有些奇怪,生在编辑家庭,自己也是编辑,面对着每天都要接触的文字,我却满怀着敬畏。比如“写作”和“作品”这两个词儿,在我心里就有千斤重。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庄严很郑重的事情,更不是随便一篇什么文字,都可以拿“作品”来冠名的。
父辈至善、至美和至诚他们三兄妹,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和爷爷学习写作文,后来集结出版了《花萼》和《三叶》两本散文集。父亲在为这两本散文集写的序里,把他们的练习称为“习作”,把他们的书称为“作文本”,称为“集子”,却没有说过他们是在写作,也没有说过那些散文是他们的作品。看起来那个时候父亲就非常谨慎,在他看来,“写作”和“作品”这样的词儿,也不是可以随便用来冠以自己的文字的。尽管父亲在为别人编书之余,见缝插针地写过不少科普文章,出过几本散文集,写过四十几万字的爷爷的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其中的许多文字真的非常独到,有自己的风格,好像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作品了,可是他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说过“我在写作”,或者“我的作品”这样的话。父亲的谦虚谨慎是发自内心的,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从小时候起,印在我脑子里的就是两个抹不去的背影:一个是爷爷,一个是父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无论什么时候走进他们各自的书房,都会看到他们趴在自己的书桌前,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在修改稿件或书写文字。爷爷和父亲房间里的书桌都面对着窗,阳光常常洒满书桌,暖暖的可人爱,以致爷爷晚年给《文汇报》写的一系列有关教育的随笔,起名就叫“晴窗随笔”。不同的是爷爷的书桌永远干净整齐,除了台灯,纸墨笔砚各就各位,伸手可得。在爷爷的面前,除了要处理的文章,一件多余的东西都没有;父亲的书桌永远乱七八糟,上面堆满了书籍和稿件,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他心里有数,你看着乱,可不能帮他收拾,一动他就找不到了,还会和你发脾气。有一点爷儿俩完全相同,那就是都太投入了,就像爷爷自己写的两句诗,“此际神完固,外物归冥邈”,意思是说,因为精神太集中,外界的事情离我已经很远很远了。尤其是到了晚年,爷爷的听力越来越差,我怕惊到他,只要有事,都会小心翼翼地走到他面前,轻声地招呼他。就是这样小心,有时候还是会吓到他,他惊愕地抬起头望着我的眼神,总会让我愧疚不已。后来每次来到爷爷的房前,我都会收住脚步,探出身子看看,如果看到他在做事,就轻轻地退身出来,不去打扰他。我告诉自己:他在写作。
出版社邀我为我爷爷的这本书写个导读,我自知无论从那个方面说,我都没有资格担当这个重任。这里写下的是我的一些随想,只是“写在前面的话”,希望对读者阅读这本书,对读者认识写作、从事写作能有所帮助。
2019年6月18日深圳
- 新华一城书集 (微信公众号认证)
- 上海新华书店官方微信书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