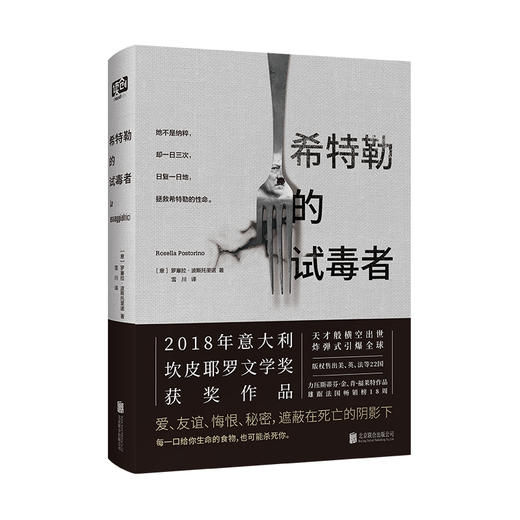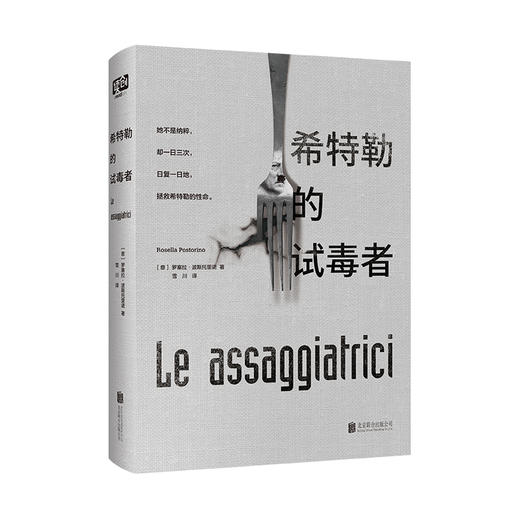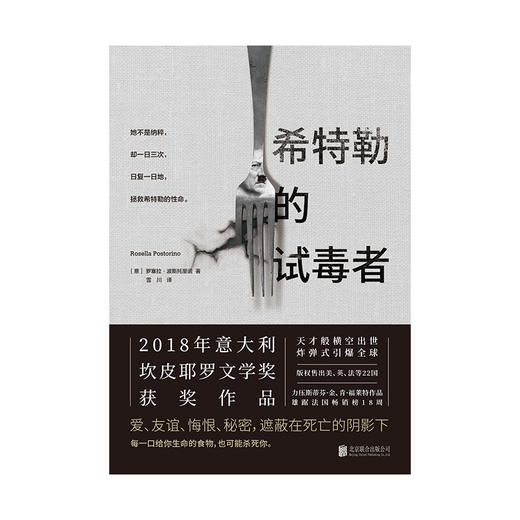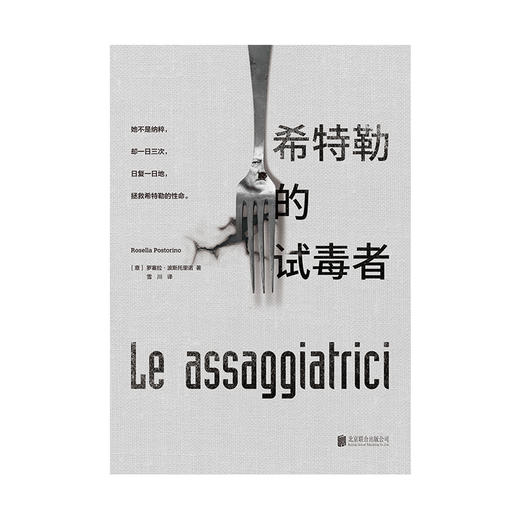商品详情

作者简介:
罗塞拉·波斯托里诺,1978年出生,意大利天才女作家。
2009年出版小说《我们失去了上帝的夏天》,获得当年的Benedetto Croce大奖和评委会特别奖。《希特勒的试毒者》一经出版,便引爆全球,雄踞法国畅销榜18周,荣获2018年意大利坎皮耶罗文学奖。
内容简介:
1943年,罗莎跟随丈夫来到他生活的小村庄,恰逢希特勒需要食物试毒者,以防止被谋害。在村长的推荐下,她成为了十多个食物试毒者中的一名。在封闭的环境和狱卒的监视下,十名年轻女子形成了联盟,秘密契约和友谊交织在一起。
作者由希特勒的最后一位试毒员玛格特·沃尔克的真实故事得到启发,讲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她用有力的笔触探寻了人类灵魂的复杂性,一段暴力又脆弱的历史,以及人在强压下强烈的求生欲望。
编辑推荐:
◎2018年坎皮耶罗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经问世便引爆全球,意大利国内狂销20万册。
作者作品首次走出欧洲,打开英语文学市场。引起国际关注,入选多项文学奖项终选名单。
获得《纽约时报书评》《嘉人》《赫芬顿邮报》等多家媒体重磅推荐,版权销售至22国,卢米埃重金购得电影版权。
◎在死亡的阴影下探寻复杂的人性
她不是纳粹,却一日三次,日复一日地,拯救希特勒的性命。处在监视和死亡的阴影下,女性的秘密和友谊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在与邪恶、内疚,以及生存的本能争斗。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作者用细腻、有力的笔触揭开一段尘封的残酷历史,反思战争与人类灵魂的复杂性。在战争面前,没有人是幸存者。
作者这样描述这个故事,“罗莎是受害者,同时,也是一个罪人。这正是历史和人性困境的迷人、复杂与伟大之处。她活下来了,却也只是活着而已——因为她时刻身处囚笼。”
媒体推荐:
“无与伦比的写作,璀璨惊艳的天赋,引人入胜,精彩纷呈……故事中只用一个手势,就能完美地表达出愧疚,羞耻,爱与悔恨的感觉。罗塞拉日后必将大放异彩。”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这本书——讲述了爱,饥饿,救赎和悔恨——最终会深深烙印在你的心上。”
——《嘉人》(Marie Claire (Italy))
“全世界每一位读者都会沉浸在这本书中,一颗心悬在喉咙里,每一秒都感同身受,直到最后的华彩一章。”
——《女性》(Io Donna)
“如一部电影大片般精彩。”
《名利场》(Vanity Fair(Italy))
“大师级的作品……一个独特的故事,每个读者都能在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
——L’Unione Sarda
目录: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试读:
第一章
我们一次进去一个。在走廊里站着等了几小时之后,我们都需要坐下来歇一歇。房间很大,四周是白色的墙壁。房间中央的长木桌上已经摆放好了餐具。看守们示意我们坐下。
我正襟危坐,双手交叉着放在腹部。我的面前摆着一只白色的瓷餐盘。我饿了。
其他的女人也都无声地坐下了。我们一共十个人。有几个妇人文雅地坐得笔直,头发束在发髻里。还有的四处张望着。我对面坐着的女孩脸蛋软软的,美中不足的是有一只酒糟鼻。她用牙齿啃下手指上的死皮,用门牙不停地咬着。她也很饿。
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饿了,这和乡下的空气或长途跋涉无关。这是因为我们胃上的那个空洞让人感到害怕。这是长年累月堆积起来的饥饿和害怕。当食物的香气钻进鼻子里时,我的心跳突突地直蹿到太阳穴,口水一下子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我瞥了一眼那个酒糟鼻子女孩。看来她和我一样。
四季豆里拌着黄油,我上一次吃到黄油还是在我的婚礼上。烤过的果椒的香味不停地挠动着我的鼻子,我的盘子已经装不下
了,但我还是没有叫停盛菜的人。而我对面女孩的餐盘里是米饭和青豆。
“开吃吧。”屋子角落里的一个声音说道,那语气听起来与其说是命令,倒不如说是邀请。他们从我们的眼神中看到了渴望。我们松了口气,呼吸也加快了。但我们一开始还是很犹豫。还没有人说祝我们有个好胃口,也许我本可以站起来说一句“感恩”,感恩今早的母鸡们如此慷慨,虽然我今天吃一个鸡蛋就够了。
我又数了一下人数。我们一共十个人,这不是最后的晚餐。
“快吃!”角落里又传来了声音。我已经吸了一根四季豆到嘴里,我感到血液在我身体的每个角落流动,从发根直到脚趾,我的心跳逐渐放缓。怎么会有食堂为我准备饭菜呢——那甜甜的果椒——这样给我准备的一个食堂,一张连桌布也没有的长木桌,亚琛1产的瓷盘和十个女人,如果我们戴着面纱,那看起来就会像十个在修道院饭厅发誓噤言的修女。
一开始我们只是抿几口,好像我们根本没有收到要全部咽下去的命令一样,好像我们可以拒绝吃一样。这些食物,这顿饭本不该由我们吃下去,只是碰巧罢了,我们碰巧有资格来到他们的餐厅。食物顺着我的食道滑落,最后着陆在我胃里的那个空洞上,但是空洞被填得越满,欲望就越大,我们渐渐地攥紧了手中的刀叉。苹果派的美妙滋味让我几乎热泪盈眶,我每一口都是越吃越多,简直是狼吞虎咽,最后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把头朝后仰,好把东西咽下去喘口气。
我妈妈曾经说过,吃饭是在和死亡做斗争。她告诉我这句箴言的时候,希特勒还没有上台,我还在柏林布劳恩斯德盖斯10 号上小学,那是个没有希特勒的时代。她在我的围裙上别了个别针,一边把书包递给我,一边警告我吃午饭时要注意,千万不要噎着。在家时我有一个坏习惯,吃饭时叽叽喳喳讲个不停,就算嘴里塞满了吃的,我也照说不误。妈妈一数落我这个毛病,我就被她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和她的死亡威胁式教育方式逗得哈哈大笑,一时间真的喘不过气来了。好像每一个为了生存所做的举动都可能让我们走向死亡:活着就很危险;整个世界更是危机四伏。
我们吃完后,两个党卫军朝我们走过来,我左边的那个女人站了起来。
“坐下!在你的位置上坐好!”
他们还没过去按她坐下,那个女人就自觉地迅速坐下了。一绺头发从她绑着的麻花辫上的发夹里松散下来,轻轻地晃动着。
“谁许你们站起来的?新的命令下来前都给我好好地在桌边待着。不许讲话。如果食物有毒的话,毒素很快就会进入你们的血液。”一名党卫军朝我们一个一个地看过去,应该是为了观察我们的反应。我们大气也不敢出。接着他转向之前站起来的那个女人: 她身穿一件巴伐利亚紧身裙,也许她备受敬重。“别担心,只需要等一个小时就好,”他对她说道,“一小时之后你们就都自由了。”
“或者死了。”他的一个同事补充道。
我感到心头一紧。那个有酒糟鼻的女孩双手捂住脸压抑着抽泣声。“别哭了。”她边上一个棕色头发的女人说道。但是好几个女人都哭了起来,也许这是一种消化反应,就像吃饱了的鳄鱼会流泪一样。
我压低声音问道:“我可以问一下您叫什么名字吗?”酒糟鼻女孩没有反应过来我在问她。我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腕,她的手弹开了,闷闷地看着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又问了她一遍。女孩转过头看了看党卫军站着的角落,一时间不知道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她能不能讲话。看守们都心不在焉,快中午了,他们也都有气无力的。也许是估摸着不会被发现,她终于轻轻地告诉我:“莱妮,莱妮·温特?”她说得像个疑问句,但这就是她的名字。“莱妮,我叫罗莎。”我告诉她,“放心吧,过一会儿我们就能回家了。”
莱妮应该还只是个小姑娘,从她胖乎乎的手指上可以看出来;她应该没有在干草房被人碰过,就算在秋收后的农闲时也没有。
1938年,在我的弟弟弗朗茨离开之后,格雷戈尔把我带去格罗斯-帕特斯奇见他的父母。“你会喜欢他们的。”他对我说道。他很是为能征服自己从柏林来的秘书而骄傲,我们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订了婚。
坐在摩托车副座上的那段旅程很棒,就像歌曲中唱的那样:“我们骑马向东行。”各地的喇叭都播放着这首歌,而且不仅仅在4月20 号放这首歌。每天都是希特勒的生日。
那是我第一次坐渡轮,也是我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出远门。赫塔把我安排在她儿子的房间里,然后把格雷戈尔赶去阁楼睡觉。但是当他的父母都睡熟之后,格雷戈尔打开了我的房门,钻进了我的被窝里。“不,”我小声地说,“别在这儿。”“那去干草房。”我睡眼惺忪。“不行,被你妈妈发现了怎么办?”
我们还从未做过爱。我之前也从未和任何人做过爱。
- 联合读创 (微信公众号认证)
- 阅读创造生活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