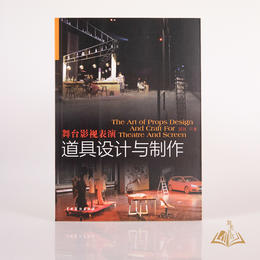商品详情
著 者:林克欢
字 数:273千
书 号:978-7-5596-2129-0
页 数:352
出 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后浪出版公司
印 张:22
尺 寸:165毫米×230毫米
开 本:1/16
版 次:2018年9月第1版
装 帧:平装
印 次: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0.00元
编辑推荐
《戏剧表现的观念与技法》是华语戏剧界一级评论家林克欢先生的重要著作,是风靡华语戏剧界二十余载的重要专著《戏剧表现论》的修订版,原版曾在内地和香港出版,如今绝版多年后修订再现。
《戏剧表现的观念与技法》依据林克欢先生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讲课提纲整理而成,融合了作者对近二三十年来世界戏剧舞台上表现语言的观察与思考,是戏剧创作、教学与观赏的重要读物。
◎ 戏剧创作者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找到符合时代、符合观众口味的舞台语言?
◎ 戏剧观众如何在世界多元的戏剧演出中提高鉴赏力?
◎ 如何从已有的舞台语言中挖掘新的可能性?
◎ 如何大胆采用新的媒介与表现方式?
著者简介
林克欢,戏剧学家,国家一级评论员。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文学部主任、院长、艺术总监。著有剧作《转折》《报童》,专著《舞台的倾斜》《戏剧表现论》《戏剧香港 香港戏剧》《消费时代的戏剧》,文集《诘问与嬉戏》《消费时代的戏剧》《分崩离析的戏剧年代》等,并编著《<红鼻子>的舞台艺术》《台湾剧作选》《林兆华导演艺术》。在200多种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300多万字的艺术评论、文艺随笔、文化论述及美学理论文章。
内容简介
本书依据作者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讲课提纲整理而成,曾以《戏剧表现论》为名在内地与香港出版,是华语戏剧界重要的理论专著。此次修订融合了作者对近二三十年来世界舞台上戏剧变化的观察与思考。全书立足于对中外戏剧演出的大量观摩,深入浅出地讨论了戏剧舞台结构和表现形式的多种可能,进而试图挖掘这种探讨的潜在应用价值:如何挖掘已有媒介、手段与舞台表现的新的可能性?如何大胆采用新的媒介与表现方式?因为舞台表现的无限可能性,潜在于观念与技法的不断发展与流变中。
这些思考既有助于编剧、导演、舞美等创作者深入了解舞台表达的诸多观念与技法,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下找到贴合时代、符合观众欣赏口味的舞台语言,又可帮观众在面对当代多元的戏剧时提高鉴赏力,还是戏剧理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读物。
目 录
修订版前言 1
前言 4
第一部分 1
第一章 扮演与扮演性 3
扮演与替代原则 3
扮演性与假定性 9
扮演性与剧场性 17
扮演的可能性 24
反串•胡撇•越界表演 31
第二章 仪式与仪式化 40
仪式与戏剧 40
作为舞台表现的仪式化 49
僵化的仪式:无意义的意义 57
没有神话的仪式 65
第三章 共享与共享空间 72
剧场的失落与回归 72
被动参与和主动参与 78
环境戏剧与戏剧环境 85
外在参与和内在参与 92
第四章 取消表现的表现意识 103
政治宣传剧:双重的反叛 103
偶发戏剧:设计与即兴 113
类戏剧:起点还是终点 121
现代戏剧之后 128
第二部分 135
第五章 舞台意象 137
意象呈现 137
意象群 144
意象叠加 150
意象与象征 158
离实写意 166
整体意象 172
原始意象与潜沉意象 181
第六章 舞台间离 187
间离的含义 187
间离的可能性 194
表演的间离 202
歌(舞)队的间离 208
附录:布莱希特戏剧在中国 217
第七章 荒诞 231
荒诞与荒诞派戏剧 231
荒诞与自由 236
荒诞与反抗 244
荒诞与嘲笑 251
视像化的戏剧时空 259
第八章 悖论 268
修辞的悖论与审美的悖论 268
神圣戏剧的悖论 272
三作为戏剧表现的悖论 277
第九章 双重叙事与多重叙事 284
复调 284
剧作的组合舞台的拼贴 294
第十章 另一种叙述 308
拼贴后现代 309
叙述与扮演 314
新文本 320
元戏剧 326
后记
出版后记
正文赏读
第一章
扮演与扮演性
扮演与替代原则
扮演,总免不了要与诸如游戏、娱乐、面具、虚构、幻象、假装一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当代社会,电视进入千家万户,竞选、追捕、行刺、交通事故、军事冲突等实况转播,有时比精心虚构的电视剧更富有刺激性,更能吸引人;而本来用来交流、沟通的语言,却被商业广告、外交辞令、政治宣传变成粉饰与掩盖的工具。有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把生活本身看成已被戏剧化了的事物,用诸如表演、角色、舞台背景一类的概念去分析人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自我表现,甚至迷信只有在各式各样的角色扮演中我们才会获得某种个性。于是扮演似乎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变成了对缺少意义的现实的掩饰,或者替没有意义的生活创造出一种虚假的意义。
然而,原始的扮演却是人类生活中的特殊需要,它涉及超越现实的集体的梦想,以及与文明发展密不可分的虚构。没有梦想就没有科学发明与艺术创造,就没有任何变革、改善生存处境的可能性。超越现实的冲动永远是人类生命和力量的表现。为梦想而抗争与在梦想中
沉醉不可同日而语。
埃德温·威尔逊(Edwin Wilson)在《戏剧经验》一书中写道:“创造戏剧的冲动是世界性的。什么地方有人类社会,它就在那里出现:不仅在欧洲,在东方也如此……在整个非洲,在新几内亚,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中,我们发现他们的宗教仪式、宗教典礼和庆祝仪式都含有戏剧因素。这些因素之一便是,由‘表演者们’在一群‘观众’面前扮演一个故事。”“不管任何地方、任何时代、任何种族的文化,这个过程都是相同的:只要一个男人或女人,站在观众面前,开始扮演另一个人,那么,戏剧就立即诞生了。”
创造戏剧的冲动就是扮演的冲动,它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之中,深深地根植于人类对感情生活、精神生活的需要。格罗塞(ErnstCrosse)认为,艺术冲动是“人类普遍所有的性质,或者比人性还要古老得多罢”。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则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或许,我们不会同意格罗塞认为艺术冲动实质上是和游戏冲动同一的东西,也即认为它是肉体和精神的能力对于无目的的、纯审美的活动的冲动。我们也可能不会同意尼采的浪漫化的酒神精神和所谓用艺术的谎言去对抗可怕的真理的形而上的慰藉。不管将逃避性的满足与补偿性的虚构抬到怎样高的地位,实际都是对艺术的贬低。但我们会同意,艺术的冲动是世界性的,深深地根植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之中。
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进行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扮演作为一种模拟性表现,无论出现在模拟式舞蹈或模拟式哑剧之中,最初几乎都是神话—巫祭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学家一再指出,最古老的巫术仪式是猎取和增加食物(即动物)的仪式。麦克斯·德索(Max
Dessoir)说:“在狩猎部族中,戏剧简直就只是动物的哑剧,它由没有词的音乐来伴奏。而在那些定居的部族中,这类演出活动更加花样翻新,但仍集中在表现最重要的动物的习性,就像现在希腊语系的农民总是集中表现公羊的习性那样。”班克罗夫特(Bancroft)这样记述因纽特人的模拟式舞蹈:“舞者通常都是青年男子,或裸着上半身,甚至也有完全裸体的。他们表演种种模拟鸟兽的滑稽形状,同时他们的动作是由击响鼓唱歌曲伴奏的。他们有时候很古怪地穿着海豹皮或驯鹿皮的裤子,头上戴着羽毛或有颜色的布。”
在这类混融性的巫术仪式中,一方面,它借助了活生生的人的扮演形式,只有在这种可视可感的物质形式中,原始人才能接通他们与神灵、祖宗及茫茫宇宙的神秘通道;另一方面,狩猎的真实对象已被其“替身”(对等物)所取代。在原始经验中,具体的感性形式是重要的,但形象却不一定必须与事物的外观酷似。扮演者只需穿着兽皮裤,戴上羽毛或只是颜色、花纹相似的织物,甚至什么也不需要,全身赤裸,只是模拟鸟兽的形状而已。重要的是在功能上发挥被围猎的作用,而不在乎形式上的差异。正如贡布里希(E. H. Gombrich)所说的:“所有的艺术都是‘制像’,而所有的制像都植根于替代物的制造。”我们在中国戏曲、日本能剧、印度古典舞剧等高度发展了的东方戏剧的表演程式和程式化的虚拟动作中,一再发现这种“替代”原则的生动运用。以鞭代马、以桨代船,是戏曲表演中常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鞭、桨并不是马、船的象征,而仅仅是马、船的替代形式。有些戏剧程式在经历了持续的替代之后,可能已变得远离其替代的对象,但约定俗成的舞台惯例,使文化背景相同的观众毫无困难地辨认出它的意思。事实上,在舞台上再现现实人生真实生活的自然主义戏剧、现实主义戏剧,是很晚才演化出来的戏剧样式,在漫长的戏剧史上只有一两百年的时间。即便是在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舞台上,那些用来制造远景幻觉的画幕、景片和道具,实际上仍然也只是一些“替代”物。
在当代社会里,人类娱乐性扮演的范围不断扩大,迈克尔·比林顿(Michael Billington)在其编著的《表演艺术》一书中,将歌剧、芭蕾舞剧、童话趣剧、音乐剧、歌舞喜剧、滑稽杂剧、独角戏、杂耍、马戏、冰上表演、傀儡戏、哑剧、独唱会、演奏会、驯兽、脱衣舞……统统放在“表演”之列。美国著名戏剧学者理查德·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则把“表演”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部分。他说:
我所称为的许多环境戏剧可以在流星娱乐、主题公园以及定点特殊演出中找到……迪斯尼主题公园以及它们的仿制品;使成千上万人受到娱乐与教育的成百“仿古村庄”和“活的博物馆”;美国内战(1861—1865)的再扮演以及其他“真实生活”演出;复兴的游乐市场、列队迅游、街头狂欢节、形形色色的文化习俗典—从罗马天主教徒到加勒比狂欢到男女易装和同性恋自尊游行;在室内与室外真实的和假的真实的空间上演的“追捕和猎杀”游戏;“侦探小说”、晚餐戏剧;邮轮、火车旅游;无数大小规模的在艺术画廊、街头、乡间的表演艺术作品;更多数量的宗教与仪式表演……甚至政府或政党的公开声明会。
人类学家则把扮演与人格面具联系起来,罗伯特·帕克(RobertE. Park)说:
“人”这个词的第一个意义是一种面具,这也许并不是历史的偶然。相反,它只是这样一种事实的认可:无论何时何地,一个人总是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他在扮演着一种角色……我们正是在这些角色中彼此了解的,也正是在这些角色中认识自我的。
在这有限的篇幅中,我们不可能涉及范围极为广泛的所有类型的娱乐性表演与竞技性比赛,也不可能涉及心理学中本我(id)与自我(ego)、社会学中自我控制与放纵等与人格面具有关的复杂内容,我们只能将论述限定在严格的戏剧学范畴之内。我们有时也将谈及生活中的扮演,那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戏剧已有意无意地模糊了生活与虚构的界限。
扮演在前戏剧(原始戏剧)、后现代主义戏剧之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不同的戏剧流派对扮演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技巧要求,但所有的扮演技巧与方法在涉及心理方面至今仍是一团谜,它涉及神话—仪式与狂迷、艺术直觉与意义抽象、朦胧感知与信仰这样一些似明未明的奇异区域。
巫祭仪式既是一种精神活动,又是一种实践活动。其精神活动直接依附于实践活动。歌舞者(扮演者)在不断重复的剧烈动作中精疲力竭,神志恍惚,进入一种忘我的狂迷状态。日本人将这种狂迷状态称作“神悬”。此时,扮演者不再是他本人,神灵附体了,神因扮演者而具有了外形。戏剧理论家河竹登志夫说:“正是在这种虔诚的无意识的演剧境况之中,才潜藏着戏剧根源的原始体验。”此后,当戏剧完全从宗教仪式脱胎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之后,不少表演艺术家仍一再追求那种难得一遇的恍惚状态,那种扮演者与角色瞬间的完全同化。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在另一层面,也即真实地再现生活的现实人物和人物性格上,要求演员与角色的完全同化。作为戏剧表演的一种心理技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有功绩的,也是实用的。但它永远也无法取消扮演者与角色身份的两重性。扮演(模拟性表现)就是从第一身份(例如因纽特人)向第二身份(例如鸟、兽等图腾形象)的转化。不同表演学派的分歧,归结为一点,便是对第一身份与第二身份转换的不同理解。
神话—仪式虽然是虚构的,但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虚构。在巫术仪式中,原始人总是把这种活动同他所期望的结果联系在一起,虔诚地在这两种事物之间建立起虚构性的幻想的联系。在神话想象和仪式操作中,总是暗含有一种真诚的信以为真的心理。没有对它的对象的实在性的相信,神话—仪式就会失去它的全部根基。同样地,任何流派的戏剧扮演,也必须建立在对虚构性艺术假定的信任上。没有这真诚的信以为真,戏剧扮演连儿戏都不如。装扮并不是装假,演员的扮演是真诚的,并不需要以虚假的面孔去欺骗任何人。一个演员并不假装是杜丽娘、陈白露或哈姆雷特,如同一个骗子假装他不是骗子那样。相反地,他创造了一种外观、一个形象,也创造了一种表演艺术。戏是演给观众看的,无论是扮演者或观看者,都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创造性的扮演。
巫祭仪式的主持者是巫师。后起的宗教仪式,也是由和尚、道士、喇嘛、牧师、阿訇等神职人员主持的。王国维说:“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董康认为:“戏曲肇自古之乡傩。”简·艾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持艺术与仪式同源说,她认为:“人们去教堂和上剧院是出于同一个动力……出于同一的人性的冲动。”这样看来,巫
师及被巫师指定为神灵附体的人,大概可以看作现代演员的天才前辈。
许慎《说文解字》对“巫”字的解释是:“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以有形事无形,以有形呈现无形,正是一切巫祭活动、戏剧表演的精华之处。它隐含着人的一切最深在的愿望与情感。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说:“有一种戏剧,我约略称之为神圣的戏剧,它也可被称作使无形成为有形的戏剧。舞台是一个能使无形显现出来的场所,这个认识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头脑之中。”“世界各地的很多观众根据他们自身经验将明确地回答说,他们透过超出日常生活经验的舞台经验,曾经见到过无形之物。”
或许,人们对神话、神祇的认识已发生变化,“绝对者”的观念已被诸如命运、道、理念、绝对真理、客观规律等观念所“替代”。神话在现代社会已发生转化与移位,当代神话切断了自身与仪式处境的联系,把古代神话化约为寓言、象征,也即用一种深度模式表现某种意蕴、某种含义的结构。只要人类对自身及宇宙神圣奥秘的探索没有完结,那么,彼得·布鲁克所说的“神圣的戏剧”便会不断地再生出来。
所谓扮演性,在我看来,便是扮演他者、显现无形(神性、意义)的舞台属性。
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苏联戏剧界围绕着假定性问题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剧院总导演奥赫洛普柯夫(Nikolai Okhlopkhov)发表在《戏剧》杂志1959 年第11、12 期上的《论假定性》等文章。奥赫洛普柯夫认为:“对于演剧艺术的丰富无比的可能性的无知或‘畏惧’,削弱或限制了戏剧艺术的力量,使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新鲜事物甚至根本无法以应有的规模、气魄和‘戏剧’色彩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认为:“幻觉主义的办法,自然主义的办法是违反戏剧艺术天性的。”“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过去现实主义艺术中为人民所批准的各种最‘稳固’、最优异的假定性因素,最广泛地发明新的因素,找寻演剧艺术的假定性手法的日新月异的特点,让这些新因素、新成分同旧因素、旧成分‘杂交’—所有这一切必将使演剧艺术的天性得到丰富,必将为新的剧本创作、导演处理、舞台美术处理提供极其多样的可能,从而出现主题、思想错综复杂,事件、情节包罗万象的戏剧演出。”尽管奥赫洛普柯夫是在现实主义戏剧的理论框架之内,充满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偏见和虚泛的浪漫主义激情,并一再声明假定性手法是为“生活真实性与高度思想性服务的”,却仍然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与来自多方面的围攻,假定性几乎被当作形式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玩意儿”与“鬼把戏”。
在经过断断续续、长达十多年的争论之后,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的提出,不仅仅戏剧界,而且电影、美术、文学各艺术门类都开始谈论、探索假定性手法的新的可能性。“开放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艺术概括形式的“开放”。这一理论的拥护者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能局限于“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这样一种概括方式,认为其他的假定性概括形式如象征、寓意、怪诞、夸张讽喻、复杂联想、非逻辑手段等,都可以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用。假定性被当作非自然主义、非写实主义的概括手法的总称,终于在苏联争得立足之地,并逐渐地确立了自身的美学地位。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80 年代中期,中国戏剧界也掀起了一场关于“假定性”的争论,而且重心同样是放在假定性与逼真性、制造生活幻觉与破除生活幻觉的对立上。舞台美术设计家薛殿杰说:“幻觉主义戏剧与非幻觉主义戏剧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前者千方百计地回避和掩饰舞台的假定性,而后者则尽可能地去利用舞台的假定性,文章就做在舞台假定性的利用上。”《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的导演耿震说:“该剧剧情发展的时间、地点,随时都在变化。全剧要出现几十个不同的时空环境。显然,用‘幻觉主义’的舞台景观演出这样一出戏,是行不通的。”因此决定“在景观方面充分利用舞台的假定性,创造一种非幻觉主义的舞台布景,灵活自由地表现剧作所规定的时间、空间的复杂变化”,“扩大戏剧的生活容量,增强舞台的表现力”。戏剧理论家童道明说:“假定性从来就是克服舞台局限性的有效手段,历来的戏剧艺术革新,总是伴随着新的戏剧假定性形式出现的。”
由于争论各方的兴趣、立场、观念各不相同,人们将假定性当成艺术概括方法,当成戏剧的基本美学思想或舞台局限性所造成的特性,认为它是由“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这一根本本质决定的”。假定性的历史成因、美学特性和舞台表现的潜力,统统落在争论各方的视野之外,在理论上几乎陷入一片混乱。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假定性的争论实际都是为了实践的需要,都与拓展舞台的表现力密切相关。当写实主义戏剧日渐走向僵化、严重地限制了戏剧家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时,人们便一次次地求助于假定性的魔法,一次次地从戏剧的源头中探寻它非凡的原始生命力。
关于这场争论的主要论点如下:
假定性是对形象进行艺术概括的一种方法,是广义的艺术性。(童道明:《论电影艺术的假定性》,载《电影艺术》,1982 年第10 期)
所谓“假定性”,其实就是舞台的局限性,或者说由局限性所造成的特性,这种特性具有不同于生活中自然形状的那么一种属性。(薛殿杰:《话剧舞台美术创作中的幻觉主义、非幻觉主义、舞台假定性》,打印稿)
是由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这一根本性质决定的。(田文:《也说几句“假定性”》,载《戏剧报》,1984 年第1 期)
作为戏曲艺术的最基本的美学思想的假定性……(李春熹:《戏曲的假定性及其形成》,载《黑龙江戏剧》,1983 年第1 期)
它是形式、手法,有好有坏。(龚和德:《回顾与展望》,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刊《业务资料汇编》,1983 年1 期)
假定性—艺术形式,一切表现“真实性”的形式、方法、手段。真实性—艺术内容,指反映在“假定性”中的客观真实。(羽军:《试论“第四堵墙”与假定性》,载《戏剧报》,1984 年第3 期)
对假定性之所以不可迷信,因为假定性本身不会产生艺术魅力。(耘耕:《对假定性不可迷信》,载《戏剧报》,1984 年第8 期)
“假定性”一词来自俄文“условность”,它的主要意思是“预先约定的”“假定的”,泛指艺术形象同它所表现对象的自然形态的有意偏离的一切手法与审美原理,包括游戏和艺术表现的“替代”原则,时空变形,也包括艺术惯例、艺术程式约定俗成的默契。
假定性与替代原则有关。当戏剧从神话—仪式中脱胎之后,有很长一段时期,扮演者仍由神职人员担任,如古希腊悲剧、中世纪的神迹剧、日本的能剧和我国的傩戏,扮演的也多是神话中的天神、《圣经》中的人物或祖宗传说中的英雄。再往后,当戏剧艺术远离宗教时,戏剧扮演中的一切替代物便逐渐丧失了“神性”。与原始戏剧中替代物被视为替代对象本身不同,它将戏剧扮演中的替代物都“假定”为对象本身。这种艺术假定,借助戏剧扮演的魔变,使一切替代物重新获得神性—超越有限对象的无限神性,诉诸观众的联觉、联想,去领略有形的物质形象背后那深不可测的无形奥秘。
假定性与扮演性密不可分。尽管布景、服装、道具、灯光,音响……均带有假定性尺度的信息,但一出戏的假定性尺度最终必须通过演员的表演才能确定。这在独角戏、哑剧等戏剧样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独角戏演员往往在一出短剧中同时扮演许多角色,演员必须借助声音、表情、姿态、站位的迅速转换,表现几个不同角色的“同时”在场。哑剧演员在一个空荡荡的舞台上演出,风、霜、雨、雪等的存在是借助演员的形体反应暗示出来的,而周围的物质环境则全靠准确的方位感、体积感、重量感等无实物动作加以表现的。戏曲艺术往往由人物赋予环境以生命。焦菊隐先生在谈及戏曲舞台上的虚拟动作时说:“只要演员心到、眼到、手到,观众就能真实地感受到。戏曲非常重视和相信观众的丰富想象力。演员只要心中有物,他就有把握把观众引到想象和生活记忆中去,使观众感到某物体的存在。”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一桌两椅,可以是宫殿、衙门、闺房,也可以是城墙、山路;日本能剧、狂言演员手中的纸扇,可以是伞、是剑、是棍子……
完全依靠情境规定和演员表演暗示给观众。中国戏曲从不讳言“假戏真做”,演员可以在耀眼的照明之下,表现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搏斗(《三岔口》),可以在小小的台面上表现腾云驾雾、穿波入海和一翻十万八千里的筋斗(《闹天宫》)……“扮龙像龙,扮虎像虎”,功夫全在“扮”上。在日本的艺谈、艺论中,有各种演员技艺的细致记述,但总的说来,演艺中“花”(艺术美的顶峰)的地位远远高于“真”的地位。所谓抽象之美、幽玄之美,无一不是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美。
- 中国舞美书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销售各类舞台美术用品,包含:灯光、音响、服装、道具、化妆用品以及各类舞美专业书籍并提供设计类服务。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