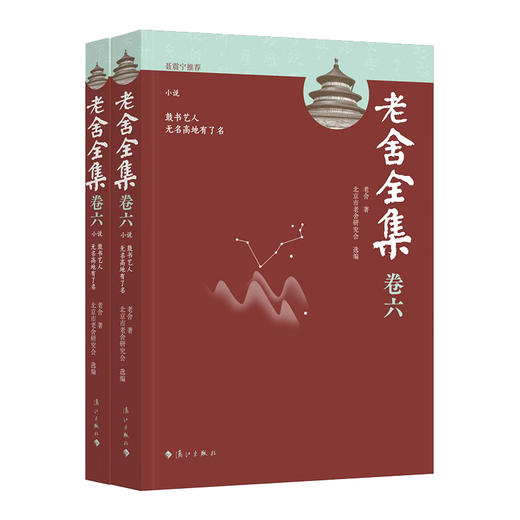商品详情

《老舍全集卷六 鼓书艺人 无名高地有了名》收录了老舍的两篇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和《无名高地有了名》是老舍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创作的作品。它们分别描绘了抗战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及抗美援朝中志愿军的革命精神,充满时代特色。文字幽默通俗、题旨性强。
北京市老舍研究会版《老舍全集》是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25周年的献礼。集中老舍先生的所有文章重新编排整合,并参照最初版本、原发报刊及手稿进行了校勘,在保留老舍先生个人注释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必要的补充和调整,使得内容更全面完整。《老舍全集》(第六卷)收入长篇小说《鼓书艺人》中英文译本以及《无名高地有了名》前者由老舍在1948年于美国纽约创作完成,后者在1954年于北京创作完成。这两部小说作品,展现了他在小说创作上的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现代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是一位多产的现实主义作家,从小说、散文到曲艺、话剧,均有涉猎。他的作品文笔生动、幽默,语言通俗,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主要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茶馆》《龙须沟》等。他的作品被大量翻译到海外,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著名作家。
001 / 鼓书艺人
203 / 无名高地有了名
345 / The Drum Singers
一
那是1938年的一个夏天。汉口的作战情况很是危急。
长江快速向东奔涌,犹如沧浪之水泥沙俱下。各色各样的难民正经历着人间苦难,他们向着战场相反的方向逃亡。飞机的底部和机翼上贴着红膏药,它们不断地投下炸弹。炸弹带着令人恐惧的呼啸声落下,冲到河面上,溅起了浸染着人血的冲天水花。
一艘叫;民生号的白色轮船,烟囱里黑烟滚滚,正在逆流而行。它小心翼翼地驶进了;七十二滩的第一个险滩,江水被两岸高耸的峭壁挤进了狭小的峡谷里。这艘轮船要奔往重庆。
客舱和货舱里挤满了难民,甲板上也没有落脚的地方。冒着滚滚黑烟的烟囱下,挤满了五六十个没了家园、没了父母的孩子。他们都被烟尘熏得浑身黢黑,看起来就像刚从煤堆里爬出来一样。
奔涌的长江如一条愤怒的巨龙左右腾挪,不断疯狂地扭动着身体撞击着布满岩石的河岸与山脉。经过一个又一个的险滩,江水骤然直下而去。船在激流中摆来摆去,像一条拼命扭动的虫子般挣扎着。汽笛声响起,船上的每个人都紧紧地屏住呼吸,希冀能够平安脱险。
每每平安渡过一个峡谷险滩,船上的人就如释重负地呼一口气,好比一场摔跤比赛中能够有一口喘息。他们中的一些人转过身来看岸边的激流与浪花,还有在漩涡中不停打转转的人和水牛,水面上只剩下黑色的头发梢和两只快速旋转的长犄角。
这艘挤满了难民的;民生号不时在江水颠簸中摇晃,汹涌翻滚的江水顺着船沿涌上甲板,把甲板上的人浑身上下打个湿透。
陡峭的悬崖遮住了太阳,料峭的寒风吹得乘客们浑身发抖。顺着山岩的缝隙,偶尔会透出一束阳光,投在江面上,映出一道美丽的彩虹。
长江两岸,翠山重重,陡峭的斜坡错落有致,皆有名号。它们形状各异,美奂绝伦,有如名家笔下挥洒的水墨。千古文人吟诗歌颂,各方志士著作传说。然而这艘白色的;民生号穿过巫峡,行至神女峰时,遭受着战争压迫的难民们并不在乎这些美景。他们不是开心的旅客,所以无心观赏古代帝王与神女幽会的高山,更无意流连于这段动人的美丽传说。
难民们既没有闲暇的兴致,更没有立足的空间,可以从容地站在船舷凭栏欣赏这景致。所有的乘客,不论贫富不管老少,都被这危险无望的前途给吓坏了。特别是当他们意识到这种种生活上的不便时,难过极了。人们无法从轮船的客舱里走出去,因为甲板上挤满了难民和成堆的行李,根本无法挪动一点儿。也正是因为没有空间,须得左脚换右脚轮番站着,所以甚至让人无法站直了好好喘口气。所有人都紧紧地挤在一起,整天就像待在一间拥挤的牢房里。但疲惫劳累的厨子和伙计们还是想方设法给乘客们提供吃食。他们打着赤脚行走在轮船各处,经过的地方都会被沾满泥灰和煤黑的脚蹭脏,一串串脚印留在包裹和行李上就像盖上了一个个的黑泥章。他们的脚落不到甲板上,所以他们只好踩到哪里算哪里。要是踩到乘客的脸上和身上,被踩的人要么尖叫,要么咒骂,混乱和痛苦交织在一起,使这本就不那么痛快的旅途更加痛苦。
;民生号上没人能够平静。的确如此,他们要么是心烦意乱,要么是怒火中烧,要么是黯然神伤。眼前的美景也提不起他们一点儿的兴趣。这真是诉不尽的悲苦,挨不完的难。
乘客中似乎只有一个人既不悲伤也不难过,虽然他也同样忍受着这些不幸,同样遭受着战乱的疾苦,同样踏在这艰辛的前途茫茫的旅程。
方宝庆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他靠着在茶馆里唱大鼓、说评书为生。他的宝贝有三样儿:一面大鼓、一对响板和一把三弦。他是个跑江湖的艺人,大半辈子都带着一家子东奔西走。这次也是一样。那个躺在满是煤灰的甲板上,每当船颠簸一下,就发出;哎哟,哎哟吭唧的人,是他的亲大哥。大伙儿都叫他窝囊废,他也的确很废物,什么事儿也不做还整天哼哼唧唧的。那个背靠着客舱壁,窝在窝囊废边上,手里拿着一瓶酒的胖乎乎的女人,是宝庆的老婆,她高提着嗓门儿,不知道正眼泪汪汪地咒骂着附近的谁。
离方太太不远,半躺半坐着的一个看起来惨乎乎、脏兮兮的丫头,是方宝庆的亲生女儿大凤。
甲板上靠近栏杆的地方坐着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她是方家的养女秀莲。秀莲和她父亲一样,也是在茶馆里卖艺讨生活。这会儿,她那娇嫩的脸上安稳从容,手里正捣鼓着她的骨牌。每当船一颠簸,窝囊废就哼哼一声,秀莲就细声地骂一句,因为船的摇晃弄乱了她的骨牌,但她的骂声既不庸俗,也不粗鲁。
方宝庆不想和家人们待在一起,他喜欢去四处溜达,因为大哥的呻吟和妻子的抱怨实在令他无法忍受。
尽管他已经四十多岁了,经历过那么多的走南闯北卖艺的日子,但依然本分、纯良而质朴,甚至一提手一抬脚都显得那么和蔼可亲。他可不是个愚蠢的人,否则这么多年他也不会过得那么顺遂,日子也还算舒坦。他天真、淳朴,像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般淘气。他要是伸一下舌头,抬一下肩膀,装出一副傲慢的样子,或者做出一个鬼脸或放肆地大声傻笑,这可不是茶馆里的表演,也不是装出来的,是真诚的。这一切都让人相信,他是为了让他自己高兴才这么干的。他的矫情和天真混在一起,像打碎的鸡蛋一样,搅和在一起,根本分不出哪是蛋黄,哪是蛋清。
当日本人进入北平时,宝庆便带着家人去了上海。当上海沦陷时,他们又去了汉口。现如今,随着日本鬼子正向汉口郊外逼近,他赶紧带着家人又跟着大批人涌向了重庆。北平是宝庆的家,他唱的就是京韵大鼓,他若想留在北平很容易,并不需要如此折腾,不用遭受这么多的苦难,也不必成为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中的一个。一脸憨态的宝庆几乎算得上是个文盲,但他是北平为数不多的能够识得几个字的鼓书艺人之一。日本人不会想着杀他,但他宁愿放弃那些个辛苦赚来的家产和可心的宝贝,也不愿意在日本旗飘扬的城市谋生。他很天真,也很烂漫。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爱国,他只知道每当他看到自己国家的国旗时,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的喉咙,在他的体内翻滚一样。
他这一家子最反对离开北平的人就是那个没用的窝囊废,他只比宝庆大五岁,但他觉得他算是长辈,就应该受到尊重。最重要的是,他还要求他在家的时候,得清静并且不能受打扰。他害怕他可能会死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他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令人讨厌极了。其实他身上没有多大的痛苦,没错,他只是想让宝庆知道他的心思没有改变。
方太太并不介意离开某个地方,不论是北平、上海还是汉口。唯一不满的是她的丈夫总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离开每个城市,所以她根本没有机会收拾好所有她希望带走的东西。她从来没有想过困难或战争时期的交通有多么的不便。眼下她小口抿着酒瓶里的酒,想着自己买的那几双穿着很舒适的旧鞋和那双穿旧了的很跟脚的长袜,要是都能带上该多好啊。但是她不得不把这些东西留下,虽然有点舍不得。她必须跟其他人一起离开。她喜欢喝酒,而且一喝起来,就没完没了地絮叨,而且舌头经常不听使唤。
宝庆不想听他哥哥的呻吟,也不想听他妻子的唠叨。他整天在甲板上钻来钻去,跟着船身东摇西晃。在船上这样走路简直就是遭罪。此外,他总是提心吊胆,要是他从熟睡的人身上跨过去时,那人突然醒来张嘴打个哈欠,他立马就会失去一只大脚趾。
他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是个卖艺的。要模样没模样,相貌平平的就像一个当铺或者百货公司里的打杂的,压根儿看不出来是个艺人。他更不像那些好的演员,不用怎么显摆,就能显露出自己的才华。不过有时他只是露上那么一手,就会让人猜不出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个子不高,但身上肉疙瘩很结实,便显得很壮。这便使他有时显得行动钝拙不灵活。但是只要他想,他就能像猴子一样敏捷和活跃。你永远猜不到跟他一起走到水坑前时,他是会跳过水坑,还是会直接把鞋子弄个湿透蹚水过去。
他的脑袋,剃了个光头,又圆又亮。他的眼睛、耳朵、嘴巴都很大,大到看起来像是松松地挂在脑袋上面,还好他的眉毛又黑又粗,保持住了他的尊严,这样就使他脸上松弛的皮肤显得不是那么可笑。这好似天上两道黑云的眉毛,抖动一下子,就会让人以为会像闪电一样撞出火花。
他喜欢笑,总是露出来他那一口好牙。他的鼻子并不出奇,但嘴唇总是那么红润、光亮。尽管眉眼间已经有了明显的中年人的皱纹,可那红色的嘴唇却使他看起来挺年轻的。
眼下,他就像那些茶房的伙计一样,光着脚在拥挤的甲板上来回踱着步。船走得很是晃荡,他光着脚是因为他在尽力避免踩到人。如果被赤脚踩到,总比被一双沉重的鞋踩到更容易得到原谅。
他挽起裤腿,露出那粗壮的、白白的小腿。他穿着一件旧的蓝绸子大褂,走动时用手提拉着褂子的下摆,以便不扫到躺在甲板上的人的脸,这样褂子的衣襟也不会随意摆动,走起来更利索。
他一只手提拉着褂子的下摆,另一只手招呼着众位朋友。出于他在表演上的习惯,他自然而然地认为周围的每个人都是观众,他应该对他们微笑,应该对他们抬手打招呼。于是他在船上来回遛着,一只手拎着他的褂子,另一只手则向碰到的各位乘客朋友挥着,他这抬脚的样子就像在迈过一条小溪,或者是在街上玩;跳加官。
他习惯了脑袋上锃光瓦亮,每两三天就剃一次头。这是他的招牌,任何一个听过他大鼓的人都记得。这光头远比他那张脸更引人注目,许多观众返场都是冲着他那光头来的。如今他有好几天没剃头了,他嘴里嘟囔着,一边胡乱抓挠着那讨厌的头发茬子,一边在甲板上溜达着。
就在登上;民生号的几个小时后,宝庆几乎认识了所有的乘客。没多久,他表现得就像是建造这艘轮船的监工。船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样东西的确切位置他都如数家珍。他知道上哪儿去给他的太太拎回瓶酒,这样她喝了就可以去睡觉,也就不会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他还知道上哪儿去给他的那个窝囊废大哥端一碗面条汤,这样也就阻止了他的无病呻吟。他也能像那些个会戏法儿的魔术师,凭空就掏出只兔子或小鸟。他还能找来阿司匹林药片,让那些患有头痛、晕船、疟疾的患者以及一些有特殊疾病的乘客得以治疗。
- 新华一城书集 (微信公众号认证)
- 上海新华书店官方微信书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