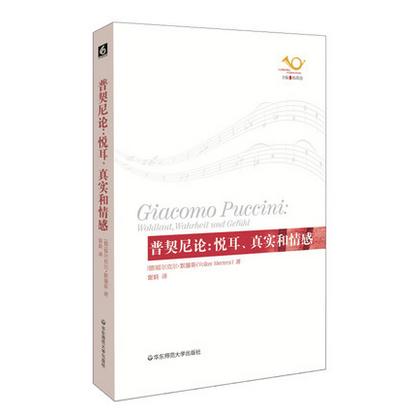商品详情


书名:《普契尼论:悦耳、真实和情感》
作者:[德] 福尔克尔.默滕斯 著 谢娟 译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号: 978-7-5675-3903-7/J.258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
定价:42.80元 开本:16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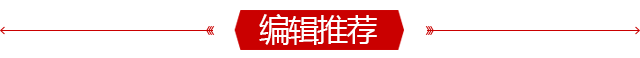
无论你知不知道有个作曲家名叫普契尼,你一定听过他的歌剧。
专业人士或许批评普契尼的歌剧通俗、质量不高,却无人否定其悦耳、动听、让人着迷。
普契尼,一个倾听普通人心声,特别是女人心声的作曲家。
普契尼以音乐表达女性情感,不仅真是切人、耐人寻味,更重要的是,“她们”经久不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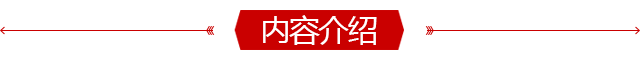
本书以普契尼的歌剧作品为主要线索,并将其置于意大利歌剧传统与欧洲音乐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试图探究作曲家在沿袭意大利传统与融合欧洲音乐发展新动向之间如何抉择以及在歌剧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作者从意大利歌剧独特的运营体系入手,结合音乐创作的文学渊源,细致分析了普契尼的每一部歌剧作品背后——歌剧工业化运营商与作曲家之间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对文学素材转变为脚本的重要影响。特别是,作者在看似不经意的论述中,勾勒了普契尼充满矛盾的一生:他继承家族的音乐素养,却放弃家族的音乐职位;他热衷名利,却小心地保持与达官贵人的距离;他热爱奢华生活,却素喜与小人物交往;唯有在音乐中,他从未表现任何的矛盾态度,而是始终如一的挑剔:挑剔剧本,挑剔演员,挑剔场景。
总之,他的精益求精——挑剔、挑剔、再挑剔——成就了他身前身后的辉煌。

作者福尔克尔•默滕斯(Volker Mertens,1937-),知名日耳曼语言文学研究专家,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著作有《普契尼论》、《托马斯•曼与音乐》,其对瓦格纳的研究获学界认可。
译者谢娟(1983-),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在读博士生,主攻中古德语文学长篇叙事诗。

译者序/1
序言/1
饱受争议的作曲家/1
卢卡学习时代/12
歌剧王国的歌剧运营商/19
《群妖围舞》——天赋还是天才?/23
《埃德加》——如何写成(砸)成功曲目?/34
瓦格纳的技巧•马斯内的旋律/47
《曼侬•列斯科》——“自由女性”带来的突破/54
《波希米亚人》——平凡人不平凡的爱情?/70
《托斯卡》——“出师作”/81
《蝴蝶夫人》——文化冲击/100
朋友与同仁/124
《西部女郎》——淘金热中的雷恩诺拉/140
《燕子》——一燕不成夏(独木不成林)/163
《三联剧》——三幅画,一出剧/177
《图兰朵》——得不到救赎的公主/203
普契尼的歌手——普契尼歌手/234
永远的普契尼——文学、电影和舞台/250
后记/260
生平大事年表:贾科莫•普契尼的一生/262
文学素材及蓝本/264
参考文献/267
音频资料推荐/273
视频资料推荐/278

饱受争议的作曲家
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生前就已名利兼收,这在歌剧作曲家中实属罕见。到如今,他受欢迎的程度丝毫未减,是世界范围内仅次于莫扎特(Mozart)和威尔第(Verdi)排在第三位的观众最喜爱的歌剧作曲家,在德国甚至排在第二位。其名曲多次被制成唱片,咏叹调成百上千次被录制。然而,赞誉多,非议也多,业内人士质疑普契尼音乐的严肃性。对许多学者而言,普契尼的作品过于通俗化,太多愁善感,其作品广为流传恰恰成了被诟病的原因。还有人认为普契尼的音乐虽悦耳动听,可音乐质量本身并不高;另外一些人则指责普契尼不重视艺术质量,一心只想着演出盈利。早期这些成见根深蒂固,直到近60年,对普契尼作品的严肃性研究才首先在英语和意大利语范围内展开,而在德语国家迄今仍未开始;究其缘由,是因为普契尼代表了在德国特别难以生存的作曲家类型。
在德国,路德维希•冯•贝多芬(Ludwig von Beethoven)首先作为思想家和眺望者成为把音乐作为启示传播给听众的先知。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在音乐中注入了世界变化和救赎的表情元素,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沿袭瓦格纳这一点。之后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nberg)又用音乐提出了道德的要求。与他们不同,普契尼希望观众震撼、感动、愉悦。对普契尼来说,剧院不是道德说教所,而是上演激情和伟大情感之地。同时代的真实主义作曲家(Veristen)鲁齐奥•雷恩卡瓦洛(Ruggiero Leoncavallo)和彼德罗•马斯卡尼(Pietro Mascagni)通过对社会的谴责而声名鹊起。普契尼另辟蹊径,他认为塑造的角色所处的社会环境仅仅是音乐所表现真实情感的前提条件,并非控诉社会的工具而已。
普契尼既非演奏艺术家也非指挥家。许多作曲家特别是德国的作曲家如韦伯(Weber)、门德尔松•巴托尔迪(Mendelsohn Bartholdy)、李斯特(Liszt)、瓦格纳(Wagner)、马勒(Mahler)和施特劳斯(Strauss),无一例外都是指挥家,威尔第在其最后一部作品《法尔斯塔夫》(Falstaff)首演中仍担当指挥,普契尼却从未指挥过歌剧;马斯卡尼不仅指挥自己的作品,而且还执棒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普契尼几乎不参与演奏表演,这与意大利的歌剧运营机制(作曲家、助理指挥和指挥之间的分工合作更加重要)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作曲家的个性特征有关。早年,普契尼就在卢卡指挥合唱队,对管弦乐声响有非凡的理解,但没有得到指挥明星统帅般的荣耀;他相对低调,有点害羞。普契尼认为,写成和完成乐谱并不意味着责任的终结,恰恰相反,歌剧的生命这时才算刚刚开始。普契尼更关注舞台表演——场景、演出、歌唱和管弦乐音效组成的统一体。只要其作品被重演,普契尼就会参与到重新排演过程中来,并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酬劳不菲):他观看彩排,对舞台、歌唱家还有演奏者进行指导,从而保证整个演出能符合他的期待和构想。
但即使在演出监督上,其他作曲家也走在了普契尼前面。威尔第试图亲自为歌剧挑选角色。为了能够有机会监控到演出的方方面面,瓦格纳建立拜罗伊特大剧院。普契尼深受后者影响,很早就观看过拜罗伊特的演出;1913年《帕西法尔》(Parsifal)版权保护到期,普契尼也在向帝国大厦延期呈文上签名,表明与拜罗伊特立场一致,他深知演出有保障对于作曲家意义非凡。普契尼从法国同仁那里学到另一招,即留下详细的导演备忘录,其中记载了舞台画面、动作、演员们的表演言语。普契尼的发行商里科尔迪把这种方法引入意大利以规范排演。
当普契尼完成学业开始为歌剧作曲,意大利音乐界正在物色威尔第的接班人,他应该同时是继承者和创新者。那时意大利传统歌剧复兴的力量主要来自德国。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内,歌剧创作成就上无人能与瓦格纳相提并论。他在乐剧(Musikdrama)方面的建树如同“连绵不断的旋律”,他打破宣叙调和咏叹调的传统形式改用通谱创作,采用主导动机(das Leitmotiv)、叙述的管弦乐(das sprechende Orchester)与富于变化的和声技巧和配器,这些均被当时的行家们视为典范。在法国歌剧界,声势浩大的革新同样如火如荼,抒情歌剧(Opera lyrique),代表作家为夏尔•古诺(Charles Gounod),特别是马斯内(Jules Massenet),逐渐取代了早先的大歌剧(Grand Opera)。人们逐渐不愿再在舞台看到国王、牧师和伟大的英雄,他们希望看到“普通”老百姓的身影。比才(Georges Bizets)的《卡门》在法国和意大利引起了轰动,让观众耳目一新。现实主义文学(意大利称为真实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代表性作家有乔万尼•韦尔加(Giovanni Verga)。
意大利作曲家们希望通过向德国学习来革新意大利歌剧,普契尼也不例外。阿尔贝托•弗朗凯蒂(Alberto Franchetti)在德国求学,阿尔弗雷多•卡塔拉尼(Alfredo Catalani)偏爱德国题材,鲁杰罗•雷恩卡瓦洛(Ruggiero Leoncavallo)则以曾亲自获得瓦格纳的鼓励为傲。可普契尼的作品要更有诗意、旋律更优美、更讨人喜欢,尽管他借鉴了法国抒情歌剧,但观众和批评家认为这才是意大利风格。当普契尼完成代表其个人风格的《曼侬•列斯科》(Manon Lescaut),人们真正看到正宗“意大利”作曲家的诞生。他创作了朗朗上口的旋律,突出了声乐,又没有为此放弃国际上正时兴的富于变化的管弦乐。
发行商里科尔迪要把普契尼培养成国家级作曲家。《托斯卡》(Tosca)以意大利为故事发生地点,也保证了该宣传造势的成功。普契尼的生平也遂了意大利人的心愿:他虽出身贫穷,其家族却有深厚的音乐传统。他来自曾经孕育了意大利“三皇冠”(tre corone)的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和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的托斯卡纳(Toskana)地区。托斯卡纳是意大利的文化重镇,托斯卡纳语也奠定了标准意大利语的基础。普契尼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了上天赐给意大利人的歌剧救世主。他不仅有“与生俱来”的天赋,且从始至终都忠于意大利传统,虽多次远游,最后总会回到故乡。他靠音乐发家致富,也并未招致非议,人们更多地把这看成是对天才和辛勤劳动的回报。观众们也原谅他对飙车的激情,而且还把这当成是先锋的标志。他常常在嘴角叼根烟,这甚而被视为城市人的标志。总而言之,普契尼正好代表了土生土长本土文化和善于交际的世界文化的完美结合,这不止让他看上去平易近人,也让他显得卓尔不群。普契尼擅长猎捕水鸟和女人,符合典型的意大利男人形象。为了逃避崇拜者,他会离开人群的喧嚣,与农民渔夫为伍,过一种“简单平凡的生活”(普契尼亲口承认比起生活在公共大众眼光中,他更喜欢后者),这让这位意大利艺术家在所有阶层中都受到欢迎,甚而促成了一种民族认同感。歌剧作为传统的意大利艺术形式,得到每位国民的青睐,并被尊为整个意大利的文化象征。1861年意大利名义上虽然得到统一,但真正的统一大业并未完成。正如意大利统一领袖人物加富尔(Camillo Cavour)所说,政治未完成的使命只有通过艺术来完成。“寻求”威尔第继任者不仅具有音乐意义,也是为了满足政治需求——这位救世者不该是政治家而应该是现代艺术家。普契尼专业的艺术家气质,时髦且低调的生活作风,让他恰好与此时代要求相吻合。
普契尼对政治态度冷淡。这点与同时代很多人相似,他们看到意大利统一后经济和社会的阴暗面失望不已,认为意大利政治方面四面楚歌。他对一战不闻不问,认为德国人入侵意大利,并在这里建立规范制度未为不可,即使他那位十分爱国的好友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为此还短期中断了朋友关系,普契尼也无动于衷。第三帝国的军队轰炸兰斯(Reims)大教堂,他没有响应世界范围内共同反法西斯的号召而受到不仅是意大利公众的谴责。在意大利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后,托斯卡尼尼和马斯卡尼公开发表言论支持祖国,而普契尼仅为慈善唱片写了首钢琴曲与歌曲《死亡?》(Morir),后来尽管他把巴黎《托斯卡》年度版税和蒙特卡洛庆祝《曼侬•列斯科》上演25周年的收入都捐给战争受害者,但明眼人仍可察觉普契尼刻意远离公开活动,只求置身事外。普契尼曾去蒙特帕苏比(Monte Pasubio)前线探望,但与其说为了鼓动士气,不如说是为了去见儿子托尼奥(Tonio)。托斯卡尼尼则冒着枪林弹雨亲自指挥演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一战后普契尼的态度仍不明确,他对日益强大的法西斯力量的立场更让人匪夷所思。他希望墨索里尼能重新建立先前由于左右翼力量而陷入混乱的国家秩序。1924年,墨索里尼任命他为议员以示嘉奖。这个独裁者很早就期望获得艺术家的支持。尽管普契尼曾积极支持过国家法西斯党,但他保持“非政治化”,任由他人说三道四。他并未退回墨索里尼政党给他寄去的名誉证书,而采取不理会的态度。托斯卡尼尼郑重警告过普契尼,这样做风险巨大,但后者并未听信。1919年普契尼写下了《罗马圣歌》献给萨沃伊的约兰德公主(Jolande von Savoyen),后来法西斯滥用该作品以达到宣传目的,这类事情虽未再发生,但堪称普契尼“非政治化”态度的后果。墨索里尼欣赏普契尼的歌剧,不是因为它们都符合法西斯的美学,而是其作品广受各阶层的喜爱。
优秀的歌剧——糟糕的音乐?
一则有趣的小故事讲到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和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chostakowitsch)曾谈到普契尼。“糟糕透顶的音乐”,布里顿说。“本,你说的没错”,肖斯塔科维奇听后如是答道,“糟糕的音乐——但是多么优秀的歌剧啊!”
该怎样理解这个评价?让我们先看看普契尼的歌剧创作过程。
首先是选材。普契尼较快知道他不想要什么,而对于想要什么得琢磨很长时间。因此他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甚至会被不同的题材吸引而脱离脚本。只有他充分肯定了要写什么才动手谱曲,这也是他鲜有歌剧半途而废的原因。但他的作品每部都很耗时,时而中断,普契尼要求甚高,特别重视编剧,由此他所有的剧本都有令人信服的戏剧逻辑,这一点有别于威尔第承认的很多其他作曲家。普契尼还要求语言富有诗意,能带给人灵感。他更青睐从名剧取材,如《曼侬•列斯科》,该剧灵感来自儒勒•马斯内的歌剧《曼侬》,两个脚本都以普雷沃神甫(Abb Prevost)1731年发表的小说《曼侬•列斯科与骑士德格里厄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波希米亚人》也上演过戏剧版本(由亨利•穆杰和德奥多尔•巴里耶创作);《托斯卡》、《蝴蝶夫人》、《西部女郎》和《大衣》都取材于当时优秀的戏剧作品,《图兰朵》则是参照一部旧的舞台剧。只有《燕子》和《强尼•斯基基》是自主创作,而后者虽不是取材于戏剧,但仍有文学题材基础。
普契尼不愿把历史人物搬上舞台,他没有完成《玛丽•安东瓦内特》(Maria Antonietta)的作曲,也不愿像威尔第那样塑造贵族角色;唯一出现王公贵族的只有《图兰朵》。吸引他目光的是“小人物”,并非人物的社会关系。普契尼不热衷于社会批判,即使在带有无产阶级气息的《大衣》(Il Tabarro)中也没有,环境只是用来显现地域特色。威尔第常采用大作家如席勒或莎士比亚(阿里戈•博伊托和夏尔•古诺)或歌德的著作题材,普契尼并没有效仿他们。有人劝他拜访当时意大利一流作家加比里埃莱•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普契尼认为他“太过敏感”。
相比之下,他更垂青用“实用编剧”写出受欢迎作品的二、三流作家(用阿尔弗莱•德•缪塞创作《埃德加》是个不成功的例外)。普契尼的高要求折磨着歌剧脚本作者,双方时有争执。作曲家注意情节发展,(几乎)总以爱情故事为情节中心,偏爱场景剧(Stationendramen)(如《曼侬•列斯科》、《波希米亚人》,特别是体现在《三联剧》的形式中),以及重视情节迅速发展的连续性。在普契尼,剧本不需要像瓦格纳歌剧中的叙事角色,而只需要提供情节(《图兰朵》是个例外)。他的歌剧靠惊人而充满激情的戏剧性高潮来加强张力,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剧”(《托斯卡》、《西部女郎》、《图兰朵》)。创作伊始,普契尼还用简单传统的音乐手法,后来改用更为精妙的手法(《西部女郎》)。除情节外,他还注重剧本的用词。普契尼与脚本作者卢伊吉•伊利卡(Luigi Illica)及朱赛普•贾科萨(Giuseppe Giacosa)合作,贾科萨专门负责脚本。普契尼清楚他要的节奏,甚至有次寄给脚本作者们“不通顺的诗句”作为节奏参照。《波希米亚人》中,穆塞塔的圆舞曲唱词原本是不可译的“Coccorico,coccorico bistecca”,贾科萨为此填词:“当我走在街上,当我独自走在街上……”(Quando m’en vo’, quando m’en vo’soletta[…])。普契尼最终按一定的节奏为此谱曲,但写出来的和刚开始所定的节奏几乎毫不相干。他期望动听而形象的诗行助他探寻音乐。普契尼钟爱“美丽且意味深远的词”可在谱曲时,又会忽略诗行美妙细腻的特点,纯粹把它们当作散文处理。诗句主要用于激发音乐家的创造性。普契尼后期的歌剧脚本则没在结构精致的诗句上花多少心思。普契尼认为编剧高于一切。但伊利卡的座右铭则是:“歌剧脚本的结构就是它所激发的音乐。”
如果说情节充满激情的戏剧性使普契尼成为众矢之的,那他的音乐就更是如此。特别是他朗朗上口的咏叹调——典型的普契尼调则更常惹来专业人士们的非议。
普契尼旋律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他使用一种下行五度然后模进上行到回音三度的曲调样式。这一旋律特征以各种变体出现。咏叹调与情节自成一体,单个曲子技巧精湛,在舞台情景中情节和人物的交汇点顺应而生。即使在某些歌剧中独唱所起作用不大(如《西部女郎》、《大衣》和《强尼•斯基基》),歌唱也占据主导地位。开唱前由乐队引入旋律,接着器乐旋律和声乐旋律相互配合,直至达到最终高潮,弦乐与人声八度平行,这种配器方式极大加强了独唱或二重唱的效果。但作曲家常因这种音乐上的可预见性而饱受批评。事实上,歌剧中的动机(如在瓦格纳乐剧中)运用——“语言上”的重复——既富寓意又朗朗上口(如《托斯卡》结尾男高音咏叹调的旋律)。普契尼创作《蝴蝶夫人》的结束标志着其创作系统的建立,该系统由动机及其变体和片段组成,从而超越了托马斯•曼所评价的瓦格纳歌剧的“联系魔法”(Beziehungszauber)。普契尼创建了一种微型编剧方式,且用不断变换速度节拍来实践它。这样既界定了大的场面,又令音乐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并让其具有符合自然言语和对话的流畅。比如穆塞特圆舞曲在51个小节中有超过30次速率变换,这位年轻姑娘的自恋个性便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普契尼严格遵守速度规定。他认为速度太慢会耽误情节发展,因此要求准确标明细微变化的音乐术语(Vortragsbezeichnungen)和力度(Dynamik)。演唱时要力求:充满激情地(Appassionato),深情地(con affetto),舒缓地(comodo),温柔地(dolce),优美地(grazioso)。因为如果不谨遵指示,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普契尼受过专业训练,他是位能辨别演唱者声音能力和极限的专家,也相应对歌手们的表演进行批判。要唱好普契尼的音乐,歌手必须出身科班,所有音域都具备支持力,声音听起来细腻;这位作曲家知道如何根据歌唱家的音域特点来增加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特色。当声音听起来不够稳定和饱满,则可作为音域过渡与连接(Passaggio),如《波希米亚人》的“多么冰凉的小手”(Che gelida manina)则暗示了鲁道夫的羞怯。《托斯卡》第二幕中大幅度跨音域演唱则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歌唱家必须能够表现极端的紧张从而对准音调,由此产生特别的强度。“动听”只是让角色有表现力的前提条件而已,即使卡鲁索也会偶尔由于表演缺乏激情而受到普契尼的批评。
普契尼密切关注同时代音乐的发展动态,并为之作出贡献。他勤奋阅读,不耻下问,不时学习同仁的音乐总谱和钢琴曲片段。普契尼曾采纳德彪西的全音阶,也曾用复调作曲,吸纳斯特拉文斯基(Strawinski)的技巧。在后期作品中,他有时采用无调,但这只是表达方式和音乐色调方面,并非意味着他为此放弃作曲基本原则。传统的听众仍然喜爱和声技巧。传统批评家们并不是讨厌《西部女郎》中偶然出现的不和谐音色,而是反对为了保持对话风格而放弃咏叙调。而这恰巧成就了现代歌剧《西部女郎》。普契尼至多放弃了小片段的优美旋律,却在快速对话中保持了悦耳性。在高潮处,和谐的声音是“强烈感情”的标志,而这一标志正是使歌剧成为一种体裁的关键。普契尼歌剧内在的真实性看似是以歌剧品质为代价来讨好观众,实际上,他花尽心思所缔造的地方色彩(couleur locale)是剧情的坚实基础,并非只是装饰而已,而是故事的真实发生地,旨在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观众们多次共同体验感受而不厌其烦,表明了普契尼的音乐美妙隽永,跟听起来一样悦耳。
普契尼并非普通的知识分子,而是高水平的作曲家。在专业和想涉足的领域,他雷厉风行,绝不拖沓。创作过程中,只要有可探寻的必要,他就追随灵感,有组织地作曲,即使(或正好)他的行为有时让人感到混乱——表现为断断续续的手稿和创作报告单。普契尼平常都在钢琴上作曲,但偶尔在闲暇时间比如打牌时倘若茅塞顿开,就会用两套乐谱记载在纸上。普契尼记住旋律与和声并标明乐器,宛如在初始主题周围搭建一个个小岛,尔后再以这些为基础,构成连续性的乐曲,逐渐形成了更大的整体,即便这些整体分布在不同的场幕。普契尼为歌剧作曲不是从头至尾或是依次按顺序,他挑选最中意的段落为切入点,直到最后所有片段连接为一体。人们甚至能听出其间的段落连接,比如《托斯卡》或《图兰朵》第二幕中有些就是动机连接而成的灵感片段。这也归功于普契尼的天才,从不留下蛛丝马迹,而是让整部作品呈现出编剧意义上的逻辑性。理查德•施特劳斯也采取同样的作曲方式,边读歌剧脚本,边记下灵感,进而加工并连接。
普契尼谈到灵感时,不像天之骄子那样自我吹嘘。1904年,《蝴蝶夫人》上演失败,他写道:“《蝴蝶夫人》的音乐是上帝传授给我的,我只是代笔而已。”与其说这是自豪,不如说是诚惶诚恐。临终时,他对脚本作者朱赛普•阿达米(Giuseppe Adami)说,上帝安排他为剧院作曲,这对他而言不仅是工作,而更多的是使命,为此他倍感荣幸。普契尼50岁甚而45岁就可以退休了,丰厚的版税收入能让他安享晚年。但通信中他常常提到作曲带来的艰辛和折磨,他一直创作歌剧,力求写成好歌剧,并为之呕心沥血、奋斗终生。
普契尼临死前,用钢琴弹奏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序曲。他停下说道:“不要再弹了,我们都是乱弹曼陀林曼陀林为拨弦乐器的一种,由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琉特琴演变而来,一般有钢弦四对,按小提琴音高定音,用拨子弹奏。——译注的半吊子,实在是可悲啊,但我们还以此为生,这扼杀了我们,我们江郎才尽,才思枯竭了。”意识到这一点,普契尼也走完了一生。关于大世界的歌剧时代已经过去,这些都属于讲述一切的19世纪。“我既不想看也不想要神话剧或清唱剧,如瓦格纳创作的《帕西法尔》;我要寻找一些更富情感的、人性化的、靠近观众的题材。”当1905有人向他建议一部关于佛的剧本时,他这样说:“关注人类和他们简单的情感。”这才是普契尼想做且能够做的。
卢卡学习时代
巴赫家族世代在图林根以音乐为生,普契尼家族则是卢卡(Lucca)的音乐世家。这从普契尼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来。其名为:贾科莫•安东尼奥•多梅尼科•米凯莱•塞孔多•马里亚•普契尼(Giacomo Antonio Domenico Michele Secondo María Puccini),其间包含了普契尼家族各代音乐家的名字,最后为姓氏。普契尼出生于1858年12月22日到23日夜间。
多梅尼科•普契尼(Domenico Puccini,1679—1758)是第一位在托斯卡纳地区卢卡城扎根的先祖,那时还属于独立共和国。多梅尼科的儿子贾科莫•普契尼(1712—1781)在卢卡和博洛尼亚(Bologna)的意大利最著名的交响乐学院学习音乐。1739年他成为卢卡圣马丁教堂的竖琴师,一年后荣膺共和国教堂作曲大师(Maestro di Cappella)。这里出于大量的宗教和政治原因对音乐有很大的需求。11月22日,圣凯奇利亚兄弟会首先开始举行音乐节,该节由晚祷、弥撒和为纪念已死会员而举行的安灵仪式组成。9月14日共和国圣徒日,在圣马丁教堂展出神圣的十字架,当然也少不了音乐。每两年一次为期三天的长老院选举,舞台上也要上演清唱剧和管弦乐套曲(或小夜曲),即声乐作品,类似于《托斯卡》第二幕中胜利场景中那样。普契尼家族参与这些庆祝活动,并为之谱写作品。
多梅尼科的儿子安东尼奥(Antonio,1747—1832)结束博洛尼亚的学业之后,于1772年子承父业,接手父亲竖琴师一职,为教堂和选举作曲。其子小多梅尼科职业道路与此相差无几,除了宗教音乐和小夜曲外,他还写了四部歌剧(1640年起,卢卡开始有了歌剧演出)。他谱写过一首感恩赞美诗合唱曲,起因是误以为盟军1800年在马伦戈会战中获胜(该主题在《托斯卡》中亦出现),当时该合唱曲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贾科莫•普契尼持有祖父们的谱子,这些作品在两百年之后即《托斯卡》首演100年后在罗马重新演奏。《托斯卡》取材自维克托里安•萨尔杜(Victorien Sardou)的同名戏剧,第一幕结束时也有感恩赞美诗合唱曲,看来这有可靠的历史渊源,人们通常都用这首颂歌来为胜利欢唱。普契尼可能看到了安东尼奥作曲的详细描述而受到启发。他的儿子米凯莱(Michele)(1813—1864)也继承祖业,像父亲安东尼奥一样在那不勒斯的乔瓦尼•帕伊谢洛(Giovanni Paisiello)门下求学,并在圣彼得音乐学院(Conservatorio S. Pietro)跟随萨韦里奥•梅尔卡丹特(Saverio Mercadante)和加埃塔诺•多尼采蒂(Gaetano Donizetti)学习音乐。米凯莱后来也荣膺圣马丁教堂的竖琴师,之后在音乐学院担任竖琴教职,还为官方教堂和国家庆祝日谱曲,不过他留下的两部歌剧并没给他带来荣耀。1864年,年仅50岁的米凯莱英年早逝。其长子贾科莫——也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当时只有5岁。
尽管父亲早逝,幼小的普契尼却已受到音乐的熏陶。他必定亲耳聆听过父亲的演奏,熟知厅堂里祖宗像上画的是谁,明白祖祖辈辈以何为生。普契尼的舅舅弗朗切斯科•马奇(Francesco Magi)同样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家。在米凯莱的葬礼上,校长乔万尼•帕契尼(Giovanni Pacini)发表悼词,谈及米凯莱孤儿的未来,他认为,普契尼应该继承祖志,只要长到能够履行这个义务的年龄,就会成为竖琴师和圣马丁教堂的作曲大师。普契尼的人生之路早已被规划好。10岁起就进入教堂男童唱诗班,《托斯卡》第一幕中滑稽场景就透露出对童年这段经历的反思。普契尼并非循规蹈矩的好学生,1872/1873学年不得不留级。在音乐学院,他也没有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才能。不过,他应该很早就开始用管风琴为合唱团伴奏,1874/1875学年末获得了管风琴表演第一名的好成绩。这一时期他开始早期创作,其中包括现存最早的是情歌《献给你》。观其一生,普契尼有效利用每一个好点子,绝不浪费任何奇思妙想;后来,他把《献给你》中“E dammi un bacio”(给我一个吻)的旋律用于《托斯卡》第三幕女主人公的唱词:“我要用上千个香吻覆盖你的明眸”的伴奏中。
普契尼仔细阅读了威尔第的《游吟诗人》、《弄臣》和《茶花女》钢琴片段,对音乐的理解由此得到很大提高。很可能早在卢卡,他就已经用同样的方式来研究自己一直奉为榜样的瓦格纳的音乐了。
卢卡的音乐生活多姿多彩,既有乐队演出,时而还有歌剧上演,但是,很少听到同时代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所以,就有了后来著名的贾科莫的“朝圣”之旅。1876年3月11日,他步行20公里到比萨去看威尔第的《阿依达》。他写道:
我无比惊讶,甚至可以说,非常恐慌。一个普通人能写出如此伟大的作品?怎能又闪耀着如此和谐的光辉?在我看来,歌剧作品中不可能产生比这更伟大的东西,歌剧院不可能呈现出更为壮观的场景。能够让观众们着魔、感动、欢呼,我要站在众人面前说:我要把我想要的和感受到的情感传递给你们,我要让你们像我一样哭,一样痛苦,我也要你们笑,如同掌握管风琴的琴键一样掌握你们。如此美妙!
这是信仰的自白,也是他一生的追求。他向往的不仅仅是掌握管风琴,而是驾驭观众的情感,借助戏剧和舞台拥有让观众或悲或喜的力量。而他至死都遵循这一人生目标。这或许是一个老掉牙的关于使命的传奇,但事实确实如此。普契尼最初的作曲就有《阿依达》的影子。《E大调交响乐前奏》(Preludio sinfonic in EDur)从序曲到第一幕都难脱窠臼,在处女作《群妖围舞》(又译《女妖》)中也借鉴了《阿依达》。
在卢卡,除了从事宗教音乐演奏和作曲,普契尼还在著名的卢卡温泉浴场(海涅写过《卢卡的沐浴》)演奏管风琴,在赌场弹钢琴。在多处进行音乐实践使年轻的乐师受益良多,其出师作《降A大调四声部弥撒曲》(Messa a Quattro voci,1951年以《荣耀经》发表)便是明证。该作品创作背景不明,有可能是大教堂教士咨议会的委托创作。贾科莫不仅弹奏管风琴,也为礼拜仪式写些小作品。作为普契尼家族的继承人他前途无量,即将在意大利最有声望的大学(位于米兰)完成学业。大家对他期望甚高,从委托这位年轻人为弥撒庆祝活动创作《庄严弥撒》(Missa solemnis)便可见一斑。据推测,1880年7月12日,卢卡为庆祝城市圣人保利诺(San Paolino)节,在圣•马丁大教堂进行此次弥撒活动。之后,《荣耀弥撒经》逐渐被遗忘,直到1952年,在芝加哥(在再次发现它的佛罗伦萨的班顿•但丁的提议下)重见天日,同年还在普契尼故乡卢卡演奏。对于刚满20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算得上是惊人之作,作品立意高远,长达45分钟,从中可以看出作曲家熟练掌握了意大利弥撒传统作曲技巧。据分析,有些地方用“老式”对位法,另一些则用“现代”歌剧风格作曲。普契尼参照的范本是多尼采蒂或者焦阿基诺•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的宗教作品,其中也吸收了同时代一些小作品采用的技巧。弥撒是实用音乐,不同于中规中矩的实用忏悔音乐(Bekenntnismusik),如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这其中还有类似歌剧脚本的句子如“赞扬你,感谢你”和“你铲除世间的罪恶”,这些句子对于阿尔卑斯山这边听众比较难以接受。作品首先表达了感恩和对献身的耶稣的同情,其次感染力丰富的颂歌将这种感情宣泄出来,如同舞台表演那样。在罗西尼的“圣母悼歌”(Stabat Mater/Cujus animam)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曲风,朱塞佩•威尔第的《安魂曲》旋律也有富有表现力的特色,如“献祭经”(Hostias)、“拯救我”(Libera me),不管是世间的还是精神方面的动机都表现出个体的情感。宗教仪式的客观性通过“老式”的句法,即按对位的方式表现出来。普契尼的创新之处在于色调丰富,早期的作品就敢于突破传统。普契尼很可能是意大利第一位给予音乐如此丰富和声技巧和配器色彩(与他的“心灵编剧”相符)的歌剧作曲家。从这部作品中,可以听到他对同时代意大利和德国音乐的理解和感受。
《祈祷歌》按传统分为三部分。出人意料之处在于,开始部分悲切哀伤,中间部分则激烈地祈求怜悯,这刚好颠倒传统作曲顺序,普契尼希望借此震撼观众。旋律“严格按照规矩”模仿对位学谱出,后来普契尼把旋律第一部分用于第二部歌剧《埃德加》。
“荣耀”立意非常宽广,是该弥撒曲最长的部分,该部分举足轻重,也是之所以该作品后来以《荣耀弥撒曲》命名发表的原因。普契尼将之分为四个段落:“荣耀经”,男高音独唱部分“我们向你感恩”,还有进行曲式的“唯有你最神圣”和由军乐引出的“与圣灵同在”。“荣耀”以朗朗上口的快活的、颇有圣诞气息的旋律开始。接着是“感恩赞”,显得更正式,更有宗教仪式气氛,从随后的男高音咏叹调“我们向你感恩”中已可以先听出后面的歌剧独唱部分。但这些曲子并非典型的下行普契尼音调。男高音唱到高音降B带来了歌剧的高潮部分,之前自成一体的管弦乐部分开始成八度平行,该技巧成了普契尼的一大标志性特色,许多后来者争相效仿。“你除去世间的罪恶”(Qui tollis peccata mundi)也带有歌剧的特色,与带有压抑氛围合唱式风格的“唯有你最神圣”形成对比。“与圣灵同在”是严格遵照传统规定所作的赋格曲,普契尼标新立异之处在于把“荣耀归于主”的旋律作为对位点引入,凯旋般地结束了全曲。
两年前普契尼曾为圣保利诺节日写过“信经”(Credo)。与“荣耀经”一样,“信经”中亦存在统一单个章节的趋势。这里有五个段落:“我信唯一的天主”,男高音独唱的“圣灵感孕”,为男中音写的“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合唱场景“复活”和再一次由军乐引出的“永生”(Et vitam)。赋格曲有别于传统,为动人的合唱乐章。C小调的“信经”主题与快乐的“光荣”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回到“我信圣灵”,其中有抒情乐章“圣灵感孕”和“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盼望永生”包含一曲天真快活的旋律,从而展示了田园安谧而宁静的幻象。
“圣哉经”简洁明了,在仪式进行过程中没有多大空间。“降福经”是传统通俗易懂的曲调,这里略显出色之处是让男中音而不是男高音来演唱。
“羔羊经”应该受到作曲家的特别青睐,后来在《曼侬•列斯科》(1839年都林[Turin])首演中再次出现,而这部作品为普契尼赢得了世界荣誉,曼侬在情人杰隆(Geronte)的豪华宫殿中,歌手唱出一段牧歌:
在高山顶峰/你迷失方向,哦,克洛丽丝:
你的双唇是两朵花/你的明眸是一眼泉[……]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认证)
- 本店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官方直营旗舰店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