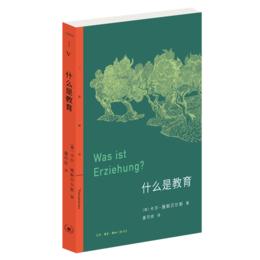商品详情

 |
前 言
绪 论
第一章 王闿运、邓辅纶与清末“拟古派”
第二章 樊增祥、易顺鼎与晚清用典派
第三章 陈衍、陈三立、郑孝胥与“同光体”
结 论

《微妙的革命》关注的是中国文学现代化一个最具挑战性的维度。通过考察古典诗歌在激进转型期的复兴,寇志明引领我们进入一个超越了“现代”之传统边界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所有的力量都可以使用迄今为止不相兼容的资源,以此更新中国文学的想象力。寇志明对其拣选的诗派和诗人的解读是最有洞察力的,他对现存研究范式的批评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性的神秘的环境。
——美国哈佛大学 王德威
寇志明质疑已被人们接受的晚清古典诗歌处于一个悠久而光荣传统的末端的观点,而认为它实际上标志着现代的开始。该书以对几位主要诗人的精致翻译和敏锐解读,为对正在进行的中国现代性之重审做出了重要贡献。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叶奚密

前 言
绪 论
第一章 王闿运、邓辅纶与清末“拟古派”
第二章 樊增祥、易顺鼎与晚清用典派
第三章 陈衍、陈三立、郑孝胥与“同光体”
结 论

序论
(编按:限于篇幅,删除大量注释,请参见原书)
19世纪晚期数十年,中国开始了一场其广度与深度在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转型。作为最后一个独立的,基本未受西方技术、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影响的非西方大国,中国迫于与外国通商的压力以及自身海防军事力量的薄弱,最终被强行拖入了一个国与国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统治权以及殖民地而激烈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对于这些竞争,这个国家并不感兴趣,更没有优势可言。正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言:
面对现代变革压力的中国文化是有史以来最独特、独立而又古老的文化,也是最庞大、最自足、最平衡的文化。因此,过去一百五十年在中国间或发生的周期性革命,是历史所需的最深刻、规模最大的社会变革。
这样的环境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传统的文学样式在这个时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连根拔除,被其“现代”对手取而代之。事实上,关于这样的根除以及替代如何发生的研究一直以来并不缺乏。西方和中国一些持决定论观点的学者就导致这种“不可避免的”对古典(实则“本土的”)文学形式和语言的排斥以及以基于西方典范、以白话文或口语书写的“现代”文本取而代之的历史原因,争相提出自己的解释。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讨论发生在诗歌领域里的情形,不过其他文学样式的“进化”大抵沿着类似的模式。
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主张以一种更能为中国大众接受的形式写作的真诚的、进步的爱国者无意间受到了西方文化扩张主义的欺骗(尽管他们不可否认地受到了西方有关语言和文学“进步”观念的影响)。我这里也并非像有些“学衡派”人士那样主张这些人要对整个文学传统的衰败负责,而且这样的传统一旦消逝,便再无恢复之可能。我只是想指出:所有客观的、对文化敏感的文学史都应当质疑,古典文学形式至19世纪末“奄奄一息”、已经到了油枯灯灭的地步这一论断。
诗歌在任何其他文明中都从未像在中华文明中这样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受到如此明显的尊重,也从未达到像在中华文明中这样成为人与人进行“实际”沟通的媒介的水平。在中国,早于贺拉斯(Horace)一千年、早于荷马(Homer)数个世纪成集的《诗经》被视为向统治者传达民意或者体现儒家仪礼以及统治原则的经典之作。《楚辞》成为描绘忠于君王而遭放逐的异议分子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古代楚国丰富的神话传说的主要来源。至隋代,中国开始施行文官考试制度,这一制度在之后的朝代中成为一个人获取功名、权力及官职的必经之路。对每位考生作诗能力的考察最终成为这一考试的关键部分。考生作诗时不但要遵守严格的韵律规则,而且要遵守有关内容、意义、效果以及特定章旨(根据传统的经典释义)的规则。总之,每一个渴望在这个唯一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仕途上建功立业的士族子弟,以及许多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掌握诗歌创作的技巧。
作为最高的文学形式,诗歌一直是人们表达热爱、愤怒、渴望、欢乐与哀愁等个人情感的工具。杜甫那脍炙人口的诗句“国破山河在”无可争议地成为集体悲剧(collective tragedy)的载体。戏剧中最强有力的句子亦总是以诗句表达。正如日本学者仓田贞美(1908—1994)所言:“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资格被称为诗的王国。”清末的旧体诗首度直面与前此任何时代都不同的现实,而且自出机杼,以自己特有的语言、意象和典故表达现实。这些诗传播出来,受过传统教育的士大夫读者将其视为一种力量,而非一种缺点或是什么需要为其百般辩解之事。19世纪末,中国文学在中国自身的文化氛围中是非常活跃的,这一点,今天任何公正的批评家在简单了解当时文学流派的数量后都不得不承认,即便这些批评家对这些诗人的作品毫无好感。

诗人高旭(1877—1925)的文学生涯鼎盛期接近于本书所讨论的时段的末期,他在1915年出版的诗集《变雅楼三十年诗征》的序言中强调了这一时期诗歌的一个独特之处:
惟三十年来,则千奇万变,为汉唐后未有之局。世风顿异,人才飙发,用夷变夏,推陈出新。故诗选之作,以三十年为断,亦以见文字之鼓吹,足以转旋世界,发扬光大,其力之大为未有也。窃尝谓:诗之奇,莫奇于此三十年;诗之正,莫正于此三十年。
对此,堪称这一时期诗歌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外国学者仓田贞美补充道:
即便我们追溯至这一时期之前(即1885年之前),由于外国文化[的引入],传统诗歌内部时代[感]日益浓厚,[以及]追求社会变革、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的激发,诗歌界形势不断变化,而这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特点。这是旧格律诗统治诗坛的最后时期,同时亦是倡导诗界革命,新思想与新意境注入旧形式的时期。这一时期,外国诗歌首度被译成旧体诗,西方浪漫主义运动的浪潮涌入[中国]。这一时期可以称为[诞生于]五四运动之后的新诗歌的发酵期。尽管这个时期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说,从中国诗歌史的角度,这一时期是相当值得关注的“重要时期”。
对我个人的研究而言,仓田的论点中最具启发性的部分,是旧体诗在这一时期仍然占主导地位。从今天的历史视角看,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正在五四运动之前。不过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不仅仅是因为它预示了五四运动,而且还因为这一时期旧体诗本身所发生的变化。仓田继续写道:
然而,迄今还没有专门研究这一时期诗歌的[学术]著作。虽然有不少诗话之类的著作,不过这些著作大多讲述诗人的佚闻轶事以及对友人作品的主观印象,缺少对这一时期诗歌进行全面研究的论著。这些[印象式的诗话]由于受到社会地位、思想立场、或者相关人士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在许多地方表现出极大的偏见。有些固执地恪守传统论诗原则,极力强调诗词的形式之美以及诗词技巧,却忽略了诗的内容[问题]。另一些论者则重点关注一首诗的思想[是否]进步[的问题],强调诗作的时代性,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功能,同时却贬低诗词最关键的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特点。诗歌[的创作]是建立在诗人的性情和个人性格、教育和文化背景、思想、人生观以及艺术观等等的基础上的,因此,诗歌自然有其自身的个性特点,这些个性特点,加上时代以及[诗人所属]民族所赋予它的种种特点,赋予诗歌一种普遍性以及对于全人类的吸引力。[我认为]除非我们达到对诗歌的更深层的理解,既考虑到其成就也考虑到其缺失,考虑到诗对当时诗界的影响以及对后世诗歌的贡献,否则我们很难理解诗歌的本质,进而对其进行历史的评估。

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生长在美国宾州、现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教授、澳大利亚东方研究会主席。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硕士、北京大学高级进修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中国文学)博士。曾任中国外文局编译专家、马萨诸塞州威廉士学院中文系主任、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佐治亚大学雅尔奇荣誉教授、北京鲁迅博物馆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植芳讲座教授。专著有《鲁迅旧体诗研究》《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中英对照鲁迅旧体诗》《精神界战士:鲁迅早期文言论文》《鲁迅略传及中、英、日文鲁迅研究专著述评》;编有英文季刊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in China之特刊“章太炎与鲁迅”。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微信公众号认证)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一家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出版机构。建店八十余年来,始终秉承“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坚持“一流、新锐”的标准,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 扫描二维码,访问我们的微信店铺
- 随时随地的购物、客服咨询、查询订单和物流...


![艺术哲学[(法) 丹纳 著;傅雷 译]](https://img01.yzcdn.cn/upload_files/2017/07/27/FrImKewCkaNOZj4Cq8lwgiQCBLxz.jpg?imageView2/2/w/260/h/260/q/75/format/jpg)

![傅雷谈艺录(增订本)[傅雷 著]](https://img01.yzcdn.cn/upload_files/2017/12/05/Fpc0tTuPpq-R_GRSc4ePX94GKM2t.jpg?imageView2/2/w/260/h/260/q/75/format/jpg)